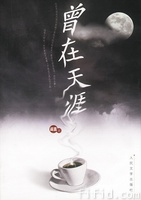作品資料
作者:閻真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遙遠的北美異國,高力偉走過了一段難忘的人生旅程,靈魂的漂泊比軀體的漂泊更令他刻骨銘心.《滄浪之水》的作者閻真以他特有的相關素細膩的文筆,逼真地描寫了一代留學生的內心痛苦和窘撻處境.無論你倆有沒有那樣的經歷,《曾在天涯》的故事都會使你感到震撼,或許還能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內容簡介
小說的主人公高力偉出身於歷史專業的研究生,這種出身很容易成為一個本土文化傳統的守護者,但高力偉畢竟是在文化開放的80年代所受的教育,對以科技文明為基礎的西方文化在理念上具有無可置疑的理解與信賴。對於任何一個飄泊在異域他鄉的天涯遊子而言,尤其是當生存這一最基本的低級關懷也得不到實現時,他的文化理念與文化根性之間就往往會發生撕裂,西方文化雖然可信卻不可親,自己所神往的加拿大以一種一成不變的冷漠應對著那些黃皮膚的朝拜者,而東方文化雖不足信卻令人親近,因為畢竟是自己的和著血液的文化根性。所以,高力偉既不把加拿大讚美成天堂,也不像有的失敗者那樣將加拿大說成是人間地獄。他從內心裡清楚加拿大無論是風景還是人情都是美好的,“不承認也不會這么幾萬里跑過來”,但這“好”“好來好去還是個人家好,又沒我多少戲”。從世俗的意義上看,高力偉在加拿大的生計不能說是失敗的,短短的三年時間他已積攢了將近5萬加元,但他最終還是離加回國,不僅金錢而且愛情也無法挽留,主要是他內心中積壓著一種強烈的文化屈辱感。確實,科學技術是沒有民族性與國家界線的,但人文精神與文化傳統卻是與民族的血緣與根性息息相關的,在自己的祖國,高力偉可以說屬於文化精英階層,但在異域文化環境中,高力偉引為自詡的文化知識百無一用,所以,高力偉絕望於加拿大的不是自己沒有掙錢的機會,而是絕望於自己的文化尊嚴在加拿大喪失殆盡。正因此,即使躋身於多倫多這樣的豪華大都市,高力偉總感到懸浮無根:“這座巨大的城市離我非常遙遠,對它我感到疏遠,我無法擺脫那種飄泊旅人的感覺。我深深感到哪怕在這裡再呆更長的時間,也仍然找不到心靈的歸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發了財,我不會感到幸福。”“加拿大,這是一個好地方,卻不是我心靈的故鄉。”
高力偉終於啟程回國了,懷裡揣著一張人人羨慕的“綠卡”。周圍的朋友打賭說他即使為了那張綠卡也還會再回來,只有和他一起在中西文化的緊張對話中煎熬過的林思文深知他不會再回來了,因為她知道“根”對於一個具有文化自尊感的人文知識分子來說是多么地重要。
小說中也用大量的筆墨描寫了高力偉與林思文為了家庭生活主導權的爭吵,林思文處處顯示出女人的能幹與固執,處處要為高力偉的前途與生計作出安排,這不僅因為她在潛意識中覺得是自己將高力偉帶到了這個令人嚮往的地方,是她用自己的獎學金支付著這個家庭的費用,而且因為她覺得自己對加拿大的異域文化與環境十分熟悉,理所當然地對這個家庭的生活安排具有最後的發言權。高力偉拚命地去掙錢,與眾不同地故意放棄攻讀學位的機會,在一些家庭瑣事上一味地堅持自己的主張,看起來好象是在堅守一個男子漢的人格,但實質上所抗爭的恰恰就是這種家庭中的文化優越感。中國的本土文化傳統是植根於宗法家族制度的,夫唱婦隨,夫為妻綱,這是典型的儒家文化觀念。所以,高力偉對男子漢人格的堅守未必不就是對自己本土文化的堅守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有必要將這部已負盛名的留學生小說置放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留學生母題中來考察,以便真正把握到這部小說所顯示的種種歷史與文化的信息。
作者簡介
 閻真
閻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