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簡介
 《小說》
《小說》它又叫《詩意的年代》。似乎源起於會議之國的小型講座會,或者是萬會之國一個小會引發了編導者的靈感。它來得相當無聊,最無聊的一群人聚在一起開一個最無聊的討論會,討論的主題是"什麼是詩意",詩意的年代何在。
開場一個象徵鏡頭,影機先是追蹤著火車,開進小城,再走到大街小巷,然後停靠酒店,走進侷促的會議室。接著,一批有頭有臉的作家殺入鏡頭,阿城、王朔、馬原、方方、余華、棉棉,從阿城的“詩意”考古開始,講到“有錢就有詩意”。各抒己見的過程中,大家談得性起,漸將詩意按壓在自我之下。鏡頭有時溜出來,看另一種風景。一旁的會議策劃人,在酒店偶遇舊愛,更能體味點點詩意。演員王彤和王志文,就演著也許由作家虛構的故事,他們的存在,比作家更真實。呂樂一個革命式的舉動:拆走紀錄片與劇情片框框,將兩者放在同一議題與空間自由對話 。
影片一開始和大部分的時間,作家們聚在一起侃“生活中的詩意”。 雖說並不有趣,但看看各色嘴臉,倒也不難看。 難得的是各人的發言盡顯各人特色和氣質。 最出乎意料的是方方,如此樸實和世俗; 最討厭的是棉棉,氣質低下; 阿城最儒雅,也最淡定; 馬原最質樸。 丁天的發言盡顯對金錢的渴望,也得到一片讚揚之聲,讓人不禁感嘆,這群中國最好的小說家群也如此,現在的小說果真是沒法讀了。
拍攝背景
 《小說》
《小說》公元1999年,中國的獨立電影裡面還有些詩意的存在。這種詩意或許有些文人的酸腐氣,或許還有些理想主義的天真和浪漫,甚至還有些老套和惡俗,可今天想要找部這樣的電影已經很難了。
《小說》最終未能通過有關方面的審查。據知情人透露,導致被“斃”的原因是內容太晦澀,過於追求形式上的新奇。1999年11月,當“金庸王朔之爭”正炒得如火如荼之際,王朔突然秘密現身蓉城,同行的還有林白、阿成、趙玫、方方、馬原等知名作家,著名影星王志文和年輕演員王彤也隨之抵蓉,直奔郫縣一賓館。原來,一干人聚在一起是在秘密拍攝一部名為《詩意的年代》的電影,由中央電視台《天天飲食》欄目四川籍主持人劉儀偉擔任製片和導演。電影講述的是一位時任校辦工廠業務經理的大學講師(王志文飾),在一小鎮推銷淘汰商品時邂逅了從前的女朋友(王彤飾),這位女朋友正好是一次作家筆會的服務人員。兩人見面後的故事發展,由王朔、林白、方方等作家討論來設定。
影片拍攝過程中,劇組一直不太願意接受媒體採訪,尤其是男一號王志文更是難睹其真容,甚至出現“王志文從後門熘走”的怪現象。拍攝接近尾聲時,影片更名為《小說》。
拍攝花絮
在《小說》中,呂樂更加強調攝影機的調度,而幾乎放棄了場面調度。這裡的長鏡頭已遠離巴贊的長鏡頭理論,創生出更加單純的鏡頭語義。看上去的拼貼格局,把紀錄片與藝術片的界限粉碎而又貼上。細微的區別是,會議現場只有畫面沒有場面,會議之外才有場面,才有活生生的遭遇與"調度"。
僵硬的、僵死的、是會議和會議上的人,活躍的世界不在這種封閉空間中。且不說呂樂是否在彈擊中國的會議體制和被會議召之即來的"要人",只看他用攝影機面對現場的姿態,就可以明了他的“考古學”方式。
主創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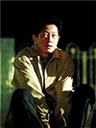 《小說》
《小說》《小說》於1999年在成都郫縣拍攝,講述名作家們的一次筆會過程,他們的議題為“這個年代還有沒有詩意”。而在他們的周遭,一對戀人重逢,舊情復燃。他們戀情的撲朔迷離暗合作家們的議題。該片邀得11個作家出鏡,王朔、阿城、方方、余華、趙玫、陳村、林白、馬原、綿綿、徐新、丁天皆是當今文學界的大腕。而影視界的另一明星大腕,王志文則出演與大學女友再次重逢的買賣人。
製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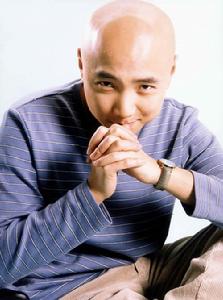 劉儀偉
劉儀偉這部電影的投資人是劉儀偉。10年前那個時候他的主業是在某台主持《天天飲食》節目。他當時選擇投拍《小說》的一個動機是“覺得世紀末大家都在致敬,我們應該向作家致敬,我就出了這么個點子:乾脆拍一個完全由作家來主導的電影。”拍攝成本只有200萬,卻囊括了當時中國作家圈中的幾位人物:阿城、王朔、棉棉、趙玫、陳村、馬原、方方、余華。全片84分鐘,近60分鐘都是在開作家筆會,聊的主題是“什麼是詩意”。剩餘的20分鐘,講的是一個俗套的愛情故事:一對大學時代的老情人再次重逢。兩人從偶遇時的興奮,到一起喝酒時互問對方家事的尷尬,再到飯後散步時的激情重溫,比較肉麻的有女人撒嬌式地要求男人再像當初她喜歡上他時那樣在學校乾涸的露天泳池裡跑圈,撒歡。最後,終於回到房間,兩人執手相看淚眼,女人一下撲到男人懷中,哇哇大哭。結局部分沒有演,而是採訪了來開筆會的所有作家對於結局的想像。最後一個鏡頭,女人扶著有些癱瘓的陳村回房間。想像和現實再次模煳起來。
影片完成後期製作後傳來送審時被“槍斃”的訊息。第一次拍電影的劉儀偉談到此事時顯得很是痛心,但不願說出被“斃”的具體原因。有趣的是,這部影片在2000年完整粗剪後拿給出品方,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的人放,結果當場就被一名電影發行策劃人評價為:“這什麼玩意?就這個放到電影院裡嗎?”於是,一直雪藏到2007年才斗膽跑出去參加了威尼斯電影節。至今仍地下著,連張盜版碟都沒有。
據透露,《小說》未能通過審查的原因,是因為影片內容很晦澀,形式過於追求新銳,與高曉松的《那時花開》如出一轍。此外,影片中作家座談的內容非議太大也是原因之一,這從王朔《無知者無畏》中收錄的部分談話內容可見一斑。比如說王朔的插科打諢依然很出彩,不但國罵連篇,觀點也相當激進,“我準備80歲的時候,吸毒而死”,此類言語應該也是該片無法過審的原因之一。
但是11年後再度在網路上熱播,當年作家們關於“詩意年代”的觀點卻依然不顯得過時,該片如今也引來了一批知識分子型的擁躉。知名媒體人魏英傑感嘆《小說》被封殺太可惜:“簡直是超強陣容啊!”導演張江南、作家慕容雪村等人也都在微博上發表了評論,繼續探討這個年代還有沒有詩意。2007年,該片還入圍了威尼斯電影節展映單元王朔對詩意的認知也很特別,他認為詩意是頹廢至極才會產生的東西,被社會拒絕至極,落到最低點,詩意就產生了,或者說是瘋癲的純粹精神的產物,有一點點的理性都是不行的,簡單說,需要藉助毒品,或者等七老八十,對這世界已經無欲無求,對周圍的環境和人已經無所求,不怕得罪朋友,摸著美女的小手兒也不會再有生理反應,變成純粹的欣賞和旁觀,詩意也就產生了。
影片評價
 《小說》
《小說》客觀上來說,《小說》是一部相當有想法和創意的電影,缺陷也相當明顯:作家們太大牌,每個人的發言都不是事先寫好的,各自觀點信馬由韁,已經處於完全不受導演和編劇控制狀態。
每個作家都對“什麼是詩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談到了詩意和物質和現實的關係。沒有繞開“錢”這個問題。王朔說,詩意和物質並不衝突。幾個女作家都將日常生活中的詩意看做最容易獲得和實現的一種詩意。還有一位男作家說,錢的力量太大了,但是等到賺夠錢再來尋找詩意,可能就很難了,不是找不到,而是壓根就不需要了。其實作家怎么看待詩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談論詩意本身就是一種情懷,或者是一種追求,只是似乎在10年之後,這看上去卻是一件極為風花雪月甚至有點裝13的事情。
之所以安排那出老情人再相聚,或許也是導演的一種一相情願。人到中年,成家立業,孩子可以跑出去打醬油了,生活還有詩意可言嗎?影片告訴你,有,還有,還真的有。但追尋初戀的感覺,陷入柔軟的回憶中,面臨道德和情感的雙重考驗,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地起。當你發現,青春真得已經不在,詩意僅僅是一段短暫地讓人不知所措的精神出軌,可能你真的會斷了尋找詩意的念頭了。
 《小說》
《小說》可是10年前,好歹還有一個想要去尋找的念頭。而出軌,也能被看做一場隆重的儀式,可以用來祭奠那些逝去的人,逝去的愛。沒有床戲,只有微笑,還有些許無奈和傷感。
影片討論的是“詩意”,片名偏偏叫《小說》。 嘴裡講的是詩意,但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直接的反應還是最現實的。 也許吧,虛構的儘管是虛構,但也逃不出現實。
這部電影,實驗性質大於觀賞性,也就是說,“玩一玩”。 象徵,可以作為一部電影的唯一目的么? 起碼,在當今的中國,似乎奢侈了一點。 不過,一個電影正常發展的健康的社會,是可以容忍和支持這樣的“玩”的。
所獲獎項
《小說》曾在第31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2007年《小說》入圍2007年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
![《小說》[2006年電影] 《小說》[2006年電影]](/img/4/301/nBnauM3X1IDN0ITMxQzM3gDO5QTM5cjN0EjM0QTNwAzMwIzL0MzL0c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