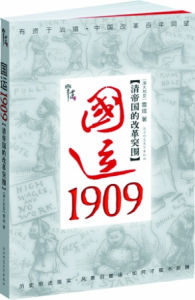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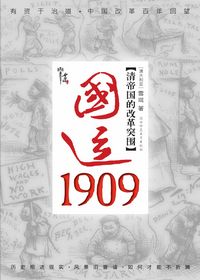 國運1909
國運1909時至1909年,改革已前所未有地成為大清國的全民共識及主流話語體系的主鏇律,意欲在國內挺腰,在國際昂首。然而對於攝政王載灃來說,最為鬱悶的是,精心設計的改革,在經過官僚體系的執行後總是會“爛尾”:明明是利國利民的仁政,最後卻被大小領導幹部轉變為擾民和斂財的工具。新的社會矛盾糾結纏葛,舊的官僚體制處處掣肘,大清國這艘巨大的航船行駛至暗礁林立的險灘。1909年這個春天的故事,竟是一步步演繹成了王朝悲劇……
作者簡介
雪珥,澳大利亞華人,非職業歷史拾荒者,職業商人。曾任公務員、記者、財經評論員、律師,現從事地產、金融、電子商務等熱門俗務。除了花費必要的時間去賺取必要的金錢外,其餘時間都投入了文物收藏、歷史研究和寫作,以海外史料解讀中國近代史,在華人文化圈中廣為流行。和訊部落格、搜狐部落格、網易部落格文化名人。海內外多家報刊專欄作家,著作有《大東亞的沉沒》《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看中日戰爭》等。
書籍目錄
第一章金鑾殿上新來的年輕人
紫禁城的雞叫
1909年:春天也有故事
愛新覺羅軟著陸
大清青年近衛軍
“橡皮圖章”雄起
大海航行“拷”舵手
第二章老官場的彎彎道
袁世凱冬眠
金槍不倒張之洞
官場如賭
第三章黃龍旗下的資本主義
“鐵老大”出軌
愛國公債終誤國
“牛”背上的大清
第四章大清國的“新新人類”
“半吊子”大躍進
難產的“美國夢”
文化有罪,漢字無理
第五章鼓與呼:世亂難為人
“爛尾”大清國
宜春沒有“春天”
在失望的田野上
槍桿子霍元甲
文摘
 醇親王
醇親王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變的狂風暴雨中展露無疑。作為朝廷中熟悉國際國內情況的少數明白人,奕劻堅決主張及早防止事態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軍事上的巨大麻煩。他的“右傾”言論遭到以端郡王載漪為首的“不明外事,專袒義和團”的“極左派”的不滿。英國外交官在發給倫敦的報告中認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間,慶親王和大學士榮祿似乎已成為對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牽製作用的僅有的人物”。載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須清除的政敵,義和團們則將他描繪成了大漢奸,攻擊奕劻的大字報貼滿北京街頭,已經失控的民間暴力清晰地將矛頭指向了這位王爺。在此後討論局勢的高層會議上,奕劻一概裝聾作啞,但從未改變自己的觀點。高喊著“扶清滅洋”動人口號的“極左派”們最後留下一地雞毛,在八國聯軍的炮聲中撒腿就跑,把收拾爛攤子乃至不得不“賣國”的髒活慷慨地留給他們本想誅之而後快的“漢奸”奕劻和李鴻章。在八國聯軍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鴻章“如一囚徒”或“受到禮遇的俘虜”,為明知不可爭的城下之盟而勉強一爭,其間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較公認的是,因為這一功勞,慈禧太后終其一生對奕劻和李鴻章都是優容有加。
醇親王是個年輕人,他成長的時代正處於現代思想在東方世界取得立足點之際,他通過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視野並沒有因為紫禁城的城牆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中國其他統治者所沒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於現代觀點,以透視的目光,從與其他世界強國的對比中來認識自己的國家。——《紐約時報》,1908年11月22日
袁世凱和慈禧太后的憲政改革正在由攝政王加以籌備,在執行預備立憲上,他顯然是真誠的。的確,很有可能他感到無力逆潮流而動,相信緩慢地往前走,試圖減少一些風險。但對於中國引入代議制的不安,不僅限於保守派,相反,一些最開明的官員,由於了解中國人的性格,也擔心憲政運動很可能失控。——美國駐華公使館代辦費萊齊(HenryP.Fletcher),1909年8月28日
中國初辦憲政,一切正在艱難,民意斷難即恃,更不可妄恃強力……貴國辦理新政,外面極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測,危險不可不防。
——伊藤博文,1909年10月23日清政府開始搞改革時姿態很消極,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之後,它對改革的活動就越來越認真了。可是在這時候,改革並不如康有為和梁啓超所主張的那樣是為了富國強兵以防禦列強的侵略,改革的目的勿寧說是為了保衛清政府不受漢人與外國人兩者的攻擊。換言之,改革是為了保住清王朝。——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等,《劍橋晚清史》
書評
100年後,我們還在河裡摸著石頭。2009年,也在水裡掙扎著想找到個小石塊的雪珥,不自量力地萌發了撰寫一部“石頭記”的夢想——回顧中國百年改革史。於是,有了這些淺薄而粗陋的文字。一年來,這些文字每周一次在《中國經營報》上與讀者見面,居然在這打醬油盛行的蝸居時代也能引起小小的反響。我深知,那只是因為這話題搔到了大家的癢處:在河裡掙扎的你我實在很想知道前人是如何摸著石頭過河的。
醇王府的主人奕譞,據說是道光眾兒子中資質最差的,和其兄鹹豐皇帝、恭親王難以相比;但晚清最後的半個世紀基本上就是奕譞一門的天下,光緒、宣統兩任皇帝都出自他的門戶。可見,政治上的最後勝利者和最大受益人,絕非那些聰明外露、個性張揚的人。
“待業”時的醇親王是一個堅定的“左派”,對執政的六哥恭親王多所不滿,認為他是個當權的“走資派”。等到將六哥擠兌下崗,他喜滋滋地挑上權力的擔子,才掂量出那不可承受之重。據說,嘗到當家人的難處後,醇親王曾跑到六哥家中,道歉認錯,虛心討教。看人挑擔不吃力,站著說話不腰疼,這是中國社會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