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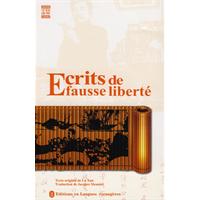 偽自由書
偽自由書《偽自由書》是魯迅的一部雜文集,收錄了魯迅在1933年所寫的雜文四十三篇。包括《觀斗》,《電的利弊》,《賭咒》,《從諷刺到幽默》,《推背圖》,《中國人的生命圈》,《大觀園的人才》,《言論自由的界限》,《天上地下》等。
《偽自由書》是1933年1月底至5月中旬,魯迅寫給《申報》副刊《自由談》的短評合集。《偽自由書》是魯迅在特定的歷史時代,以雜文為武器進行政治鬥爭和思想批判的戰鬥記錄;然而,它透過個別事件揭示的客觀規律,它剖析具體事物的精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卻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它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武器。本書為法文版。
作者簡介
魯迅(1881.9.25—1936.10.19),原名樟壽,後改名樹人,字豫山,後改為豫才,祖籍河南省正陽縣,從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時(1918年5月),始以“魯迅”為筆名。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說、雜文為主,代表作有: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等,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舊事重提》),《野草》,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南腔北調集》《三閒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雜文》等。
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國小語文課本等,已成為家喻戶曉的藝術形象小說《祝福》《阿Q正傳》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北京、上海、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同時他的作品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
序言
這一本小書里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為止的寄給《申報》上的《自由談》的雜感。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並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里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郁達夫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日:那是可以的。
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日: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迴避創造社裡的人物。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於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日可以。但應而至於“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於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裡,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里看見一篇文章,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里的第一篇《崇實》;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乾”,有時也用“乾”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於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於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並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都是做著關於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於左翼文學者。此外為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後,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麼關係。但另有幾篇,是因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並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里,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是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於上海寓廬,魯迅記。
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里已經說過了。到這裡,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
這也並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並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只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菸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著這樣的一段——“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醜陋,人復貧窮,向為泥水匠,曾傭於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異常,人亦猥瑣。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與盛相遇,楊奸其女。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奸十餘次,當派探員將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確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系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姦罪論,應請訊究。
鏇傳女父盛寶山訊問,據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詰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並將被告誘姦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將被告扭入捕房雲。繼由盛金弟陳述,與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系被告將我喚去,並著我不可對父母說知雲。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慾奸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系將盛女帶出遊玩之次數等語。劉推事以本案尚須調查,諭被告收押,改期再訊。”在記事裡分明可見,盛對於楊,並未說有“倫常”關係,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號和頭號字的——攔途扭往捕房控訴乾叔奸侄女女自稱被奸過十餘次男指系遊玩並非風流它在“叔”上添一“乾”字,於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準“逆倫”的重犯了。中國之君子,嘆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鋪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只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幾句奇文,他們便什麼“員外”什麼“警犬”的狂嗥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志士。
魯迅作品
| 魯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他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髮像刷子一樣直豎著,濃密的鬍鬚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毛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