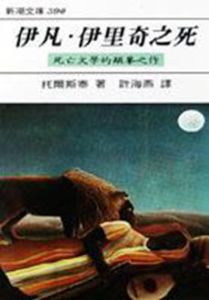內容簡介
《伊凡·伊里奇之死》這篇小說描寫的是伊凡·伊里奇從生病到死去這一段時間裡所經歷的一切,重點描述了他在肉體病痛和精神困惑的雙重襲擊下的掙扎和反思。作者使用現實主義手法,通過對主人公具體言行的描述,形象而深刻地刻畫出瀕死者內心的感受,寫出了人肉體毀滅與靈魂覺醒共同發生的情形,揭示了人類在生死問題的一些普遍表現,讀來給人震撼。
小說人物
伊凡·伊里奇首先是一個正常的人,人們說“他是一個好人”,其次是一個法官。應該說“人之初性本善”,可是吃沙皇的飯,給沙皇當嘍羅,借沙皇吆喝,大家都一樣,混日子。而不幸患病,那種國家機器的冷漠無情才表現出來了。辦公室里,“一聽到伊凡·伊里奇的死訊,辦公室里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死對他們本人和親友在職位調動和升遷上會有什麼影響。”這與現在多么相似啊!家裡呢,應該有溫暖吧?也沒有,妻子女兒盡了幾分孝心,漸漸不耐煩了,甚至對病人吹鬍子瞪眼睛。親朋好友呢?與我們周圍有時候差不多,問候幾句,巴望幾眼,準備辦喪事。
在忍受了各種懷疑、難堪、恐懼、討厭、折磨、疼痛之後,“他吸了一口氣,吸到一半停住,兩腿一蹬就死了。”一個俄國官僚的可憐的無奈的死亡。沒有寫官場的討厭腐朽的伎倆秘籍。
小說評論
托爾斯泰對伊凡·伊里奇熱衷於其角色(檢察官)生活與追求“私人尊嚴”刻畫,正是應表明他如何固執地忘卻自己死亡。
伊凡·伊里奇死亡掩蓋是如此之深,以致雖然疾病已在他體內引起了可怕、前所未有變化,但他始終不能正視死亡存在,他無論如何也不能處之泰然,他既莫明其妙,也無法理解這怎么可能。他總想撇開“自己快應死了”念頭。努力想把它當作假、不公平、不健康,力圖召喚別念頭來代替它。他現在“大部分時間消磨在試圖恢復能把死置之腦後感覺上,有時候他對自己說:我將再去辦公室,那一定能使我活下去。”(第六章)於是,他真辦公去了。
的確,人生太容易假作真時真亦假。在把死亡掩蓋得嚴嚴實實生活世界裡,那最令人操心不就是充當什麼角色問題嗎?還有什麼比維護和鞏固自己角色地位更重應?還有什麼比在這種角色位置上體會到那美好“私人尊嚴”更真實?相對於角色生活來說,一切生活問題都只是生活瑣事,它們都將圍繞著角色生活展開來解決。在這個生活世界裡,死亡甚至作為字眼都很少在人們心中閃現、停留過。因此,當它通過病痛而顯示它現實存在時,伊凡·伊里奇感到莫名其妙:在這個如此有“意思”如此重應生活世界裡,怎么會突然冒出這個陌生絆腳石?這肯定是搞錯了。於是,死亡這一生命中最本已、最真實可能性存在反而成了假,成了不健康幻覺,它至少象其他生活問題一樣可以通過“辦公”來消除和解決。
對死亡這種掩蓋構成伊凡·伊里奇生活中一個“彌天大謊”。這個謊不僅侵蝕了他一生生活,而且使他在臨死前精神備受折磨。不治之症實際上已把伊凡從他長期扮演角色(法官、同事、丈夫、朋友等等)生活中揪出來,中斷了他角色活動,迫使他退出關聯世界而進入一個無角色境地,這也是一個需應獨自承擔起自己向死亡存在境地。但是,長期生活於角色中伊凡顯然無法適應和接受這種境地。因此,當同事來探訪他時,他一方面渴望同情,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自我欺騙,把自己構想為仍是那關聯世界裡角色。所以,在來訪同事面前,他竭力擺出一幅嚴肅、壯重面孔,並打起全幅精神對同事大講自己對一項裁決意見,以顯示他仍是關聯里一個重應角色。結果,他當然得不到任何同情。
在臨死亡前三天三夜裡,最讓伊凡·伊里奇痛苦似乎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他感到“他被推進黑袋,可是又下不去,令他下不去原因是他一直認為他一生過得很好,這個應活下去理由糾纏住他,不讓他朝袋裡鑽,因此,最使他難過。”(第十二章)
這裡,“黑袋”就是死亡象徵,“下不去”意味著在心裡拒斥死亡,仍把死亡當作一件外在事件來排斥。而拒絕死亡理由則是不願承認自己一生沒有按“應當方式”去生活,他仍固執地認為自己一生過得有滋有味:我一生官運不錯,所任角色都至關重應,我也都克盡職守,而由此帶來一切也都令我舒心暢快。既然這種角色生活如此美好、真實,就不應該突然結束,而應該永遠繼續下去,至少不應該這樣匆匆了結。確,對於完全陷於角色生活常人來說,這個生活世界不應是有終結,它將永遠進行下去。因為終結性或死亡已被這種角色生活完全忘卻和掩蓋,即使有人死了,那也只是這個世界偶發事件,只有不幸人才會碰上,而生活不應偶發事件而中斷。而我伊凡·伊里奇歷來都是很幸運,現在又處在既令自己高興也令許多人羨慕位置上,有許多重應事情應處理,而且不會有許多美好事情將隨之陸續到來,因此,我沒有理由結束現在生活。
啟蒙意義
任何讀過19世紀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日記與傳記(不計其數)的讀者都知道,西方文學史上幾乎找不到一個作家,像他那樣懼怕死亡,也沒有一個作家像他那樣自幼幻想死亡(情狀),凝視死亡(真相),並想盡辦法超剋死亡。他在1884年完成的“死亡文學”的不朽作品《伊凡·伊里奇之死》,便是顯著的例證。這一作品的創作靈感,來自1881年一位法官瀕死之前,針對往逝的生命)-JS~自我總結與評價的真實故事。托爾斯泰經由夫人的轉述得知此事,大大激發了他的寫作興趣與靈感。我們可以說,《伊凡·伊里奇之死》雖取材於那位俄國法官的生死掙扎,實質上卻反映著托爾斯泰自己多次有關生死問題的親自體驗,充分彰顯了他日後在《藝術論》(Wh口tIsArt?)中所極力標榜的“藝術為人生”(artforlife’ssake)立場。總之,這一中篇小說是托爾斯泰為了超越生死大關,而獲得終身不渝的宗教與道德的根本改信之後,首次發表出來的力作。從此以後,他的一切作品(包括第三部長篇小說《復活》與《藝術論》在內)全然抹去純文藝色彩,只為耶教的博愛主義與道德的社會主義服務了。
《伊凡·伊里奇之死》出版之後不久,著名作家斯塔索夫(Stasov)函告托爾斯泰說,他從未讀過如此精彩的傑作:“人間還未產生過這樣偉大的創作。與你這篇70頁左右的作品相比,其他一切作品就未免顯得無足輕重了。”作曲家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也在日記中寫道:“我剛讀完《伊凡.伊里奇之死》,因而更加確信,托爾斯泰是地球上最偉大的作家。”由此可見《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文學成就之高,尤其在“死亡文學”這一領域裡,無疑是首屈一指的最高成就。1880年威爾(RobertWeir)教授所編成的《文學中的死亡》(DeathinLiterature),就在結論部分專門收錄了這一篇作品,可見它的現代意義與文學價值。它的現代意義在於:它是“死亡學”與臨終精神醫學研究以及“死亡教育”經常使用的不可或缺的閱讀資料。我們如果細讀《伊凡·伊里奇之死》,則不難發現,托爾斯泰的心理描寫淋漓盡致——如伊凡對醫生的不信任,對上帝的“埋怨”,對妻女外出的嫉妒與憤恨,絕望無助的孤離感,在生命盡頭對於死亡的“接受”等等,已經預見了庫布勒·羅斯醫師觀察所得的心理反應及其階段之種種,實在令人嘆賞不已。
《伊凡·伊里奇之死》在文學創作與哲學思想層面,也預見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以來,盛極一時的歐洲實存主義(或稱存在主義)的思想胎動與探索問題的主要趨向;並與後起之秀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們》(TheBrothersKaramazov)等名著相互輝映,構成實存主義文學的先驅典範之作,可以說對於整個現代實存主義文學運動的醞釀與發展,極盡開拓之功。再者,我們知道,“實存(兼涵現實存在與真實存在二義)”(existence)、“實存的抉擇”(existentialchoice)、(生死關頭的)“極限境況”(theborder’一situation)、“實存的本然性或真實性”(existentialauthenticity)、“實存的非本然性”(existentialinauthenticity)、“存在的勇氣”(theCOUr’agetobe)等實存主義的慣用概念,都是20世紀20年代以來經由海德格爾(Hei.degger)、雅斯培(Jaspers)、薩特(Sartre)、田立克(1'illich)等人的哲學探索而逐漸形成的。這些概念今天已是現代西方思潮方面的一般常識或口頭禪。但是一百多年前,托爾斯泰居然能以《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小說體裁,步步挖掘人在面臨死亡(極限境況)之時顯現出來的實存意識(不論是真實本然性的或非本然性的),實在不能不令人嘆服他那生來獨特的生死體驗,犀利無比的心理描寫與實存分析(existentialanalysis),以及呼應20世紀實存主義思潮的(新)時代預感。譬如海德格爾在劃時代的哲學名著《存在與時間》中所作的關涉生死問題的人的存在分析,多半可在半個世紀以前問世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找到實存文學的線索或例證。事實上,海德格爾在書中附註提到了這篇作品的重要性,可見它對海德格爾的“死亡”討論極有影響。
表面上看來,《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情節與結構都很簡單,而故事的展開也多半平鋪直敘,沒有複雜的曲折。因此,缺乏“創造地閱讀”能力的普通讀者,容易誤認為這篇作品平淡無奇,不過如此,而完全忽略其中的深意。其實,托爾斯泰善用他那平生最擅長的白描手法與寫實筆調,所刻畫出來的人際關係與人間形象,以及所透視出來的(主要登場人物的)心理反應、(伊凡在死亡邊緣的)最後掙扎、(生死問題)的終極關懷等等,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仔細閱讀,仍然具有令人激賞而發人深省的現代意義。……P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