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
簡介
操派兵抄追殺曹兵的楊昂、楊任之後,勝得陽平關,又得南鄭。
操計收龐德又得東川。
西川人聞操至,皆懼,孔明以書與孫權,交割荊州三郡,教權領兵攻打合肥,操提兵殺奔濡須塢來。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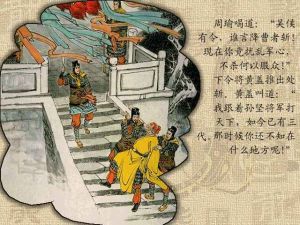 《三國演義》第六十七回
《三國演義》第六十七回卻說曹操興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個寨柵,迎敵曹兵。兄在漢寧,多撥糧草應付。”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即日起程。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睏,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夏侯淵、張郃急上得馬,四下里大兵擁入,曹兵大敗,退見曹操。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若遠行疲睏,可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眾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為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即引軍回寨,謂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許褚曰:“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憚勞。”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看張衛寨柵。三匹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柵。操揚鞭遙指,謂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言未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褚大呼曰:“吾當敵賊!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二將。楊昂、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退去,其餘不敢向前。徐晃保著曹操奔過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卻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操重賞四將。
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勢未見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兵每日提備,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為名,使賊懈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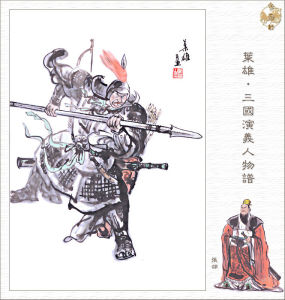 張郃
張郃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紥住。卻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散,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大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占了寨柵。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夾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著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並諸寨。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張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卻說曹操提軍將進,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哨探,正迎著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不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槍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被淵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閻圃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圃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曾行。現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
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斗,使其力乏,然後擒之。”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夸龐德好武藝。曹操心中大喜,與眾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操曰:“何由得人入南鄭?”詡曰:“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卻於夤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卻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校,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副,今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
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遠去埋伏;卻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卻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提備,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急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
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徑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甲為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賣此一陣。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閻圃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于山坡上喚曰:“龐令明何不早降?”龐德尋思:“拿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鉤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曹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為實。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炮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廩府庫,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閉庫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為內應。操得書,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而待斃矣。某守城,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魯從之。閻圃諫魯休出。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開。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拜。操大喜;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封魯為鎮南將軍。閻圃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即命斬之於市曹示眾。後人有詩嘆曰:“妨賢賣主逞奇功,積得金銀總是空。家未榮華身受戮,令人千載笑楊松!”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智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曹操嘆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守關隘,不可犯矣。”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卻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淝,懼孫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遣舌辯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淝,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為使?”伊籍曰:“某願往。”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荊州,知會雲長,然後入吳。
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何為?”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為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所有荊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今合淝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東川,即還荊州全土。”權曰:“汝且歸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眾謀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為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淝,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回;又去餘杭取凌統回。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現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谷於合淝,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淝。”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為先鋒,蔣欽、潘璋為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為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卻說軍馬渡江,取和州,逕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麾蓋。權回寨,問眾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淝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權從之。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寧手執鐵鏈,冒矢石而上。朱光令弓弩手齊射,甘寧撥開箭林,一鏈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眾多降,得了皖城,方才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報皖城已失。遼即回兵歸合淝。
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三軍,重賞呂蒙,甘寧諸將,設宴慶功。呂蒙遜甘寧上坐,盛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甘寧殺父之仇,又見呂蒙夸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知其意,推開果桌起身,兩手取兩枝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至筵前。眾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二人休念舊仇,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孫權再三勸止。至次日,起兵進取合淝,三軍盡發。
張遼為失了皖城,回到合淝,心中愁悶。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個,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是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攻合淝。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張遼將教帖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將軍之意若何?”張遼曰:“主公遠征在外,吳兵以為破我必矣。今可發兵出迎,奮力與戰,折其鋒銳,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李典素與張遼不睦,聞遼此言,默然不答。樂進見李典不語,便道:“賊眾我寡,難以迎敵,不如堅守。”張遼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顧公事。吾今自出迎敵,決一死戰。”便教左右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曰:“將軍如此,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聽指揮。”張遼大喜曰:“既曼成肯相助,來日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先斷小師橋,吾與樂文謙擊之。”李典領命,自去點軍埋伏。卻說孫權令呂蒙、甘寧為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陸續進發,望合淝殺來。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迎。甘寧出馬與樂進交鋒,戰不數合,樂進詐敗而走。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催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炮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已到。凌統手下,止有三百餘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張遼引二千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折丈余,並無一片板。孫權驚得手足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約馬退後,再放馬向前,跳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余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後人有詩曰:“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淝。退後著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寧、呂蒙引軍回救,卻被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中數槍,殺到橋邊,橋已折斷,繞河而逃。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棹舟接之,乃得渡回。呂蒙、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眾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卻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興兵進取,恐合淝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悌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眾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稍定,已有提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岩等隘口。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來。正是:鐵騎甫能平隴右,旌旄又復指江南。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賞析
從整個歷史看來,建安二十年並非一個很特殊的年份,即便在漢末諸侯混戰的建安中,也是如此,在此之前,官渡的建安五年,赤壁的建安十三年,在此之後,關羽兵敗荊州的建安二十四年,都遠比此一年重要顯眼的多。但是,在這一年中,發生的兩件事,對之後三國鼎立的局面也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這便是在本回演義中提到的曹操平定漢中和孫權兵敗逍遙津。
曹操早有奪漢中之心,當時天下,北方為曹操所控制,而南方則是孫劉聯盟之天下,而在上一年劉備得蜀之後,不在曹劉孫三家控制之下的惟有漢中和遼東公孫兩處了,而遼東地處邊遠,對當時的戰局影響不大,所以實際上唯一游離在三家勢力之外的只有漢中張魯了,而在當時的局勢下,欲想在三家之外獨立求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漢中的地理形勢更是如此。
漢中與蜀地本同屬益州管轄,劉焉任益州牧時心懷不軌,遣張魯入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而在劉焉死後,張魯坐大,劉璋與張魯反目,殺張魯母親與弟弟,於是蜀地與漢中分成兩地相互攻伐,劉璋請劉備入蜀的一大目的便是請劉備攻打張魯。從地理形勢上看,漢中與蜀地唇齒相依,孫權欲攻蜀遣使於劉備時便談到:“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而在曹操攻打漢中時,黃權便對劉備言道:“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而在曹操獲取漢中後,司馬懿與劉曄都進言乘勢再取蜀中,(曹操回之:“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這便是之後得隴望蜀這個成語的源頭。)在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之事,益州楊洪也談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若想要蜀中安全,漢中必然要得於手,反之亦然。
曹操攻漢中並不順利,在陽平關下他幾度生起退兵之意,最後破陽平關之敵也是意外之勝。史栽:
“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嘆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侍中辛毘、主簿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
應當說,此時的曹操已經失卻了活力,曹操的智謀還如以往一般,凡戰事也是親歷親為,但是卻日漸暮氣,身邊重要的謀士一個個逝去的緣故,往日為之鎮守後方的荀彧已經在建安十七年離世了,而向為軍前謀主的荀攸也在之前一年的建安十九年逝世,現在的曹操也已經過了花甲之年了,已成老翁了。這次攻陽平關,三年後與劉備爭漢中,曹操都是在戰不多時便起了退兵之心,當年還有荀彧進書勸阻,如今還有誰呢?“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在曹操年少時根本就不會有這樣的想法,更別提說出口了。此時的曹操已經老了,智力雖還未消退,但是戰意雄心卻日漸淡薄,此時的他或許也已經明白,在他有生之年,擊敗孫劉,一統天下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然而,此時發生的奪取漢中就成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這不單是曹操親征獲取的最後一次大勝利,也是奠定日後三國基礎的一次大事件。
曹操攻取漢中雖然在陽平關遇到了波折,但是總體來說可以是一場異常輝煌的順利,甚至可以與當年不戰而得荊州相比,陽平關一破,張魯隨即逃亡,而寶貨倉庫並不銷毀,盡歸曹操之手,不久張魯便舉家歸降。漢中可以說以及完整的落入曹操之手。當時天下大亂,諸多人為避禍而遷徙,其中劉表的荊州,劉璋的益州,張魯的漢中相對比較穩定,就成為了遷徙的重點地區,比之荊州益州來說,漢中雖然不及,但是也相當的富庶,關中之民遷入極多。若是劉備先得漢中,則可利用漢中之資以謀關中之地。然而和當年的荊州一樣,曹操先得漢中,並盡取其資其民,這一來曹操盡可以漢中之力威脅益州,二來曹操遷漢中之民,“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這其中應該不乏五斗米道的信徒,日後五斗米道在魏晉流傳甚廣應該是有這些人的功勞,這可是日後道教的正宗。或許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也為了五斗米道的傳播立了大功,畢竟治病是宗教傳播的一大途徑,有點扯遠了。)之後劉備雖取漢中,但是得到的漢中已經不是完整的漢中,就好象當年荊州一樣。周群稱劉備與曹操爭漢中:“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雖然有些誇張,但是倒也不甚為太過。這使得日後蜀漢欲出漢中北伐在物力人力缺欠了許多。(尤其在不久便失去荊州的情況下,影響更大。)從某種意義上說,漢中在建安二十年的歸屬是日後蜀漢不得出川其中的一根稻草。
當然,劉備並不是看不到這點,只是他也有自己頭疼的事,建安十九年他才得到益州,而之後孫權便來索要荊州了,甚至大軍壓境,劉備不得不回到荊州以敵孫權,所以在得到漢中被曹操攻取的訊息後他雖然派黃權去迎接張魯,但是畢竟已經太晚了。而劉備回荊州做的一件事則和我們要說的本回的另一大事件有關。這就是孫權兵敗逍遙津
我們在之前借荊州一章的最後曾經說到,孫權借江陵給劉備的最終結果是兩家重分荊州,這一次重分孫權是利用了劉備後方有曹操這個大患而達到了目的。而另一方面看,曹操在劉備的後方漢中,這也意味著曹操的後方大為空虛,這使得孫權再度起了攻合肥之心。
兩淮之地的重要性,我們在好幾章中都談到了,江東要安全,獲取兩淮是極其必要的,建安十九年孫權便派呂蒙攻取皖城。(演義中將取皖城和攻打合肥混為同一時期先後發生的事,但是實際上這是兩年發生的兩個事件。)而建安二十年孫權與劉備重分荊州,獲取三郡,勢力大張,而曹操遠征,合肥在短時間內得不到曹操的支援,這使得孫權取合肥之心又起。於是糾集大軍北進,然而結局是極其悲慘的。孫權大軍先是被張遼李典八百人殺的大亂,演義在此段尚不及史書精彩,演義中有兩次孫權與張遼之戰,除本回外,便是五十三回,但是實際上只有建安二十年的這次而已,而且尚還缺少了下面史書中所談到的八百人破吳軍之事,我們看史書中載:
“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沖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
而後在逍遙津被張遼偷襲,演義中主要寫便是逍遙津之戰,演義中和史書中的記述相差無幾,這戰在戰事上遠不及那八百人破吳軍精彩,不過卻是險些捉住孫權,孫權在逍遙津當真可稱得上落荒而逃。合肥之役,曹魏軍以少戰多,卻戰果輝煌,這對於吳軍的打擊甚大,演義中說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雖然是小說家言,也不能不說孫權軍在此戰後,對於駐守合肥地區的曹魏軍有了恐懼心理。在之後許多年,孫權尤稱:“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可見此戰對於孫權本人與吳軍的影響有多大,在這種心理陰影下,吳軍對兩淮地區的攻伐很長時期內陷入了無心也無力的狀況之中,再之後曹操南下,雖然沒有獲取大的戰果,(這是在建安二十一年冬天發生的事,但是演義中卻寫成緊隨合肥戰役之後,這明顯有誤,那時曹操還在漢中呢,插上翅膀也飛不回來。更別說曹操自漢中回來軍隊休養整頓了好一段時間才再次出征了。)但是孫權在次年卻遣使求和,這不能不說是在赤壁之後孫權作出的一大轉變,而這一轉變很大程度上與合肥戰役中張遼所部的表現大有干係,原本孫權一直希望能獲取兩淮之地,以保障江東安全,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進展尚還算順利,但是合肥一役卻讓他感受到了挫折,對於北方的曹魏,他暫時不敢動兵了。
疆土既然不得北進,那就要另尋出路,如此一來,西面的劉備軍便成了目標,四年之後孫權破盟攻打關羽,不能不說與建安二十年的合肥大敗有著某種程度的聯繫。
回評
毛宗崗批語
操以許褚為忠臣,是賊臣亦愛忠臣也;操以楊松為賊臣,是賊臣亦惡賊臣也。然但以褚之助己者為忠,猶未為知忠臣;能以松之助我者為賊,則真能惡賊臣矣。夫賊而即見惡於賊,亦何樂而為賊?以賊而亦知賊之可惡,復奈何而自為賊哉?
龐德之背馬超而從曹操,猶不至如楊阜之攻馬超以助曹操也,而君子以為無異;不惟無異,且有甚焉。凡阜之所以涕泗縱橫,必欲破馬超而後快者,不過以韋康之見殺耳。阜為康之參軍;而為康報仇至於如此之激;德為馬騰家將,而乃甘心事一殺馬騰之曹操,是獨何心哉?君子曰:龐德於是乎不及楊阜。
操之得隴而不望蜀,蘇子瞻以為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斯固然矣。然操之懷懼者三:前以初破袁紹之眾;遠行疲敝,跋涉江河,致有赤壁之敗;今以初平張魯之眾,歷險阻,越山川,不恤其勞而用之,安能料其必勝乎?一可懼也。使荊州會合東吳而乘虛北伐,將奈之何?二可懼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蕞爾之城,猶能焚我師而挫我銳,況今有西川之地而欲與之抗衡?三可懼也。操實有此三懼,而假託知足以為辭,此奸雄欺人之語耳。
孫、劉之分荊州,非孫、劉之分之,而曹操分之也。何也?曹操不下東川,則荊州不可得而分也。前此之許分而不果分,非關公之阻之,而孔明阻之也。何也?伊籍不至荊州,則荊州又不可得而分也。交割三郡,但有諸葛瑾來,而無蜀中之使命偕之以來,關公已知孔明之佯許矣。若雲“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伊籍一至,關公即便交割耶?
兵有遲則得,速則失者,郭嘉之定遼東是也;兵有速則得、遲則失者,呂蒙之取皖城是也。城有戰則失、不戰則不失者,曹拱之守潼關是也;城有戰則能守、不戰則不能守者,張遼之守合淝是也。或遲、或速、或戰、或不戰,用兵之道,變動不拘,可當《孫子》十三篇讀。
金雁橋之斷,孔明以此擒張任;小師橋之斷,張遼不能擒孫權,非張遼之拙於人謀,而實孫權之邀有天幸也。君子於檀溪之奔,知成都之景歷有歸;於逍遙津之脫,亦知陵之王氣有驗。
李贄總評
只一龐德,孟德多方以得之,如何不千成大事業?世上惟有妒賢嫉能者幹事不成,未有愛才惜士而事不濟者也。
至此方以三郡還吳.孔明固為國也,亦為兄也,公義私心,可稱兩盡。大略三國事體盡在孔明掌中,或遲或速,或行或止,無不如意。真是見定者不忙也
鍾敬伯總評
至此方以三郡還吳,孔明固為國也,亦為兄也。公私可稱兩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