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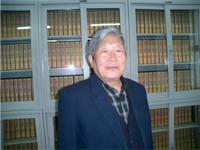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張廣志教授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張廣志教授產生背景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胡鍾達教授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胡鍾達教授形成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晁福林教授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晁福林教授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沈長雲教授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沈長雲教授繼1979年黃現璠發表《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後,他再接再厲,緊接著於同年11月14日又公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侯紹莊等同志商討中國奴隸社會問題》(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79年11月14日)一文,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無奴論”主張。兩文發表後,立即得到了史學界有識之士的積極回應。最早回響者當屬青海師範大學張廣志教授,他於1980年發表了《略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一文(《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1、2期) 論文發表後張廣志立即將文章寄給了黃現璠,表明了自己堅定支持黃現璠“振聾發聵”的“無奴主張”。黃現璠於回信中鼓勵後學張廣志大膽研究、勇於創新,在這一領域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2008年6月17日下午筆者通過電話採訪張廣志教授時他所言)張廣志果然不負前輩厚望,在這一研究課題研究中連連推出佳作,成為“無奴學派”的開派元老之一。繼張廣志之後,黃現璠的學生、廣西民族學院(現廣西民族大學)資深教授黃偉城不甘落後,連續推出《試論奴隸社會並非階級社會首先必經的歷史階段兼論商朝不是奴隸社會》(上、下)長篇論文(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2、3期)。這些文章皆共同主張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論”,“無論學派”三先驅黃現璠、張廣志、黃偉城應時而生,由此亦標誌著“無論學派”的形成,從此之後這一學派開始在學術界逐步嶄露頭角。
發展壯大
第一階段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葉文憲教授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葉文憲教授接踵而來的便是胡鍾達的《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兼評五種生產方式說》(《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3期);曹成章的《關於傣族奴隸制問題的質疑》(《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李汝能的《茂汶羌族地區沒有經歷過奴隸制社會階段》(《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等等文章或論文相繼面世。
在“無奴學派”茁壯成長的最初十年形成發展期中,還有兩部著作值得重墨一筆,一是“無奴學派”領袖黃現璠與學生黃增慶研究員和張一民教授合著的中華民族史上第一部《壯族通史》。作者於書中專列“秦漢時代壯族社會性質”一節,著重以考古學的成果論述了壯族歷史未經過奴隸社會問題。[9]正如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傑弗理·巴洛教授明確指出:“由於對馬恩著作的理解混亂和解釋不清,對這個地區(指中國壯族聚居地——筆者按)的傳統的中國解釋仍使人表示懷疑。傳統看法認為:壯族在宋以前屬奴隸社會,因而不可能建立國家,只是後來由於與大漢族的關係即被拖進封建社會。黃現璠,這位公認的壯族歷史學家、歷史系教授雄辯地論證了一個曾多次遭到詰責的觀點:傳統解釋不符合壯族社會。黃認為公元前221年秦國與東甌、西甌、閩越和南越的戰爭,表明壯族已經有了一個國家——西甌。黃現璠的觀點引出了許多難題……黃關於壯族祖先在秦入侵時已建成西甌國的觀點有潛在的價值。”二是“無奴學派”主將張廣志教授將此前發表的有關“無奴論”的論文結集為《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研究》一書於1988年出版。作者於書中從理論和民族史兩個角度論證了在中國商周時代和一些少數民族的初始階段社會中雖然皆存在奴隸制,但不是奴隸社會,而是封建社會。第二階段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滿都爾圖研究員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滿都爾圖研究員“無奴學派”發展到21世紀,進入到一個“總結期”。在2000年~2009年的這一階段,“無奴學派”的研究成果呈現出對前20年研究的回顧與總結的特點,這方面的成果以沈長雲的《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顧與前瞻》(《歷史研究》2000年 第4期);呂喜林的《關於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認識與反思》(《陰山學刊》2001年第2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反思與前瞻》(《紀念中國先秦史學會成立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 年);晁福林的《總結與創新——張廣志教授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序》(《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王長坤、魯寬民、尹潔合撰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唐都學刊》2005年第三期);莫金山的《回顧深刻 反思冷靜——評張廣志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學術論壇》2004年第3期);祝中熹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讀後(《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七十年<上、下>》(《文史知識》2005年第10、12期)等為代表。
意義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陳淳教授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陳淳教授貢獻
在“無奴學派”的第二階段“發展壯大期”中,該派學者們的學術貢獻,著重表現在:由於他們對於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深化探索和多維度考察,進一步強化了“無奴學派”的“無奴論”於論理、論據、論證等方面的說服力,從而使得“無奴學派”的主張更加深入人心,促使一些學者紛紛揚棄舊說,加入“無奴學派”陣營,晃福林便是代表之一。從他於1980年發表的《我國的奴隸社會始於何時》(《學習與探索》1980年第2期)一文顯而易見,早年他是主張“有奴論”的。但是經過十幾年的研究以及受到“無奴學派”主張的影響,晃福林先生終於幡然醒悟,自己過去的“有奴論”主張存在問題,從而在1996年以後發表的一些論著中一改前非,開始“反戈一擊”,積極主張“無奴論”。羅新慧博士在1998年發表的一篇“書評”中指出:“古史分期問題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近年來又趨於活躍,在最近幾年的研究中,一個顯著特點是‘五種生產方式說’遭到懷疑,否定奴隸時代在中國上古時期的存在,成為一些史家的共識。”可說道出了“無奴學派”主張日益為史學界有識之士廣為接受的實情。
影響
形成發展期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段忠橋教授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段忠橋教授如果說在“無奴學派”的“形成發展期”中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陸續出版,還只是謹慎地規避古史分期問題,那么在“無奴學派”的“壯大期”中,商傳、曹大為、王和、趙世瑜主編的《中國大通史》(晁福林為編委之一)則公開宣稱“不再套用史達林提出的‘五種社會形態’單線演變模式作為裁斷中國歷史分期的標準”,而且“避免籠統使用涵義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明確提出“中原王朝不存一個以奴隸制剝削形式為主體的奴隸制階段”。正如葉文憲指出:“在各種分期的新說中都已不見‘奴隸制’或‘奴隸社會’的字樣,說明奴隸制不等於奴隸社會、奴隸社會不是必經階段、三代不是奴隸社會等觀點已被很多人接受。”由此可以推論,《中國通史》對古史分期中“五階段論”的揚棄以及《中國大通史》確立的“不再套用‘五種社會形態’的演變模式”,可說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受到黃現璠先生所主張的中國在原始社會之後,沒有經過奴隸社會,而是直接進入“領主封建制”社會的新說以及晁福林主張的直接進入“氏族封建制”社會等古史新分期觀不同程度影響的結果。
總結期“無奴學派”形成20年後,進入21世紀最初10年的總結期。到了總結期,已是“一大批史學學者勇敢地放棄原來的觀點,基本認可中國無奴隸社會說。如何茲全先生放棄了魏晉封建論,認為中國無奴隸社會。”“有奴論”的郭沫若派四大幹將白壽彝、楊寬、吳大琨、田昌五皆相繼轉變立場,放棄原來的“古史分期五種形態”定式,贊同“無奴論”。
主張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玉時階教授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玉時階教授早在1962年,黃現璠於《土司制度在桂西》一文就明確指出:“學術主張,理應百家爭鳴,不能隨便戴上違反馬列主義或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高帽。看過馬克思著作的,首先應該認同這一點,始好討論問題。”從而公開反對將科學化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公式化和“規律至上化”。這一主張可說成為了“無奴學派”的共識。這種共識所體現出的共性特點,當為“早期無奴論”學者所無。一些學者將改革開放新時期後形成的“無奴論”當作是對“早期無奴論”的繼承,這是一種誤識,理由在於:兩種“無奴論”的主體所處的時代背景、史學素養、挑戰對象和論戰性質不同。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針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論述中,20世紀30年代“早期無奴論者”借用或使用過的一些概念和論據,如“部民社會”、“氏族封建”、“氏族制度”、“商業資本”等等,同樣被“無奴學派”的一些學者重新拾起再用。
無奴論“早期無奴論”學者的一些“無奴論”主要是針對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上海聯合書店出版,1930年3月初版)一書展開論述的,而“無奴學派”的“無奴論”,大多是針對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出版的郭沫若新著《奴隸制時代》展開論述。由於郭氏前後兩書所論內容的不同,因而“早期無奴論”學者與“無奴學派”對郭氏前後之書展開批評的切入點有所不同,主張自然相異。客觀地說:郭氏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重要價值主要在於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引入中國學術從而開風氣之先。但是,由於時代的局限和資料的欠缺,該書成文過於草率,以致缺陷難免,正如郭氏在1947年4月該書的新版《後記》中坦誠承認,自己“在材料的鑑別上每每沿用舊說,沒有把時代性劃分清楚,因而便夾雜了許多錯誤而且混沌”。1953年11月,他又在《1954年新版引言》中說該書“輕率地提出了好些錯誤的結論”。繼而在《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他再說:該書寫得“實在是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錯誤的判斷,一直到現在還留下相當深刻的影響”。而《奴隸制時代》則不同。相對而言,《奴隸制時代》可說是郭沫若的馬列主義史學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在這本論文集中,郭氏通過對井田制的興廢、殷周人殉的史實、奴隸與農奴的區分、漢代政權的實質以及古文字的發展等眾多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圍繞中國古代史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分期展開論述,最後將中國古代史上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分界確定在春秋與戰國之交。郭氏根據古典文字的記載以及對於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將古漢語中“臣”、“眾”、“朋”、“庶人”、“鬲”等等皆作為“奴隸”解釋。黃現璠於1979年發表的《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長篇論文,主要就是針對郭氏新著《奴隸制時代》展開論辯的。黃氏於文中首先主張:“研究歷史,什麼是奴隸制?什麼是奴隸社會?固應分清。什麼是通例?什麼是特例?也要懂得……奴隸制與奴隸社會,不能混為一談,把特例當作通例,更不應該。”[12]接著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為指導思想,從世界一些國家的歷史事實出發和以史事為據,對奴隸制與奴隸社會的區別展開了全面分析和論證。黃現璠的這一主張顯然是針對郭氏於《奴隸制時代》中所言的“我不否認中國社會發展的某種程度的特殊性,但我卻堅信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發的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絕對正確的”[13]這段話有感而發。黃現璠進而通過對馬恩學說關於奴隸制論述的分析,通過對日耳曼、南斯拉夫、西斯拉夫、東斯拉夫、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鮮、越南等一些民族和國家古代史的簡略論述,通過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詮釋,通過對希臘、羅馬古代社會與東方古代社會的比較研究,通過對古文字“眾”、“民”、“邑”、“方”、“夕”、“庶”、“鬲”、“苣”、“仆”、“臣”、“宰”、“隸”以及“農奴制”、“生產工具”、“土地私有制”、“殉葬”、“家庭”、“奴隸數量”、“家庭奴隸”、“戰爭俘虜”、“貢助徹”、“父權家長制”的剖析,從而得出“三點結論:(一)世界古代各國歷史發展,絕大多數都沒經過奴隸社會,直接近入封建社會,即希臘、羅馬典型奴隸社會,也不是一開始就直接進入奴隸社會。(二)由無階級的社會進入有階級的社會,最初被壓迫剝削的階級是農奴,不是奴隸。農奴的產生,比奴隸早。因為農奴制的封建社會制度,最容易與農村公社制度結合起來。農奴產生的條件,也比奴隸簡單,故首先發生。(三)家庭奴隸制的產生,也比較容易。世界各國古史都有。人們常誤會他們為奴隸社會,多半由此。但制度是現象,不是本質,是一回事,能否達到奴隸社會,又是另一回事,不能相提並淪。”[14]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張明富教授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張明富教授而黃現璠關於中國少數民族歷史絕大多數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社會發展跳躍論”或“社會發展跨越論”,早在1957年即初露頭角,當時他已主張:大多數史料充分證明壯族社會在唐以前“是氏族部落制,不是奴隸或封建制”。[15]接著他在1962年發表的兩篇論文中,又以壯族古代史為依據對其主張加以了深入論證,進而斷言:宋代儂智高起義前的壯族社會“不可能是奴隸社會,只能是氏族部落末期的社會。顯而易見,桂西土州縣的領主封建社會是建立在氏族部落末期基礎上的。”[16]繼而他在1979年後相繼發表的論著中,再度重申:“少數民族的歷史分期,是由各民族的歷史發展、經濟情況而定,正待我們共同研究決定。我只有一個主張,他們絕大多數也都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直接進入領主封建社會或古書稱為“行國”或“居國”的部落社會(四川涼山彝族,一般說是奴隸社會,尚待進一步研究)。”黃現璠提出的這一少數民族社會形態發展的“跳躍論”或“跨越論”,無疑是針對郭沫若先生在《奴隸制時代》(1954年版)一書中依據胡慶均的涼山彝族調查資料來論證他的奴隸社會普遍說而言的。
黃現璠關於少數民族史及其社會形態研究的重要成就,主要表現在“兩破五立”。 “兩破”為破除了正統的歷史觀和大民族中心主義觀念;破除了中華民族史研究中長期存在的不平等思維體系。“五立”為重新建立了一種科學化的思維體系——少數民族看待世界的哲學和文明史觀;為一門新學問或新學科“壯學”確立了一個歷史“起點”;對傳統的“文明”和“民族”定義進行了重新界定;為喚醒少數民族復興民族文化的內心覺醒和自覺意識樹立了正確理解“文明精神”與“科學態度”的認識論;為少數民族“發現自我”重構了一種全新的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
黃現璠主張中國少數民族絕大多數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的“跳躍論”,同樣得到“無奴學派”代表人物以及“黃派”弟子的普遍認同和支持。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曹成章“認為傣族社會在原始社會末期逐漸出現家長奴隸制以後,由於本身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沒有發展到奴隸占有制階段,形成奴隸占有制社會,就向封建社會過渡了。”[17]隨後,李汝能,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吳扎拉·克堯,中國社科院民研所研究員滿都爾圖,青海師大張廣志教授,西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杜昆,黃現璠的學生黃偉城、黃增慶、張一民、玉時階以及私淑弟子韋文宣等教授或研究員,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姚舜安,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況浩林,麗水地委黨校王克旺,貴州省社會主義學院原教研室主任張永國,王勝國,中央民族學院嚴英俊,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編輯部編審段啟增,李本高,福建博物院院長楊琮,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顏恩泉、王明富通,雲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何平,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廖君湘,雲南省紅河州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毛佑全等學者先後對錫伯族、西盟佤族、珞巴族的阿帕塔尼部落、珞巴族的博成爾部落、橙人、匈奴、鮮卑拓跋部、突厥、回紇、吐蕃、南詔、契丹、党項、女真、蒙古、南詔社會、壯族、瑤族、毛南族、畲族、苗族、努爾哈赤時期女真社會、中東南各少數民族、西甌社會、東南亞各國、哈尼族等古代社會性質展開了論述,從不同角度論證了“中國少數民族古代史上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問題,共同主張“無奴論”。
諸如此類一脈相通的主張,充分表明黃現璠主張中國少數民族絕大多數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的“跳躍論”得到“無奴學派”各路“英雄豪傑”的廣泛支持。在“無奴學派”代表人物張廣志、黃偉城、縱瑞華、曹成章、祝中熹、韋文宣、沈長雲、楊琮、莫金山、晁福林、朱晞、易謀遠、張永國、王學典、陳淳、王贊源等人的論著中,皆有大量推陳出新、見解獨到的觀點。在中華各民族史的古代社會形態研究中,“無奴學派”領袖黃現璠首倡的“跳躍論”以及他點名或不點名地對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日知、鄧初民、童書業、束世澄、尚鉞、楊向奎、吳榮曾、侯紹莊等人的“有奴論”的否定;張廣志對郭沫若、剪伯贊、呂振羽、王靜如、馬長壽、韓國磐、王輔仁、尚鉞、蔡美彪、林乾等人於漢族史和部分少數民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反駁;曹成章對方國喻於傣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反擊;杜昆對馬長壽於南詔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批駁;縱瑞華、沈長雲在奴隸社會普遍階段說和中國古代奴隸制問題上分別與“有奴論”者陳唯聲、田昌五的商榷;張永國對賀國鑒於苗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挑戰;易謀遠對胡慶均、劉堯漢等人於涼山彝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回擊,莫金山對范文瀾、郭沫若古史分期觀的抨擊;王慶憲對馬長壽、林乾等人於匈奴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詰責;段忠橋在“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上與奚兆永的論戰;陳淳主張“由於早期國家性質的討論明顯存在意識形態導向,使不同觀點和立場所據之‘理’不再中立和對等。因此,我們思考和探討這個問題時,需要隱去郭沫若等學者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光環,完全從學術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這一切既反映出“無奴學派”長年有備而戰的特點,又體現出他們的“無奴論”論著極具說服力的特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賓夕法尼亞狄根森大學人類學教授希爾對費孝通於涼山彝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置疑,希爾認為“20世紀50年代集體化改革之前小涼山奴隸制度特有的社會經濟進程表明,諾蘇社會曾是個擁有奴隸的社會,但它並不是奴隸社會。”日本現代研究中國甲骨學名家島邦男(1908~1977)於遺稿中直言不諱地否定郭沫若的“殷代奴隸社會說”,同樣不可忽視。他於遺稿《殷代非奴隸社會一證》中運用甲骨學博識,從甲骨卜辭中出現的“農業、畜牧、祭祀”等文字和記事的論證中,逐一反駁了郭沫若主張殷代“眾”字為“奴隸”以及殷代為奴隸社會的論點,提出了殷代非奴隸社會的可信一證。希爾、島邦氏的這種認識,如同上述美國、日本學者對黃現璠主張“無奴論”持肯定態度的認識一樣,表明中國“無奴學派”的主張事實上已經影響到國外,並獲得了國外一些學者對中國古代社會“無奴論”認識的共鳴。由此又呈現出“無奴學派”與20世紀30年代的“早期無奴論者”不同的一個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