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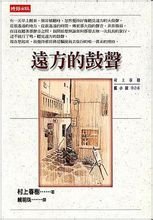 遠方的鼓聲
遠方的鼓聲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8月22日)精裝: 196頁
ISBN: 9787532754533
條形碼: 9787532754533
ASIN: B005DWGPW2
內容簡介
這是村上春樹的遊記,時間為1986-1989年,遊歷地區為歐洲,主要為希臘、義大利兩個國家。
“一天早上睜眼醒來,驀然側耳傾聽,遠處傳來鼓聲。鼓聲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從很遠很遠的時間傳來,微乎其微。聽著聽著,我無論如何都要踏上漫長的旅途”——作者聽得的微乎其微的“遠方的鼓聲”,最終成了您手頭上這部可觸可觀的《遠方的鼓聲》。
村上的遊記具有個人特色,他幾乎不寫人所熟知的名勝古蹟,而是與普通居民共同生活,描寫他們的日常工作、飲食起居等,以及他們的所思所想,富有深度感,對讀者了解這些國家的真實狀況有很大幫助,文筆也幽默有趣,可讀性很強。
圖書目錄
遠方的鼓聲——寫在前面
羅馬
羅馬
兩隻蜂——喬治和卡洛1986年10月4日
蜂飛了1986年10月6日 星期天 午後睛
雅典
雅典
瓦倫蒂娜
斯派賽斯島
抵達斯派賽斯島
海島淡季
老港
緹坦尼亞電影院的深夜
來自荷蘭人的信、島上的貓
斯派賽斯島上小說家的一天
暴風雨來了
米科諾斯
米科諾斯
港口和范吉利斯
撤離米科諾斯
從西西里到羅馬
西西里
南歐跑步情況
羅馬
比拉·托雷克里
凌晨3時50分的昏死
去梅塔村途中1987年4月
梅塔村
春天的希臘
帕特拉斯的復活節周末和對壁櫥實施的大屠殺 1987年4月
從米科諾斯去克里特島、浴缸之戰、101號酒宴大巴的光與影
克里特島的小村莊和小旅館
1987年,夏天和秋天
赫爾辛基
馬洛內先生的房子
雅典馬拉松和退票還算順利 1987年10月11日
雨中的卡瓦拉
卡瓦拉駛發的客輪
萊斯博斯
佩特拉(萊斯博斯島) 1987年10月
羅馬的冬天
電視、意武疙瘩湯、普雷特
羅馬的歲末
米爾維奧橋市場
隆冬時節
倫敦
1988年,空白年
1988年,空白年
1989年,復原年
康納利先生的公寓
羅馬停車種種一
藍旗亞
羅得島
春樹島
卡爾帕索斯島
選舉
義大利的幾副面孔
托斯卡納
雉鳩亭
義大利的郵政
義大利的小偷
奧地利紀行
薩爾茨堡
阿爾卑斯的麻煩事
尾聲——旅行結束
文庫本後記
點評鑑賞
1.
在旅行中,村上先生並非總保持著90分的狀態。
這當中的失望、緊張、迷茫、沮喪,與路途中的所見所聞一同被他記錄下來。因此當這些文章編輯成冊,整本書的觸感並不十分溫暖。
但這是一本給人以生之力量的書,當厭倦了去摸索橫埂在人與人之間的巨大鴻溝時,當在日常生活的旅行中精疲力盡時,摸一下冰冷的書頁,總會覺得一切都如暴風雨後的希臘島嶼般可以逐漸重建。它鼓勵你以自己的秩序去對抗所有的不可知與不可控,以主觀的微弱力量去讓身邊諸事不至於淪陷。是的,這是本相當主觀的書,但相比《雨天炎天》里微妙的客觀,我還是更喜歡村上在這集子裡的肆意表達。
書里那一句關於旅行的話某一天我忽然明白:我哪裡都可以去,同時又哪裡都不能去。因為我是自由的,但我已永遠被禁錮在“我”這一存在中了。
2.
就個人來說,比起遊記中的景物,我似乎更中意活色生香的真實景物。
不然,小說里的精妙景物片斷也好。
不過,對於村上春樹這樣寫作的人,對於《遠方的大鼓聲》這樣特殊的遊記,是可以網開一面的吧。
“遠方的大鼓聲
邀我作漫長的旅行
我穿上陳舊的外套
將一切拋在腦後”
這土耳其的古老歌謠,足以開啟村上的希臘羅馬之旅了。
《遠方的大鼓聲》中的希臘羅馬,不是地圖上的希臘羅馬,不是荷馬史詩里的希臘羅馬。在每年有幾百萬人出國的今天,歐洲紀行的文章並無特別扣人心弦之處。
《遠方的大鼓聲》的魅力在於,也許它只是單單屬於村上的希臘羅馬紀行。
這本小書收錄的文章,都呈現出一種近於日常素描般的畫面。然而,就在那三年間,村上完成了兩本小說,《挪威的森林》和《青春的舞步》。他說:“在那樣孤立的異國生活中,我只是單純地默默地寫著小說。”儘管,這本書里提及《挪威的森林》或《青春的舞步》的部分微乎其微,我們還是能從其氛圍中感受到希臘羅馬之旅和這兩本小說的吻合之處。如果不是宿命性地滲進了異國的影子,《挪威的森林》或《青春的舞步》也不可能成為現在這樣的小說。一個人處於完全和他異質的環境中,也許會更深入自己的內心。這本書可以說具有某種過渡性的意義,把在歐洲流離的作者的自我意識以文章的形式留存下來,和在日本的不流離的作者的心靈相互印證。
拋開這些,《遠方的大鼓聲》卻驚人地易讀。被畫成洋菇狀的希臘地圖,鐵達尼電影院裡放映李小龍的電影時,從銀屏前緩緩走過的巨大黑貓,一邊喝酒吃乳酪一邊開車的司機,神出鬼沒的羅馬小偷,總是休假的義大利郵局,村上奇妙的觀察角度和淡淡的詼諧仍然引人入勝。這本書不禁讓我想起他在《且聽風吟》里的一句話:“冰涼的葡萄酒,溫暖的心。”貫穿全書始終的是各種各樣的葡萄酒,各種各樣的音樂,以及各種各樣的人生。那種對生命細節的注意真是溫暖人心。
關於旅行,村上說:“現在在這裡過渡的我、這一時的我本身,我,以及我的工作本身,不也是一種所謂的旅行的行為嗎?而我任何地方都可以去,任何地方也去不成。”這很像佩索阿《惶然錄》里的說,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要旅行的話,存在就行。
命運是一段漫長又短暫的旅行,我們能到達的地方何其之多,又何其之有限。
而寫作者的眼睛也許能捕捉到更動人的景觀。
3.
剛剛看完村上春樹的旅歐遊記《遠方的鼓聲》。村上從37歲到40歲,在歐洲旅行居住3年,其中各種經歷感悟後整理之後,編成此書。
從希臘開始,以羅馬為中心,還有西西里、奧地利等地。旅行範圍可謂之廣。我地理學的不好,對於歐洲文化也沒有任何概念。所以確切的說,我看這書時,時常伴有發蒙的感覺。不認識的地名,容易混淆的人名,無法想像的食物……喔,我得承認很多地方看不懂、不理解。
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對這書的喜愛。我一般是在不想聽課的時候拿出這書來看,經常不可抑制的想大聲笑或是會心一笑。哈哈,這是一本讓我快樂的書,讓我感覺到生活真實的書。
雖然我沒看過別的遊記,但我覺得村上的這本寫的還是與正常遊記不同的。不談各地名勝古蹟、標誌性建築,不談正統美食,也沒有介紹了不得的經驗,只是敘述自己旅歐的生活,生活的細微瑣碎之處全部得以展現。所以,說它是遊記,莫如說它就是普通的生活記錄。
讓人發笑的地方那么多,希臘的“死狗現象”,奧地利修車游,開錯路的羅馬公交司機……哈哈,現在想起來還想笑。
翻譯者林少華老師把村上的這本遊記拿來和余秋雨的旅歐遊記《文化苦旅》比較,結果是很難找到共同之處。想來也是,像余秋雨那么有文化責任感的作家,是不可能把遊記寫的如此貼入生活,生動詼諧的。文化責任感是一個沉重的東西,你在背負他的時候獲得了深刻而失去了一些趣味。倒不是說村上就不深刻了,但我想所謂深刻不一定是要時時刻刻方方面面的體現,文學的使命不僅是帶來深刻,也是帶來趣味、帶來休閒娛樂。相比那些厚重到看過讓人心裡壓抑的書,我更想看點輕鬆的書。因為我看書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放鬆。
也許有人看過這書之後會產生想追尋村上的足跡,去歐洲旅行的想法。可是,這些想法我卻沒有。並非因為村上的描寫我不中意。恰恰相反,看到他提到的很多地方都會產生“呦,這地方不錯,以後有機會想去看看。”但這和想去旅行有很大不同。因為,現在所呼喚著我的聲音並非這個,我能感到自己被什麼所牽引著呼喚著,但是並非去遠行。我應該有自己現在所更應該做的事情。雖然我說不好他是什麼。
現在好像很熱衷旅行。趁著年輕時都走走,開眼看看世界的廣闊無可厚非。可是只要去遠方走一走就真的能為我們帶來什麼切實的改變嗎?我們明白自己不斷向遠方前進的目的嗎?我們真的有那么熱愛生活嗎?現在西藏,雲南之類的地方成了很多人所嚮往的地方。“去追尋一場心靈的升華吧”“去讓心靈回歸平靜吧”……好的初衷,可是現實真有如此理想嗎?漫無目的的遊蕩,心被放在哪裡?感悟在何處啊?
如果要去遠行,至少需要了解一些生活的真諦,構築了大部分的自我體系。否則,也許容易迷失吧。
其實,我也很想去遠方走走,但我在等待著那個來自我心底的,呼喚我的聲音……
相關版本
1.
作者:(日)村上春樹
譯者:賴明珠
出版社: 北嶽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01年9月
頁數: 305
定價: 15.00
裝幀: 平裝
2.
作者:村上春樹
譯者:賴明珠
出版社: 時報文化
出版年: 2000年9月
定價: NT280
叢書:村上春樹作品集
作者介紹
村上春樹(1949年1月12日-),日本小說家、美國文學翻譯家。29歲開始寫作,第一部作品《且聽風吟》即獲得日本群像新人賞,1987年第五部長篇小說《挪威的森林》在日本暢銷四百萬冊, 廣泛引起“村上現象”。村上春樹的作品展現寫作風格深受歐美作家影響的輕盈基調,少有日本戰後陰鬱沉重的文字氣息。被稱作第一個純正的“二戰後時期作家”,並譽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學旗手。
後記
前言中也寫了,《遠方的鼓聲》這本書是1986年至1989年約三年旅居歐洲期間的記錄。離開日本長期住在外國是第一次,現在回頭讀起來,類似興奮的東西似乎滲出了字裡行間,氣勢那樣的東西也可能多少有一些。儘管事情發生在不久以前,但近來我也自己對自己感佩起來:當時到底是年輕氣盛啊!若是現在,坦率地說,有許多地方大概不會那樣想、那樣寫。這些文章終究是“那時的產物”,出文庫本之際,除了個別行文,原則上沒有改動。
從歐洲回來,大約在日本生活了一年以後,因心有所想——解釋起來話長,姑且以“心有所想”來表述——我移居去了美國,到寫這篇後記的此時此刻,已大約生活兩年。在為出文庫本而重讀此書的時間裡,再次感到旅居美國和旅居歐洲的確完全不同。就有趣無趣來說,旅歐期間有趣得多。歐洲有“不知今天發生什麼”的刺激性,因而消耗劇烈,有時累得渾身癱軟,但有趣還是有趣的。單單在路上漫步、去超市購物或在高速公路開車都常常會忽然看到意外場面,讓人目瞪口呆,每次都切實感到歐洲這個社會高深莫測。
但在美國生活,這種“純粹的驚訝”就沒有歐洲那么多。這個國家,我覺得絕大部分事物都像是建立在可以預測的基礎上的。就是說,美國是形形色色的種族和信仰各種各樣的宗教的人聚集之後形成的國家,因而若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預測,那么作為國家就難以成立。如果沒有眼睛可以看到、嘴巴可以說明的共同觀念,那么社會本身就有可能分崩離析。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美國沒有多少生活本身的日常性刺激(犯罪刺激固然有,但那種反社會性質的東西是另一回事)。不過,若說美國這個國家是否因此枯燥無味,也很難那么簡單概括,其中“可以預測”本身的刺激也是有的。僅僅依靠這類整合性notion(觀念、概念)就能使nation(國家)得以成立嗎——如果從這一根本疑問出發,對美國一步步加以解析,有些難以解釋明白的東西就會浮現出來。關於這點,我打算在另一本書中好好寫一寫。
寫完這本《遠方的鼓聲》以後,有很長時間沒去歐洲。這裡所寫的義大利這個國家讓我相當氣惱,離開時再也不想去了,而在三四年過後的現在卻十分懷念,種種景致和男女在腦海中浮現出來,一種期盼隨之高漲:啊,那裡還想去一次!那東西還想吃一次!義大利確是那樣的國家。世間有兩種人,一種人“印象極佳,現在卻很難想起長什麼樣”,另一種人“那傢伙相當厚臉皮又做事馬虎,但現在也能清楚記起長相”。不用說,義大利百分之百屬於後者。那個國家遲早還想去一次,久居倒是另一回事。
希臘讓我中意的,大概是某種節制性。我們出國期間,日本地價正漲到登峰造極,泡沫現象相伴而生。過些時候回日本一看,不由為日本社會突如其來的改頭換面而目瞪口呆。尤其是在希臘那種儉樸的社會中生活過一段時間之後,回日本就像突然被拋進了重力不同的世界,只能懷有“這到底算什麼呀”的感慨。這點至今仍然記得。若以體溫表示社會狀況,那么希臘這個國家是“平溫社會”,日本則似乎是“低燒社會”,而在泡沫經濟時代似已進入“準高燒社會”,二者落差之大讓我多少產生中暑之感。我是小說家,不是評論家,無意對各種現象居高臨下地說三道四評頭品足,但我覺得我們差不多到了需要來自“平溫社會”的視點的時候了。在這個意義上,希臘這個國家以及得以在這個國家生活過一段時間,我想對於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去外國,確實讓人感到“世界好大”,但與此同時,“文京區(或燒津市、旭川市)也好大”這一視點也是完全存在的。哪一個作為視點我想都是正確的,並且認為,只有這樣的微觀視點和巨觀視點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懷有更為正確、更為多元的世界觀才會成為可能。如果說我三年時間裡通過寫這本書有什麼體會的話,那便是人應該有這種複合式眼睛。我這個人,無論對什麼事,只有在試著寫成文字之後才能夠準確把握和理解,因此寫這本書讓我好歹認識和領會了其中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說,這本書對於我、或者對於我的小說乃是重要的記事簿和速寫本。一讀之下即可得知,裡面並沒有寫什麼了不得的東西,也沒集中有用的信息,若能讀起來輕鬆愉快,我就心滿意足了。
或者,如果哪位讀完之後想去長時間旅行,並像筆者這樣以自己的眼睛看各種各樣的東西,那么對我這個作者來說可謂莫大的欣喜。旅行這玩意總的說來是讓人疲勞的,但或許只有通過疲勞才能獲取知識,或許只有通過勞頓才能得到歡欣,這是我通過持續旅行認識到的一個真理。
序言
這是村上春樹自1986年10月開始旅歐三年期間的遊記性隨筆集或隨筆性遊記。
“一天早上睜眼醒來,驀然側耳傾聽,遠處傳來鼓聲。鼓聲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從很遠很遠的時間傳來,微乎其微。聽著聽著,我無論如何都要踏上漫長的旅途”——作者聽得的微乎其微的“遠方的鼓聲”,最終成了您手頭上這部可觸可觀的《遠方的鼓聲》。
興之所至,剛剛譯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捧起了余秋雨先生的《行者無疆》和《千年一嘆》。同是旅歐遊記(,《千年一嘆》包括中東),同是擁有龐大讀者群且依然走紅的東方當代作家,兩人筆下的歐洲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結果發現,找出二者的相同之處比找出其不同之處不知困難多少倍。這是因為。,第一,秋雨先生是帶著歷史去的,每到一處,首先憑弔歷史遺蹟,抒懷古之情,發興亡之嘆,探文明之源,觀滄桑之變。而村上對各類遺址和出土文物基本上不屑一顧,他感興趣的更是眼前異國男女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和日常性行為模式及其透露的個體生命信息。第二,秋雨先生是帶著中國去的,“身在曹營心在漢”,無論看什麼,總忘不了將異邦和故國比較一番,有濃得化不開的家國意識或士子情懷。而村上基本上把日本瀟灑地扔去一邊,“情願在異質文化的包圍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腳下”。第三——這其實是先決原因——兩人身份不同、任務不同。秋雨先生兩次都是受香港鳳凰衛視之邀,考察“人類歷史上所有產生過整體影響的文明遺蹟”,而村上純屬個人行為,不掛靠任何公司任何組織,自己掏腰包帶著老婆想去哪就去哪,既非走馬觀花的遊客又不是安營紮寨的居民,“勉強說來,我們是常駐遊客”。
例如,同是第一次到羅馬,秋雨先生當即詩興大發,由衷感慨“偉大”一詞非羅馬莫屬:“只有一個詞……留給那座唯一的城市。這個詞叫偉大,這座城市叫羅馬。”(《行者無疆》)村上則懊惱地斷言:“羅馬是個吸納了無數的死的城市,所有時代所有形式的死盡皆充斥於此。從凱撒的死到劍客的死,從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羅馬史連篇累牘儘是關於死的描述。元老院議員若被宣布榮譽死亡,首先在自己家裡大設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後慢慢切開血管,一邊暢談哲學一邊悠然死去。”(《凌晨3時50分的昏死》)當秋雨先生神色凝重地面對元老院廢墟反覆解讀羅馬如何偉大的時間裡,村上百無聊賴地坐在公園草坪上看修女、看警察、看美少女、看熱氣球、看狗,還看人接吻:“離我坐得位置不遠的地方,一對年輕男女緊緊抱在一起接吻,吻得非常之久非常之認真。半看不看地看人接吻的時間裡,覺得自己本身也接起吻來。”(《蜂飛了》)旅居羅馬兩年多時間裡,印象最強烈的是羅馬無所不在的小偷扒手之流。村上的太太也被搶走了挎包(包里有護照、機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一個開機車的年輕男子從後面趕來,一把抓住她的挎包帶。她本能地握緊不放,大約持續了三十秒。儘管周圍有幾十人之多,但都往別處看,佯裝未見,不願意介入,作出渾然不覺的樣子。互相搶奪了一會,最後挎包帶斷了,男子拿包離去。眾人這才如夢初醒地來到她身邊,七嘴八舌安慰道‘真不得了啊’、“啊請在這兒坐一下’、‘我給警察打電話去’、‘那不是義大利人,是南斯拉夫人’。這種時候的義大利人又可謂親切之至——嘴皮子上的親切,倒也容易。”此時此刻,村上到底懷念起祖國日本來——東京斷不至於有如此表演。
再說一下希臘。當秋雨先生面對愛琴海立有很多潔白石柱的懸崖峭壁沉思埃斯庫羅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至孔子、老子、釋迦牟尼的時候(《千年一嘆》),村上則對著海灘游泳女郎“朝著初秋太陽挺起的乳峰”,認真總結“愛琴海規則”——“具體地說,來到愛琴海以後,(A)女孩子心想反正是愛琴海,這么做理所當然,遂以習以為常的手勢暴露乳房;(B)男人也做出視而不見的神情,就好像說畢竟是愛琴海,那么做也無所謂一當然,偶爾也會用眼角斜瞥一眼,但即使那種時候他們也顯得從容不迫,仿佛在說這東西見得多了。此乃基本規則,從容才是至關重要。”(《海島的淡季》)
如此說來,秋雨先生一定活得愁眉苦臉而村上一定活得一身輕鬆了?卻也未必。“兩千五百年前,希臘哲人在大海邊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印度哲人在恆河邊思考人與神的關係,而中國哲人則在黃河邊思考人與人關係。”(《千年一嘆》)在人際關係波譎雲詭錯綜複雜這點上,同為東方人的秋雨先生和村上似乎頗有共同語言和共同感受,這點雙方在書中都按捺不住。旅歐期間村上寫了《挪威的森林》,書很快出版。“說起來甚是匪夷所思,小說賣出十萬冊時,我感到自己似乎為許多人喜愛、喜歡和支持;而當《挪威的森林》賣到一百幾十萬冊時,我因此覺得自己變得異常孤獨,並且為許多人憎恨和討厭。”他最後概括道:“羅馬充滿羅馬才有的麻煩事,東京充滿東京才有的麻煩事……無論我們置身何處,都只能和麻煩事相伴而行,同麻煩事一起生存。”(《義大利的小偷》)不同的是,秋雨先生歸結於“中華文明的雜質”,村上則概括為自身的“經驗教訓”。
以上所言,純屬興之所至,並不是想就兩人的遊記作品進行系統性比較。何況二者在時間上至少相差十年——儘管歐洲十年間變化不會很大——且兩人旅途所花時間也長短有別。但不管怎樣,對比著翻看幾頁確是一件頗有興味的事。
村上在他的書中最後這樣寫道:“至今我仍時常聽見遠方的鼓聲。安靜的午後側耳傾聽,會在耳底感覺出它的迴響。”
或許可以說,每個人都有惟獨自己聽得見的遠方的鼓聲,一如小時候在鄉下每次聽到山那邊傳來的演戲或扭秧歌的鼓聲,心裡就怦怦直跳急著出門。人生途中的每一階段都會有鼓聲在遠方呼喚自己整裝待發,聲音再弱我們也會聽見,即便不是在“安靜的午後”。
林少華
2005年2月25日於青島·窺海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