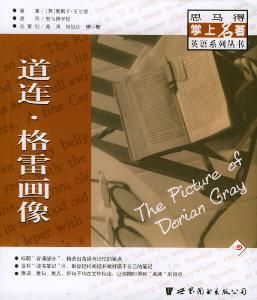小說情節
道連·格雷本是個單純的少年,在他的生活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兩個人:畫家霍爾華德和朋友亨利勳爵。霍爾華德為藝術而生活,他在道連身上所投注的感情,轉化為了他藝術的靈感,尤其表現在創作道連·格雷的畫像上,使這幅畫作成了他繪畫生涯中難得的精品。畫像是他藝術和情感的結晶,給他帶來歡樂的同時,也給他造成了不少痛苦。所以他時刻關心道連,生怕他過多地受到亨利勳爵的不良影響。也正是他所作的這幅畫像,引出了一連串問題,推動著小說情節的發展。而玩世不恭的亨利勳爵,是道連的“精神導師”,一個享樂主義者,有著一整套似是而非的個人主義理論,用雄辯的口才和充滿智慧的警語包裝起來,輕而易舉地使人接受。他諄諄教導道連要充分享受生活,趁年輕的時候及時行樂,不要抵制誘惑,相反要隨心所欲,去實現自己的每個幻想。道連是他的個人主義理論的試驗品,所以他要時刻跟蹤他,觀察這種試驗的效果。他之所以接近道連,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那就是道連身上有著他所珍視而又缺乏的東西:青春。道連在亨利的“教導”下,個性由單純變為世故,靈魂由純潔轉為污穢,最後走向自身的毀滅。道連、霍爾華德和亨利三個人物,通過性格上的互補和依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成了小說結構內在的黏合劑。
本書是一部內涵非常豐富的小說,要充分地挖掘綜,對讀者來說是一個挑戰,正是因為如此,它也就更富有吸引力。
王爾德《畫像》中的唯美主義主題
一、
藝術的宗旨是展示藝術本身,同時把藝術家隱藏起來,奧斯卡·王爾德如是說,王爾德是十九世紀末唯美主義的代表,在其諸多堪稱“唯美”上午作品中,以《道林·格雷的畫像》和戲劇《莎樂美》最有代表性,小說《畫像》,的內容極為廣泛,寓意也層出不窮,本文試圖從文學與藝術的角度,對其中所蘊涵的藝術與現實、模仿與真實的意象進行解讀,無疑,這是一種可寫式的“誤讀”,或許王爾德早已對其作品所要遭受的“誤讀”有所準備,因此,在前言自序中就寫道:“對一件藝術品的看法不一。說明這作品新穎、複雜、重要。《畫像》,正是如其所說的作品。
文本中有兩個道林·格雷,第一個是仿佛用象牙和玫瑰花瓣作成的阿多尼斯一樣的美麗容貌的少年,一個則是充滿神秘的道林·格雷的畫像。後者象徵著永恆的餓藝術,而前者則是與藝術相對應的現實,而在文本中,畫像中的道林和現實中在道林曾一度“調換”,畫像成為道林生活中的靈魂之鏡,無時無刻不反應道林的所做所為,而且將歲月流逝3的印記也一併記錄。
而生活中的道林卻一度“永駐青春”,正因為如此,道林才肆無忌憚的沿著亨利勳爵所倡導的方式生活,王爾德認為不是藝術反映生活,而是生活反映藝術。我們不妨說,他的藝術觀和柏拉圖的理念觀有很大的相似性。
柏拉圖認為現實世界是對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詩(藝術)是對生活的模仿.因此,也就是對理念的模仿的模仿。所以更加不真實。這似乎與王爾德和唯美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藝術沒有道德取向”,大相逕庭。
但是我們從理念的的特徵來看,那么其和王爾德所倡導的“藝術”,是有很多共同之處的,在柏拉圖看來,理念是一種抽象的原型存在,而這種抽象的“原型”,是完美無缺的,而對其模仿而創造出來的現實世界,卻因為“只是近似真實的東西”,而存在著缺陷。
而唯美主義和王爾德所說的“藝術”,其實就是不同於現實世界的一種美,而這種美,就是對現實世界的缺陷和苦難的克服和超越。唯美主義中的“美”,其實也是一種抽象的完美的原型,其和理念,只不過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不同而已。實質上都是一種理想化的“存在”,無論是柏拉圖,還是唯美主義者,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去尋求一種超越現實的理想的“在”,柏拉圖採取的是哲學的追思,而王爾德則藉助於文學和藝術方式。
可以說,他們都是德希達所說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者,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稱之為理念,而在王爾德的藝術觀中則稱為美,柏拉圖的理念,偏重於善和道德,因為他是站在“理想國”的城邦統治者的立場上,而王爾德認為美並不關乎道德,而是應超越於善與惡之上,他是顯然站在藝術的角度上。
因此,他認為“藝術家沒有道德取向,如有,那是不可原諒的風格的矯飾”在王爾德的《畫像》中,美的象徵,就是道林的畫像,儘管畫像曾一度為道林靈魂和內心變化的顯示者.
但最後,畫像仍然恢復了本來的狀態,即美戰勝了醜。畫像對道林所起的是一種鏡像的功能,藝術成為生活的“反映”,整個文本幾乎都在詮釋這一“現實主義”的觀點,而文本卻在最後又將這一“顛倒”的事實扭轉過來,從而表達了他的唯美主義觀點。
王爾德在闡釋他的“美”的觀點時,就曾提起過柏拉圖的理念,“在那兒,就像一股清風從高地上帶來健康一樣,作為藝術之魂的美就呈現於感官之前,孩子們的靈魂不知不覺地,逐步被引向一個與知識和聰明相和諧的境界。”他所指的就是“柏拉圖的完美城市”,也就是理念中的原型城市,他所嚮往的美,可以說深受柏拉圖理念的影響。
王爾德又說,“在這動盪和紛亂的時代,在這紛爭和絕望的可怕時刻,只有美的無憂殿堂,可以使人忘卻、使人歡樂,我們不去往美的殿堂還能去往何方呢?”美的殿堂無非就是他和唯美主義的又一個“理想國”。
二、
在文本中,道林愛上了一個叫西比爾的戲劇演員,而道林之所以愛上她,並不是因為她的美貌,而是因為她的表演藝術,而西比爾只懂得表演,而對生活和愛情一無所知,在道林的眼中,她是藝術中人物的化身,他愛的其實不是真實的西比餌,而是他飾演的角色。
道林從她的演出中感受到一種藝術之美,這使他熱淚盈眶,而因為“她集世上所有的女主角於一身,她並不只是個體。”道林為之熱淚盈眶的是西比爾在莎士比亞戲劇中所扮演的《皆大歡喜》中的羅瑟琳,《辛白林》中的伊摩琴,《哈姆雷特》中的奧菲麗婭。
道林為之傾倒的是虛構中的藝術形象,而西比爾之所以表演的惟妙惟肖,是因為她除了戲劇,根本不了解生活和愛情。道林一直把她看作劇中的人物,而她卻對人生一無所知,她甚至不是她自己。正如文本中所說:“今晚她演伊摩琴,”“明晚她演朱麗葉”,當亨利問道林什麼時候她才是西比爾呢的時候,道林答到:“永遠不可能是。”
在文本中,西比爾就是遠離生活的藝術形象化身。而當西比爾愛上道林時,她才從戲劇的夢幻中醒來,在文本中西比爾對道林說:“在認識你之前,演出是我惟一的現實生活,我只生活在劇院裡,我想那都是事實……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透了自己一直參與的無聊演出,看出了它的空洞、虛假和愚蠢。”
正是因為她認識到了藝術的虛構性,“意識到我的台詞是不真實的,不是我的話,不是我要說的話,你給我帶來了更高尚的東西,一切藝術都不過是它的影子。”
因此,她再也無法想像以前一樣的表演,她的轉變,就是由虛構的藝術向現實的轉變。但這並沒有給她帶來愛情。因為道林愛的是藝術,換言之,是西比爾表演的形象,西比爾在他的眼中簡直是個天生的藝術家。而西比爾的“覺醒”,使她對戲劇表演沒有了興趣,正如她對道林所說:“對我來說,你勝過一切藝術。
既然如此,我與戲中的傀儡又有什麼關係呢!今晚一上台,我不明白怎么會什麼感覺都沒有了。我原以為會非常出色。但發覺自己無能為力。”她因為認識到了現實中的愛情,對藝術中虛構的愛情有了清醒的認識,進而背棄了藝術,轉向現實。但是,這卻讓她失去了愛情。因為她只有作為藝術表演中的人物時,才為道林所愛,而當她成為真正的自己時,即西比爾時,而不是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道理年對她的愛情就消失了。
道林說道:“我愛年一是因為你了不起,因為你有天分,有才智,因為你實現了偉大詩人的夢想,賦予藝術的影子以形式和內容,可是年百秒這一切都丟掉了……現在你對我以毫無意義在……失去了藝術,你一無是處。”道林對藝術理想的破滅,也導致了西比爾對愛情的絕望,她離開了剛剛認識到的現實世界,或許,她本來就應該生活在藝術世界之中,現實扼殺了藝術,反過來她對藝術的背離讓她失去了愛情。王爾德認為“生活模仿藝術甚於藝術模仿生活。”西比爾也像她說飾演的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悲劇女主人公一樣,為愛情的幻滅而死。完成了她最後的一次愛情藝術。
她的悲劇在於她將生活看的高於藝術,他曾對愛情有過浪漫的幻想,她雖然認識到了現實生活,但並沒有真正擺脫戲劇的浪漫因素影響。沒有意識到道林迷人外表下的自私和冷酷。西比爾之死是在於她從藝術世界轉向現實世界,因為王爾德認為“一切壞的藝術都是返歸生活和自然造成的,並且是將生活與自然上升到理想的結果。”作為藝術形象化身的西比爾背離了藝術,並且將生活上升到理想,所以才導致藝術的損壞和現實愛情的破滅。但個她不再具有藝術的特徵時,他自然要消失。這正是王爾德藝術和現實不能共存的藝術理念在文本中的投射。
文本中寫道:“這位姑娘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所以她賓個沒有真正的死去,對你來說,她至少是一個夢,一個遊蕩於莎士比亞戲劇,使之更為動人的幽靈,一支使莎劇音樂更加歡快醇厚的蘆笛。”“她一接觸現實生活,就把現實生活給毀了,同時現實生活也毀了她,她便因此而消遁。”在王爾德的《畫像》中,無論是敘事的情節,還是人物的語言,都蘊涵著他關於理想與現實,美與醜的對照等主題和理念。既有部分的情節暗示,又有貫穿於文本的隱喻
三、
文本中處處都交織著現實與理想,藝術與真實的對話,無論是優美的畫像,純真的美貌少年,以藝術為生命的畫家霍爾華德,還是生活在戲劇中的少女西比爾.都在這種對話中象徵或隱喻著藝術的意象,而文本中的主人公道連·格雷則是以一種雙重影象出現的。
相互對映的畫像和現實人物,霍爾華德是藝術家和作者的化身,在他的眼裡,藝術就是美,藝術高於一切,他是王爾德及唯美主義藝術觀的顯現者。但是在文本中他並不抽象。
霍爾華德說:“每一幅喲內個感情畫出來的畫像,畫的是藝術家不是模特,模特兒不過是偶然介入的。是一種誘因,畫家在彩色的畫布上所揭下的不是模特兒,而是畫家本人,我不願拿這畫去展出,是因為它暴露了我自己心靈的秘密”。
其實畫家只是注重道連·格雷的形式。也可以說他的美的瞬間顯現。“他的人格向我啟迪了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一種嶄新的藝術風格。“藝術的價值在於將飄忽不定、瞬息萬變的現實世界中的閃光瞬間用相對固定的形式凝定下來。而繪畫正是把那最美的意象用藝術形式表現出來。畫家作品中的畫像是作者的理想的投身,正如書中所說:“因為不知不覺之中,我已經在畫像中表露了一種奇怪的藝術崇拜。畫像里,我自己的東西太多了,哈利——我兆斤毫的東西太多了。”
無論是畫像,藝術家,還是作家,在作品中表現的無非是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象。而作品的內容,只是他表達或顯現自我的形式。因此,與其說霍爾華德畫的是道連·格雷,不如說是他理想中的完美人格。他代表的是藝術家,而畫像則象徵著藝術和理想。
而他的朋友亨利勳爵,代表著和藝術相對的現實,而道連在他的影響和教導下,逐漸的“異化”,與畫家在為其畫像時的人格之間的疏離,最後蛻變為一個自我主義者,儘管道連在外表,即形式上沒有任何的變化,但在精神實質上卻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當然這一切都表現在畫像的變化上。
道連在看看到畫家為他所作的畫像後,先是“恍然大悟似地意識到了自己的美貌,而後由亨利關於青春短暫的話想到有朝一日自己隨著時光流逝而變老後的醜陋不堪。他因此希望”要是永遠年青的是我,而變老的是畫像多好!為了這個目的——為了這個目的——我什麼都願意給!是的,我願意獻出世上的一切。我願意拿我的靈魂交換。”
王爾德在文本中重複了原型的母題,我們可以想到歐洲文學史上最負盛名的詩劇——歌德的《浮士德》,年老的浮士德博士與魔鬼魔菲斯特用靈魂做交易,讓後者滿足他的一切欲望,而魔菲斯特果然使他重返青春,並用自己的魔法讓浮士德上天入地,不斷的滿足其的願望。
在王爾德的文本中,亨利勳爵無非又是一個魔菲斯特的化身,他向道連宣揚他的“自我”觀念,“生活的目的在於自我發展,充分實現自我的天性——是我們每個人來到世間的目的。如今,人們倒怕起自己來了,忘記了他的最高職責,也就是對自己應負的責任。”“我相信,人的一生要是活得充分徹底,人就是要是抒發一切情感,表達一切思想,實現所有的夢想——我相信,世界將沉沒於新的喜悅之中。於是我們會忘掉中世紀的一切弊病,回到希臘的理想中去——也許是一種比希臘的理想更好,更豐富的東西。”
亨利的道德和人生說教。其實就是王爾德自己的觀念在文本中的投射,道連就像浮士德在魔菲斯特的誘惑下不斷追求夢想的實現一樣,他在亨利的思想觀念引導下,開始了背離原來自我的享樂主義追求。與浮士德不同的是他並不是主動的去追求自己的美好理想,而是被動的要求欲望的滿足。
浮士德在與魔菲斯特的關係中一直是處於“主人”的地位,他只不過是藉助魔鬼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不受其負面的影響,因此最後他的追求越來越高,他的自我在追求中不斷的豐富,最後得出了智慧和人生的真諦,靈魂獲得了拯救。
而道連·格雷則相反,他視亨利為“精神導師”,處處受其影響,而與畫家霍爾華德漸漸的疏遠,他的自我在欲望的擴張下逐漸變得扭曲,他在拒絕西比爾的愛情後,也曾一度蒙發過悔恨之情,決定不見亨利勳爵,至少不再聽他的話,但是一旦見到了亨利後,他的思想又發生了動搖,在他和畫家的談話中,他還沒有完全成為亨利自我享樂主義的精神俘虜。
直到他讀到亨利給他的一本書,那本書“作品的主人公,那個獨特的巴黎青年,奇怪地兼有浪漫氣質和科學氣質,在道連看來成了兆斤毫的原型,說真的,他覺得整部書包含了他自己的故事,卻在他身臨其境之前就寫成了”。
這體現了王爾德關於藝術與生活的觀點,他認為“生活模仿了藝術,遠甚於藝術模仿生活”,在文本中,道連·格雷正在模仿書中的人物,從此以後,他真正的成為了一個自我享樂主義者,一個“浮士德”式的追求者,他迷戀於時尚,曾一度為羅馬基督教的儀式所吸引,而後又為神秘的徹底解脫主義所打動,研究香水及其製造的秘密,傾心於音樂,迷戀奇珍異寶,然後又轉向刺繡和北歐國家寒冷的房間裡充作壁畫的掛毯,以及基督教的法衣。
他的容貌依舊年輕,而畫像卻日復一日的變得醜陋和猙獰,那正是他靈魂墮落的寫照,他雖然有時討厭畫像和他自己,但更多的時候卻為自己的享樂主義而自豪。
畫家霍爾華德的畫,不僅是對道連·格雷青春與美貌的再現,該呢感灌注了自己一對藝術與美的崇高感悟,他賦予畫像一種超然的完美人格,而在道連的願望不可思議的實現後,隨著他靈魂的墮落和邪惡欲望的不斷增長和歲月的流失,畫像也漸漸變得醜惡、猙獰和衰老。畫像正是對道連鏡像式的反映,正是藝術反映生活的隱喻。而畫像隨道連的變化而變化,正是藝術反映生活,而對藝術本身的損害和扭曲,藝術越是反映現實生活,藝術就越遠離美,就如同畫像隨道連的劣跡增多而變得越來越醜一樣。
在畫家的眼中,畫像里有他千載難逢的理想,那理想就是美,但是現實卻不斷的對理想進行篡改,畫家以自己的理想所造就的藝術美隨著道連的自我主義行徑而越來越少。當道連給他看畫家自己的作品,道連稱之為只有上帝才能看到的東西時,他看見的竟是一幅自己都認不出來的畫面:“在越來越稀少的頭髮上,殘留著某種金子般的顏色,肉感的嘴巴上有一抹猩紅,麻木的眼睛依然保留著一絲可愛的天藍色,高貴的曲線並沒有完全從輪廓分明的鼻孔和柔軟的喉部消失。”
畫像的變化象徵著畫家——我們也可以稱之為作者理想的破滅。道連已經完全背離了畫家最初對他的期望,他實質上是正在不斷的篡改作者的作品,通過他不斷的接受衡量一的自我主義理論和欲望不斷擴張的生活。
在畫家勸他改邪歸正時,“道連·格雷朝畫像瞥了一眼,突然衝著霍爾華德泛起了一種難以控制的仇恨,似乎畫布上的形象向他提醒了這種仇恨,並通過獰笑著的嘴,輕地注進入他的耳朵里,他內心涌動著困獸般的瘋狂,厭惡那個坐在桌子旁邊的人,超過了平生所厭惡的一切。”
道連因對畫家的厭惡,而將仇恨移到畫家身上,他終於完成了篡改作品的最後一步,殺死了畫家。在文本里,“作者之死”的主題顯露了出來,羅蘭·巴特在《作者之死》中認為只有在作者死去之後,作品才可以脫離作者的權威,而隨意的對其進行闡釋和解讀。
而道連·格雷正是以自己的行動來對作品,即畫像進行背離作者原意的歪曲。而最終導致了“作者之死“。畫家死後,道連更加肆無忌憚,沒有了作者權威的作品,其解釋的空間不再受到限制。道連徹底的“自由”了。
在文本中,以道林·格雷為代表的醜惡現實,儘管其表面是美的,卻一直在侵蝕著理想,藝術在醜惡的行經面前不斷被破壞,但是,這賓個不符合作者的唯美主義觀念,王爾德認為“一切壞的藝術都是返歸生活和自然造成的,並且是將是將生活和自然上升到理想的結果,生活和自然有時候可以用作藝術的部分素材,但是他們對藝術有任何用處之前,它們必須被轉換為藝術的常規。藝術一旦放棄它的想像媒介,也就放棄了一切。”
因此,在文本的結尾,藝術與現實的最後衝突出現了,道林對自己的靈魂進行反思,終於認識到“對他來說,美貌不過是假面,青春是一種諷刺,充其量青春是什麼呢?是一段幼稚不成熟的時期,一段情緒淺薄,思想病態的時期,為什麼他老是穿著青春的號衣呢?青春已經損害了他。”
道林似乎幡然悔悟了,而且他決定要過一種新生活“新的生活,這就是他所需要的,也是他所等待的,當然他已經開始了新生活,無論怎么說,他已經放過了一個天真的姑娘。他以後永遠不再去引誘天真,他要做個好人。”當他自以為自己真的改惡從善而去看畫像的時候,發現“畫像只不過眼睛裡多了狡猾的神色,嘴角的曲線添了虛偽的皺紋。”
他徹底認識到,自己所謂的翻然悔悟只不過出於虛榮心的自欺欺人,現實中美好的想法只不過是他為好奇而嘗試的克己。呀撕下一直罩在心靈上虛偽的面紗,要毀掉畫像,他不但消滅了作者,又要毀滅畫家的作品以及它的一切內涵。這是美和醜,理想和現實的最後較量,也是唯美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觀的較量,最終道林倒地而死。
“他一臉的憔悴、皺紋滿布面目可憎。”而“牆上掛著他們主人的一幅栩栩如生的畫像。同他們最後一次見到時一樣。奇蹟似的顯得那么年輕,那么英俊”。畫像是藝術和美的象徵,青春容易逝去,但藝術和美卻永恆不朽。
王爾德通過文本中道林與畫像的敘事,表現了他唯美主義藝術至上的美學觀念,“生活模仿藝術甚於藝術模仿生活。”“撒謊——講述美而不真實的故事,乃是藝術的真正目的。”
四、
在現實生活中,王爾德更像文本中的亨利,他和其摯友道格拉斯的關係,卻如同畫家霍爾華德和道林一樣,文本中畫家對道林說:“你已經成了我看不見的理想的可見的化身。”和王爾德在信中對道格拉斯所說的“你是一切可愛東西的化身。”表達的是同一思想。亨利和霍爾華德是王爾德藝術和生活理念在文本中的投射。但是,在文本的最後及其揭示的主題是藝術戰勝了生活,在王爾德心中,藝術和美,是永恆至上的。
享樂主義者的畫像
《道連·格雷的畫像》是十九世紀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唯一的長篇小說。總的說來,這篇小說的寫作手法很典型,詞藻異常華美考究,能很好地反映作者的唯美主義理念。但其主題是否“符合道德”具有不小的爭議。
《道連·格雷的畫像》講述了這樣一個在現實框架中構築,但主題表達卻超乎現實的故事:年輕英俊的道連·格雷的美貌激發了畫家霍爾華德的靈感,使其創作出自認為最好的作品——道連·格雷的畫像。道連在與霍爾華德的朋友亨利勳爵的談話中痛感容貌的不可久留與韶光的易逝,看著畫像中英姿勃發的自己許下願望:希望自己能青春永駐,而畫像代他承受歲月的痕跡;他願以靈魂為交換代價。這個不可思議的願望後來竟實現了。道連·格雷受亨利勳爵的享樂主義思想影響,一步步走向道德墮落的深淵。他隨意而殘忍地對待深愛他的女演員茜比爾·文,最終她因無法經受熱戀後冷淡的巨大落差而自殺。道連剛開始還為此內疚,決心遠離亨利勳爵和他那“微妙而有毒的理論”。但他沒能這樣。他屈從於最本我的內心,回歸了奢靡的享樂主義,並陷得越來越萬劫不復。與此同時,他的畫像在逐漸蒼老,臉上不再如從前般純潔而是猙獰可怖——他本人卻一如當初。後來,道連·格雷刺殺了看到變化後畫像的畫家霍爾華德,並威脅一個學化學的朋友毀屍滅跡。此後他受良心折磨決定棄惡從善,然而發現在做了他認為的“好事”之後畫像的面容還是沒有絲毫變化。他最終懷著毀滅罪證的心理用刀刺向畫像,刀卻扎進了他的胸口。那一刻,道連·格雷與他的畫像各自還為本來面目。
對故事的主題很難有個準確的定義:作者一方面詳盡地描繪了上流社會享樂主義者生活,似乎對其沒有特別的反感;另一方面又給了小說道連·格雷自作自受的傳統價值觀模式的結局。小說剛出版時曾受到無數非議——它與維多利亞時代主流的追求莊重、禮儀的風範相悖——它們針對的都是小說中人物的生活問題。所以,王爾德礙於社會主流而可以設定這樣的小說結尾的可能性未必不存在。此外,其主題或許還具有一定的同性戀傾向:對道連·格雷美麗容貌的描繪就能體現這一點。我認為,說這本書的主題是“享樂主義者的畫像”再好不過,它所展現的圖景都沾染著濃厚而艷麗的色彩,似在批判又似在鼓吹享樂主義生活。
再談王爾德的文字特點。王爾德在中國出名的主要是他的童話《快樂王子》,想必大家都讀過,也都能感受到其中詞藻的華麗、想像的瑰麗。據我讀過的王爾德的作品來說,這是他一貫的特點,這本《道連·格雷的畫像》可謂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所信奉的,是一種唯美的思想,是“Art for art’s sake”的純粹。所以他的作品符號性意味很濃,能將他所熟識的那種上流社會精英文化思想展現得淋漓盡致;但眼界較為狹隘,主題往往流於表面,很難起到一針見血的深刻作用。可這無可非議。文學本身就是多樣的,堅持針砭現實誠然意味深長,但“Art for art’s sake”也應被認為是中嚴肅的文學態度。王爾德能將一種文化通過他那與之極相似的文風描繪得如此唯美,也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然此種唯美也有其必然的弊端:王爾德的文字常有堆砌賣弄之嫌,且會因過分重視對華麗場面的描寫而造成不必要的拖沓。拿這本《道連·格雷的畫像》來說,第二章中亨利勳爵與道連·格雷的對華極其精彩,作者無須以一個全知的心理分析者身份出現就已通過亨利勳爵的話闡述了享樂主義的中心觀點,為下文的展開作了詳盡鋪墊。但是,亨利勳爵的話中比喻泛濫,而其中相當大一部分不甚貼切,有明顯可以唯美化的痕跡,這就失去了作品的簡潔和人物性格俄準確性與真實性。
書中塑造了三個典型形象,畫家霍爾華德、道連·格雷和亨利勳爵。長江文藝版的導讀中借用弗洛伊德理論說這三個人分別代表超我、自我及本我。此言極是。小說藝術總是先於心理理論的,擁有敏銳觀察力的王爾德早在十九世紀就已天才地意識到了人的性格矛盾,用將其分離的方法使三個形象更為明確直觀。超我總追尋高尚、與人本性不符的生活;本我屈從於誘惑,放任自由;而自我,永遠是游離於超我與本我之間的那個,正如道連一再墮落中的幾次短暫的悔悟。書中道連道德與容貌背道而馳是種錯位的對比,最後一切還歸本身時人們能感受到無與倫比的美感,感嘆只有美是永恆的。
最後我想談談我認為的這本書最大的不足:主角的形象略顯蒼白。小說伊始便以亨利勳爵與霍爾華德的對話切入,而後延伸至亨利勳爵向道連·格雷灌輸他的理論。這一過程始終是以亨利勳爵為中心的,他的言行使一個具有綺靡神秘氣質的男人躍然紙上,場景和畫面的描繪精彩絕倫——這個人物的塑造從一開始就相當成功。而本書的主角道連·格雷呢?能找到的表現其性格的語句有:“神情活像年輕的希臘殉道士”、“撅起嘴巴”。可以看出,作者竭力把他描繪成一個純真的孩子形象,但很明顯道連·格雷比起濃墨重彩、有血有肉的亨利勳爵來說是非常蒼白的,只有個被強行定義的軀殼,缺乏能把他與其他人區分開來的標誌性性格。這就喧賓奪主了。後來,作者只對導致道連墮落的個別場景作了描寫,對這個過程卻是一筆帶過。最後我們突兀地看到一個與亨利勳爵觀點驚人一致的道連·格雷,卻不知這個人是怎樣由開始那個似乎完全沒有人格的道連變化而來的。我認為作者採用場景式的敘事方法來展現這樣一個人性改變的故事是錯誤的選擇,它只能揭示結果、無法構築過程,而人性當是由一連串或大或小的事件經過或多或少的時間形成的,不可能由單一的孤立意外一手促成。
話說回來,縱然《道連·格雷的畫像》有諸多不足,它還是本文學價值挺高的書。其中不乏有獨特見地的思考、生動形象的表述,對畫面捕捉的準確性更是嘆為觀止,人物對話也拿捏得自如、自然,毫無造作之感。
受道連格雷影響的人物
夜訪吸血鬼-萊斯特(by Anne R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