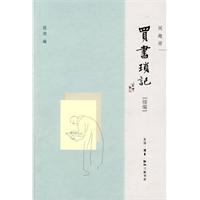推薦
書痴與書賈,誰也離不開誰,又常常鬥智鬥勇;但買的沒有賣的“精”,給書痴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自己的微少的“優勝紀略”, 就是許多精明而又富人情味的書店老闆和夥計,被他們稱之為書友,甚至當作老師。許多文人學者,是在書攤攤主或書店老闆的關照下,與書結下不解之緣的。
數十位有“書癖”的人,講述自己和別人買書的故事:有的是收藏“癖”,在版本、版次上頗有所得;有的是興趣所致,在某幾類上收穫甚豐;有的是隨心所欲,只要喜歡就是好的;更有囊中羞澀者立讀於書鋪、書攤,終日不願離去……
簡介
買書、賣書、訪書、搜書、燒書,內視生命惘惘難明也好,每有會意得意忘形也罷,離不開、繞不過的都是一個“書”字。本編四十五篇文章,從北京的琉璃廠、隆福寺到上海的福州路、文廟,從香港的二樓書店到台北的舊書街,從蘭登書屋到德國大學的舊書攤,姜德明、韓石山、傅月庵、鍾芳玲等,用如花妙筆,寫下舊書情緣。既有書痴偶然遇到心儀已久的愛書時那種故友重逢之感,也有書賈和書迷往來中那些視如己出之情;既有舊書肆繁華之時文人墨客的傳聞軼事,也有時變世移之後對舊書街沒落的搖頭嘆息。一本舊書,聯繫著歷史滄桑,也包蘊著書生情意。買賣之間,留散之中,書肆夢回,幾許況味,都在這一縷書香中隱現。
目錄
前言
上編
賣書記
燒書記
滬上訪書記
天南海北訪好書
杭州訪書記
上海訪書記
一次“淘書”的微茫記憶
莫五九的“第二個春天”
舊書肆
網上淘書記
長春訪書記幸
書肆夢回
在中國書店買書
逛舊書攤記
在香港逛二樓書店
愛書和藏書
舊書緣深解亦難
何妨一上樓書店
無名書店
茉莉二手書店
海上淘書記
舊書有什麼好玩的?
台北舊書街滄桑
光華斷想
百城堂書店
下編
在牛津
洛城訪書記
在蘭登書屋分店
內山書店小坐記
哈佛訪書記
在劍橋書店裡聽講座
巴黎購書
德國大學的舊書攤
悠長的書香
圖賓根書店瑣憶
柏林的舊書店
在斯堪的納維亞買舊書
德國大學校園書攤
日本淘書記——東京篇
日本淘書記——京都篇
一個書商之死:懷念艾倫
米克瑞特
賣書郎與補書娘的故事
俄羅斯買書記
都靈書生活
媒體評論
談及舊書肆,免不了要提提北平,北平的舊書肆又以一廠二寺最出名,廠即琉璃廠,二寺即慈仁寺與隆福寺,而琉璃廠尤其是個大書海,具有幾百年的歷史,藏書十倍於前述的“二寺”。到了民國以後,慈仁寺(今名報國寺)卻書影全無,隆福寺則由一些趕會期的浮攤,發展成四五十來家店肆,為琉璃廠半數左右。
——老雕蟲《舊書肆》
我仿佛聽到輕微的噝噝聲,是書在哭泣,一下子讓我想起孩提時代同父親燒書的情景。那時候頭上有隆隆的炮聲,街上有刺耳的鐵蹄聲,敵人已經衝到我們的大街上了。現在呢,我為什麼要燒書?還像個賊似的?火光熏蒸著我的臉,我感到汗水的濕潤,也許還有淚水。是煙熗的,還是我太懦弱了? ——姜德明《燒書記》
人生貴自適,買書未必為了書,讀書也未必為了知。王國維愛鑽牛角尖,“但解購書哪計讀,且消今日敢論旬”,這是內視生命惘惘難明,遺得日算一日,其中自有深意;陶淵明豁達自放,“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是張開視野,把書當成了指月的那根指頭,得意忘形了。前賢典型歷歷在眼,買書賣書,藏書散書,論到底,也不過就是浮生夢塵之一耳,新舊良窳無論,千卷買進終復去,或許,來去之間的“那一點意思”才是更值得掛念寶貴的吧!
——傅月庵《無名書店》
在德國,不管是老大學,還是新大學,舊書攤都是校園中的一道特殊風景線。熟悉柏林自由大學的人,都不會忘記大學核心建築“銀樓”旁的書攤,長長的一排,沿樓錯落排開;去過哥廷根大學的人,想必不會忘記“哥廷根七君子廣場”後面的書攤;去過卡塞爾大學的人,在去大學食堂的路上,不會不留心身邊的書攤。而我印象最深的,當屬柏林洪堡大學的舊書攤。
——洪捷《德國大學的舊書攤》
書摘插圖
上編
賣書記
姜德明
買書是件雅事,古人向來愛寫藏書題跋,常常是在得書之後隨手而記,講起來多少有點得意。賣書似乎欠雅,確實不怎么好聽。先不說古人,黃裳兄跟我說過,他賣過幾次書,傳到一個“大人物”康生的耳朵里,那人就誣他為“書販子”,果然在“文革”開始後,有人便盯上了他的藏書,來了個徹底、乾淨地席捲而去,還要以此來定罪名。賢如鄧拓同志,因為需用巨款為國家保存珍品而割愛過個人的藏畫,亦被誣為“倒賣字畫”。
我也賣過書,一共賣了三次。
頭一次可以說是半賣半送,完全出於自覺自愿,並無痛苦可言。那是天津解放後不久,我要到北京投奔革命了。風氣所關,當時我的思想很幼稚,衣著如西裝、大衣之類與我已無緣,我就要穿上解放區的粗布衣,布底鞋了。舊物扔給了家人。最累贅的是多年積存的那些舊書刊,五花八門,什麼都有。為了表示同舊我告別,我把敵偽時期的出版物一股腦兒都看成漢奸文化當廢紙賣掉了。這裡面有北京出版的《中國文學》,上海出版的《新影壇》、《上海影譚》,還搭上抗戰勝利後上海出版的《青青電影》、《電影雜誌》、《聯合畫報》(曹聚仁、舒宗僑編),等等。有的覺得當廢紙賣可惜,如北京新民印書館印的一套“華北新進作家集”等,其中有袁犀(即李克異)的《貝殼》、《面紗》、《時間》、《森林的寂寞》;山丁的《豐年》;梅娘的《魚》、《蟹》;關永吉的《風網船》、《牛》;雷妍的《白馬的騎者》、《良田》等。再加上徐訐的《風蕭蕭》和曾孟朴的《魯男子》(這是我少年時代最喜歡讀的一部小說),等等,湊成兩捆送給我的一位堂兄,讓他賣給專收舊書的,好多得幾個錢。這也是盡一點兄弟間的情誼,因為那時他孩子多,生活不富裕。我匆匆地走了,到底也不知道是否對他略有小補,也許根本賣不了幾個錢。
留下的很多是三十年代的文藝書刊和翻譯作品,還有木刻集,包括《蘇聯版畫集》、《中國版畫集》、《英國版畫集》、《北方木刻》、《法國版畫集》、《抗戰八年木刻選》,等等。臨行時,幾位同學和鄰居小友來送別,我又從書堆中撿出一些書,任朋友們隨便挑選自己喜愛的拿走,作個紀念。我感到一別之後,不知我將分配到天南海北,更不知何時才能再聚。可是風氣已變,記得幾位小友只挑去幾本蘇聯小說,如《虹》、《日日夜夜》、《麵包》之類,別的都未動。
這就是我第一次賣書、送書的情況。
到了北京學習緊張,享受供給制待遇,也無錢買書。後來,我已做好了去大西北的準備,可分配名單卻把我留在北京。幾年之後。社會風氣有變,人們又講究穿料子服了,我也隨風就俗,把丟在天津家中的西裝、大衣撿了回來。參加“五一”遊行的時候,上面號召大家要穿得花哨些,我穿上西裝,打了領帶,手裡還舉了一束鮮花,惹得同伴們著實讚美了一番。當然,也有個別開玩笑的,說我這身打扮像是工商聯的。
我把存在家中的藏書全部運到了北京。
生活安定了,辦公的地方距離東安市場近,我又開始逛舊書攤,甚至後悔當初在天津賣掉那批書。
第二次賣書是在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的時候。
那時既講煉鋼,又講煉人。人們的神經非常緊張,很多地方都嚷嚷著要插紅旗,拔白旗,而批判的對象恰恰是我平時所敬重的一些作家和學者。整風會上,也有人很嚴肅地指出我年紀輕,思想舊,受了三十年代文藝的影響。我一邊聽批評,一邊心裡想:“可也是,人家不看三十年代文藝書的人,不是思想單純得多,日子過得挺快活嗎?我何苦呢!”有了這點怨氣和委曲,又趕上調整宿舍搬家(那時我同李希凡、藍翎、苗地諸兄都要離開城外的北蜂窩宿舍,搬到城內來)。妻子一邊幫我收拾書,一邊嫌我的書累人。我靈機一動,也因早有此心,馬上給舊書店掛了個電話,讓他們來一趟。
第二天下班回到家裡,老保姆羅大娘高興地搶著說:“書店來人了,您的書原來值這么多錢呀。瞧,留下一百元呢!”望著原來堆著書的空空的水泥地,我苦笑了一下,心裡說:“老太太,您可知道我買來時花了多少錢嗎?”他拉走的哪裡是書?那是我的夢,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淚水……羅大娘還告訴我,那舊書整整裝了一平板三輪車。不過,當時搬家正需要用錢,妻子和孩子們還真的高興了一場。我心裡也在嘀咕:就這樣可以把我的舊情調、舊思想一股腦賣掉了?我這行動是不是在拔自己的白旗!
這一次,我失去了解放前節衣縮食所收藏的大批新文學版本書。其中有良友出版公司和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文學叢書”,包括有《四世同堂》在內的老舍先生的全集(記得當時只留下其中的兩本,一是老舍先生談創作經驗的《老牛破車》,一是錢鍾書先生的小說《圍城》。現在這兩本書還留在我的身邊)。失去的還有幾十本《良友畫報》,整套的林語堂編的《論語》和《宇宙風》。還有陳學昭的《寸草心》,林庚的《北平情歌》等一批毛邊書,都是我幾十年後再也沒有碰上過的絕版書。
那時我並不相信今後的文學只是唱民歌了,但是我確也想到讀那么多舊書沒有什麼好處。我頂不住四面襲來的壓力,為什麼我就不能像別人一樣地輕鬆自如?有那么多舊知識,不是白白讓人當話柄或作為批判的口實嗎?趁早下決心甩掉身上的沉重包袱吧。
第三次賣書是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那時的風聲可緊了!《林家鋪子》、《北國江南》、《李慧娘》都成了大毒草,連“左聯”五烈士的作品也不能隨便提了。我的藏書中有不少已變成了毒草和違礙品,連妻子也為我擔心。那時人人自危,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愛上了文藝這一行,真是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這是自投羅網,專愛“毒草”!深夜守著枯燈,面對書櫥發獃,為了妻子和孩子的幸福,也為了自己的平安,我又生了賣書的念頭。這一次又讓舊書店拉走了一平板三輪車書,連《列寧全集》、《史達林全集》也一起拉走了。我想有兩套選集足夠了。第三次賣掉的書很多是前兩次捨不得賣的,幾乎每本書都能勾起我的一段回憶,那上面保存了我少年時代的幻想。我不忍心書店的人同我講價錢,請妻做主,躲在五樓小屋的視窗,望著被拉走的書,心如刀割,幾乎是灑淚相別。妻子推開了門,把錢放在桌上愴然相告:“比想像的要好一點,給的錢還算公道。可是,這都是你最心愛的書呢……”我什麼也沒有說。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個不幸的人,懦弱的人。我在一股強風面前再一次屈服了。
不久,“文革”來了,我們全家都為第三次賣書而感到慶幸,因為拖到這時候連賣書也無門了。
風聲愈來愈緊,到處在抄家燒書,而我仍然有不少存書。這真是劣根難除啊,足以證明我這個人改造不徹底。若在第三次賣書時來個一掃而光該多乾脆,不就徹底舒服了嗎!書啊書,幾十年來,你有形無形地給我添了多少麻煩,帶來多少痛苦,怎么就不能跟你一刀兩斷?我應該愛你呢,還是恨你!
大概人到了絕望的程度,也就什麼都不怕了。這一次,我也不知道何以變得如此冷靜和勇敢。我準備迎受書所帶給我的任何災難,是燒是抄,悉聽尊便,一動也未動。相反地,靜夜無人時,我還抽出幾本心愛的舊書來隨便翻翻,心涼如水,似乎忘記了外面正是一個火光沖天的瘋狂世界。
然而,居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的殘書保留下來了。二十年來,我再也沒有賣過一本書。
今後,我還會賣書嗎?不知道。
一九八六年七月
燒 書記
姜德明
“七·七”事變那年,我還是個孩子。我蹲在父親身旁跟他一起燒過書。父親識字不多,但愛集郵,也有一些附有圖片的書和畫報,上面難免有蔣介石的像和抗日的內容,日本人見了是犯禁的。有些郵票也燒了,因為上面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
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書的厄運又來了。大街小巷都在燒書,整個北京城布滿了火堆。
我們宿舍大院燒書的那天,我卻顯得異常鎮靜。那是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往日也許很多人已帶著孩子去逛公園,或在窗明几淨的房間裡看書、寫作,至少在準備幾樣可口的小菜吧。可是今天大院裡死樣的沉寂,好像有什麼不祥之兆。兩天前,宿舍里幾名“積極分子”便貼出破四舊的倡議,說我們大院裡沒有動靜是不忠,號召星期日採取“革命行動”。果然就在這個美好而平靜的上午,在“積極分子”的指揮下,剎時間在大院中間就形成兩座書堆,冒起了濃煙和火光。
女兒噔噔地跑上樓來報信:“爸爸,快點,人家都燒書了,不然的話要到各家來搜查!”我湊到窗前往下看,火苗老高,煙味也衝上五樓。燒書的人少年子弟多,那幾位“積極分子”一邊燒著書,一邊還衝樓上喊:“誰家有封、資、修,誰家明白,免得挨家去搜!”被吆喝的當然有我在內。
望著女兒和我的書櫃,我茫無頭緒。兩天前我就下了決心:一本書也不燒。不是我頑固抗拒,是我無從下手。一本本書都是我多年來在各地搜尋來的,是我的心血結晶,要燒,就來個徹底乾淨地全部燒掉。但我自己決不動手,誰若採取“革命行動”就任意來吧。我跟女兒商量:“還是再等等看,要燒得全燒。你都看見他們燒的是些什麼書?”女兒說:“有《紅樓夢》、《水滸》,還有《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對了,還有老舍、巴金的小說。”父女相對默然。我看出女兒對我的態度有點不以為然了。突然響起了敲門聲,我們一驚,莫非真的要來採取“革命行動”了?我搶上前去開門,原來是隔壁的鄰居老趙。他探身進來問我:“怎么辦?真得往樓下去燒書嗎?”我說不想去,拖拖再看吧。他很高興地說:“行,你不去,我也不去。反正你比我的書多,而且我還沒有老書。你那么多老書都不燒,我還怕什麼。”說著退身而去。
也有人讓孩子送下幾本不三不四的書去充數,不懂事的幼童們則圍著火堆拍手亂叫,看熱鬧。火光微小了,孩子們的興致也沒了,大概帶頭燒書的幾位“積極分子”的肚子也餓了吧,就此收了兵。
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時候,宿舍傳達室門前貼了一張捷報,鼓吹了一番昨天的“革命行動”,又警告那些死保四舊的人們應該如何如何,否則絕無好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