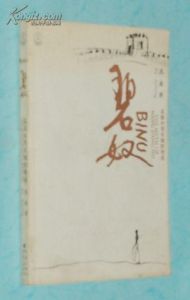創作背景
“重述神話”由英國坎農格特出版公司發起,全球包括英、美、中、法、德、日、韓等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出版社參與的全球首個跨國出版合作項目。歐洲媒體將其稱之為“國際出版界的一大奇蹟。”已加盟的叢書作者包括諾貝爾獎、布克獎獲得者及暢銷書作家,如大江健三郎、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齊諾瓦·阿切比、若澤·薩拉馬戈、托妮·莫里森、翁貝托·艾科、中國作家蘇童等。
重慶出版社是“重述神話”項目在中國大陸的惟一參與機構。《碧奴》即為中國著名作家蘇童所書寫的“重述神話——中國篇”。此外,中國著名作家李銳、葉兆言也已加入“重述神話”的寫作,分別闡釋中國古代的不同神話。
在古老的中國傳說中,孟姜女是一位對愛情忠貞不渝、徒步千里為丈夫送寒衣的奇女子。
此番“重述神話”的小說中,蘇童將主人公的名字由孟姜女改為碧奴。“重述神話”全球出版項目中,不少西方作家的重述都選擇了以後現代手法解構傳統神話,闡釋出另一番意義。蘇童認為,自己只是將家喻戶曉的孟姜女改名為“碧奴”,從來沒想過要顛復孟姜女的故事,“我不會採用解構的方式去改變人們對孟姜女這個美麗傳說的印象。”其中“眼淚”這一細節得到極大的鋪陳:“我的小說無疑更偏重以‘眼淚’表達情愫。孟姜女哭長城的精髓在於‘哭’,我將重心放在研究眼淚,這個小說可以說是一部眼淚的歷史,敘述了哭的種種姿態、類別、淵源等歷史故事。”
書名由來
事實上,在兩千多年前的那個時代,大多數女人並沒有名字。從顧頡剛的考證來看,他傾向於孟姜女是齊國人,而姜是當時齊國的大姓,孟是排行,所謂“孟姜女”就是姜家的第二個閨女。因此我在起名字的時候,腦子裡就出現了這樣一個無名無姓的女人的形象。“碧奴”這兩個字寫起來非常美,念起來也很好聽。“碧”這個字有一種蒼涼的感覺,與故事的基調也比較吻合。我為主人公起好名字以後,一種創造的感覺開始伴隨我。
蘇童序言
很高興<<碧奴>>能與世界各國讀者見面!
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已在中國流傳了二千年,神話流傳的方式是從民間到民間,我的這次“重述”應該是這故事的又一次流傳,也還是從民間到民間,但幸運的是已經跨出國門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神話是飛翔的現實,沉重的現實飛翔起來,也許仍然沉重。但人們籍此短暫地脫離現實,卻是一次愉快的解脫,我們都需要這種解脫。
最瑰麗最奔放的想像力往往來自民間。我寫這部書,很大程度上是在重溫一種來自民間的情感生活,這種情感生活的結晶,在我看來恰好形成一種民間哲學,我的寫作過程也是探討這種民間哲學的過程。
人類所有的狂想都是遵循其情感方式的,自由、平等和公正,在生活之中,也在生活之外,神話教會我們一種特別的思維;在生活之中,盡情地跳到生活之外,我們的生存因此便也獲得了一種奇異的理由。在神話的創造者那裡,世界呈現出一種簡潔而溫暖的線條,人的生死來去有率性而粗陋的答案,因此所有嚴酷冷峻的現實問題都可以得到快捷的解決。
在“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裡,一個女子的眼淚最後哭倒了長城,與其說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不如說是一個樂觀的故事。與其說是一個女子以眼淚結束了她漫長的尋夫之旅,不如說她用眼淚解決了一個巨大的人的困境。
如何說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永遠是橫在寫作者面前的一道難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孟姜女,我對孟姜女的認識其實也是對一個性別的認識,對一顆純樸的心的認識,對一種久違的情感的認識,我對孟姜女命運的認識其實是對苦難和生存的認識,孟姜女的故事是傳奇,但也許那不是一個底層女子的傳奇,是屬於一個階級的傳奇。
我去過長城,也到過孟姜女廟,但我沒見過孟姜女。誰見過她呢?在小說中,我試圖遞給那女子一根繩子,讓那繩子穿越二千年時空,讓那女子牽著我走,我和她一樣,我也要到長城去!
特點
在書中,蘇童將一個經典的,用眼淚灌注的神話,用曼妙的語言,演繹得魔幻動人。 這裡的人們不允許哭泣 書的開篇就說到了對眼淚的禁錮:“北山下的人們至今不能哭泣。哭泣的許可權大致以年齡為界,孩子一旦學會走路就不再允許哭泣了,一些天性愛哭的孩子鑽了這寬容的漏洞,為了獲得哭泣的特權,情願放棄站立的快樂。” 於是,母親藉助巫術讓嬰兒立刻停止哭泣而沉沉睡去;女孩子除了眼睛,根據各自的生理特點,動用了各種人體器官引導眼淚,眼淚便獨闢蹊徑,流向別處去了。家住北山下的碧奴燦爛如花,她是用頭髮來哭泣的,而且哭得不加掩飾。她的頭髮整天濕漉漉的,雙鳳鬟也梳得七扭八歪,走過別人面前時,大家都躲得遠遠的。 從頭髮中流出的淚水,一路陪伴碧奴,直到丈夫失蹤,她的眼淚一直流到了山外,更多人知道了憂傷的碧奴,而她的腳趾也開始哭泣。 青蛙的前身是一個盲婦人 碧奴去河邊雇馬找尋失蹤的丈夫,卻被一隻青蛙一路追隨,而她無意中發現青蛙的前身竟然是一個盲婦人,而這個盲婦人曾經劃著名木筏順流而下,沿河尋找她失蹤的兒子。她悽慘的叫聲吵醒了河兩岸寂靜的黎明,那令人驚恐的聲音預示著末日的迫近,果然洪水很快到來,盲婦人被沖得不知去向。 碧奴揣著那隻瞎眼的青蛙去北方尋夫,她們都要找到心愛的人,之後經歷了很多故事,也有了後來眾青蛙共赴長城的壯觀景象。碧奴為自己舉行葬禮 碧奴和青蛙歷盡千辛萬苦,一路上經歷了鹿人和馬人阻撓,後來在一個男孩的監督下,要親自為自己掘一方墳墓:“碧奴端詳著那棵松樹下草草劃出的墓線,依稀看見死神在那個方框下欠起了身子,焦灼地等待著她。”於是放聲大哭,烏黑的頭髮開始放肆地嗚咽。哭完以後,碧奴和男孩開始討論到底把自己埋在何處才合適,此時青蛙不知去向。
《碧奴》則用她和她的眼淚,變成了一部蘇童的神話時代百科全書。
書評
《碧奴》:蘇童的綠色夢魘
文 / 百慕
熟悉的人都知道敝人對數字九情有獨鍾,看似一種獨特的品行,持有的人多了,最終淪為俗人。九月的陽光有金子一樣的顏色。作為大俗人我不能拒絕。所以,再優秀的作品,還是要炒作的。蘇童的新書九月上市,還好我沒有去看那些轟轟烈烈的宣傳。直接切入主題。
依稀記得東西方的神話如出一轍,我反覆用淺薄的辭彙提醒自己,那只是夢被重述了。
夢是經過處理的現實,有辯識不清的輪廓和一擊即碎的完美。
人們不願面對它殘缺和真實,於是一代又一代不知疲倦地粉飾太平。
就像我忍不住要對那些美夢發表評論,而在評論之前又反覆聲明,聲明它的可信性和不可信性同樣不容忽視。
人是這樣矛盾的動物。源自內心不肯放低的尊嚴。一邊欺世盜名,一邊懺悔贖罪。
蘇童的陰鬱是優雅的。他可以用最乾淨清脆的語言去描繪一個遍體鱗傷的夢境。於是我們聞到信桃君門前帶著死亡訊息的野百合花的香味,接下來又為淚泉的來歷輕微顫動,半山腰上殺氣騰騰的羽林軍仿佛是一道凝固的素色風景。蓬頭垢面的碧奴美若天仙。但是反過來,一路平淡的行走看似波瀾不驚,實則風起雲湧。只是對人間百態的麻木講述卻像一根根針,扎進碧奴的腳板心,痛徹旁人心扉。
但凡傳說都是美麗的。所以孟姜女的名字唯美而略帶微苦。
碧奴,人如其名,天賦美色,生在社會的底層。她的故事永遠是對萬里長城最柔韌的控訴。
所謂滴水穿石,我們不應該將一種真愛假託於任何毫不相干的理由。
一個與己無關的事實如何能打動我們。唯用一種或另一種語言生動地描述。再溶入現代人所謂的高尚品味。再後來,原本無人問津的陽春白雪空前火爆,接下來,整個世界被商業化。所以啊,生在俗世就不該再憤世嫉俗,笑納所有變故吧。繁華的都市裡找不到原始叢林,叢林中也沒有傳說中的隱士或高人。大家都在為一己之私拼搏,然後故作清高地對認識不認識的人批叛一番。謂之陶冶,謂之眾人皆濁我獨清。唉,扯遠了。
我膜拜傳說中的女人們,因為她們已化作塵埃成為歷史,不可能再令我失望。
我可以盡力使之美輪美奐,因為死無對證,可以妒煞當今所有不甘心的人。
是現實壓榨著我賴以欺騙世人的華麗軀殼。我不得不躲閃到一個只有仙子出沒的地帶。
那裡沒有爭寵奪愛,沒有飛短流長,永遠只有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順理成章的結局。
我可以旁若無人地看戲,看到入迷時,百感交集,或留下片言隻語。
當我抽身離去時,早已預料身後黑壓壓一片猜測,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自己。
我能說什麼呢。人生如戲而已。
我感動於一個又一個悽美的神話,那種若即若離的幻覺常常使我在某個邊緣忘乎所以。
忘了自己身處險境,黑暗中的狼群虎視眈眈,而自己又被一片虛假的溫暖模糊了雙眼,那種溫度是不恆定的,可以在最不設防的時候將你擊潰。
所以親愛的,跟你們講,除了自己,誰也別信。
蘇童的字,多多少少迎合了少年們跳躍的想像,和不甘平淡的表達方式。沒有刻板的對話模式,所有的對白像是筆者本人內心的獨白,其中穿插著簡潔精闢的概括。“老人的回憶冗長而哀傷,就像一匹粗壯的黑帛被耐心地鋪展開來,一寸一寸地鋪開,孩子們在最傷心處剪斷它,於是無數噩夢的花朵得以盡情綻放。”
----以史詩般的浪漫向後世敘述一個不會識文斷字的亂世。幾乎是所有詩人的理想。他們希望這個世界永遠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這裡仍然有腐爛的芳香,卻尋訪不到頹廢的痕跡。我們看慣了太多標榜另類的死亡理想。
有太多的人屈解了寂寞和孤獨的真實含義。那是再無對手,再無知音之後的高處不勝寒。我相信就算是過去的波德萊爾,他也有求生的本能,他對這個世界仍然滿懷希望,而豐衣足食的人們為什麼一定要無病呻吟。
生與死的近距離對視不應該只發生在對生活無能為力的那一刻。
即使是傳說,碧奴所遇到的一切醜惡人性都早已在現實生活中見怪不怪。
年輕人問,生活的真諦是什麼;老人回答,是好死不如賴活。審問內心,有多少人敢於承認。
我記憶猶存的兩個片段,一個是淚泉的來歷,一個是人市,是相當諷刺的。在某種悖論下,人的感恩也會成為原罪;有人永遠認不清自己的角色,以己之短笑他人之長。
其實一段旅程一個故事,都在不斷地隱喻。
人名地名,包括被架空的歷史,無一不是尖銳的指向,看似遠離塵世,實則諷喻現實。
全文整體的寓意仍然不能脫離愚公移山式的經典執著。
碧奴是孤獨的,孤獨到她的清白身世使任何一個聽者疑雲重重。
當所有的路都被封閉時,唯一的出路是披荊斬棘。所以我們大多數人走到這一步時萬念俱灰,以為自己真的錯了,只有碧奴思前想後不認為自己千里送寒衣有什麼不對。無知即無畏。
她行走的姿態狼狽不堪。所以最終必然瀟灑地站立於長城之巔。
背負著所有人的唾棄上路,一個山地女子沿河尋子的魂魄是碧奴唯一的追隨者,也是她原本瘦弱的肩上的負荷。
那些嘲笑,背叛,陷害,無一不是她漫長尋夫路上的快樂插曲。
大智若愚的道理人人都懂,可是實現的時候卻那么難,需要和自己的本能抗爭。
大多數時候,我們不願接受委屈和被誤解,睚眥必報的本領天生就會。
蘇童的思維中規中矩,映射著千百年來儒家思想的精髓。人之初,性本善。關於邪惡的極限被一筆帶過,不忍展現,比如鹿人是孩子,芹素是死人。他們對她的貪慾僅止於金錢和虛榮。而這條人類的劣根性已經被社會默認,所以談不上罪惡。
我們已無需再赤裸裸地討論生死和愛恨。如果說口號會流於媚俗,所謂的另類作品中被不斷揭示的厭世氣息已經俗不可耐。就是這樣天馬行空,然而栩栩如生地刻畫天空,飛鳥,大自然,古代社會人文,不動聲色地闡述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待生命的凝重。關於生與死,愛與恨,善與惡,真與偽,早就涇渭分明。不必多言。
這個時候,筆者已不會受到眾人的質疑,大家也已不再追究豈梁的死活,那是既定的事實。人們只想從這個婦孺皆知的傳說中探測到一絲新的希望。最後,萬豈梁似乎變成了美麗的金線蝴蝶,在斷腸岩下展翅欲飛。我們終於如願以償,可以再一次地粉飾血淋淋的現實。
作者簡介
蘇童,男,1963年生。1980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妻妾成群》、《傷心的舞蹈》、《婦女樂園》、《紅粉》等,長篇小說《米》《我的帝王生涯》、《武則天》、《城北地帶》等。小說《米》《紅粉》先後被搬上銀幕,《妻妾成群》被張藝謀改編成《大紅燈籠高高掛》獲得威尼斯電影節大獎,《婦女生活》改編為電影《茉莉花開》後,獲得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獎。現任江蘇作協副主席,為中國當代文學先鋒代表作家之一,多部作品翻譯成英、法、德、意等各種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