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滅亡》
《滅亡》 1923年5月,19歲的巴金跟隨哥哥堯林離開四川老家,乘船順江而下,到達上海。4年後,他又去往法國。走出四川與出國是巴金人生的兩大轉折。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就是在法國巴黎寫成的。《滅亡》反映的是1926年左右,在北伐戰爭之前,軍閥孫傳芳統治下的上海的生活,塑造了一個以生命向黑暗社會復仇的職業革命者杜大心的形象,這位主人公得了嚴重的肺結核病,卻忍住極大的痛苦為反抗專制制度而拚命工作,他對自己個人的前途失去了希望,對黑暗壓迫下的人類前途也感到絕望,然而他還是要盡力奮鬥。雖然他也被人愛過,但那種絕望、虛無而又要拚死抗爭的心態最終使他喪失了愛情,甘願消耗生命以殉事業,求取良心的安寧。
內容簡介
小說《滅亡》以在北洋軍閥統治下沾滿了“腥紅的血”的上海為背景,描寫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因而尋求社會解放道路的知識青年的苦悶和抗爭。塑造了一個以生命向黑暗社會復仇的職業革命者杜大心的形象,這位主人公得了嚴重的肺結核病,卻忍住極大的痛苦為反抗專制制度而拚命工作,他對自己個人的前途失去了希望,對黑暗壓迫下的人類前途也感到絕望,然而他還是要盡力奮鬥。雖然他也被人愛過,但那種絕望、虛無而又要拚死抗爭的心態最終使他喪失了愛情,甘願消耗生命以殉事業,求取良心的安寧。響徹全書的是這樣的呼聲:“凡是曾經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這也是小說的主題。主人公杜大心懷有“為了我至愛的被壓迫的同胞,我甘願滅亡”的決心,最後,他為“信仰”而英勇獻身。
作者簡介
 巴金
巴金 巴金(1904.11.25—2005.10.17)四川成都人,無黨派,1921年於成都外語專門學校肄業。1923年到上海,1927年至1929年赴法國留學,寫成中篇小說《滅亡》,次年發表於上海《小說月報》,被視為他的創作生涯的正式開端。1929年回國後,在滬從事翻譯、創作、出版工作,三十年代的《家》、《春》、《秋》 (合為《激流三部曲》),四十年代寫於重慶的《寒夜》,長期流傳不衰,被認為中國現代文學長篇小說的重大成就。1935年至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50年後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1953年9月後先後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藝月報》、《收穫》、《上海文學》主編。1962年後任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1977年至1983年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198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2003年3月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創作短篇合為《英雄的故事》、《明珠和玉姬》、《李大海》等短篇小說集,並有散文、報告文學集問世,《隨想錄》五卷被文化界譽為“講真話的大書”1958年起陸續出版《巴金文集》(十四卷本),1987年起出版《巴金全集》(二十六卷本)。
2003年11月,國務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榮譽稱號。
創作背景
 青年時期的巴金
青年時期的巴金 在巴黎,巴金原本想學經濟,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一下子獲得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契訶夫、左拉等文學大師的作品,如饑似渴地閱讀後,他被深深感動了。關於《滅亡》的寫作,巴金後來寫道:“每夜回到旅館裡,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疲倦的身子,就點燃了煤氣爐,煮茶來喝。於是巴黎聖母院的鐘聲響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這樣的環境裡過去的回憶繼續來折磨我了。我想到那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我想到那過去的一切,心就像被刀割著痛,那不能熄滅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為了安慰這一顆寂寞的年輕的心,我便開始把我從生活里得到的一點東西寫下來。每晚上一面聽著聖母院的鐘聲,我一面在練習簿上寫一點類似小說的東西,這樣在三月里我寫成了《滅亡》前四章。”
《滅亡》是巴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由葉聖陶推薦發表在1929年出版的《小說月報》上。當時《小說月報》已是全中國最有名望的文學期刊。巴金從此闖入文壇。
《滅亡》這個書名有雙重的意義。除了控訴、攻擊和詛咒外,還有歌頌。《滅亡》歌頌了革命者為理想英勇犧牲的獻身精神。書名是從過去印在小說扉頁上的主題詩(或者歌詞)來的。這八句關於“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的詩決非表現“革命也滅亡,不革命也滅亡”的虛無悲觀的思想。唯一的證據就是:這八句詩並非我的創作,它們是我根據俄國詩人雷列葉夫的幾句詩改譯成的。雷列葉夫的確說過“我知道:滅亡等待著第一個起來反抗壓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且他自己就因為“起來反抗壓制人民的暴君”,領導十二月黨人的起義,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絞刑架上。他是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願滅亡的英雄。我這幾句改譯的詩不僅歌頌了十七世紀俄國農民革命的領袖哥薩克英雄拉辛,也歌頌了為俄國民主革命英勇戰鬥的十二月黨人,也歌頌了一切“起來反抗壓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
評價
 晚年時期的巴金
晚年時期的巴金 在巴金漫長的創作生涯中,小說《滅亡》的命運十分特別。它是青年巴金在法國留學期間完成的。可以說是巴金文學生涯的標誌性起點。作為一部成名作,它在誕生之初即被評論界譽為“現代文壇不可多得的佳作”,成為廣受讀者追捧的暢銷書。但與巴金日後的作品相比,它又被普遍認為算不上一部上乘之作。它的命運之多舛,如今想來,發人思考:從1929年出版單行本算起,到1951年7月,共印行28版(次)。而在隨後的55年裡,再沒有出過單行本。在理性缺席的年代,《滅亡》甚至因為“無政府主義的狂熱”,幾乎遭到全面否定的厄運。連巴金自己編選的十卷本《巴金選集》,竟也沒有將它收入。晚年也很少提及,似乎也有迴避的嫌疑。
2008年,是《滅亡》創作完成80周年,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推出了新的單行本,以示紀念。糾纏於作家當時的意識形態,以圖在小說主人公身上得到什麼印證已經不再有什麼意義。重要的是,當年遠離祖國,才24歲的巴金究竟想通過革命者杜大心的滅亡來表達什麼?怎樣理解序言中他說“橫貫全書的悲哀卻是我自己底悲哀”呢?
巴金離開祖國赴法留學之時,正是北伐革命軍將軍閥孫傳芳的軍隊驅逐至長江以北之際。國共合作名存實亡,各地連年戰爭,流氓土匪橫行。“整個國家罩滿了烏雲,廣大人民流不完的血淚、訴不盡的痛苦!”小說主人公杜大心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他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啟蒙,是一個已經覺醒的革命者。真誠地要求革命並堅信新世界的必然到來,卻不知如何去爭取。他痛恨黑暗的現實,又痛感反動勢力過於強大,自己過於微弱孤單,因此悲觀地認為自己將在光明到來之前必然滅亡。他苦悶、抑鬱、悲哀,處於人群之中,卻感到“只有他一個孤零零的生人”;他還患有嚴重的肺病,為現實中的不公平和被壓迫者的不幸深感苦悶的同時,認定自己不配有幸福,也不能有愛情,決然地離開了他深愛的姑娘,用工作壓抑愁緒。當戰友張為群被殺害之後,他終於下定了走向“滅亡”的決心。射向戒嚴司令的子彈是復仇,射向自己的那顆則是成全——杜大心認為,只有這樣的方式才能使自己得到良心上永久的安慰,才能了結肺病以及無望的生活帶給他的一切苦痛。
作品感人至深的並不是宣揚了什麼主義,而是融絕望與抗爭於一體的獻身精神。甜軟抒情的戀愛情節與悲憤暴烈的場景互相穿插,形成奇特的感染力。英雄至上的氣象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中難得一見,儘管這是一個在暗夜裡絕望呼叫的英雄。杜大心的出現,對那些在革命受挫處於低潮時期而思想情緒又陷於苦悶彷徨的青年,無疑是一種鼓勵和鞭策。
《滅亡》的價值,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它真誠地反映了對於“信仰”的追問——這幾乎成為巴金小說的一種核心價值。“信仰”是一個人內心最崇高的、並願意為之不懈奮鬥的東西。它不僅是一個“彼岸”,還是一條通向彼岸的路。杜大心的悲劇性在於他雖然能看到彼岸,但腳下無路。或者說,當他以為,一種理想非得以與世界的隔絕來實現時,他便陷入了青年人常常會遭遇的“極端”。面對消滅矛盾最直接的辦法——死亡,巴金說,“我自己是反對他採取這條路的,但我無法阻止他,我只有為他底死而哭。”作家自己實踐著的,正是李冷兄妹所選擇的道路——拒絕家庭賦予的幸福和安樂,投身積極的創作以完成對自我的救贖。誠如巴金自己對於《滅亡》的評價:“《滅亡》不是一本革命的書,但它是一本誠實的作品。”正是這種誠實的掙扎和激情的表達,鑄就了《滅亡》在文學史上的特殊意義。回望一個日後被尊為真正有良心的作家的成長之路,這種掙扎毋寧說是一種寶貴的希望。
巴金自談《滅亡》
 《滅亡》
《滅亡》 《滅亡》當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且我的寫作方法也大有問題。這不像一個作家在進行創作,倒像一位電影導演在拍攝影片。其實電影導演拍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我最後決定認真寫這本小說,也不過做些剪接修補的工作。我以後寫別的小說,不論是短篇、中篇、長篇,有的寫得順利,幾乎是一口氣寫完,有的時寫時輟,但它們都是從開頭依次序寫下去的。例如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就是一口氣寫下去的。這部作品的初稿我曾經投給《小說月報》,但很快就被退回,說是寫得不好。編者的處理是很公平的。《死去的太陽》的失敗並非由於一氣呵成,而是生活單薄。更重要的原因是:硬要寫小說,這裡面多少有點為做作家而寫小說的味道了。這箇中篇初稿的題名是《新生》,退回以後,我就把它鎖在抽屜里,過了幾個月偶然想起,拿出來改寫一遍。那時我翻譯的阿·托爾斯泰的劇本《丹東之死》剛出版,我就引用了《丹東之死》中的一段話放在小說前面,根據這段話改寫了小說的結尾,而且把書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陽》。但是即使做了這些加工的工作,我仍然沒法給我的失敗的作品添一點光彩。為了退稿,我至今還感激《小說月報》的編者。一個人不論通過什麼樣的道路走進“文壇”,他需要的總是辛勤的勞動、刻苦的鍛鍊和認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場”都只能助長一個人的驕傲而促成他不斷地後退。但這都是題外的話了。
《滅亡》出版以後我讀到了讀者們的各種不同的意見。我也常常在分析自己的作品。我常常講起我的作品中的“憂鬱性”,我也曾虛心地研究這“憂鬱性”來自什麼地方。我知道它來自我前面說過的那些矛盾。我的思想中充滿著矛盾,自己解決不了的矛盾。所以我的作品裡也有相當濃的“憂鬱性”。倘使我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參加了火熱的實際鬥爭,我便不會再有矛盾了,我也不會再有“憂鬱”了。《滅亡》的主人公杜大心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在他的遺著中有著這樣的一句話:“矛盾,矛盾,矛盾構成了我的全部生活。”他的朋友李冷說:“他的滅亡就是在消滅這種矛盾。”(見《新生》)杜大心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消滅他的矛盾,所以他選擇了死亡。他疲倦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他覺得“只有死才能夠帶來他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夠使他享受安靜的幸福”。他自然地會採取用暴力毀滅自己生命的一條路:報仇、泄憤,殺人、被殺。杜大心並非一般人所說的“浪漫的革命家”,他只是一個患著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我寫杜大心患肺病,也許因為我自己曾經害過肺病,而且當時我的身體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動,容易憤怒。倘使杜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例如說找到了共產黨,他就不會感覺到“他是一個最孤獨的人”,他是在單獨地進行絕望的鬥爭;他就不會“憎恨一切的人”,甚至憎恨他自己。因為孤獨,因為絕望,他的肺病就不斷地加重。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易激動,更容易憤怒,更不能夠冷靜地考慮問題。
倘使有一個組織在領導他,在支持他,他決不會感到孤獨,更不會感到絕望,也不會有那么多的矛盾,更不會用滅亡來消滅矛盾。
我不能說杜大心的身上就沒有我自己的東西。但是我們兩個人(作者和他的主人公)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杜大心是單獨地在進行革命的鬥爭,我卻是想革命,願意為革命獻出一切,而終於沒有能參加實際的革命活動。但是我們兩個都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這一點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會寫出杜大心這個人物來。要是我走了另一條道路,也許我就不會寫小說,至少我不會寫出像《滅亡》這樣的作品。有些細心的讀者,只要讀過幾本我的作品,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求什麼東西。我自己也說過我的每篇小說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號。事實上我缺少一種能夠消滅我的矛盾的東西。我不斷地追求,卻始終沒有得到。
我今天無法再諱言我的思想的局限性。我在寫《滅亡》以前和以後常常稱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有時候我也說我是一個克魯泡特金主義者,因為克魯泡特金主張無政府共產主義,不贊成個人主義。但是我更喜歡說我有我的“無政府主義”,因為過去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嚴密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組織。在所謂“無政府主義者”中間有各種各樣的派別,幾乎各人有各人的“無政府主義”。這些人很不容易認真地在一起合作,雖然他們最後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大同世界。其實怎樣從現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任何一派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沒有具體的辦法,多數的“無政府主義者”根本就沒有去研究這樣的辦法。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真正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有少數人也承認階級鬥爭,但也只是少數,而且連他們也害怕聽“專政”的字眼。我講的是那一個時期西歐的“無政府主義”的情況,因為我過去接觸到的,過去受過影響的都是這些外國的東西。我接受了它們,卻不曾消化,另外我還保留而且發展了我自己的東西。這兩者常常互相執制,有時它們甚至在我腦子裡進行鬥爭。所以我的矛盾越來越多,越無法解決。我坦白地承認我的作品裡總有一點外國“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但是我寫作時常常違反這個“無政府主義”。我自己說過:“我是一個中國人。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而且說實話,我所喜歡的和使我受到更大影響的與其說是思想,不如說是人。凡是為多數人的利益貢獻出自己一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愛。我寫《滅亡》之前讀過一些歐美“無政府主義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傳或傳記,例如克魯泡特金的《自傳》;我也讀過更多的關於俄國十二月黨人和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俄國民粹派或別的革命者的書,例如《牛虻》作者麗蓮·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羅斯》和小說《安德列依· 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爾的《回憶錄》。我還讀過赫爾岑的《往事與回憶》,讀了這許多人的充滿熱情的文字,我開始懂得怎樣表達自己的感情。在《滅亡》裡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響是突出的,雖然科茹霍夫和杜大心並不是一類的人。而且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說高出我的《滅亡》若干倍。我記得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說里也有“告別”的一章,描寫科茹霍夫在刺殺沙皇之前向他的愛人(不是妻子)告別的情景。
《滅亡》裡面的人物並不多。除了杜大心,就應該提到李靜淑和她的哥哥李冷,還有張為群和別的幾個人。所有這些人全是虛構的。我為了發泄自己的感情,傾吐自己的愛憎,編造了這樣的幾個人。自然我在生活里也或多或少地看見過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們的服裝和外形。像王秉鈞那樣的國民黨右派我倒見過兩三個。他們過去也曾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後來卻換上招牌做了反動的官僚,我帶著極大的厭惡描寫了這樣的人。“殺頭的盛典”我沒有參加過。但是我十幾歲的時候見過綁赴刑場的犯人和掛在電桿上示眾的人頭。我也聽見人有聲有色地談起劊子手殺人的情形。《革命黨被捕》和《八日》兩章多少有些根據。 我去法國之前住在上海舊法租界馬浪路一個弄堂里。我和兩個朋友同住在三樓的前後樓。房東可能是舊政客或者舊軍人,他和幾個朋友正在找路,準備招兵買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來的北伐軍。不知道怎樣,有一天他的一個姓張的部下在華界被孫傳芳的人捉去了,據說是去南市刻字店取什麼司令的關防,給便衣偵探抓去的。他的妻子到房東家來過一兩次,她是一個善良的年輕女人。她流著淚講過一番話。後來房東一家人全躲到別處去了,只留下一位老太太看家。不久我就在報上看到那位張先生被殺頭的訊息,接著又聽說他在牢里托人帶話給房東:他受了刑,並未供出同謀,要房東以後照顧他的妻子兄弟。過兩天我就上船去馬賽了。兩三個月以後我偶然在巴黎的中法聯誼會或者這一類的地方看到幾張《申報》,在報上又發現那房東的一個朋友也被孫傳芳捉住殺頭示眾了 。孫傳芳退出上海之前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頭。要不是接連地看到殺頭的訊息,我也不會想到寫《殺頭的盛典》。那位張先生的砍頭幫助我描寫了張為群的英勇的犧牲和悲慘的死亡。
關於李靜淑我講得很少,因為她也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我只見過她的外形、服裝和動作。我指的是一個朋友的新婚的太太。我創造李靜淑出來給我解決愛與憎的問題。結果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我曾經同一位年紀較大的朋友辯論過這個問題,《最後的愛》一章中李靜淑講的一段話,就是根據他的來信寫成的。
關於《滅亡》我已經講了不少的話。我談創作的過程談得多,談人物談得少。我在前面說過我創造人物來發泄我的感情,解決我的問題,暴露我的靈魂。那么我在小說里主要地想說明什麼呢?不用說,我集中全力攻擊的目標就是一切不合理的舊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來。貫穿全書的響亮的呼聲就是這樣一句話:“凡是曾經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所以《滅亡》並不是一本悲觀的書,絕望的書。不管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有多大,作品的缺點有多少,《滅亡》決不是一本虛無主義的小說,否定一切的小說,也不是恐怖主義的小說。
《滅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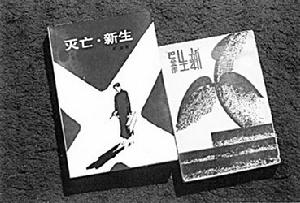 《滅亡》
《滅亡》 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我又是一個孤兒。
我有一個哥哥,他愛我,我也愛他,然而為了我底信仰,我不得不與他分離,而去做他所不願意我做的事情。但是我不能忘記他,他也不能忘記我。
我有一個“先生”,他教我愛,他教我寬恕。然而由於人間的憎恨,他,一個無罪的人,終於被燒死在波士頓,查理斯頓監獄的電椅上。就在電椅上他還說他願意寬恕那個燒死他的人。我沒有見過他,但我愛他,他也愛我。
我常常犯罪了!(I have always sinned!)因為我不能愛人,不能寬恕人。為了愛我底哥哥,我反而不得不使他痛苦;為了愛我底“先生”,我反而不得不背棄了他所教給我的愛和寬恕,去宣傳憎恨,宣傳復仇。我常常在犯罪了。
我時時覺得哥哥在責備我,我時時覺得“先生”在責備我。親愛的哥哥和“先生”啊,你們底責備,我這個年青的孩子實在受不下去了!我不敢再要求你們底愛、你們底寬恕了,雖然我知道你們還會愛我,寬恕我。我現在所希望於你們的,只是你們底了解,因為我一生中沒有得到一個了解我的人!
我底“先生”已經死了,而且他也不懂中文,這本書當然沒有入他底眼帘的機會。不過我底哥哥是看得見這本書的,我為他寫這本書,我願意跪在他底面前,把這本書呈獻給他。如果他讀完以後能夠撫著我底頭說:“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罷,從今以後,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你哥哥底愛總是跟著你的!”那么,在我是滿足,十分滿足了!
這本書里所敘述的並沒有一件是我自己底事(雖然有許多事都是我看見過,或者聽說過的),然而橫貫全書的悲哀卻是我自己底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淚來寫這本書的,但為了不使我底哥哥流眼淚起見,我也曾用了曲筆,添加一點愛情的故事,而且還編造了杜大心與李靜淑底戀愛。
自然杜大心不是我自己,我寫其餘的人也並沒有影射誰的心思。但是我確實在中國見過這一類的人。至於我呢,我愛張為群。
巴金
1928年8月
參考資料
[1] 光明網 http://www.gmw.cn/CONTENT/2005-10/18/content_319633.htm
[2] 易文網 http://biz.ewen.cc/books/bkview.asp?bkid=164638&cid=508542
[3] 聖才讀書網 http://www.1000book.com/Product.aspx?productId=329683
巴金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 | 激流三部曲 | 《家》[小說] | 《春》[巴金小說] | 《秋》 |
| 愛情三部曲 | 《霧》 | 《雨》 | 《電》 | |
| 抗戰三部曲 | 《火》 | 《馮文淑》 | 《田惠世》 | |
| 人間三部曲之一 | 《寒夜》[巴金小說] | |
中篇小說 | 人間三部曲之二、三 | 《憩園》 | 《第四病室》 |
其他 | 《春天裡的秋天》 | 《滅亡》 | 《死去的太陽》 | 《砂丁》 | 《萌芽》[巴金作品] 《新生》[巴金小說] | 利娜 | |
短篇小說 | 《英雄的故事》 | 《明珠和玉姬》 | 《電椅》 | 《抹布》 | 《將軍》[巴金作品] | 《神·鬼·人》 《沉落》 | 《發的故事》 | 《小人小事》 | 《李大海》 | |
散文集 | 《孔老二罪惡的一生》 | 《海行》 | 《旅途隨筆》 | 《點滴》 | 《生之懺悔》 | 《短簡》 | 《控訴》 《夢與醉》 | 《感想》 | 《龍·虎·狗》 | 《廢園外》 | 《旅途雜記》 | 《靜夜的悲劇》 | 《願化泥土》 《華沙城的節日—波蘭雜記》 | 《大歡樂的日子》 | 《堅強的戰士》 | 《友誼集》 | 《讚歌集》 《傾吐不盡的感情》 | 《賢良橋畔》 | 《大寨行》 | 《控訴集》 | 《十年一夢》 | 《再思錄》 | 《無題》 《懷念》 | 《納粹殺人工廠—奧斯威辛》| 《慰問信及其他》 | 《煙火集》 | 《生活書局在英雄們中間》 《序跋集》 | 《憶念集》 | |
| 傳記憶作 | 《巴金自傳》 | 《憶》 | 《隨想錄》 | |
文學譯著 | 《科學的社會主義》 | 《麵包略取》 | 《獄中與逃獄》 | 《薇娜》 | 《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 《為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 | 《一個賣魚者的生涯》 | 《蒲魯東的人生哲學》 | 《前夜》 | 《丹東之死》 《草原故事》 | 《秋天裡的春天》 | 《過客之花》 | 《自傳》 | 《獄中記》 | 《俄國虛無運動史話》 《門檻》 | 《夜未央》 | 《告青年》 | 《一個家庭的戲劇》 | 《叛逆者之歌》 | 《父與子》 | |
| 理論 | 《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合著) | 《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 | 《談契河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