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歷
楊 貴:男,漢族,1928年10月生,河南衛輝人,曾用名楊紹青、楊甦甡,1943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相當於國中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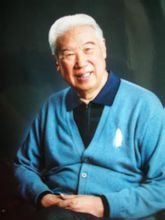 楊貴
楊貴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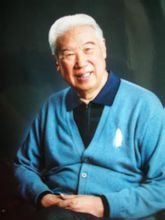 楊貴
楊貴楊 貴
,男,1928年5月28日出生,漢族,河南省衛輝市(原汲縣)羅圈村人。曾用名楊紹青、楊蘇甡。
1936年八歲時,在羅圈村讀私塾,直到1941年因國民黨政府把老師抓走,關進監獄,從此羅圈村學校就停辦了。在家裡幫助母親做些家務事和農活。
1942年秋冬,參加組織山區人民抗糧鬥爭。後因壞人告密,敵人抓四次,都未得逞。
1943年春,共產黨解放汲縣山區,被選為羅圈村農民抗日救國會副主席,領導減租減息。同年四月,參加中國共產黨,任黨支部書記。6月,被選為汲縣一區農民抗日救國會副主席。
1945年春,縣委掉任汲淇縣五區抗日救國聯合會主席。10月,任五區區長。
1947年4月任淇縣五區區長。7月6日,在淇縣三里屯村反擊國民黨匪軍包圍戰鬥中負傷,回後方治療。9月傷未痊癒,又調淇縣前方指揮部工作。
1948年2月,因二區閆惠民區長犧牲,被調二區任區長。
1948年10月,任中共淇縣六區區委書記兼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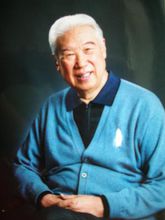 楊貴
楊貴1949年7月,任中共淇縣縣委委員,仍兼六區區委書記。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淇縣縣委委員,縣委辦公室主任兼任淇縣五區區委書記。
1950年8月,任中共湯陰縣縣委宣傳部長。
1952年12月,任中共安陽地委辦公室副主任。
1954年5月任中共林縣縣委書記。
1958年,安陽、新鄉兩地委合併後,任中共新鄉地委委員兼林縣縣委第一書記、林縣武裝部政委。
1962年安陽地委恢復後,1965年任中共安陽地委副書記兼林縣縣委第一書記、林縣人民武裝部政委、紅旗渠建設總指揮部政委。
1966年12月“文革”開始,被罷官批鬥。
1968年4月,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擔任林縣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林縣縣委書記、林縣武裝部政委,繼續領導紅旗渠建設配套工程。
1969年7月,調洛陽地區,任地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
1972年10月,任中共安陽地委書記兼林縣縣委第一書記。
1973年2月,任中共河南省常委,省委分工任省生產指揮部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副指揮長,仍兼安陽地委書記、林縣縣委第一書記。六月,協助省委書記劉建勛抓全面工作,到省委辦公。
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1973年11月16日,周恩來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調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負責人,仍兼河南省、地、縣職務。
1979年調五機部工作,到山東渤海農場任副場長。
1982年12月,調農業部工作,任國務院三西辦公室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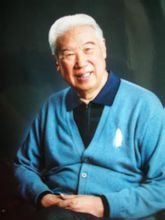 主席接見楊貴
主席接見楊貴1986年,國務院成立扶貧辦公室,任扶貧辦公室顧問。
1992年,任河南省紅旗渠精神研究會名譽會長。
1995年6月,離休。
1996年山西省委、省政府聘為山西省引黃入晉顧問,參加工程考察和研究工作。
2000年,中國醫科院腫瘤防治研究會聘任顧問。
2002年9月,被選為北京豐臺方莊地區僑聯主席。
2006年3月,中央批准職級為副部長級。八月,中央批准享受中央、國家機關部長級醫療待遇。
中共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
建紅旗渠
2009年08月20日 16:44人民網
國內外參觀過紅旗渠的人很多,但見過或了解楊貴同志的人卻不多。實際上,從紅旗渠的決策指揮到建成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楊貴與紅旗渠就一直分不開。我和許多新聞記者曾多次採訪楊貴與紅旗渠,自然也就和楊貴與紅旗渠結下了幾十年的情結。現在,《楊貴與紅旗渠》就要出版了,我樂意也應該為楊貴與紅旗渠寫幾句話。
楊貴同志小我7歲,15歲入黨,在太行抗日根據地經歷了戰略相持到戰略反攻的艱難歲月。他17歲當區長,帶領武工隊保護民眾,打擊敵人,在解放戰爭中身經百戰,至今臂膀上還留有敵人的槍傷。全國擁軍模範靳月英的丈夫,就是為掩護楊貴而犧牲的。我1998年訪問靳月英,她還能唱出50年前的納軍鞋歌謠———“納呀、納呀、納軍鞋,楊貴、楊貴、好區長,鞋壯、路長、打勝仗,保衛咱解放區好時光……”可見,年輕的楊貴在老區人民心中的分量。
建國初,楊貴擔任林縣縣委書記。他不忍心林縣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後還受乾旱缺水的煎熬,組織縣委一班人深入民眾,調查研究,“摸大自然的脾氣”,決心帶領全縣人民“重新安排林縣河山”。1955年起相繼修建了抗日渠、天橋渠、英雄渠和3箇中型水庫,1960年動工興建紅旗渠。當時正值國內三年困難時期,國際反華勢力又卡我們的脖子,面對重重困難和來自上下兩個方面的反對、指責,楊貴和縣委堅信,修建紅旗渠符合林縣人民的根本利益,依靠民眾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夠建成。經過5年艱苦奮鬥,1965年建成了最艱險的總乾渠,1966年又建成了3條幹渠。對紅旗渠和林縣山區建設的成就,新華社、《人民日報》、《河南日報》等許多新聞媒體和記者都及時作了宣傳。周恩來、李先念、譚震林、陶鑄等中央領導也多次表揚楊貴和林縣縣委,《人民日報》曾兩次發社論稱讚“林縣縣委是全縣人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核心”。我作為新華社領導成員,曾參與組織、編髮過這些報導,對楊貴和紅旗渠是由衷敬佩的。
我第一次採訪楊貴與紅旗渠是在1966年春。之前,1965年12月我和馮健到鄭州為召開國內分社工作會議調研,就打算到林縣採訪報導紅旗渠。只因為周原說到焦裕祿和豫東災區的情況,就先去了蘭考。1966年2月,我們采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發表後,在林縣長期深入基層的新華社老記者華山看後很激動,要我一定到林縣去一趟,寫寫林縣縣委書記楊貴和那些修建紅旗渠的英雄們。華山與我一起在延安“魯藝”學習,在東北解放戰場並肩戰鬥,幾十年情同手足。1965年,華山寫的反映紅旗渠建設的《劈山太行側》報告文學,已引起我很大興致。
3月,我又去蘭考寫了篇《再訪蘭考》,4月便趕往林縣。華山一見我,非常高興,領著我跑遍了紅旗渠的整個工程,一起採訪了楊貴、馬有金等縣委領導和紅旗渠特等勞模路銀、任羊成、常根虎、王師存、李改雲等。記得楊貴對我說:“我們是為了人民修渠,依靠人民修渠,所以才敢想敢幹,又實事求是,靠的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我說,“你這三句話就是建設紅旗渠實踐形成的紅旗渠精神。”採訪中許多勞模和幹部民眾都說:俺楊書記就像你寫的焦裕祿,一心為俺林縣人謀幸福。紅旗渠是一渠水,一渠糧,一渠電,一渠社會主義的蜜,是俺林縣人民的生命水、幸福源……遺憾的是,正當我們準備深入采寫楊貴與紅旗渠時,國內形勢突然變化,我不得不匆匆趕回北京,接著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我們宣傳楊貴與紅旗渠的計畫也不得不被迫中止。這件事無論對我還是華山,心靈上一直是個難平的創傷。
“文化大革命”中,楊貴被打成“走資派”撤職罷官,長期遭受批鬥毒打。林縣民眾暗中保護他,給他兜里塞雞蛋,往他懷裡揣烙餅,把他從造反派的囹圄中搶出來送到山西李順達勞模家,後又輾轉來到北京,躲在新華社記者胡敏如、方徨和程競明、李後家裡。不久,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幾位記者聯名寫信給周總理反映楊貴與紅旗渠的情況,周總理指示河南把楊貴保護起來。我當時自身難保,但也為我們的記者仗義執言暗自欣慰。這樣,楊貴到1968年才被“三結合”,得以出來工作,繼續組織紅旗渠支渠配套工程。
1969年冬,我第二次到林縣去。那時,紅旗渠支渠配套工程已全部竣工,楊貴剛被外調,可省里軍管負責人卻在林縣組織批楊貴、肅流毒,說“楊貴穿新鞋,走老路”,“紅旗渠是唯生產力論的活標本”。我到離縣城不遠的胡家莊看望華山,他住在兩間石砌的小屋裡,生著煤火爐,吃飯自己做,生活很清苦。華山本來就有肝病,說到有人批楊貴和紅旗渠,氣得滿臉漲紅,說“上面有人搗鬼”。我勸他少動怒,或者回鄭州或北京治一段病,他說,“和老百姓在一起,我才活得痛快!”這樣,我想再次采寫楊貴和紅旗渠的願望又一次落空。
1972年10月,康克清同志到林縣參觀紅旗渠。華山聞訊找康大姐反映情況並寫了一封長信,用大量事實揭露了造反派在河南軍管負責人支持下誣衊紅旗渠、迫害楊貴和大批幹部勞模的倒行逆施。康大姐看後覺得問題嚴重,及時把華山的信送給國務院領導傳閱。周總理看後當即要河南省委常委、省軍區黨委常委和楊貴同志來京匯報批林整風。會上,周總理拉著楊貴的手質問那個負責人,你為什麼反紅旗渠?為什麼整楊貴同志?在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制止了造反派在林縣的倒行逆施並解放了楊貴同志。黨的十大楊貴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後,周總理又提名楊貴到公安部擔當重任,處理複雜局面。
那是一段特殊時期,各種矛盾錯綜複雜。但楊貴同志沒有辜負總理、先念、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託。在那段歲月里,我和楊貴以及到水電部工作的鄭永和同志相互勉勵,兢兢業業。不想一段時間後,一些人卻和林縣“文革”中的造反派聯合起來,藉機否定楊貴與紅旗渠,致使一大批修建紅旗渠的勞動模範和幹部民眾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儘管1979年中央已調楊貴到五機部工作,1982年又任國務院“三西辦”副主任,但在林縣一提紅旗渠,就被指責為“楊貴流毒”。然而,林縣人民對楊貴與紅旗渠的感情是隔不斷的。90年代初楊貴兩次回林縣,廣大幹部民眾潮湧般撲向楊貴,場面非常感人。時任河南省委領導的李長春同志感慨說:我們每一個領導幹部都要像楊貴同志那樣,保持與人民民眾的血肉聯繫;離開崗位多年還依然受民眾擁護和愛戴。新華社記者武成德根據現場採訪寫了篇《楊貴同志回林縣受到民眾歡迎》的內參稿,在領導幹部中引起了很大反響。
1993年,河南省委作出了在全省學習林縣人民創業精神的決定。國務委員陳俊生又專程到林縣考察並向中央寫報告,江澤民、李鵬、溫家寶等中央領導都作了重要批示。那年初冬,我和馮健、周原重訪河南,原計畫在豫西、豫中採訪後再到林縣,沒想到由於大雪封山,把我們困在了安陽。任羊成等幾位紅旗渠勞模得知後,特地趕來安陽看望我們。我左手拉著任羊成,右手拉著王師存,問馬有金、路銀、常根虎等其他勞模的情況。當年的鐵姑娘隊長郭秋英說:他們已含冤去世了,俺仨也是替他們來給您說說心裡話……說著說著,勞模們不禁失聲啜泣,我和其他在場的人也止不住熱淚盈眶。我一邊盡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邊勸慰他們:以前不愉快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紅旗渠是咱中國人的驕傲,更是林縣人民的驕傲。你們是紅旗渠的功臣,人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這次難忘的相見後,我寫了篇《兩張閃光的照片》,追記了我和任羊成等紅旗渠勞模幾次相見的情況,收在了《十個共產黨員》一書中。不想,王師存看到我的書不久就離開了人世。
1998年深秋,我和楊貴一起重訪紅旗渠。當任羊成和郭秋英在青年洞口對我說,當年楊貴書記和民眾一起同甘共苦修渠,比現在正在播出的電視劇《紅旗渠故事》更艱苦、更生動時,我一手拉住楊貴,一手拉住任羊成動情地說:“正是有了楊貴這樣的縣委領導,有了任羊成為代表的修渠勞模和電視劇里‘劉技術’那樣的工程技術人員,才創造了紅旗渠這樣的人間奇蹟。江澤民同志前年在這裡已經說過,‘不要忘記洞中歲月,不要忘記修渠的人!’”
回到北京後,我和許多了解楊貴和紅旗渠的老同志都感到,江澤民同志強調的“不要忘記修渠的人”並未完全落實,曾兩次向中央領導和河南省委寫信反映楊貴同志以及紅旗渠勞模的情況。既然在新時期還要大力弘揚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幹、實事求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紅旗渠精神,就應該讓楊貴和所有修渠有功的人揚眉吐氣!
2002年6月,林州市新一屆領導班子特地邀請我和楊貴前往參加新落成的紅旗渠紀念館開館儀式。河南省委副書記王全書代表省委講話說:紅旗渠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古有都江堰,今有紅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楊貴。當年,紅旗渠的策劃者、建設者之所以決心修建這樣一條太行山上的人造天河,就是為了發展生產力,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幾十年後,紅旗渠精神之所以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就在於紅旗渠精神與“三個代表”是完全一致的……看到任羊成、李改雲、郭秋英等紅旗渠勞模和所有到會的人都熱烈鼓掌,我和楊貴會心地笑了。
那天下午,我和楊貴住到了遠離縣城的石板岩山區,還一塊上山看了家鄉人為活在福建人民心中的縣委書記———谷文昌修建的“文昌閣”。不想,許多勞模、幹部和民眾還是冒雨趕來看望楊貴。走了一撥,又來一撥,等候的人排起了隊。有的就是來見個面,握握手,有的乾脆帶著照相機來合個影,還有的怕我們著涼帶來了衣服,甚至山西平順、壺關兩縣的幹部民眾也聞訊趕來了。傍晚,離我們住處五六里的陳改蓮非要拉楊貴和我到她家吃飯,說楊貴“文化革命”挨斗在她家沒吃好飯,幾十年來她一直心不安。這一說,我和楊貴只好去了。吃著山韭菜包的素餃子,喝著炒米雜麵湯,不禁回想起三年前我們從青年洞下來路過任村桑耳莊,許多民眾給楊貴捧來柿子、核桃、山楂、板栗硬往我們兜里塞。林縣人民對楊貴同志的那種感情,令我十分感動。
現在,《楊貴與紅旗渠》一書經過作者幾年收集材料和辛勤寫作,就要出版了。儘管書中的楊貴還不夠鮮活,有些話沒能講透,一些章節詳略欠當,分寸的把握也還值得商榷,但作者確實收集了大量素材,傾注了自己的心血,且能夠秉筆直書,客觀真實,感情質樸,語言流暢,還楊貴與紅旗渠本來面目,實屬難能可貴。至於我這篇序言對楊貴與紅旗渠的敘說,與人民民眾心目中的楊貴與紅旗渠相比,多一句,少一句,深一點,淺一點,又有何妨呢?
本文是穆青同志為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楊貴與紅旗渠》一書所作序言。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圖片說明:195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在新鄉火車站接見中共林縣縣委第一書記楊貴。楊貴向毛澤東匯報了林縣水利建設情況與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