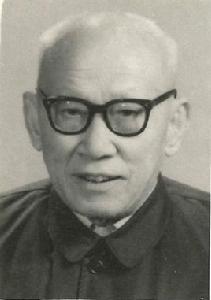人物簡介
 1939年的梁若塵
1939年的梁若塵梁若塵(1903—1990),名公溥,又名工甫,廣東省豐順砂田南溪村黃崗坪人。民國7年(1918年)就讀於豐順縣立一中。
時值“五四”運動興起,進步學生成立學聯會,聲援北京學生的正義行動。梁若塵積極參加學聯會組織的宣傳查貨隊、巡迴演講團,到附近圩鎮向民眾宣傳“五四”運動,呼籲全縣人民行動起來,抵制和查禁日貨,喚起民眾,奮起救國。
民國14年(1925年),梁若塵從事在中共領導下的新聞工作,先後擔任汕頭《潮商公報》、《嶺東日日新聞》、《紅旗報》和潮梅通訊社、汕頭國民通訊社等的記者、總編輯、社長、經理等職。翌年,梁若塵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出任黃埔軍校《黃埔潮》主編。
民國16年(1927),“四·一二”政變後,白色恐怖遍及全省各地,梁若塵回豐順活動。是年9月,南昌起義軍來潮梅地區,中共潮梅特委負責人郭瘦真派遣梁若塵趕往八鄉山組織武裝隊伍,迎接起義軍,當他與隱蔽在湯坑的潮梅特委宣傳部部長丁願接頭研究後,準備帶領武裝進山之際,得知國民黨軍隊兩個團在湯坑集結。梁若塵又火速趕到汕頭向起義軍報告。
起義軍在湯坑戰役失利後,他經香港去廣州參加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他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後南渡東南亞,輾轉到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從事教育和新聞事業。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梁若塵以《南洋商報》記者身份回國,赴華東、華南等地采寫抗戰新聞。1941年後,他在韶關創辦《時報》、《新報》、《明星報》,任總編輯、社長。後報紙遭國民黨當局查封,梁若塵被捕入獄,鏇得組織營救方才出獄。
民國34年(1945年)7月,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尹林平指示梁若塵,在廣州創辦《晨報》,不久又被查封。翌年,他赴香港,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廣九支部主任委員。先後任香港《願望周刊》編輯、新聞學院教務長、達德學院副教授、中國新聞通訊社社長等職。
民國38年(1949)9月,梁若塵參加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教導團。廣州解放後,他歷任廣州軍管會文教接管處新聞組長,廣州人民印刷廠總廠長,《聯合報》管委會副主委兼經理,《廣州日報》經理,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廣州市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名譽館長等職。
1957年,在反右派的鬥爭中,梁若塵受到錯誤處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衝擊、迫害。在嚴峻的日子裡,他胸懷坦白,立場堅定,顧全大局。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梁若塵先後出任廣州市第七、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民盟中央候補委員、委員、參議委員,民盟廣東省委副主委、常委、顧問,民盟廣州市委副主委、主委、名譽主委等職。他積極參政、議政,聯絡海內外各界人士開展統戰工作,組織編寫文史資料。
1990年8月19日,梁若塵在廣州病逝,終年87歲。臨終前,他囑咐家屬將其稿費、存款捐給家鄉發展教育事業;8月31日在廣州殯儀館舉行追悼會,由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市政協主席張漢青主持,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賴竹岩致悼詞。
人物生平
“五·四”運動帶來的覺醒
梁若塵原名梁公溥,廣東豐順人,生於1903年。他在豐順中學念書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全國展開。當時豐順縣城也經常吹響“國危矣,國亡矣,大家奮起來救國!”的戰鬥號角,他也曾多次參加到遊行宣傳隊伍中去。他是豐順中學學生會的骨幹,擔任學生會出版牆報的負責人。他常用梁元、梁昂的筆名在牆報上發表評論形勢的短文,由此培養起對新聞工作的興趣,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還參加抵制日貨,打擊投機商販的活動;還當過推廣國語的隊員,聯合組織小隊伍到縣內各墟鎮推廣國語。
1922年他受聘於汕頭的一家報紙《群聲日報》為特約通訊員。這是他投身於新聞事業的開始,其時年僅19歲。他寫的通訊稿多是揭露貪官污吏的苛政和惡勢力欺壓民眾的社會現實,因而引起豐順縣當權者的反感和暗中追查。
1923年梁在豐順縣中學畢業後,留校任數學教師。學校的監學(即總務)吳蕾秋嫉忌他的才幹,因此,他被調到縣督學局工作。梁當了半年閒散了督察,深為不滿,加上反動勢力的逼迫,離開了豐順縣,來到汕頭。
當時豐順縣縣長杜錫珊之兄杜寶珊在汕頭開辦了《潮商公報》,招收辦報人員。梁得到國民黨員陳永年的介紹,當了《潮商公報》的外勤記者。
國民革命軍第一次東征進入潮汕時,梁積極采寫有關革命的新聞報導。反對國共合作的杜寶珊對此有所不滿,認為梁的思想及行動對他辦報的政治目的不利,就藉故調他任“獨學社”的駐梅州特派記者。“獨學社”實則是杜一幫人搞的半公開文化組織,用來反對國共合作的宣傳工具。梁識穿杜的詭計,憤然離開《潮商公報》。
在大革命的風雨中成長
在一位同行黃錫光的介紹下,梁結識了中國共產黨潮汕地區領導人賴先聲同志,並得到他的信任和鼓勵,進入共產黨領導的潮梅通訊社任記者。潮梅通訊社是1925年11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徵到汕頭時,中國共產黨通過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宣傳部,由廣州派出年輕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黃光明、趙慕儒、詹展育等人到汕頭市創辦的,是當時潮梅地區第一個公開活動的革命通訊社。
當時的汕頭市,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暗中鬥爭激烈,何應欽以國民革命第一軍軍長名義兼潮梅綏靖委員,周恩來以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名義兼潮梅行政專員。《嶺東民國日報》是國民革命新政權建立後出版發行的進步報紙。而以何應欽為首的右派勢力,則以汕頭“新國民通訊社”為活動的組織。其頭頭張凌雲,與國民黨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有勾搭,得到何應欽及蔣介石的支持。因此,張凌雲及其一手把持的“新國民通訊社”便成為何應欽和其他反動勢力的代言人。
在一次反英運動的民眾會上,張凌雲以“新國民通訊社”頭目的身份登台講話,肆無忌憚地用指桑罵槐的手法,公開攻擊革命的、進步的地方政權,惡毒辱罵以周恩來同志為領導的地方官員。當時與會民眾大嘩,揮拳捋袖,指斥張的誣衊,張的發言未完即被民眾哄下台去。梁若塵將此事如實生動地寫成新聞稿,由潮梅通訊社發給各報。第二天,《嶺東民國日報》全文刊登了,其他報紙則刪節發表。《嶺東民國日報》直屬於中國國民黨汕頭特別委員會,社長李春濤和主要的記者、編輯都是中共黨員。何應欽見報後,大為惱火。於是用中國國民黨特別委員會領導人名義,命令該會秘書長廖伯鴻(中共黨員)立刻召開委員會討論,並指名要潮梅通訊社派人列席。潮梅通訊社正在研究對策時,一位姓蕭的同志(中共黨員)轉達彭湃同志的指示,要梁若塵以潮通社身份列席會議,並鼓勵潮通社堅決和他們作鬥爭。
在黨的鼓勵和支持下,梁若塵充滿信心地參加了這次審判式的會議。會議一開始,身穿戎裝的何應欽的代表,高傲而惱怒地坐在主席台上,兇狠地講了幾句恐嚇威脅的話之後,便追問潮梅通訊社的人到了沒有,追問那條“破壞革命合作”的新聞是誰寫的?梁若塵理直氣壯地站起來回答:“是我寫的。”跟著說明這條新聞完全是照錄張凌雲的講話原文和會場上民眾對張的態度如實地寫出來的。那代表又追問你是什麼地方人?懂不懂潮州話(張的講話是用潮州話演講的)?梁即以潮州方言應答,有力地證明他所寫的張凌雲的話,文字是不會弄錯的。由於梁若塵義正詞嚴,敢於鬥爭,使那次會議沒有什麼結果,那位何應欽代表也無可奈何。但到第二天,潮梅通訊社即接到通知,嚴令即日起停止發稿,宣布關閉潮通社。這場鬥爭,梁鋒芒初露,也鍛鍊了他的勇敢意志和策略思想。 中共潮汕地委宣傳部負責指派汕頭國民外交後援會秘書方達史(中共黨員)協助梁若塵籌辦新的通訊社。經過一段時間分頭活動,爭取了汕頭商民協會、汕頭總商會等社團中的進步人士的資助,於1926年初夏,用汕頭國民外交後援會的名義,成立了汕頭國民通訊社,由梁若塵任社長,參加編輯、採訪工作的有朱寶岱、楊拱垣(二人均為中共黨員)和馬赤人等。
國民通訊社發稿後,引起了國民黨中右派勢力的嫉恨,新國民社的張凌雲、陳述經等千方百計進行破壞,一方面通過他們把持的《新國民日報》寫文章冷嘲熱諷,另一方面挑撥離間,要各報拒絕採用國民通訊社的新聞稿。但他們的陰謀並沒有得逞,隨著革命潮流的不斷高漲,國民通訊社也發展壯大起來,活躍在汕頭地區的新聞戰線上。他們還經常把新聞通訊稿發給廣州的《民國日報》、《國民新聞》和《工人之路》等報社。
國民通訊社順利發展,敵對分子是不會甘心的。一天下午,何應欽的得力幹將何玉書來到國民通訊社,剛坐下便嘻皮笑臉地對梁若塵說:“給你帶來一個好訊息,何總指揮要你以隨軍記者的身份出發,做東路北伐軍的宣傳工作。”梁若塵敏銳地意識到,事情並不那么簡單,裡面肯定會蘊藏著陰謀詭計。於是他冷淡地回答:“讓我考慮一下再答覆你吧!”梁當即向中共地委秘密辦事處負責同志作了匯報,並說出了自己對此事的看法,認為他們的意圖是為了釜底抽薪,搞垮國民通訊社。匯報時,彭湃同志在場,指示梁若塵留在通訊社繼續工作,另派徐琛、余哲貞夫婦和鄭棟材4人(均系共產黨員)隨軍出發。他們進福建後,留在閩西漳州、福州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一天(即1927年4月11日),徐琛夫婦被反動派逮捕,不久被殺害;鄭棟材僥倖逃出。
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國民革命陣營起了激烈的分化,革命與反動勢力的鬥爭公開化、白赤化。廣州如是,潮汕一帶也如是。代表蔣介石、何應欽的實力派,在蔣介石炮製的所謂整理黨務案後,於同年秋間,把一直由國民黨左派人士掌握的《嶺東民國日報》的領導權奪去,交給投機分子方乃斌等主持,而原社長李春濤、編輯丁願、李春蕃(均為共產黨員)都被排擠出報館。轉眼間,這張擁護國共合作的報紙,變成了反動勢力(包括“民團”、“保衛團”)利益的代表。迫於形勢,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要創辦一張新的報紙,指派梁若塵和蕭師孟負責籌備,於1927年春節前,對開的《嶺東日日新聞》正式出版了。梁若塵為該報的發行人兼經理(仍兼汕頭國民通訊社社長),編輯有丁願、李春蕃等。該報的經費來源,是通過進步民眾團體分頭徵集。從一創刊,報紙每日銷數便成為汕頭地區各報之冠。《嶺東日日新聞》出版了約3個月,1927年4月15日清晨,連同汕頭國民通訊社一起,被反動軍警包圍搗毀了報館。當日臨時代理報務的巫丙熹同志(汕頭書店經理)被捕。在事件發生前兩天,梁若塵因奉地委之命,負有臨時通訊任務,由汕乘外國郵船赴香港轉廣州,要向廣州區委遞交秘密檔案,故未被捕殺。但當時香港《華字日報》仍有“汕頭赤黨分子楊石魂、梁工甫(即梁若塵)被捕的新聞誤傳。
在“四·一二”事件後的第二天,梁若塵得到在船上的共產黨人的掩護和幫助,以水手的身份帶著檔案赴廣州特約聯絡點——市公安局,與鄭春榮見面。鄭與梁是高等國小時的同學,秘密負責潮梅地區黨組織的聯絡人。梁若塵從鄭那裡得知中共廣東區委已疏散,並留下指示:凡潮梅地區來的檔案,均由送檔案的人自行銷毀,各自回原地區堅持工作,開展武裝鬥爭。梁於4月19日化裝改名乘日本船潛返汕頭,然後設法與黨組織取得聯繫,進行隱蔽的活動。
“四·一五”潮汕反革命事變(即所謂清黨)中,國民通訊社被封閉,編輯朱寶岱、記者楊拱垣和一位通訊員被捕,押解到廣州,同年10月幸獲釋放。
“八·一”南昌起義軍在1927年9月下旬到達汕頭。革命委員會派藍裕業、羅伯良和梁若塵迅速籌備出版《紅旗報》。但是,9月29日晚,正當《紅旗報》創刊號即將開機印刷的時候,突然接到黨的保衛員的通知,市區主力部隊正在撤退,報紙出版工作立即停止,工作人員自行隱蔽,轉入地下。
同年11月間,梁若塵在廣州奉地下黨組織之命,到黃埔軍校擔任校報《黃埔潮》的主編。12月11日廣州起義的當天,梁若塵又奉組織命令緊急籌備出版《紅旗報》。與他一起接受任務的有丁願、董芝(女)、丁彥等。選定原七十二行商報為館址,同時運用該報原有編輯出版的各種設備,於12月12日趕緊編排創刊號。誰料,到了該日深夜又突然接到通知,必須緊急疏散,編排好的《紅旗報》創刊號,也隨著軍情的急變而放棄出版。這樣,梁若塵經手編輯的兩張《紅旗報》,都是已弄好了版樣,卻未能正式和讀者見面。梁若塵每談及此事時,都感到無限憤慨惋惜! 流徙南洋 堅持新聞工作
廣州起義失敗,大批革命同志流血犧牲了。按照黨的指示,非武裝人員自行掩蔽。梁若塵得到親友、同志的幫助,僥倖逃脫。幾天后,輾轉得到李濟深批發的一張委任狀,寫明派梁若塵往海外宣傳慰問華僑,因此得以通過檢查關卡,離開廣州,經香港往新加坡。
梁若塵於1927年12月,化名梁忠殊,由香港乘印度的客貨船“地刺華”號到了新加坡。在此之前的10月1日他曾被香港扣押過10天,然後解交給廣州市公安局收押,並宣布他永遠不準重到香港的。此番他偽裝奔喪,混過碼頭印籍警員,僥倖得到順利登岸。停留在香港兩天,得到一家旅店老闆的幫助買到船票的。那老闆姓林,他的侄子是共產黨員,曾與梁在汕頭共事的。
從1928年至1937年,梁若塵在東南亞居留和工作了10年,先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流轉居留,從事新聞、文化工作,還穿行過菲律賓、寮國、高棉和越南。當年這些東南亞國家還在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除泰國名義上是獨立王國)。據梁自己的回憶。這10年間他創辦或參與過工作的報紙、雜誌有:檳榔嶼的《南洋時報》、《檳榔嶼小報》、《中南晨報》、《現代日報》和《南洋導報》(半月刊);在新加坡的《南洋商報》、《愛國周刊》。這期間,他還給上海《東方雜誌》寫專題通訊,介紹印尼、緬甸等民族獨立鬥爭等文章。據所知,他當年用的筆名有“楚囚”、“力行”、“加衛”、“余學步”、“疾風”、“勁草”、“百孝”、“忠殊”等不下十個,其中“楚囚”用得較多。“若塵”原來也是筆名,後來作為正名使用了。此外,他還在馬來亞的怡保鎮得到一位熱心愛國事業的巨商後裔姚先生出資開辦一家書店,取名“朋友書店”。在文化比較後進的地區,傳播進步書刊,還別出心裁開設一個報刊租借部,讀者可親身到書店租借,或由書店派人送書刊上門。
梁若塵在那十年中,一再流徙各地,這是非主觀所願,主要出於迴避殖民地統治者和各種反動勢力的迫害。1932年他離開親自參加創辦的《中南晨報》報社,而接任總編輯工作的××,是曾在莫斯科混過日子的托派分子,在抗日戰爭的中期充當蔣介石派駐廣東後方的特務武裝別動軍的政治指導員。
1931年何香凝女士到馬來亞各鎮動員愛國華僑捐款籌辦社會公益事業,梁若塵等多次將何大姐的活動、談話在報上發表,不料空穴來風,竟然有些自命為反蔣的勇士者,攻擊梁等人為“改組派”。對此,梁寫了一篇《改組派進棺材》的社論,在《中國晨報》刊登,讓讀者分辨是非黑白,使那些散播謠言者自動緘口。
梁若塵於1935年應陳嘉庚女婿李天游的邀請,並得到《現代日報》負責人莊明理的支持,辭去檳榔嶼《現代日報》職,到新加坡任《南洋商報》的編輯主任。
該報是陳嘉庚公司獨資經營的。梁到《南洋商報》之初,很想了解陳老先生對祖國形勢的看法。當時日本侵略軍一步步進迫,蔣介石卻胡扯什麼“攘外必先安內”,瘋狂向紅軍各根據地進攻。雖然《商報》一貫是站在愛國親僑的立場上,但情況複雜,報社對國內動態的報導如何掌握其尺度,還得進一步弄清楚。有一天報社秘書長李天游轉達了陳老的答覆:“除不許攻擊孫總理中山先生外,什麼話、什麼新聞都可講可發表。”梁若塵聽後頓覺心中有數,便與報社的編輯、經理兩部的進步同人,放開手腳處理業務,使報紙在讀者面前有耳目一新之感。抗日戰爭全面展開,梁若塵回國擔任該報戰地記者。不久胡愈之等進步文人加入並主持該報,使它成為一家有堅強戰鬥力的、聲譽甚高的中文報紙。可以說,該報與4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華商報》,成為兩盞相互輝映的愛國明燈,共同對團結東南亞華僑、港澳同胞,堅決擁護抗戰,反對賣國投降作出貢獻。
抗日戰爭中輾轉辦報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由於曾在綏遠、熱河與馮玉祥等聯合抵抗日本侵略軍而被蔣介石流放到歐、美的方振武將軍,從法國經新加坡回國。梁若塵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陪同方振武將軍在馬來半島各大城市向華僑宣傳抗戰救國。同年9月又以《南洋商報》特派記者名義陪同方將軍由香港入內地。他順道在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廣泛採訪軍、政和社會各界人士,然後把國內人民團結抗戰的所見所聞,寫成通訊,寄到新加坡和香港發表。最後他到了南京,拜訪八路軍駐京辦事處主任葉劍英同志,將海外及回到國內行經各地的見聞向葉反映。交談歷三小時。結束之際,葉對梁說,你離開祖國足有十個年頭,今次回來需要加強對政治形勢和黨的基本政策的學習。葉隨後指點他到武漢時拜訪董必武同志,請他幫助。與此同時,梁還訪問了葉挺同志,聽取關於組織抗日新四軍的介紹,梁在戰火向南京進迫時,寫了一篇《在首都訪兩葉》通訊,寄給《南洋商報》發表,讓讀者更加深刻認識到:抗日戰爭已到了嚴峻時刻,而中國共產黨堅決團結軍民,保家衛國。
一個星期之後,梁若塵在南京面臨陷落時隨同疏散官民重到武漢,得到董必武同志接見,梁向董老請求到延安學習。董老熱情地回答:你是海外回國採訪戰地新聞的,還年輕體壯,加上通曉廣東地方方言(廣州、客家、潮州各種語言),你回到廣州工作不是很方便嗎?!至於加強學習,只要立場堅定,接近民眾,勤奮工作就是最好的學習。於是梁又到衡陽小住十天,靜心閱讀沿途得到的報紙、雜誌和各種資料,特別是有關抗戰論文進行認真學習。 戰爭形勢日緊,後方交通阻塞,行動不便。梁離開南京時,幸得邵力子的幫助,領到國民黨軍政部簽發的“戰地記者證”,很順利地回到廣州。日本空軍轟炸廣州石室教堂時,梁冒著硝煙拍攝了幾幅石室被炸的現場照片,交給當時的《民族日報》製版刊登,該報因此聘梁為特約記者。梁回國幾個月後便與國內報紙取得職務性掛鈎。
梁若塵在廣州一面與同業加強聯繫,采寫各種新聞通訊,寄到海外發表,同時經常與廣州新聞工作者交流宣傳抗日救國的經驗,結識了李子誦、葉廣良等老報人。
1938年春,余漢謀派丁培綸、丁培慈兩兄弟以廣東綏靖公署和廣東政府的名義前往東南亞各地,向華僑募捐,用以購買飛機參加抗戰。丁培慈(又名丁願)在大革命時期曾與梁若塵一起從事新聞工作,這次特意邀請梁一同前往。梁爭取到《民族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協同丁氏兄弟到東南亞各地宣傳“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抗戰思想。
他們穿行過菲、新、馬、泰、老、柬和越南等地,為期四個月,行程超萬里。返回廣州後,由丁培慈寫成小冊子,紀述華僑擁護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反對中途屈辱妥協,雖然當時戰況緊張,但他們仍然趕印出來,向市民散發。
1938年初冬,廣州淪陷了,梁若塵從韶關經清遠轉進廣東抗日軍隊新建立的指揮基地翁源,隨後應余漢謀的高參黃范一的邀約,繞道到香港,協助籌備余漢謀出資創辦的香港《時事晚報》。梁沒有在報社內掛名。晚報的主要人員中有4名分別是從日、德、英、俄歸來的留學生,其中任主筆的是國際問題專家喬冠華(筆名喬木)和朝鮮義士李本植,負責採訪部的是鍾道生。這家晚報宣傳抗日救國思想,幫助愛國人民樹立抗日必勝的信心。晚報曾對華中及華南部分地區戰局的失利,一再作側面分析,號召海外華僑以物質支援英勇抗戰的華北、華中的敵後游擊隊。晚報的言論招惹國民黨右派的忌恨和破壞,出版不到一年,便被勒令停辦。
梁若塵為了配合晚報的發展,曾組織一個向海外中文報紙發布新聞、評論的時事通訊社。因通訊社沒有向香港政府登記註冊,至此也只好停止發稿。梁並沒有因此偷閒,他一面給新加坡、曼谷的幾家中文報寫通訊,一面撰寫有關南洋各地僑情的文章,用幾個筆名(包括梁若塵一名)給《世界知識》等報刊發表,因此他又被人們譽為南洋問題專家。
1939年,在中國青年學會的支持下,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成立,該學院的領導班子群賢薈萃,著名的老報人郭步陶、金仲華、劉思慕、葉啟芳等先後擔任過院長。梁若塵也曾擔任該院的教務長,並講授新聞採訪學課,他曾發動第一屆男女學生共8人組成戰地新聞工作組,奔赴廣東抗日前線及後方采寫新聞,同時參加軍隊政治部工作。中國新聞學院的學員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曾為革命作出不少貢獻。1948年該院老學員在廣州成立校友會時,梁被推舉為會長。在中國青年記者會香港分會委託和支持下,進步的“中國新聞通訊社”在香港成立,作為中國新聞學院的學生實習場所,同時向香港和海外中文報紙傳送新聞稿和專題評論。梁被指定擔任社長,葉廣良任主編。
梁若塵在港一年多期間,還多次應邀到“華員協會”、“電車工會”等團體作形勢報告,激勵聽眾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各盡其力為抗日救國作出貢獻。
為民主與解放而鬥爭
1940年冬,梁若塵決定由香港回廣東臨時軍政中心的韶關。動身之前,在一家咖啡店與廖承志、夏衍、喬冠華等同志飲茶,商討回內地的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前幾天,他回到了韶關,事件發生的訊息已傳到他耳邊了。而當地的報紙初則隻字不提,後則反而加罪於新四軍,顯然不會作如實報導了。梁於是找到了重慶國民黨報《中央日報》駐廣東的記者汪鏗(汪是中國青年記者學會會員),動之以情,激發他對國民黨不講真話、隱瞞事實真相的義憤,商定共同創辦一家“講公道話”的報紙。汪的夫人陳翼還推薦了鄔維梓參加。他們僅花了十來天時間,就辦妥了註冊手續,將一份小型四開八版隔日出版的《時報》送與讀者見面。當時,正值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惡浪中,廣東省國民黨的黨、政當局就把這份說公道話的報紙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出版至同年11月,因《時報》如實報導香港被日軍占領的訊息。當年廣東省長李漢魂授意省保全司令部以“泄露軍事秘密”為藉口,封閉報社,同時誘捕梁若塵、汪鏗兩人,收押於第十二集團軍軍法處(芙蓉山廟堂)。
《時報》原工作人員吳華胥、鄔維梓等不避風險,在擁護國共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的知名人士張良修、王鼎新、陳卓凡等支持下,取得國民黨省黨部宣傳部青年部長發給《新報》的出版執照,在梁、汪出獄之前出版了,仍由梁若塵任社長。新出版的《新報》本著《時報》宗旨“講公道話”,反對向日本侵略者妥協投降。出版約3個月,反動的當權者藉口《新報》的出版執照重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不予批准,指示新聞檢查處查封《新報》。 “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弦歌。”1942年7月間,梁若塵、吳華胥、鄔維梓、林玲(筆者曾用名)、陳乃桐和鍾健等恢復出版由鍾健出名註冊的《明星報》,經費由一位愛國青年商人黃季川主動資助。但是出版不到半年,國民黨反動權勢者,又藉口《明星報》曾停版超過一個月,出版登記證已失效,不能繼續出版。從創辦《時報》起,到《明星報》停辦不滿兩年時間,辦報班子基本沒有改變,出版宗旨也堅定貫徹,但“三出娘胎”,歷盡艱難,然而梁仍沒放棄他的追求。1943年6月他們又將一份《晨報》送與韶關的讀者。這份報紙得到更多讀者的支持,影響迅速擴大,經濟上也能獨立。直到1945年1月下旬,韶關淪陷的前一天早上,才忍痛停版。
韶關淪陷前,梁若塵等早有應變準備。淪陷之日,全體員工迅速轉移到陽山縣,支援《北江日報》擴大出版。這家報紙是地方堅持抗戰人士倡辦的。梁若塵和趙元浩則通過廣州中共地下組織同志介紹轉到東江抗日根據地,找到中共廣東臨時省委。1945年7月接受黨的指示,梁、趙和鄔維梓進入廣州準備迎接抗日戰爭勝利即將來到,並籌備出版《廣州晨報》。1945年8月18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晨報》(四開版)就和廣州市民見面了。8月26日擴大為對開的《廣州晨報》,跟著又增出對開版晚報。可是同年11月底被國民黨反動軍、政實力派封閉。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軍、政兩方勢力都想對該報加以利用和控制,向梁若塵施以種種誘餌,梁等不為所動;他們見軟的辦法不行,就施用橫暴手段,勒令停版。當時得到輿論界的支持和“國大代表”劉侯武、張良修、蕭佛成等三人為之質詢,廣州行營一些地下共產黨員從中幫助,曾得過暫時復版,最後又於11個月底則派軍隊封鎖報社大門,並強令停止工作;同時密令逮捕梁若塵和趙元浩等三人,幸而得到在張發奎司令部里的“共產黨特支”秘密通知,梁、趙兩人才能及時轉往香港,免予被捕。
梁若塵1945年12月重到香港,從事各種愛國民主活動和文化出版工作,創辦過一家沒有向香港政府註冊的新聞通訊社,向海外中文報紙供稿,同時參加創辦《願望》周刊,向海外和內地發行。當時為這周刊寫稿的有郭沫若等同志。
為新中國的新聞事業服務
1949年9月,梁若塵應召進入內地,預定到贛南迎接南下大軍。10月21日回到廣州,參加軍管會接管和處理原在廣州的報紙、通訊社、廣播電台等工作,接著擔任新創立的大型新華印刷廠的總廠廠長。1950年在廣州參加出版《聯合報》。該報是解放後第一家由各民主黨派聯合創辦的報紙。他被推舉為報務委員會副主任兼經理,李章達任報務委員會主任,蕭雋英任副主任。1952年《聯合報》主動停版後,廣州市黨委辦的《廣州日報》出版,梁若塵任經理。
1955年梁若塵調任廣州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長,由這時起,他與持續三十多年的報人生活告別了。雖然報人生活並不輕鬆,但長期來與紙、筆、油墨結了緣,他還是依依不捨的;此後,他還擔任了廣州市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名譽館長等職。
1957年,在“反右派”的鬥爭中,梁若塵受到錯誤處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衝擊、迫害。在嚴峻的日子裡,他胸懷坦白,立場堅定,顧全大局。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梁若塵先後出任廣州市第七、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民盟中央候補委員、委員、參議委員,民盟廣東省委副主委、常委、顧問,民盟廣州市委副主委、主委、名譽主委等職。他積極參政、議政,聯絡海內外各界人士開展統戰工作,組織編寫文史資料。
1990年8月19日,梁若塵在廣州病逝,終年87歲。
臨終前,他囑咐家屬將其稿費、存款捐給家鄉發展教育事業。8月31日在廣州殯儀館舉行追悼會,由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市政協主席張漢青主持,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賴竹岩致悼詞。
人物評價
梁若塵由1919年辦學生牆報開始,到1955年改行文化工作為止的36年中,他經手創辦和參與工作過的報刊和通訊社共有26家,其中報紙18家,通訊社4家,雜誌4家,其經辦報刊通訊社之多,在新聞史上,這是一個很不平凡的業績。他的足跡遍及寒、溫、熱三個地帶;曾三次入獄,兩度臨捕逃脫,歷盡坎坷,實為國內外報界所少見。回顧他在那風雨如晦的歲月里,不論在國內白色恐怖中,還是在國外帝國主義的險惡的魔爪下,他總是盡智竭力開拓一個又一個對革命有利的新聞陣地,就象在霧靄蒼茫的淺灘逆流而上,留下一個個的腳印。這些腳印與中國各個時期的戰鬥歷程相聯繫著。
梁若塵同志待人坦誠熱情,善於與不同觀點的人交往,化阻力為助力;他對工作嚴肅認真,從創辦報社、通訊社,經營管理到采寫新聞、編輯發行,他都在行,可以稱得上是辦報的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