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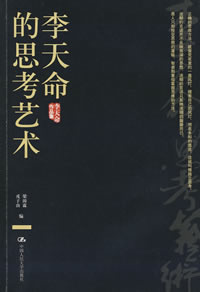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香港哲學鬼才李天命作品完整版首次完整版首次面市大陸,牟宗三、金庸、倪匡、張五常眾名流傾力推薦。
他的著作奇少,卻暢銷不衰。《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出版至今,單在香港就前後印了54次近10萬冊;《破惘》印了12次;新作《殺悶思維》於2006年7月出版後,四個月印了9個版次,創造了學術書的銷售奇蹟。
正確的思維方法,就像荒夜裡的一盞風燈。提著自己的風燈,照亮未知的旅途,這就叫做獨立思考。迷糊的言語並不反映高深的思想,迷糊的言語只反映迷糊的腦袋而已。愚人只知接受思想的灌輸,智者則重視掌握思維的方法。
內容簡介
這一是本怎樣的書?
這是一部浪蕩與沉思的作品。
它浪蕩在遊戲與學術之間,不做偽學問,也不做死學問。
它沉思生命的意義、思維的旨趣,守衛邏輯,反擊荒謬。
這本書有什麼主要內容?
這本書的主題是思維方法,重點在思考藝術。
它以幽默而無懈可擊的思路講授思維方法,演示思考藝術。
它以非哲學的形式講述哲理,拋棄正襟危坐,換上機鋒妙談。
這本書展現了怎樣的心靈?
這本書推重騎士精神,提出愛情宗教。
它以堅定不移的精神思索天人之際,探索邏輯的起點與哲學的終點。
它以矢志不渝的情感尋找人世間安身立命的基石,求得人生的圓滿。
一語總括:
這是一部讓人嘆為觀止的哲學著作,一手持劍,一手拈花,刺破詭辯,撫觸溫柔;不在公式上繞圈,不在術語上矇混,撇開無謂的枝節,直探思考的真義與人生的真諦。
作者簡介
李天命,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他講授數理邏輯,專精思考方法與天人之學,把高深玄奧的哲理講得如敘家常,通透易懂。
他幽默機敏,能言善辯,詞鋒犀利,常使人無處可藏而噤若寒蟬,人們稱他為“小李飛刀”。
他劍走偏鋒,其哲學思想與正統哲學大異其趣,不屑理會衛道者視之為出軌異端。
他的講座一票難求,座無虛席,聽眾每每擠滿演講廳的樓梯過道,不得其門而入者只能望門興嘆。
他惜墨如金,著作奇少,卻部部暢銷,且歷久不衰,屢創番港學術圖書再版及銷售紀錄。
他的讀者三教九流,既有社會名人、學者專家,又有販夫走卒,升斗市民,傳說甚至有職業殺手熟讀其書。
他是冷銳的思想家,又是溫柔的詩人;他的詩“天馬脫羈,飛仙遊戲”,清麗秀雅,風姿綽約。
他深居簡出,不露行跡,謝絕一切不必要的應酬和曝光,專事思考,冷眼觀世,透著幾許神秘。
目錄
代序
編者語
導引篇
浪蕩與沉思——李天命先生談經歷和思想
一、從老人精到學生會會長
二、搗蛋反叛與主動讀書
三、留校開新科,留學賭沙蟹
四、從邏輯到新詩,從飛刀打架到勃拉姆斯
五、反學術遊戲,向下接不向上爬
六、語理分析,角度形上學,禪
七、守則自決,明智假裝,反煩瑣主義
八、被踢出校的野蠻人
從騎士精神到愛情宗教——《浪蕩與沉思》(續)
九、寬鬆原則與大丈夫精神
十、浮淺時代與空谷之旅
十一、武質文化觀:悍烈精神暨玉碎原則
十二、基點哲學(1):事件實在論
十三、基點哲學(2):九一主義
十四、基點哲學(3):愛情宗教
與李天命博士談思考方法
一、表達能力的訓練
二、思考方法提要
三、獨立思考與個人理想
李天命博士論思考的關鍵
主題篇
思維方法與獨立思考——《思考與心魔》前奏
序
第Ⅰ部(本論):語理分析
一、思維利器:方法學第一環
二、意義與釐清
第Ⅱ部(餘論):語言與思想
一、破枷鎖論
二、破混糊論
三、思想虛妄之根
跋:從獨裁思想到獨立思考
思考與心魔
序
導論:語害批判
第Ⅰ類語害:語意曖昧
一、實例展示
二、術語迷彩
三、由虛浮至錯亂
第Ⅱ類語害:言辭空廢
一、重言句與信息內容
二、論空廢命題
第Ⅲ類語害:概念滑轉
一、概念混淆
二、概念扭曲
總結:論封閉系統
一、偽贗說明
二、真理使者的真理幻覺
思辯與宗教——《從血路之旅到天國之旅》前奏
引言:來龍去脈
第Ⅰ部:批評與批駁
一、不夠公平?
二、虛晃一招?
三、上帝與石頭
四、上帝超越邏輯?
五、信仰馬腳及其他
第Ⅱ部:詭辯與思辯
一、順手一刀破盲辯
二、思辯之道
從血路之旅到天國之旅
楔子:反詭辯系統
序幕:血路之旅的寓言
一、錯的故事
二、錯的教訓
第Ⅰ部:四盲
一、喻盲
二、諷盲
三、語理盲
四、邏輯盲
第Ⅱ部:三妄
一、標準妄
二、斷章妄
三、不相干妄
第Ⅲ部:五伎
一、東拉西扯之伎
二、無中生有之伎
三、魚目混珠之伎
四、訴諸詆詬之伎
五、退縮逃溜之伎
第Ⅳ部:窮途
一、尖弱愛仇敵
二、一泡
結幕:天國之旅的起點
思辯隨筆——《血路之旅到天國之旅》變奏
引言:思考方法與思辯範例
一、豪言壯語
二、謬誤與訛誤
三、辯論的關鍵
四、由全能到至能
結語:思維邏輯vs思維科學
附論:批判思考&創意思維
後記:耶、佛、道、心
(香港版)終定本·跋
參考篇
神不存在?!——哲學家李天命智斗神學家韓那
一、支持神存在的論證
二、撥開迷霧免遭誤導
三、倒下來的只是稻覃人
四、對準死穴一刀了結:“上帝”的概念曖昧可疑
五、信不信由你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
評李天命的《思辯與宗教》
向李天命道歉
為李天命未能一矢中的而感到意外
宗教與思辨——回應李天命博士的“思辯與宗教”
從《評李天命的(思辯與宗教)》一文說起
附錄
鋒銳才華與魔力魅力——從飛刀小子到哲學沉思者
一、思想鋒利,文採風流,浪蕩不羈
二、才氣縱橫:詩與文,思考與論辯
三、毀譽默然,無敵是最寂寞
編附:李天命詩數首
談李天命的思考方法
一、李天命與語理分析
二、從語理分析到語害批判
三、獨立思考:從方法到藝術
書摘
浪蕩與沉思——李天命先生談經歷和思想
一、從老人精到學生會會長
李先生,從大學時代開始,你即與哲學結下不解之緣。起初你是怎樣念起哲學來的?其間曾否考慮過轉系或就業的問題?
有的人從小就被哲學問題困擾,我屬於這一種人。大約五歲的時候,有一次,我獨自在街上“流浪”(那時的小孩,能走路的大都會得溜到街上玩,不像現在的小孩子,沒有大人陪伴就不準到街上去)。我一面“流浪”一面想:“我是誰?為什麼有我?為什麼有這個世界?”這樣邊走邊想,“流浪”到靈糧堂(嘉林邊道和太子道交界處的教堂)門外,忽有聲音仿佛自天上來:“天命!”抬頭一看,原來是父親找我回家吃晚飯。他問我一個人低著頭背著雙手在街頭踱步乾什麼,我說:“想問題。”然後告訴他我想些什麼問題。他一聽就哈哈大笑,回家之後把經過告訴媽媽哥哥們,他們聽了也大笑起來。那時我只覺得莫名其妙,不知有什麼好笑,只是傻兮兮地跟著一起笑。到長大了才明白:原來小孩子想那些問題,可算得是“老人精”(小老頭)。
第一次接觸到“正規哲學”,是在升上中學以後。在一個下雨天,我走進孟氏圖書館避雨(後來改名為孫逸仙圖書館)。窮極無聊,隨手找些書來消遣,偶然拿到一本中譯的《哲學概論》,便隨意翻閱。雖讀得似懂非懂,但有個印象:那些常困擾我的問題大概就屬於哲學。
到了中學畢業,懵懵然跟著大家一齊報考中文大學,我報的第一志願就是哲學。由於不想進其他學系,事實上也想不出有什麼其他系好讀,於是便在“第二志願”(那時不設“第三志願”?)一欄內仍然填上“哲學”(我以前經常忘記要守規則,這時毛病又發作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轉系,也沒有擔心過就業前途的問題。在我看來,畢業之後只要不餓死便可以了。倘若志向只在“飛黃騰達”,一開始就不會報讀哲學系了。我從小就心高氣傲,到大學時期更目空一切,視俗世如無物,自以為憑自己的條件,要是從事其他行業,也能出人頭地的。結果念了哲學,那完全是興趣使然。
現在純粹由於興趣而讀書的人不多,你那個時代的大學生一般是怎樣的呢?
當時我所接觸到的大學生,一般都比較“浪漫”,不那么“現實”,讀書多從興趣出發,追求異性時則往往不顧一切。那時沒有現今學生之間流行的那句格言:“不怕她醜,最要緊的是易上手。”我們比較熱心於課外活動,比較關心思想、文化、時代、人類前途等方面的問題,雖然每每流於空談、高調,但如果定要兩者擇一,我寧取這樣的年輕人而不取那些“年少老成”、從來沒有傻過也從來沒有天真過的年輕人。就以學生會來說,那時的學生會常有多個候選內閣煞有介事地出來競爭,我做會長那一屆就須得擊敗另外兩個候選內閣才能當選。但現在的學生卻往往因為做學生會工作沒有實利可圖而組不成閣。今天有不少學生太過勢利,缺乏理想。這個評語也許不完全正確,因為他們也有他們的理想,那就是金錢。許多人正是根據這個“理想”來考慮念什麼科系的。
二、搗蛋反叛與主動讀書
你以前讀書的態度和方式,跟時下的學生比較起來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我做學生時,反叛性很強,經常不守規則。譬如體育,所有大一同學都去修這科,我偏不修。體育老師吳思儉先生年年叫我去上課,提醒我不修體育不能畢業,但我硬要等到大四那年才去修。又如“社會學導論”,那是哲學系學生的必修科,我平時不去上課,要交的功課有幾位很可愛的同學替我做,年終考試就不及格。該科老師何太太叫我去補考,我就是不肯去。她很憤怒,說:“必修科不及格不能畢業。”我說:“將來的事將來再算。”幸好世事就是那么巧:到大三時,“社會學導論”不再列為哲學系必修科,否則我能否畢業便很成疑問了。總之,我做學生時經常有搗蛋的傾向,例如考“中國哲學史”不及格,就是因為不好好地去答問題,卻去分析、挑剔題目,結果唐君毅老師就給我不及格。
我這種搗蛋反叛的作風固然不足為訓,但是現今學生那種太過循規蹈矩的態度也有缺點。今天的學生大都採取“被動讀書”的方式,只看學科指定的參考書,甚至唯讀課堂上抄下來的筆記。我認為做學生時不妨偶爾吹牛、誇大,回到家裡便會(便應)心虛膽怯,然後“挑燈夜讀”。以前我喜歡硬找一些老師沒有講過的書來念,可以增加吹牛的本錢。分析哲學、科學哲學、存在主義、數理邏輯等等都是這樣子開始念起來的。讀中大[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學校根本沒有這些課程,我就到圖書館自己找書看。後來進芝加哥大學,數理邏輯是博士班的必修科,我摸到系主任的辦公室,要求在課堂外考核我的數理邏輯水平,希望能夠破例:免修該科。結果如願以償。這得歸功於“主動讀書”的習慣。
三、留校開新科,留學賭沙蟹
傳說你在美國念博士時,從沒有在學校出現過,卻溜到別的地方去了。實情是怎樣的呢?
我也聽過有謠傳說我從沒有在芝加哥大學逗留過,說我的學位是在拉斯維加斯賭場拿的。其實我是去了加拿大,每逢學期終結要考試就乘飛機回芝加哥,平時則留在加拿大經常賭沙蟹。現任教於香港大學統計學系的吳啟宏兄,那時在加拿大念博士,慷慨提供自己的房子做沙蟹戰場,常有各路英雄雲集。本人大殺四方,正是樂不思蜀。一天忽接到牟宗三老師的長途電話,說他立刻就要退休了,叫我即回。我如夢初醒,論文根本未動工,只好告別戰友,把論文高速寫好就回香港。算起來,我也並非從沒有在芝大出現過,約有兩個月的時間是在那裡度過的。這點現今在中大任教的幾位芝大校友也都知道。
事實上我向來有缺課逃學的習慣。我最反對大學還要點名,硬性規定學生上課,那是侮辱了大學生的獨立判斷能力。你講得好別人自然來聽,講得不好就該自我檢討,靠點名來逼學生上課有什麼意義?
中大一直有點名制度,你那時經常缺課,怎能過關?
全賴師長輩寬容,不拘小節。譬如修“中國通史”,那是文學院必修科,我到臨近學期終結才去上課,孫國棟先生抽樣點名點到我,我說:“到!”全班哄堂大笑起來。我摸不著頭腦,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後來才知道,原來孫先生每次點名都會抽到我,但每次都無人應,接著他總會停一下,左右望望,今次竟然例外,竟然有人說“到”,同學們就覺得好笑。我缺課這么多,孫先生卻是大人有大量,讓我考試及格。
其實我能去考試,還得感謝教務長王佶先生。學期結束時他把我叫去,要替我算一下各科缺席的賬。一算之下,缺課缺了100節左右,依校規不準考試。我結結巴巴,心裡正盤算著要吹什麼牛,他卻開口說:“下次不可以這樣了!”直到如今,我每想起王先生就深感懷念。
你讀大學時的師長輩與今天大學裡的講師、教授比較起來,其作風或風範有沒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今天大學裡的教師之中,以下三類人為數不少:一類像小商人,一類像公務員,一類像身體孱弱的退休紀律部隊隊員,難見有風流人物。我以前遇到的師長輩多溫潤儒雅的長者。唐端正先生是我的第一位哲學老師,真誠親切,到現在我見到他仍能感受到他的赤子之心。唐君毅老師和牟宗三老師更是當代大儒,宏博精深,海量汪涵。記得我修讀牟老師的“宋明儒學”時,還是一貫作風,經常缺課,臨考試的前一天就打電話問他是不是“真的要考試”。他說:“當然真的!怎會是開玩笑的呢?”我問可不可以改期,他說:“當然不改!”到下學期開課,我缺席如故,同學走來告訴我,說牟老師在課堂上大罵:“李天命這個東方阿飛,平時不來上課,考試前一天就打電話問我是不是真的要考試,還要我改期,天下間哪有這樣的事!”不過罵歸罵,牟老師對我始終循循善誘,悉心教導。他一早已看出我的思想路向和人生態度都與他迥然大異,甚至天南地北,背道而馳,但還是容得下我,兼且用心栽培,這份胸襟人格,實非常人能及,每一想起就使我感動不已。
聽說在牟先生做系主任時,你以助教身份擔任講師的工作,具體情況是怎樣的呢?
我進芝大之前,在中大當了一年助教,由牟老師推薦我開兩門以前從沒有在中大開設過的課程,那就是“高等邏輯”和“科學哲學”。普通邏輯由講師教,新開的高等邏輯由助教來教,這個責任大概只有牟老師才擔當得起,或者說這一“怪招”大概只有牟老師才有功力施展出來。此外他還介紹我到校外課程部講“語意學”、“分析哲學”和“存在主義”等課程呢。
四、從邏輯到新詩,從飛刀打架到勃拉姆斯
分析哲學、數理邏輯等學科與存在主義看起來南轅北轍,你的興趣應是多方面的吧?可以談談你的興趣嗎?
許多人以為講思考方法、數理邏輯等“硬文化”就不能講文學藝術、人生哲學等“軟文化”,其實兩方面是並行不悖的。我向來喜歡西方的古典音樂和中國的古典文學,這些興趣在中學時就已養成。在街外浪蕩、賭博、打架,回到家裡念唐詩、宋詞、古文,或者聽拉赫瑪尼諾夫、貝多芬、勃拉姆斯……這是我中學生涯的一面。到進了大學,我培養出許多不同的興趣,比如一方面讀分析哲學、數理邏輯,一方面讀存在主義、寫新詩。以前在《中國學生周報》、《盤古》等報章雜誌上寫,有個時期且負責編《盤古》的《風格詩頁》,近年則在《博益月刊》的《詩葉》上寫。
不過寫東西只是我人生的一個非常小的部分。我最怕理論繁複而生命蒼白。我不喜歡長篇大論“談”生活,我喜歡充充實實“過”生活。我從來不是書蟲,也不屬於文人形態,更不屬於學究形態。我認為只有蠢材、庸才才會浪費生命花時間去寫那些自己心底里也知道是沒有真正價值的、而且也沒有人會有興趣看的、只是以“學術”之名去掩飾而其實轉眼就會被拋入廢紙桶里的廢料。若要做這種蠢事,我寧願把時間用來嬉戲。
事實上我很喜歡玩,尤其喜歡驚險刺激。至於拍拖(談戀愛),就更不用說了,相信任何人都會喜歡的。那時除了喜歡這種“活動”之外,我還喜歡飛刀、賭沙蟹、“閘”腳踏車、划艇、爬山、滑滾軸溜冰,等等。其中最喜愛的而且也是最擅長的,就是飛刀和賭沙蟹。以前曾把飛刀的入門手法教過幾個哲學系的學生,但他們後來都沒有練好,真有點可惜。在我來說,興趣的多樣化是很有意義的:一來興趣的滿足本身就有自足的價值,二來對於我的學習很有幫助。浪蕩了一段時間之後,常會心慌起來,特別容易記起“勤有功,戲無益”的古訓,這時讀起書來就會格外起勁的了。
五、反學術遊戲,向下接不向上爬
無論讀起書來怎么起勁,你花那么多時間去玩樂嬉戲,會不會妨礙研究工作呢?
什麼研究工作!科學家做研究工作是天經地義,那是實學。哲學家搞研究工作是哲學的墮落,那是把戲。西方哲學家的典範,蘇格拉底,他的工作就是思辯。就是思考和辯論。他搞過什麼“研究工作”了呢?孔子、孟子、老子、莊子、釋迦、六祖、耶穌、維根斯坦等人,他們當然有他們的“學”,但那不是現今讀哲學的人搞的那種餖訂式的research,不是那種所謂的“研究工作”。這類“研究工作”絕大多數是自欺欺人的學術遊戲。英美方面如戴維森(Davidson)、達米特(Dummett)等人玩這種遊戲玩得十分出色,嚴謹精細,但終歸是遊戲,碎屑煩瑣,迷失了哲學的方向。歐陸哲學方面也往往是玩學術遊戲,而且每每玩得非常笨拙,暖昧空洞,不堪分析利器一擊,可謂屬於九流的級數。至於其他等而下之者,所玩的學術遊戲或“研究工作”,則九流也不入,只能算是“偽學術遊戲”罷了。偽學術遊戲不能與非歐幾何之類的“數學遊戲”等量齊觀,這裡不必細論。我們要留意的是,玩這種遊戲的人喜歡把“無用”美其名為“純學術”,以“純學術”之名去文飾其“無用”的實質。假如要玩這種“純學術”的話,我看只消隨便用左手的尾指的小指甲的一小部分,去逗弄一下,就能玩得很不錯的了。
但無論如何,哲學教師不以研究工作來評核,那么可參考什麼來決定升遷呢?你怎樣看升遷的問題?
依我的理想看,哲學家根本無須理會升遷的問題。他的人生意義絕不在此。理學院、醫學院等比較不容易弄虛作假的地方不在此論,就我所知,除了極少數例外,升遷與否一般取決於兩個因素:其一是學術遊戲或所謂的“研究工作”,其二是人事關係或鑽拍工夫,尤以第二個因素為主。以上所講是否實情,圈內人都心知肚明。
我一向自覺要遠離這兩個因素。我以前有一疊稿子拿了去友聯出版社,有幾十萬字,那就是牟老師在我的《存在主義概論》的序言裡提到的《分析哲學》(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這疊稿子與《存》先後拿到友聯,《存》先印了出來,《分》正要付印,我到友聯社長林悅恆先生那裡把稿子“騙”了回來。台灣《鵝湖》雜誌社的一些友人知道此事,多次勸我把稿子給他們拿去印,我一直支吾。這疊稿子和《存》同一時期寫。《存》沒什麼大錯,比同類中文書寫得較為清晰有條理一點。《分》所談的問題屬於我的本行,其水平自然比《存》要高,至少思路清晰,有系統條理。我大學時期寫的東西都能做到這一步,無須忸怩不好意思講。許多看過這疊稿子的學生、朋友都認為沒有理由不拿去印,一再催問我。現在我可以在這裡把原因說出來,同時也算回答了“為什麼牟老師寫的序言提到的那部書沒有了下文”的問題。《分》的付印對於升遷或許有用,對於讀者卻沒有什麼用,那就是唯一的原因了。這書印出來會有500多頁,若以我近年的語文功力來估計,其真正受用之處5頁就能講完。我最厭惡且瞧不起大而無當的磚頭厚書,缺乏誠真,自欺欺人,既浪費自己的生命,也浪費讀者的生命。這樣看來,《分》即使勝過許多庸書,卻仍然屬於我厭惡的學術遊戲或所謂的“研究工作”的範疇。這疊稿子是不會印出來的了,就讓它塞在抽屜底,不再一顧。
至於怎樣遠離前面所講的第二個因素,要說簡單也很簡單,就是潔身自愛,有所不為。知我者都知我平日只跟學生在一起,那是向下接而不是向上爬的路。我自覺地要走這條路。在“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會議”的大會總結討論中,劉述先先生說:“李天命是天生的表演者,跟他的學生是最多的。”我嘉許這個觀察。我覺得知識分子以年輕人比較純潔可愛,較有赤子之心。很多人一到中年就易變成老油條。孟子說“見大人則藐之”,老油條未見大人已軟,一見大人就可入口溶化。所以最好還是冷眼旁觀,保持距離,免受油漬玷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