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五中全會再提改革中國提前進入改革深水區
 改革深水區
改革深水區2010年在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一句話引來廣泛注目:“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公報中的一系列戰略部署,從加強和改善巨觀調控,到發展現代農業;從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到加快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從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到推進行政體制改革,也無不透露出極強的改革意識。作為一次為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發展確定方向、謀劃藍圖的會議,這些無疑表明:改革開放將在這個人口占世界1/4的大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人民網報導,改革開放,是在32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作為中國發展的一項基本戰略被提出的。30多年過去,中國翻天復地的巨變,已經證明了這一決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然而,3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面臨的發展環境,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都已經全然不同。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何五中全會要再次提出深化改革開放,並且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加以強調?細讀全會公報,就能找到答案。
公報中的一個重要判斷,是中國“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歷史上看,無論是明朝中期“地理大發現”後工業革命的開始,或19世紀末東方與西方的文明碰撞期,還是以科技革命為特徵的第三次浪潮時代,這幾次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中國都因為種種原因錯失了。而今天,在信息化浪潮、全球化環境之下,如果不能抓住機遇,很可能再次被時代拋棄。
十六大提出:本世紀頭二十年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還再次重申了十五大所規劃的戰略目標:在新世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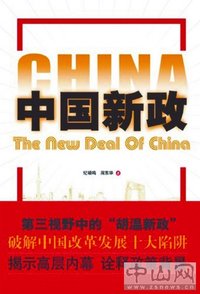 改革深水區
改革深水區一個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2000年,中國GDP為近8.94萬億元;2009年,這個數字已經達到33.5萬億元。期間的增長,已經遠遠超過了“翻一番”的程度。
可以說,中國提前進入了改革的深水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30多年後的今天,與改革開放初期面臨著相同的情況:要繼續發展,需要破除長期積累下來的體制機制弊端,需要觸動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這個時候,強調以“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正當其時。
另一方面,公報對“十二五”時期發展的總體要求中,強調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科學發展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可以說是發展的一個指針;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心詞“轉變”,本身即含有改革、改變的意思。改革,可說是蘊藏於這個主題與這條主線背後的另一個中心詞。
現在中國的發展也呈現出階段性特徵,一些新矛盾新問題不斷湧現。比如投資消費關係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再比如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還有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社會矛盾增多等。這些都要求我們,繼續變革體制機制,更新發展理念。科學發展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是基於此而提出的“改革”。
當然,在不斷的改革之中也要看到不變的東西。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整個世界和平和發展的主題也沒有變。實際上,正是這些“不變”和“變”的共同作用,才決定了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去改革,去發展,去實現更加美好的未來。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經歷著一個個“破—立—破”的螺鏇上升過程。正如列寧所說:“發展是按所謂螺鏇式而不是按直線式進行的。”辯證法告訴我們,不變則難免會倦怠,難免有暮氣,難免裹足不前。有破有立,才能不斷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激發向上的活力。而這,也正是“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的關鍵所在。
概述
在中國經濟度過了危機中最困難的一年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內部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迫使中國開始在
 改革深水區
改革深水區經濟結構調整上“動真格”。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們認為,中國已經邁入經濟體制改革的“深水區”,其成敗直接關係到調結構的大計。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從“保增長”到“調結構”,其中最大難點和突破點在於政府要“下決心衝破傳統阻力,出台體制改革措施”。
2009年歲末,親身經歷了中國經濟發展“最困難的一年”的50位國內經濟學家,在一項影響中國經濟發展主要問題的問卷調查中,選擇的前五位都是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壟斷行業扭曲資源配置、消費需求不足、權力缺乏監督、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從前都是先解決一些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也不太容易傷及既得利益集團。再往下走,必然要對現有的利益格局進行較大的調整,難度要大得多。”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學家莊健說。
 改革深水區
改革深水區他指出前幾年的國企收入分紅試點雖然是一次突破,但在分配面和比例上都很有限,國有資源收益並沒有轉移到老百姓手中,讓全體人民受益。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部部長張小濟認為,經濟結構的調整繞不開壟斷行業改革這道坎。
“政府過多干預市場資源配置必將導致效率低下,威脅公平競爭。金融危機時政府的救市措施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危機過後經濟要恢復再平衡,市場自身的作用才是主導。”張小濟說。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胡錦濤總書記近日講話強調,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必須通過堅定不移深化改革來推動。
打破壟斷的重要一環是資源要素的改革。莊健認為要素價格的改革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
 改革深水區
改革深水區“勞動力工資、能源價格、資金成本被人為壓低,這還是一種粗放的發展方式。這個問題不解決,轉變經濟成長方式就是一句空話。”莊健說。
對於資源價格改革可能助推通脹預期,莊健認為,如果現在不改革,隨著經濟的回升改革的難度會更大。況且改革不一定就要提價,應當讓市場發揮主導,建立有彈性的價格機制。
代表和委員們還指出,城鄉二元制結構固化甚至加劇城鄉差距,對人、財、物流動形成牽制。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達到1978年以來的最大水平。去年城鄉收入比為3.33:1,較2007年的3.32:1和2008年的3.31:1擴大。
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是來自廣東佛山的一位農民工。她說:“人們不能只從口頭上關心農民工,而要真正讓他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險、住房等方面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權利。這需要各級政府在財政體制上做出相應保障,需要企業負起責任,從機制上落實農村流動人口的基本就業權利。”
莊健認為,只局限於現在的進展,過分強調困難是不行的。隨著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勞動力短缺將會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他建議政府制定一個時間表,只有讓“農民工”這個詞消失,才能真正實現城鎮化。
代表和委員們指出,調整收入分配是體制改革的另一個焦點。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律師協會名譽會長陳舒說,“調整收入分配”表面看是經濟問題,深層次看是體制問題,涉及各個階層的利益再分配,敏感複雜,阻力較大。
“這需要在很多層面衝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加大力度消除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弊端。”陳舒說。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董明珠認為,收入分配改革既涉及政府的調控措施,也涉及勞動者的收入比重和企業發展的需要,需要均衡考慮。
“在我看來,中國的企業應當形成收入分配責任觀念,企業經營者在這一方面應當有自律精神,除了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營管理和分配財富外,還應該主動為廣大勞動者謀福利。從政府角度來說,以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為基礎、形成勞動者收入合理平穩提高的機制,也是當前的一個重要改革方向。”她說。
解析
有學者認為,中國改革具有三大特點。第一,我們的改革是漸進性改革,而非突變性改革,在保證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地推動改革。前蘇聯的改革是突變性改革,一夜之間私有化,蘇聯共產黨下台,國家解體。我們這種漸進式改革有利也有弊。利是保證社會的穩定,沒有動亂,改革平穩順利;弊是改革的成本分期付出,成本太大,隨著改革的深入,深層次矛盾積澱得越多,就越難以解決。第二,我們的改革是執政黨和政府主導型的改革,是在執政黨和政府的設計、策劃和推動下進行的。政府作為一個有既得利益的集團,在改革的初期是改革的推動者,但改革到了
 改革深水區
改革深水區“深水區”,由於觸動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改革就會放緩。當前倍受矚目的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後、久突不破就是政府主導型改革的必然結果。第三,是由淺到深、由點到面、由局部到整體的有層次的改革。
應該說,這種概括是比較符合實際的,我國改革20多年,進入“深水區”後方知:改到深處是結構,改到難處是體制。2004年的中國改革,便是在這個背景下進行。
2004年開局,中央高度強調重視三農,三農問題再次被寫進中央一號檔案,5年內取消農業稅的訊息對於中國九億農民而言,無疑是激盪人心的春訊。農民種糧的積極性開始恢復,夏糧全面增收。農民的命運再次被關注起來,但是我們同時關注到,這並不意味著此前城鄉二元體製造成的社會割裂正在獲得修復。因為,攸關城鄉二元體制變革的兩個根本性障礙——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現行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制度——並未有任何變革的跡象。前者說到底是一種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身份制殘餘,它使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迄今不能平等地、有尊嚴地、自由地在自己的國土上徜徉、遷徙和創業。而後者使農村土地的產權不能明晰並自由流轉,九億農民中的絕大部分只能被迫捆綁在那一坨有限的土地上覓食。
 改革深水區
改革深水區搜狐財經發起的2004國企產權改革大討論,從傳媒界到理論界再到決策層,其影響深遠,被理論界認為不亞於當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顯然,國有企業的命運直接影響到未來中國經濟的命運,此次討論之所以引起全社會關注,表明中國經濟命運處在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其實,這樣的討論至少在十年前就開始了,只不過沒有像今年這樣藉助傳媒的力量引發得民意洶洶而已。較早關注並一直堅持探究國企產權改革公正性問題的秦暉、何清漣等學者,早在幾年前就提出反對國企改革中“賣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與“界定式私有化”,強調產權改革公正與否比“激進”與否更為重要。當然,包括秦暉和我們在內,大多數的人們並不反對(甚至還積極期望)使現在名義上屬於全體國民所有的國有資產實實在在地明晰化,但這有個前提,就是使產權明晰的程式、方式和規則必須是公平、公正和公開的,而這正是橫亘在中國國企改革之路上的一道難題。
2004年銀行改革的大手筆,便是中央痛下決心動用外匯儲備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資,同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股改提速,從建行股份掛牌到中行股份掛牌,中國的金融改革大刀闊斧,從央行九年來首次加息到人民幣匯率面臨升值壓力,今年的金融改革一直處在激流之中。中國改革中風險最大的領域正在破局,而中央一再強調,中國的銀行改革不能失敗,金融改革正在背水一戰。銀行改革主要指向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國有存量金融資產明晰產權,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以轉換其機制;另一方面是做大增量,推進民營銀行的建立和發展。2004年初,一度風傳國家對民營銀行的政策口子可能有所鬆動,但一年過去,仍舊是只聞雷聲,不見雨點。同時,而也有學者提醒,在中國金融開放的同時,警惕金融危機的悄然來臨。
 改革深水區
改革深水區2004年的股市被人稱為患了“全流通死結下的休克低迷症”。早在約兩年前,“國有股減持”風傳一出,股市就暴跌至幾乎崩盤,迄今萎靡不振,這其實是國有資產在國民心理上的“負數效應”的體現。
巨觀調控是2004年的大背景,從經濟是否過熱之爭到出台多項巨觀調控措施,最終到央行加息,中國經濟已基本上實現軟著陸,較成功地規避了未來經濟運行中可能出現的危機。同時,巨觀調控的措施也由以行政力量為主轉而更多採用市場化的調節手段,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在巨觀調控中悄然變化。但值得引起警惕的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大行其道使巨觀調控的效果大打折扣;而巨觀調控本身也使一度甚囂塵上的行政對經濟的強行干預重新抬頭。
因為巨觀調控的大背景,2004年民企的命運與國企的命運一樣引人關注,從江蘇鐵本到寧波建龍,從劉永行的東方稀鋁工程擱淺到民企龍頭上海復星被銀監會列入銀行慎貸名單,從中國民企標桿新疆德隆的垮坍到格林柯爾發展備受質疑,這一切都表明,中國的民營企業在經歷了高速增長之後,在巨觀調控中,其發展模式正在經受新的考驗。未來的中國民企應該如何發展?這是2004年留給人們的一個值得深思的命題。
經過對2004作為一個經濟年度的簡單而難免掛一漏萬的爬梳整理,我們更加明確了一個傾向性的看法,那便是,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改革並不僅僅取決於效率,更取決於這場改革能否恪守起碼的公平和正義的底線。要恪守這個底線,就必須在這場關乎每個國民利益分配的改革中讓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有起碼的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話語權、參與權。而能夠保障全體國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這種平等的話語權和參與權者,只有公共選擇—監督機制(即民主機制)。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還剛剛開始。
地方試點
浙江省的義烏市被稱為“中國權力最大縣”。義烏官員稱,能放的權已經放了,用一句俗話形容就是改革將進入“深水區”。(見《瀟湘晨報》2010年7月24日)。而今,陝西省政府辦公廳行政干預法院審批恐怕也是躺入“深水區”的又一現象吧!那么,什麼是“深水區”?如何面對“深水區”?
“深水區”是人們談論地方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改革的一個常用詞。所謂“深水區”,用另一個角度而言就是“麻煩區”。不改革則已,一改則牽動方方面面的神經,觸及一些人的利益,引起一些人們的抵制干擾;對於官員而言,所謂“深水區”也往往是政治風險的代名詞,一不小心,就會惹上官場是非,甚至可能會危及官帽。因此,對“深水區”人們總是小心翼翼,左右猶豫,止步不前。 誠然,與大自然大江大海有淺水區深水區一樣,無論經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抑或是行政體制改革,都有淺層次與深層次之分。謂之淺層次,一個特徵是,風險小一些,麻煩少一些,推進容易一些。淺層次改革之所以能順利推進,恐怕原因也在此。
但是,與“深水區”才能藏大魚一樣,只有推進深層次改革才能真正解決發展中的瓶頸與矛盾,促進生產力發展。那么,經濟、文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深水區”在哪裡?從社會的滿意度來說,到目前為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既得利益要不阻礙改革、要不改變改革的方向,要不挾持改革以圖私利。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效,遠遠彌補不了經濟發展對這些社會領域的破壞程度。在住房領域,地方政府只有對擴張房地產市場的動力有興趣,而對於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顯缺乏興趣。比如,就浙江義烏而言,僅2009年金融機構存款金額達586.2億元,在其頂頭上司金華全市的存款總額中占了大頭。按照時下中國金融制度,義烏不能設立銀行分行。很多商業銀行要先在金華設立金華支行才能踏進義烏金融界。而今,義烏享受省管縣的待遇,省金融機構可以越過金華徑直在義烏設支行機構。這樣一來,義烏支行與頂頭上司金華支行由原來的老子與兒子關係立馬變成了兄弟關係。
從推動事業進步,提高工作效率而言,這種省去層次關係的改革大有必要,值得倡導。但對於某些人們而言,卻是大逆不道甚至視作洪水猛獸的。箇中原因也不言而明:傳統官念作怪。
人們心目中的傳統官念,就是長官意志,下級必須絕對服從上級。一旦改革了這個格局,就是大逆不道,就有可能遭遇被批評被穿小鞋甚至被摘官帽的待遇。因此,擴權式的體制改革往往被人們視作畏途,視作“攔路虎”。這也是至今在某些地方省管縣難以推進步履維艱的癥結所在吧!
由此說到省管縣。自從十七大提出試行省管縣的部署以來,媒體為此曾熱鬧一陣子,但很快變成了靜悄悄,有些地方甚至銷聲匿跡。分析箇中原因,步入了“深水區”恐怕也是共同原因。上一級官員所持的心態是,擔心權力下放,自己手中沒權,顯不了官場權威,更沒有了往昔的權力風光。因此,對省管縣之類的改革抱不點頭態度,即使上頭追下來,也是以所謂“深水區”需慢慢來的理由進行搪塞。可見,在“深水區”背後,折射的是對改革不熱枕,對傳統官念的戀戀不捨情結。沒有改革,既得利益集團就會繼續憑藉其本能,繼續以破壞社會的方式來求得經濟的增長;沒有改革,社會也會繼續感到無力和無助,繼續其各種具有破壞性的抗爭或者暴力。
“深水區”不能成為改革止步不前的理由也是很明顯,改革發展的形勢迫著人們去趟“深水區”。時下,無論是加快結構調整,轉變經濟方式抑或是推進民主政治依法治國都迫切要求推進方方面面的改革。深化改革是實道理、打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