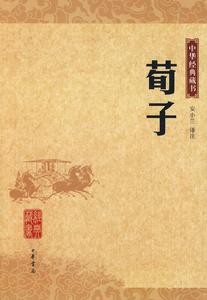荀子
荀子(前313年-前238年)名況,時人尊而號為“卿”;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戰國時期趙國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提倡性惡論,常被與孟子的性善論比較。對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當的貢獻。思想主張
荀子的思想偏向經驗以及人事方面,是從社會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秘主義的思想,重視人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後提出“禮”,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範。以孔子為聖人,但反對子思和孟子為首的“思孟學派”哲學思想,認為子貢與自己才是繼承孔子思想的學者。荀子和孟子的“性善”說相反,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生來是“惡”的,“其善者偽也”,須要“師化之法,禮義之道”,通過“注錯習俗”、“化性起偽”對人的影響,才可以為善。
在天人關係上,荀子反對天命、鬼神迷信之說,肯定了“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即自然運行法則是不以人們的意識為轉移的,主張“明於天人之分”,認為天有“天職”,人有“人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
荀子主張“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
荀子繼承孔子的地方,還在於他對於禮和師法的重視,堅持儒家“正名”之說,強調尊卑等級名分的必要性,主張“法後王”即效法文、武、周公之道。又由於主張“性惡論”,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荀子成為後來出現的法家的開啟者。
其他思想主張
荀子在經濟上提出強本節用、開源節流和“省工賈、眾農夫”等主張。《史記》記載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荀子的“帝王之術”,通過李斯後來的實踐,體現出來。北宋蘇軾在《荀卿論》中說:“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
荀子·性惡
原文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yín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其偽也。
故枸木必將待隱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製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題解
本篇闡述了荀子學說的基本觀點,即人性惡。在這段文字中,荀子首先提出人性是惡的,而善則是後天人為的。人自降生時起,就好利、疾惡、好色。放縱這些本性就會帶來不良後果。只有師法、禮義才能矯正和約束人性,所以古代的聖人“起禮義、製法度”來化導人的情性。
原文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之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之人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題解
孟子認為:人之所以要學習,是因為性善,這是不對的。人的本性是天生的,它不需要學習和修飾,人性飢則欲食,寒則欲暖,勞則欲休。但在禮義的約束下,就能做到節制和辭讓。所以,善是後天的、人為的。原文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斫目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也,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強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題解
禮義是聖人制定的,並不是人生來就有的。聖人之所以不同於普通人,就在於他能約束本性,追求性情以外的事物,於是制定出禮義和法度。人們之所以喜歡善,是因為性惡,就象窮人想富有、卑賤想高貴一樣。原文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嘩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隱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矣。直木不待隱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隱栝矯烝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題解
孟子“人性善”的觀點是不對的。善,是指正理平治,惡則是偏險悖亂。人如果天性善,那又要聖王和禮義乾什麼?正因為人性本惡,所以聖人立禮義法度,使人歸於善。孟子之說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原文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斫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埏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眾人也;然而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
題解
禮義是聖人制定的,但並非聖人的本性。這就如同瓦器是陶工造的,但不能說瓦器就是陶工的本性一樣。如果人性本善,那就不會有夏桀之類的暴君,堯舜也就不可貴了。原文
“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遍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
題解
普通人也可以成為禹。為什麼這么說呢?禹能夠成為禹,就在於他行仁義法正。如果現在的人都具有明了仁義法正的資質,都具備實現仁義法正的工具,那么他們也是可以成為禹這樣的聖人的。原文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其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共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
繁弱、巨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祿,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巨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污慢、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題解
智有聖人、士君子、小人、役夫之分,勇有上勇、中勇、下勇之別。文中提出人只有求賢師、擇良友才能懂得堯禹之道、忠信之義。這是身邊環境決定的。同理,若與不善之人相處,則必受其殃。佛教天台宗中的“性惡說”
性惡說的明確提出,始見於隋代智顗的《觀音玄義》。其重要論點是:一、善惡都是性德本具。性德本有,是因果根本。性德了因種子修得即成般若,究竟即成智德菩提;性德緣因種子修得即成解脫,究竟即成斷德涅槃;性德非緣非了即是正因,修得成就即是法身。了是顯發,緣是資助;緣因資助了因,顯發正因法身。緣了二因既具有性德善,也具有性德惡。二、修中善惡可斷。一切法不出善惡,由性中善惡起作修中善惡,然後產生世出世法。修中善惡屬於事用,才可論及染淨逆順。闡提是染逆之極,斷修善盡;佛是淨順之極,斷修惡盡。三、性中善惡不斷,只是善惡的法門。諸佛向門而入,則修善滿足,修惡斷盡;闡提背門而出,則修惡滿足,修善斷盡。人有向背,門終不改。性既不可改,復不可斷壞。四、佛和闡提的差異在達與染。佛雖不斷性惡,而能達於性惡,不為惡所染,因此永無復惡;闡提染而不達,與此為異(參閱宋知禮《觀音玄義記》卷二)。即修惡達性惡,是性惡說的根本理論。智顗對於“性”的解釋是:性以據內,內性不可改。如竹中火性,雖然不可見,不能說沒有。心也一樣,具一切五陰性,雖然不可見,不能說沒有。如果用智眼觀察,就能知心具一切性(參閱《摩訶止觀》卷五上)。這說明性是本具的理體,性惡雖是修惡的理體,不可改,不可斷,但若能達於性惡,就可不為惡所染。智顗曾經著重指出了“達”的意義:善與實相相順是佛道,惡與實相相背是非道。如果了達諸惡非惡而是實相,就是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如果對於佛道生著,不消甘露,佛道也就成為非道(參閱《摩訶止觀》卷二下)。可見達性惡就是達實相,性惡也就是實相。
智顗曾在闡釋“非行非坐三昧”中詳細說明歷諸惡修止觀的要點,這就是即修惡達性惡的具體方法。善惡是相對的,相對的惡未可盡為觀境,應當以顯著的惡即與事六度相反的六蔽作為修止觀的對象。善法修觀,其蔽不息,當於惡中而修觀慧。若蔽恆起,此觀恆照。當知蔽即法性,蔽起即法性起,蔽息即法性息。常修觀慧與蔽理相應,能於一切惡法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破除作為六蔽根本的無明,顯出法性,乃至諸佛,盡蔽源底(參閱《摩訶止觀》卷二下)。他在闡釋“觀煩惱境”中並曾說到:“四分煩惱不得隨,隨則使人入惡道,復不得斷,斷則成增上慢。應當觀煩惱暗即大智明,顯佛菩提,惑則不來。”觀的方法是三止三觀:四分煩惱,體之即空,是體真止和入空觀;觀諸煩惱藥病等法,是隨緣止和入假觀;觀諸煩惱同於真際,是息二邊止和入中道觀。如果入惡無觀,放心行不調事,是名大礙,何關無礙;是增長非道,何關佛道(參閱《摩訶止觀》卷八上)。
這樣,如果了達性惡,惡也就成了善。智顗在闡釋“三法妙”中曾經指明了這一點:凡夫心一念即皆具十法界,一一界悉有煩惱性相和惡業性相等。無明煩惱性相即是智慧觀照性相。因為由迷明才起無明,如果解無明,即是明。又由惡有善,翻惡即善。惡即善性,未即是惡;遇緣成事,即能翻惡。如竹有火,火出還燒竹;惡中有善,善成還破惡。因此即惡性相是善性相(參閱《法華經玄義》卷五下)。宋代智圓曾經更明白地說:“性中之惡,惡全是善。理體無差,豈應隔異?”(《請觀音經疏闡義鈔》卷二)
按照智顗以前弘地論師等的見解,佛斷惡種子盡,只作神通現惡化度眾生。智顗認為作神通現惡是作意起惡,不是不可思議理,能任運應惡,這與外道無異。他的意見是:佛不斷性惡,機緣所激,慈力所熏,還能起惡,同一切惡事化度眾生。但是這種起惡跟一般的起於修惡不同,雖起於惡而是解心無染,通達惡際即是實際。因此他在說明佛“修惡不得起”之後,接著就以“不染故不起”作為它的解釋(參閱《觀音玄義》卷上)。這一意義,就是但除其病,不除其法,也就是不斷煩惱入涅槃(參閱《請觀音經疏》)。
唐代湛然對性惡說也曾加以闡明,他特別注意到防止性惡與實惡的混淆。他指明以達惡為善也必須離惡。如《華嚴經》中婆須密多得菩薩離欲際法門,能化所化並是因欲而得離欲。對於惡法修觀,是由於惡可改,起意義在於不可恣惡和存惡。例如對於貪慾修觀,即是以觀推究,令欲破壞。既經四句推檢,能使貪慾泯然,但有妙觀,無復貪慾。因此而使欲轉為智,智慧型進道,運至涅槃。他說明從事來看,六蔽有起息,法性無起息;從理而說,俱無起息。因此六蔽和法性,其體不二,終成絕待,無蔽無性,亦無起息。若得此意,就能但觀貪慾即是法性,而得性空和相空(參閱《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二之四)。這明確顯示了修觀能息六蔽,使之轉而為智,因而有破惡和達性的功能。
宋代知禮對性惡說曾力加闡揚,他建立性惡說為天台宗義的特點,認為性中具善,諸師亦知;性中具惡,他皆莫測(參閱《觀音玄義記》卷二)。他揭示性惡說的要義在於智照和無作,破斥了山外認為性惡無消伏義的說法。這就是說:眾生本來未曾離惡,初心人創心修觀都從見思發端,由於藏通別三教不談性惡,見思不即理性,既非性惡,定為能障,必須別緣真中二理,別修觀智,才能破此見思惑心,顯出本有常住之體。這樣就有了能緣所緣和能破所破,惑智對待,境觀不忘,因而成為有作之行。圓教既談性惡,見思即是理性,惑既即是性惡,只用此惑而為能觀;惑既為能觀,又復為所觀,一心三觀,圓頓十乘,更非別修,當處絕待,豈非性德之行。這樣還有什麼能緣所緣和能破所破,非但所觀無明是與法性體性不二,而且能觀觀智即是無明。能所一如,境觀不二,才能初心即修中觀,造境無不真實,成為無作之行(參閱《釋請觀音疏中消伏三用》、《對闡義鈔辯三用一十九問》、《絳幃問答三十章》第二十五問、《教門雜問答七章》第一問)。
知禮又以此義闡釋煩惱即菩提,反破當時禪者講者以天台所說同於禪宗達摩門下尼總持和道育斷惑證理翻迷就悟的見解。他的主要論點是:煩惱生死既是修惡,全體即是性惡法門,所以不須斷除和翻轉。天台所明“即”義,直須當體全是。不是二物相合,因此不同於尼總持的斷惑證理;也不是背面相翻,因此不同於道育的翻迷就悟。又既煩惱等全是性惡,也不可以說是一向本無。由即而論斷,就無可滅;由即而論悟,就無可翻。圓教佛法界是十法界互具,所以不須壞九法界或轉九法界。圓教所論斷證迷悟,只從情和理兩方面來看:情著則十法界俱染,有惑可斷,為惡所迷;理融則十法界俱淨,不斷而證,了迷即悟(參閱《十不二門指要鈔》卷上、宋可度《十不二門指要鈔詳解》卷一、宋宗曉《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四“天童四明往復書”)。
知禮又以性惡理論闡釋懺法中的無生懺。一切罪相無非實相,十惡、五逆、四重、八邪都是理毒的法門和性染的本用,以此為能懺,即此為所觀,惑智本如,理事一際,能障所障皆泯,能懺所懺俱忘,終日加功,終日無作。這樣就是最上第一懺悔,能了我心自空,罪福無主,觀業實相,見罪本源,法界圓融,真如清淨(參閱《修懺要旨》)。
知禮詳盡闡發了即修惡達性惡的一家大旨,也同時對性惡和修惡作了嚴格的區分。他曾指明:性惡跟性善一樣,都是體具微妙法門清淨功德,與《大乘起信論》中所說“過恆沙等諸淨功德不離不斷”等更無少異。至於一切世間生死煩惱妄染之法,都是修惡,雖全性起而違於性,故須永滅。因此在證會時,修惡雖盡,性惡常存(參閱《答日本國師二十七問》第二十三問)。
元代懷則繼續發揚了知禮的論點。他在《天台傳佛心印記》里首先談到:“今家性具之功,功在性惡。”他認為諸宗不知性具惡法,不了性惡即佛性異名,因而必須翻九法界修惡,證佛法界性善。這是獨標清淨法身,都不出於但中之義,從四教說偏屬別教,未可稱為圓頓心印。他舉出《摩訶止觀》所明十乘妙觀觀於十境,一一皆成圓妙三諦,顯示了九法界修惡當體即是性惡法門。性惡融通,無法不趣,任運攝得佛法界性善。用這樣的絕待妙法作為觀體,才是終窮究竟極說,也就是佛祖正傳心印。
他對於即修惡達性惡的見解,也發揮了智顗和知禮的觀點。迷情須破,法不可破。因此用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觀,達此一念修惡之心即是三千妙境或法界,相相宛然,事理本融。既然情消理顯,修惡就不屬所破而屬所顯了。既達性惡,就無修惡可論,可以說修惡斷盡。修惡既即性惡,也可以說修惡何嘗斷。因此,斷與不斷,妙在其中。佛達性惡,廣用諸惡化度眾生,乃是妙用無染,表現為性惡法門。性惡法門無染礙之相,而有性具之用。這種性具的妙用,如君子不器,善惡俱能,體用不二。別教行人不達性中具惡,如淳善人被無明所牽,就會造惡。
他曾論及性善惡和修善惡的劃分界限。善惡相對,可以從十法界次第迭論:六法界為惡,二乘為善;八法界為惡,菩薩為善;九法界為惡,佛法界為善。九法界為惡乃是惡之際,佛法界為善乃是善之極。上面說九法界修惡當體即是性惡法門,乃是就極而論。
明代傳燈著《性善惡論》,更詳盡地闡釋了天台一家的性惡理論,主要是承繼了知禮和懷則的說法。
他曾論及性和修的區別:台宗言性則善惡具,言修而後善惡分。性於善惡未形,本來還不應當以善惡論;但是以修而觀於性,修既有善惡,性豈得無善惡?既然修中善惡可分,性中善惡無分,性惡就能任運攝得性善,而使性中善惡與修中善惡不同。修中善惡確然有升沉苦樂的差別,性中善惡則體具三德,皆不二而二,二而不二,並沒有升沉苦樂的差別。
他對於即修惡達性惡的解釋是:性善性惡乃是真如不變之體,修善修惡則是隨緣差別之用。正因為真如不變體中具有善惡二性,隨緣時才能有善惡之用。世人日用根塵相對,凡起一念,必屬一法界,一法界生起是事造,九法界冥伏是理具。事中九法界是全性惡以起修惡,事中佛法界是全性善以起修善,既全性起,有何一法不即佛法。九法界既從性惡以起修惡,修惡遍處即性惡遍處。而性惡融通,九法界性惡遍處即佛法界性善遍處。如能觀修惡即性惡,就可以任運攝得佛法界性善。這正如同即波見水,即器見空一樣,不須轉側以明此心而見此性。由此了三德性,離三惑染,順理無作,就是圓教的稱理圓修,也就是隨淨緣造成佛法界。這時佛法界現起,九法界冥伏,其實所具九法界毫無所改。因此,即修惡達性惡,乃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妙門,訓人為善的大道。
傳燈對於用惡度生的性惡法門,作了詳細的闡述,並就佛和菩薩分為究竟性惡法門,分真性惡法門,相似性惡法門和觀行性惡法門,分別列舉了降魔等等事跡。他說到性善法門是常,性惡法門是變,有時善不足以化度,就不得不施於惡。其實這裡的惡只是以“不順”為義,並非是真正的惡。例如降魔時,變魔逆境以為順境,或變魔順境以為逆境,用來惱亂其心,使之於惡得盡。因此,性惡法門乃是佛菩薩大權的能事,是稱性施設的妙用,是慈善根力所現。他提出了建立性惡法門的五大因緣:一、理體本來具足善和惡;二、由惡照性,可以成修;三、果地圓證了十法界性,一無所改;四、果地能圓起十法界用,無謀而應;五、眾生根性不同,菩薩度生必須有性惡法門,才能示現無量,或如《華嚴經》中婆須密多等以三毒而作佛事,把自己由修惡悟入性惡的法門用以利生,眾生入道也必須有性惡法門,才能適應於由惡緣翻邪歸正的情況。
性惡說的依據,從智顗所說佛不斷性惡、闡提不斷性善來看,是出於《大般涅槃經》南本卷三十二對於佛性有無的四句料簡。懷則《天台傳佛心印記》並曾指出此說通於諸大乘經,不過立名不同。如《華嚴經》中的十法界,迷則俱染,悟則俱淨:《法華經》中的諸法實相,諸法是同體權中善惡緣了,實相是同體實中善惡正因,九法界十如是惡緣因,佛法界十如是善緣因,又如《請觀音經》中的毒害,即是性惡。此外如性淨性穢,理明理暗或常無常雙寂之體,都是一體的異名。
智顗親承陳代慧思,性惡說的淵源可以從慧思的著作里看到。《大乘止觀法門》卷二曾說,如來藏具足染淨有其二種:一是性染性淨,二是事染事淨。心體或淨心具足染淨二性而無異相,一味平等。無明染法實從心體染性而起,由於無明體暗,不知從心而起,不知心性平等。因其不能稱理而知,所以說它是違性。智慧淨法實從心體淨性而起,由於智慧明利,能知悉從心生,能知心性平等,因其稱理而知,所以說它是順性。這樣,眾生遇佛方便教化,隨順淨心,就能證真如。又卷一說,眾生和佛悉具染淨二性,法界法爾,未曾不有。雖因熏力起用,先後不俱,染熏息而轉凡,淨業起而成聖;然其心體二性實無成壞。因此,就性而說,染淨並具;依熏而論,凡聖不俱。大乘止觀法門所用的名相和解釋雖稍有不同,但是對於性惡說的要義都已經具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