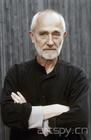彼得•卒姆托獲得這個獎項,使他加入了此前的“普利茲克建築獎”獲得者的行列。這些獲獎者包括著名建築師讓•努維爾(Jean Nouvel)、弗蘭克•蓋里(Frank Gehry)和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授予彼得•卒姆托這個獎項,是為了表彰他設計的各種各樣的建築物——包括教堂、博物館、高級住房和溫泉設施。
“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審團的建築師、教授、作家和設計師讚揚彼得•卒姆托設計的永久性的建築吸取了建造地點的文化,並且顯示了對當地的環境的尊重。
普里茲克基金會2009年4月13日宣布,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獲得2009年普里茨克獎。頒獎典禮將於5月29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獎金額10萬美元。 (Peter Zumthor作品欣賞)
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1943年4月26日生於瑞士巴塞爾,曾在巴塞爾和紐約學習設計。1979年建立自己的事務所,主要作品包括
Thermal Baths VALS, Vals, Switzerland, 1996年
Kunsthaus (Art Museum) Bregenz,Bregenz, Austria,1997年
Swiss Pavilion, Expo 2000,Hannover, Germany,2000年
Harjunkulma Apartment Building,Jyväskylä, Finland,2004年
Art Museum Kolumba Cologne, Germany,2007年
Brother Klaus Field ,2007年
本屆評審包括前倫敦泰特畫廊委員會主席Lord Palumbo,智利建築師Alejandro Aravena,日本建築師坂茂,瑞士人Rolf Fehlbaum,美國Rice大學教授Carlos Jimenez,芬蘭師Juhani Pallasmaa,義大利建築師Renzo Piano和美國作家Karen Stein。
2009年普利茲克獎獲得者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說:
“我認為現代建築必須反映出所附帶的任務和自身本質。建築不是一輛車或者一個象徵,能將其本質顯著的表現出來。在社會中,建築以自己的語言抵制浪費,讚美精簡。
我認為,建築語言的結構問題不在於具體的風格。每個建築均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因特殊的用途而建立,我的建築試圖回答這一從簡單事實中湧現出來的問題,並且通過儘可能精確的方式表達出來。”
1999年,卒姆托以其明亮的玻璃盒子式的奧地利布雷根茨美術館(ArtMuseumBregenz)榮獲了第六屆歐洲建築師密斯·凡·德·羅獎。
這是一幢什麼樣的建築呢?在布雷根茨康斯坦斯湖畔,布雷根茨美術館像一盞明亮的燈,空間主體是一個六層(地下兩層,地上四層)的方形玻璃盒子,相同尺寸的鋼和玻璃用大的鋼夾子以鱗片狀的排布方式固定在鋼框架上,就像為建築添加了一層有靈性的皮膚,它是光潔的,反射著天空和湖面的光影色彩,隨著一天中光線的強弱而變化,建築,仿佛也有了生命。
卒姆托對於光線的變化極為敏感,這幾乎成了卒姆托作品的一大特徵。1986年,他為邱爾古羅馬考古遺址設計了圍欄,就借鑑了威尼斯傳統的半閉百葉窗原理,在純淨的觀感中創造出魔幻般的光影效果。
在基督教教堂中,光線喚醒我們的感知。卒姆托就像一位建築教士,在平凡中書寫靜謐的詩篇。他不是一位城市地標建築的熱衷者,他似乎是一名隱士,喜歡跑到人跡罕至的偏遠地區(比如阿爾卑斯山區),去尋找他內心真正熱愛的建築。於是,從他的手下出現了仿佛中世紀手工作坊出產的精緻藝術品。
這和他的人生經歷不無關係。他父親是專門製作家具的木匠,卒姆托也像柯布西埃那樣以學徒的身份學習木工,20 歲時更進入了巴塞爾藝術與工藝學校,從工藝的角度,他學到了設計的真諦。
而且,卒姆托給人的印象仿佛是建築界的普魯斯特,生於金牛座的他性格內斂,喜歡追憶,仿佛要將往事之光踩在腳下,永遠地收藏在自己的被窩裡似的。還記得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中著名的關於“小瑪德萊娜”點心的描寫嗎?
母親著人拿來一塊點心,是那種又矮又胖名叫“小瑪德萊娜”的點心,看來像是用扇貝殼那樣的點心模子做的。那天天色陰沉,而且第二天也不見得會晴朗,我的心情很壓抑,無意中舀了一勺茶送到嘴邊。起先我已掰了一塊“小瑪德萊娜”放進茶水準備泡軟後食用。帶著點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齶,頓時使我渾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發生了非同小可的變化。一種舒坦的快感傳遍全身,我感到超塵脫俗,卻不知出自何因。
普魯斯特總是著迷於這些能夠讓他回到童年時代的記憶細節。而卒姆托同樣如此,他說他經常在設計前記起,童年時走入姨媽家花園時曾經握過的門把手——形似湯匙背的金屬門把手。對他來說,這個門把手仍然是進入那個充滿著異樣氛圍和氣息的世界的特殊符號。他記得腳踩在礫石地上的聲響,上了蠟的橡木樓梯閃爍著柔和的光澤。他還能聽到沉重的大門在身後砰地關上,他穿過黑暗的走廊走進廚房,那是整幢房子中唯一被真正照亮的地方……
童年時這個細小的記憶像一壺釅茶,隨著歲月的累積越來越濃烈,讓卒姆托不得不一次次地回想起這個人生的片斷: “當我設計建築時,時常發現自己陷入到遙遠、半忘卻的記憶中。於是我試圖找到記憶中的真實景象,找到它們在此時對我的意義,這種瀰漫在簡單事物中的勃勃生機如何對我產生幫助。在這裡,每一個物體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和形式。雖然我不會去模仿任何一種形式,它們的完整性和豐富性依然可以啟發我的思緒。這是我以前曾經見過的。儘管如此,我知道一切都是新的、不同的,對以前作品的任何模仿都不可能表達出記憶中的神秘魅力。”
位置、材料、空間和光線的感覺,就是他編織往事的材料,在往事中,卒姆托體悟著傳統與現代撞擊下的火花,用一種安靜的傳統的姿態,他闡釋了現代設計的可能性:自然樸實而又令人驚艷。因為他是真正思索建築和人之間的關係的建築師,他說:“建築具有自己的領域,它與實際生活存在著物質的聯繫。我並不認為建築是一種信息或象徵。它首先是生活的容器和背景,敏感地容納著地板上腳步的節奏,容納著工作的專注,容納著睡眠的寂靜。”
讓建築得到感悟
“整體使細節得到感悟。”卒姆托的口吻讓人不禁聯想到建築大師柯布西埃。
柯布西埃在《走向新建築》中曾經寫下過這樣富有詩意的句子:“牆壁以使我受到感動的方式升向天空。我感受到了你的意圖。你溫和或粗暴、迷人或高尚,你的石頭會向我說。”
建築也需要感悟!它不是冷冰冰地站在你面前。此時,建築師們追求的不再是建築外部形體上的誇張震驚效果,而是反觀內心,建築也不再以張揚的後現代形式挑戰觀者的視覺神經,對他們來說,建築就是每一個細節組成的整體,就是從每一個細節出發,讓它們散發出仿佛教堂般聖潔而寧靜的光。
卒姆托、赫佐格和德默隆的風格都可以歸入極簡主義的陣營之中,顯然,這種建築風格和瑞士中立國遠離戰爭、生活安逸平和不無瓜葛。在這裡不會有利伯斯金(新世貿大廈和猶太人博物館的設計師)面對“9·11”和猶太人遇難時的痛苦心結,田園牧歌般的生活籠罩著城市與田野。
相關詞條
-
彼得卒姆托
《彼得卒姆托》是2007年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大師》編輯部。
內容簡介 目錄 -
彼得·卒母托
彼得·卒母托,男 ,1943 年4月26日出生,出生於瑞士巴塞爾(Basel),畢業於美國紐約普瑞特學院,普利茲克獎獲得者。
基本信息 人物經歷 創作風格 人物語錄 作品列表 -
彼得·祖索爾
彼得·卒姆托 (Peter Zumthor )1943年4月生於瑞士巴塞爾的建築設計師,早在80年代就為人熟知了。到了90年代,他的作品更是層出不窮,這...
主要成就 影響作品 -
牆體與外立面
設計師彼得·卒姆托設計。該項目是卒姆托在英國完成的第一座建築,其中包含了非常有影響力的荷蘭設計師皮耶特·奧多夫專門設計的花園。在彼得·卒姆托設計的展館中央是一座花園,建築師希望該花園能使參觀者變成觀察者。彼得·卒姆托...
基本信息 編輯推薦 目錄 -
科隆美術館
of the archbishopric Cologne)由瑞士建築師彼得·卒姆托設計...1997年 建築師彼得 卒姆托(Peter zumthor...。 2009年普利茲克獎獲得者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說...
館舍介紹 建築時間 建築師 -
瑞士瓦爾斯溫泉浴場
獲得者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說...的溫泉中。1996年瑞士著名建築師彼得•卒姆托用當地...石材變得登峰造極 而且卒姆托的設計概念,空間的組織規律和空間劃分特徵,光...
-
溝通:建築師與建築師的交往
·賴特,漢斯·扎格,彼得·卒姆托。目錄與建築師的交往之路:謀求溝通...·卒姆托 後記 建築師(按姓氏英文字母順序排序) 魏納·布拉...。 溝通——建築師與建築師的交往 阿爾瓦·阿爾托,約瑟夫·艾伯斯...
圖書信息 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目錄 -
世界博物館建築
,馬斯特里赫特,1990—1995海爾曼·柯迪亞克彼得·卒姆托美術館,布...·福斯特設計的尼姆市卡里藝術中心,雷姆·庫哈斯設計的卡爾斯魯厄德國新媒體藝術中心,彼得·卒姆特設計的布雷根茲茨簡約主義藝術中心,倫佐·皮阿諾設計...
圖書信息 內容簡介 圖書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