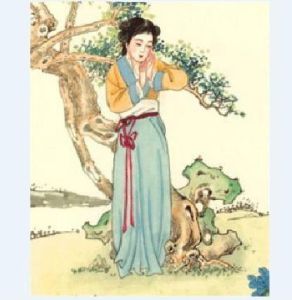故里姜塬
很久很久以前,豫北太行山腳下(今河南衛輝市西北一帶)湖水蕩漾,樹木蔥鬱,山清水秀。這裡聚集著一個小部落,男女只有幾十個人。在這個小部落里,有一名叫姜塬的姑娘,長得很美麗。她心地善良,手腳勤快,深受大夥的愛戴。被大家推選為族長。白天,他們一起上山狩獵,下湖捕魚;晚上,他們歡聚在一起,分享勞動果實,載歌載舞,共享天倫之樂。
且說姜塬姑娘年過而立,膝下沒有一男半女。她終日滿腹惆悵,悶悶不樂。
冬去春來,冰消雪融,風和日麗、鳥語花香。涓涓溪流曲徑通幽。一天勞動之餘,姜塬姑娘離開大夥,獨自一人沿著小溪往上走。走啊,走啊,翻過一架架山,越過一道道溝。她正走著,突然,從遠處的天上飛來一隻灰喜鵲,嘴裡銜著一條紅頭繩,落在她的面前,朝她“喳喳喳”地叫個不停。姑娘很奇怪,她緊跑了幾步,上前一把拽住處了紅頭繩。灰喜鵲銜著紅頭繩的一頭在前面飛,姑娘拽著紅頭繩的另一頭在後面跟著跑。飛呀飛,跑呀跑,不覺來到了小溪的源頭。山泉叮咚,如珠似玉,五光十色,異常美麗。灰喜鵲丟下紅頭繩飛走了。姜塬姑娘跑得口乾舌燥,她扔下紅頭繩,雙手捧起甘甜清洌的泉水一飲而盡,頓覺心曠神怡,春意蕩漾。她躺在青石板小憩了一陣後,高高興興地順著羊腸小路一步一步走下山來。
且說,族裡的人半天不見姜塬姑娘,心裡非常著急。正在尋找時,只見姜塬姑娘從遠遠的小山坡上走來,人們驚喜地迎上前去問長問短。姜塬姑娘興高采烈地講述了灰喜鵲引路的經過。說著說著,只見她的肚子慢慢隆起,並一陣一陣疼得厲害,豆大的汗珠一個接一個地從額頭上滾下來。姜塬姑娘不由得害怕起來,一位老奶奶上前說道:“姑娘別害怕,那喜鵲是神鳥,神鳥引路,你喝了神水,八成是懷了孕,這都是上天的安排,可是一場大喜呀!”大家聽了,都為姜塬姑娘高興。
花開花落,冬去春來,光陰整整過了三年。瑰麗的朝霞染紅了半邊天,世間一切都顯得楚楚動人。這時那隻灰喜鵲又飛來了,落在姜塬姑娘窗前的一棵大楝樹,“喳喳喳”地叫了三聲,人們聽見喜鵲的叫聲,連忙放下手中的活兒,飛快地跑回村里,就聽見嬰兒墜地的哇哇聲。人們明白,這是姜塬姑娘生了孩子。
在姜塬姑娘的辛勤哺育下,孩子得得特別出奇。他一落地就會爬,剛滿月就會走路,不到倆月就會說話,才滿五歲,就身高丈二,膀大腰圓,力大無比。十歲就能擒拿猛虎。他和母親一樣,十分勤勞,非常勇敢。他經常和大家一起上山打獵,不斷把野馬、野牛、野豬捉加有禮貌飼養。他經常和大家一起下田種莊稼。他和大家一起耕種、鋤地、捉蟲,選種。遇到其他部落來偷他們的財物,他和大家一起,拿起木棍,樹枝勇猛地同盜賊搏鬥,每次都是把盜賊打得抱頭鼠竄。這個部落在姜塬的母子帶領下,迅速成長為一個較大的姜氏部落。後來,這個部落的首領曾幫助禹王治理洪水,幫助商湯南征北戰打江山。到達殷商後期,他們同西伯侯姬氏同事盟主殷商,結為莫世之交。姜氏同西伯侯姬氏互通婚姻,好上加親。
人們為了紀念姜塬姑娘,就把這裡稱作“姜塬”了(一九七五年,太公泉發現一座唐代縣令墓葬,出土墓碑記載,“太公泉古稱姜塬”)。
清明祭姜塬
每年的清明節這一天,海內外的華人代表都要到陝西省黃陵縣的黃帝陵前,公祭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五帝之首的黃帝,因為大家都是炎黃子孫。炎黃子孫只祭奠黃帝,冷落了炎帝,好在誰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黃帝的子孫,還是炎帝的後裔,因而也沒人太叫真,去為炎帝抱不平。前幾年河南省又開始公祭顓頊、帝嚳二帝。今年,甘肅省天水市早早大造輿論,要在羲皇故里天水舉辦第一次全球華人公祭比黃帝資格更老的人文始祖、三皇之首的伏羲。好在不是什麼壞事,更不會有誰反對,也就在七月初如期舉行了。
看來在我們這個國家裡,“男尊女卑”的觀念還很根深蒂固的,許多人連炎、黃二帝中到底誰是自己的老祖宗都沒有搞清楚,就糊裡糊塗地認祖歸宗頂禮膜拜。但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有著至少兩億多現代子孫的老祖奶奶,一直被冷落在陝西省武功縣武功鎮的一個無人關注的小村子邊。剛巧這個村子就是散人的祖籍,一個叫羊尾溝的小村莊,這位老祖奶奶就是《詩經。大雅。生民》中歌頌的“厥初生民”的姜嫄。
《史紀 周本紀》載: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由棄到周武王姬發,歷史上記載得明明白白,是第14代。
看了這兩處記載,可以肯定地說,不同於大量的史前傳說人物,姜嫄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而且是周人的女祖宗。她生了棄,也就是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教民稼穡”的后稷,后稷的第14代孫周武王聯合天下諸侯,推翻了殷朝最後一個君主殷紂王,建立了周王朝。其實,根據《帝王紀》所說,周的祖先棄和殷的祖先契,兩人都是帝嚳的兒子,一個是元妃姜嫄所生,一個是次妃簡狄所生。帝嚳還有一個兒子,名字叫放勛,就是五帝之一的堯,是帝嚳的另一個次妃慶都所生。這樣算,棄、契、堯三人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但是查一查地圖,就發現白紙黑字的記載竟然南轅北轍,根本不可能。棄和他的母親姜嫄住在陝西西部的周原上,契和他的母親簡狄生活在河北中部,堯和他的母親慶都居住在山西南部,帝嚳在今天的商丘,而且不是同世之人,帝嚳怎么能是他們共同的父親呢?姜嫄是踩了巨人的足跡懷孕的,生了棄;簡狄是吃了玄鳥蛋懷了孕,生了契;好像堯的母親慶都生堯沒什麼異常說法。說白了,姜原和簡狄都是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末期的女人,生的孩子“知其母不知其父”沒什麼丟人的。但兩人生的兒子對華夏民族都有著卓越的貢獻,並且兩人的後代子孫都成了後世的帝王,所以,後世做史的人“為尊者韙”,硬給倆人強加了一個賢明的帝嚳做父親。
雖然父親不確定,但棄的母親是姜嫄,這是毫無問題的。姜嫄生棄,棄的14代孫姬發建立了周王朝,大封姬姓子弟為各諸侯國國君,據說光是周武王就有近百個同父異母兄弟,再加上像畢公奭這一類叔伯兄弟,總有上百人吧。按照這些人功績的大小和血緣的遠近,周武王給他們不同等級的爵位,分別被分封到全國各地。這些人又在自己的封地逐漸形成了新的氏族。隨著“姓”和“氏”的同一,一個“姬”姓逐漸分化成許多姓氏,這些新的“姓氏”的後代在後來又或者以父名為姓、或者以國為姓,或者以封地名為姓,或者以官職名為姓,或者按以後的職業為姓,就陸陸續續形成了今天的許多姓氏。例如,周武王姬發封弟弟姬旦的(又稱周公旦)大兒子伯禽為魯侯,他的就是今天魯姓的開山鼻祖;到周宣王時,周宣王又封他的弟弟姬友為鄭桓公,姬友就是鄭姓的祖宗。到今天,姜嫄這位老祖母的子孫,有人做過粗略的估算,不下兩億人。根據《元和姓篹》記載,大約今天姓周、姬、魯、鄭、畢、楊、蔣、柯、茅、管、蔡、吳、孫、白、萬、燕、沈、衛、方、柳、賀、孟、董、溫、毛等近百個姓的主體,賈、何、潘、顏、曹、戴、郭等十多個姓的大部分人,王、劉、胡等姓的一部分人,都是姜嫄老奶奶的子孫後代。
姜嫄老奶奶生育、培養、教育的兒子棄,是開創華夏農耕文明的偉大的農藝師。在棄的總結、提高過程中,他的母親既是他的啟蒙人,又是他的助手和傳道者,后稷的豐功偉績傾注著母親的心血,母子倆共同推動了中華農業文明。只不過作為女性,她只能被兒子頭頂的光環所淹沒。她的許多後人中,又有許多偉人名人,在中華民族歷史的長卷中,都為推進中華民族的統一、強盛和發展,建立了不朽的功績。然而大家把她遺忘了,至少是冷落了。雖然在陝西、山西的好幾個地方,都有被傳為姜嫄墓的遺蹟,在上個世紀,經過嚴格的考證,其它的“均為後世人所附會”,只有坐落在陝西省武功縣舊縣城武功鎮西南不到兩公里的塬上,依山為冢,松柏環保的這座不大的陵墓,才是真正的姜嫄墓。武功縣就是遠古有邰氏的故地。姜嫄墓下面不遠處,武功鎮東門外漆水西畔的后稷教稼台,如今被整修一新,偉大的后稷當年就是在這裡教民稼穡的。漆水發源於陝西省的麟遊縣,由西向東流到武功,折向南流入渭水。后稷和他的族人長期就活動在漆水以南和以西、汧水(現在叫千水)以東、渭水以北這一大片被叫做“周原”的地方。
幾乎沒有人來緬懷憑弔這位偉大的老奶奶,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一位詩人來過這裡,他和我一樣,都和這位老奶奶不沾親帶故,臨別給當時的縣長孫某留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文明歷史五千載,薑母恩功可蓋天。”孫縣長自己都不知道姜嫄是他的老祖宗,所以,詩人在歌頌薑母之外的另一層意思算是白扔了。
眾人的祖宗沒人敬,黃帝例外,那是為凝聚團結海內外華人,讓大家不要忘記我們有共同的一個根,就像所有的蒙古人都說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孫一樣。可是,對姜嫄這位偉大的女性,中華民族不該忘記她,她的子孫們更不應當冷落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