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荷蘭學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分析奧地利、比利時、瑞士和荷蘭政治系統,歸納出協商民主理論;在社會上不同階級、地域、文化等所產生的分裂,被所屬陣營納入系統之中,形成“柱狀化”(英語:Pillarisation;荷蘭語:Verzuiling)結構稱“柱狀體”(英語:Pillar;荷蘭語:Zuil),以此結構為前提的聯合政權內,各陣營進行“協調的政治”(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具有以下特徵:
大聯合內閣,納入各柱狀體的菁英
比例性,國會及公共資源等依比例分配之
區域自治,創立個體意識及允許不同文化共同體的法律
相互否決權,各群體共識仍需多數決,少數群體有權否決,但也會被其他群體回報否決阻撓
另外,以協商民主為基礎進而推展出“共識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理論。
理論實質
協商民主的實質,就是要實現和推進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協商民主與選舉(票決)民主結合起來的過程中,始終要體現“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這一現代民主精神,並把它作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內容,引導民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解決利益矛盾,共同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主要形式
 協商民主
協商民主協商民主對於歐美來講,是正在討論和研究的一種新的民主形式。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關注並提出協商民主理論,主要是為了破解選舉(票決)民主的困境,彌補選舉(票決)民主的缺陷。因為西方的傳統是以選舉(票決)為民主的主要形式。自古希臘、古羅馬以來,這種選舉形式在西方的歷史傳統中早已形成。他們是在研究選舉(票決)民主的不足中提出可以用協商民主來彌補其不足。對他們來講,協商民主是新事物。
對中國來講,恰恰相反,中國人學會選舉(票決)民主是近代以來的事情,而且現在我們還不是很成熟,還在繼續完善。而中國人對協商民主是有悠久傳統的。就以我們黨來說,早在建國初期就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人民政協是我國實行協商民主的主要渠道之一。在政協這個機構里,各個黨派、各個階層、各個界別、各個民族、各個宗教的政協委員,都能夠按照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要求,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獻計獻策。西方協商民主還主要停留在學者層面上,還是一種民主理想,而我國的協商民主早已經通過政治協商會議這種組織形式在實施,而且還在積極探索新的協商民主形式,如浙江溫嶺、河北邯鄲的民主懇談會就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順便說一下,協商民主可以有多種形式,不僅僅指的是政治協商會議里的協商,還有其他許多形式。比如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或者人民政府召開公共政策聽證會,比如有的地方實行的民主懇談會,都是協商民主的形式。協商民主在中國不是水土不服,而是深受歡迎,我們完全可以通過這種形式來保證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由柳洪平創建。
產生背景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協商民主異軍突起,在羅爾斯、哈貝馬斯等著名政治哲學家的推動下,協商民主逐漸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承認,成為當代西方民主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步步緊逼下,人們發現:“協商民主是一種具有巨大潛能的民主類型,它能夠有效地回應文化間對話和多元文化的社會認知的某些核心問題。”
實際上,無論是在希臘城邦的民主政治中,還是在現代的民主理論家盧梭、杜威那裡,我們都能發現協商民主的影子。儘管人們可以把政治意義上的協商追溯到古代雅典時期,但協商民主理論作為一種民主理論模式的興起則只是上個世紀末的事情。一般認為,第一次在學術意義上使用協商民主概念的應該是1980年約瑟夫·畢塞特(Joseph M. Bessette)在《協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數原則》一文中首次使用“協商民主”一詞。後來,伯納德·曼寧(Benard Manning)、喬舒亞·科恩(Joshua Cohen)等人都曾經對此做出過若干討論。
羅爾斯和哈貝馬斯的加入使得協商民主聲勢大振,兩個人都在自己出版的著作中提到協商民主。尤其是哈貝馬斯以話語理論為基礎,將偏好聚合的民主觀念轉換為偏好轉換的理論,從而使協商民主真正地成為上個世紀末最引人矚目的民主理論。其後,大衛·米勒(David Miller)、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辛格、喬治·瓦拉德斯(Jorge Valadez)等人的加入使得協商民主的研究更加波瀾壯闊,成為當代西方重要的民主理論之一。
協商民主的興起有其複雜的社會背景,但毋庸置疑,解決多元文化帶來的問題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從單一的均質社會到多元的異質社會的轉化打破了普遍主義宰制下的、同質的民主文化的概念。多元現代性的挑戰不僅來自複雜的公共事務,更來自多元文化領域。
哈貝馬斯理論
在哈貝馬斯那裡,協商民主的過程也就是共識形成的過程,也即民主的過程,這被米歇爾曼視為法理髮生學。哈貝馬斯認為,由於基本原則的差異,這一過程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可能,同化共識、交疊共識、協商共識是其中最典型的三種方式。
第一種可能即所謂的同化共識,即:“只要任何一種正義觀念都不可分割地為某種特殊的善的概念所浸染,那么,即使是在判斷正義問題時,我們也不可能超越我們自己的自我理解和世界觀所確定的視角。在這種情況下,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只能以同化的方式達成一致,或者是他們放棄自己的標準為我們所同化(羅蒂),或者是我們放棄自己的標準而皈依他們的(麥金泰爾)。”應該說,同化共識更強調文化的轉型與替代,適用於傳統文化向現代文明的過渡。
另一種可能是交疊共識。哈貝馬斯以羅爾斯為代表指出:“如果我們考慮到‘現代’世界觀的多樣性,由於其內在的普遍主義潛力,它們是能夠互相寬容的,那么,我們就可以指望在政治正義問題上達成一種重疊的共識(羅爾斯)。”交疊共識更適合亞文化多元區別並不是極端的情況,尋找多元文化交集,從而形成共識,並在這一基本共識上建立民主政治是自由主義的一貫主張,在英美文化中更為典型。
在這兩種可能之外,哈貝馬斯更推崇協商共識。即“相對於各自的自我解釋和世界觀,每一方都參照一個共同接受的道德視角,在話語的均衡狀態(和互相學習)的條件下,這種道德視角要求各種視角不斷地消解自己的中心地位。”
協商民主仍然是一種基於自由主義的民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實現多文化共存的途徑仍然離不開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然而,現代憲政民主對文化多元的複雜現實缺乏應對性,如果不加以改造,多元文化主義的訴求亦很難得以滿足。因此,現代憲政民主必須更新其制度形式從而適應多元文化主義的要求。包括羅爾斯、哈貝馬斯、金里卡、蓋爾斯頓等人在內的所有政治思想家均表達了這樣一個願望。
協商民主強調了協商與對話在解決多元文化背景下民主問題的重要性,但對於協商的過程卻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塔利闡釋了一種文化間的對話,這一對話是以共識的自由與協商原則、平等對待以及相互承認等一系列內容組成的,在那裡,參與者能從他們歧異的文化和政治傳統出發創製一個共同的政體。塞拉·本哈比(SeylaBenhabib)則提出了一種“複雜的多元文化對話”(complexmulticulturaldialogue)的模式,把個人視為公民社會內部文化交流與競爭過程的核心。海庫·帕瑞克(BhikhuParekh)構想了一種多數與少數之間的對話。他為這一對話設定了一個起點,一個是社會中“可操作的公共價值”(operativepublicvalues),另一個是文化間評估(interculturalevaluation)的產出過程。
在協商民主模式中,哈貝馬斯以協商民主為核心的憲法愛國主義的解決方案十分引人注目。哈貝馬斯以自由主義的憲政框架為基礎,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解決多元文化主義的憲法愛國主義理論。哈貝馬斯認定:“我們必須把民主過程植根於一種“憲法愛國主義”之中。”這樣,哈貝馬斯就將多元文化的解決寄託於所謂的“憲法愛國主義”。在他看來,每一個民族國家對憲法原則的解釋,都是從自身的歷史經驗語境出發的,因此,它能做到在倫理上保持不偏不倚。
憲法愛國主義構成了哈貝馬斯合法的法律秩序的重構的一個前提,也就是說,合法的政治法律制度都需要以憲法為基礎展開。哈貝馬斯指出:自由主義政治文化的首要特點是相信:“能夠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創造並維護一種超越所有差異的共同的公民意識,這個特點就是所有的人都共同依據承諾平等權利的普遍主義憲法原則。”
哈貝馬斯指出:“任何一個群體,如果要把自己建設成一個由自由而平等的成員構成的法律共同體,就必須作出一個原初決定。為了合法地通過成文法調節他們的生活,他們進入一種共同的實踐為自己制定一部憲法。制定憲法實踐的意義在於共同探求並確定參與者必須互相承認為公平和有效的權利(在上文所說的前提之下)。因此,這種實踐要依靠兩個先決條件:以成文法作為有約束力的調節規則;以話語原則作為理性的審慎協商和決策的指導原則。”
以憲法愛國主義為基礎,哈貝馬斯從哲學角度分析了移民與政治認同的雙層同化。即:
“(1)贊同解釋視界範圍內的憲法原則。解釋視界是由公民的倫理—政治方面的自我理解和當地的政治文化所決定的;這就意味著認同接納社會中公民自主制度化以及公開使用理性實踐化的方式和方法;
(2)再進一步的同化就是要做好文化適應的準備。這種適應不光是外表熟悉,而且要深入體會當地的生活方式、文化實踐以及文化習俗;這種同化貫穿到了倫理—文化一體化層面之中,所以相對於(1)中所要求的政治社會化而言,這種同化對於移民傳統文化的集體認同產生了更加深刻的影響。”
哈貝馬斯試圖以其協商理論為基礎,以憲法愛國主義解決多元文化衝突。在他那裡,憲法愛國主義的倫理內涵一方面不能有損於法律制度對於亞政治層面上的倫理共同體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它還必須加強多元文化社會中彼此共存的生活方式的多元性與同一性特徵。在這裡,哈貝馬斯試圖通過在亞政治層面保持倫理共同體的中立性,公民的總體性就不再是由某種實體性的價值共識來加以維持,而只是由有關合法的立法程式和行政程式來加以保證。
在哈貝馬斯看來,公民要在政治上保持一體化,需要有一個共同擁護的合理信念,即“政治公共領域中交往自由的發揮、解決衝突的民主程式以及法治國家對於統治的引導,都為約束非法權力和確保行政權力體現所有人的利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樣,在文化與制度之間就達成了這樣一個良好的互動,即“普遍主義的法律原則表現在一種程式主義的共識之中,而這種共識從憲法愛國主義角度來看又必須扎概到各種特定的政治文化的歷史語境中去。”
圖書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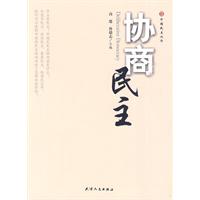 協商民主
協商民主書
名: 協商民主
作者:高建,佟德志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0-3-1
ISBN: 9787201064956
開本: 16開
定價: 4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