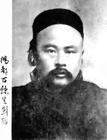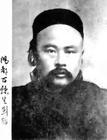劉鶚(1857~1909)
正文
近代小說家。字鐵雲,別署洪都百鍊生。江蘇丹徒(今鎮江市)人,寄籍山陽(今淮安)。出身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場文字。他承襲家學,致力於數學、醫學、水利學等實際學問,並縱覽百家,喜歡收集書畫碑帖、金石甲骨。其《鐵雲藏龜》一書,最早將甲骨卜辭公之於世。早年科場不利,曾行醫和經商。光緒十四年(1888)至二十一年,先後入河南巡撫吳大澂、山東巡撫張曜幕府,幫辦治黃工程,成績顯著,被保薦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知府任用。光緒二十三年(1897),應外商福公司之聘,任籌采山西礦產經理。後又曾參與擬訂河南礦務機關豫豐公司章程,並為福公司擘劃開採四川麻哈金礦、浙江衢嚴溫處四府煤鐵礦,成為外商之買辦與經紀人。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事起,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劉鶚向聯軍處購得太倉儲粟,設平糶局以賑北京飢困。三十四年(1908)清廷以“私售倉粟”罪把他充軍新疆,次年死於烏魯木齊。劉鶚生當封建王朝統治即將徹底滅亡的前夕,一方面反對革命,同時也對清末殘敗的政治局勢感到不安和悲憤。他認為當時“國之大病,在民失其養。各國以盤剝為宗,朝廷以朘削為事,民不堪矣。民困則思亂”(給黃葆年的信)。他要求澄清吏治,反對“苛政擾民”,以緩和階級矛盾。在西方文明潮水般湧入的情況下,他開出的“扶衰振敝”的藥方是,借用外國資本興辦實業,築路開礦,使民眾擺脫貧困,國家逐步走向富強。他在給羅振玉的信中說:“晉礦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但在帝國主義對中國加緊侵略步伐並大肆進行經濟掠奪的情況下,劉鶚對外商又多所遷就,其所定之制往往有損於國家主權和人民利益,因此“世俗交謫,目為漢奸”。
劉鶚信奉太谷學派,為太谷學派創始人周太谷弟子李光炘的得意門生之一。他曾在給黃葆年的信中說,“一事不合龍川(李光炘)之法”,“輒怏怏終夜不寐,改之而後安於心”。又在《老殘遊記》中借璵姑與黃龍子之口宣揚他所承襲和發揮的太谷學派精義,以為宋儒理學的理、欲之分不近人情;在處世接物上倡導以人情為根據,做到“發乎情,止乎禮義”。同時認為儒、釋、道三教殊途同歸,其根本都在“誘人為善,引人處於大公”。他又在給黃葆年的信中說,該派的“聖功大綱,不外教養兩途”,推黃“以教天下為己任”,而自承“以養天下為己任”。太谷學派之精神對劉鶚一生思想、行事及小說創作都有深刻的影響。
劉鶚的小說《老殘遊記》是晚清的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全書共20回,光緒二十九年(1903)發表於《繡像小說》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後重載於《天津日日新聞》,始全。原署鴻都百鍊生著。作者在小說的自敘里說:“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說是作者對“棋局已殘”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難遭遇的哭泣。
小說寫一個被人稱做老殘的江湖醫生鐵英在遊歷中的見聞和作為。老殘是作品中體現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搖個串鈴”浪跡江湖,以行醫餬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同情人民民眾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俠膽義腸,盡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隨著老殘的足跡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東一帶社會生活的面貌。在這塊風光如畫、景色迷人的土地上,正發生著一系列驚心動魄的事件。封建官吏大逞淫威,肆意虐害百姓,造起一座活地獄。
小說的突出處是揭露了過去文學作品中很少揭露的“清官”暴政。作者說“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歷來小說皆揭贓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第16回原評)。劉鶚筆下的“清官”,其實是一些“急於要做大官”而不惜殺民邀功,用人血染紅頂子的劊子手。玉賢是以“才能功績卓著”而補曹州知府的。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衙門前12個站籠便站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於朝棟一家,因和強盜結冤被栽贓,玉賢不加調查,一口咬定是強盜,父子三人就斷送在站籠里。董家口一個雜貨鋪的掌柜的年輕兒子,由於酒後隨口批評了玉賢幾句,就被他抓進站籠站死。東平府書鋪里的人,一針見血地說出了玉賢的真相,“無論你有理沒理,只要他心裡覺得不錯,就上了站籠了”。玉賢的邏輯是:“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語說的好,‘斬草要除根’。”為了飛黃騰達,他死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屠刀。老殘題詩說,“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殺民如殺賊,太守是元戎”,深刻地揭示了他們的本質。剛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他曾拒絕巨額賄賂,但卻倚仗不要錢、不受賄,一味臆測斷案,枉殺了很多好人。他審訊賈家十三條人命的巨案,主觀臆斷,定魏氏父女是兇手,嚴刑逼供,鑄成駭人聽聞的冤獄。
小說還揭露了貌似賢良的昏官。山東巡撫張宮保,“愛才若渴”,搜羅奇才異能之士。表面上是個“禮賢下士”方面的大員,但事實上卻很昏庸。他不辨屬吏的善惡賢愚,也判斷不出謀議的正確與錯誤。他的愛才美德,卻給山東百姓帶來了一系列的災難。“辦盜能吏”玉賢是他賞識的,剛弼也是他倚重的,更為嚴重的是他竟錯誤地採用史鈞甫的治河建議,廢濟陽以下民埝,退守大堤,致使兩岸十幾萬生靈遭受塗炭。
在小說中楔入的桃花山一段插話中,著重寫了隱居在荒山中的兩個奇人璵姑和黃龍子。通過兩人的言行宣揚了作者所信奉的太谷學說,同時對當時的革命運動,即所謂“北拳南革”,即北方的義和團和南方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進行了惡毒的詆毀和詛咒,攻擊他們都是“亂黨”。義和團來勢猛,他說“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革命黨起勢緩慢,他認為“莫說是皮膚小病,要知道渾身潰爛起來,也會致命的”;告誡人們不要“攪入他的黨里去”,表現了作者落後、反動的一面。小說的第一回,就是作者對於當時政治的象徵性圖解。他把當時腐敗的中國比作一艘漂浮在海上行將被風浪所吞沒的破舊帆船。船上有幾種人:一種是以船主為首的掌舵管帆的人,影指當時上層的封建統治集團。作者認為他們“並未曾錯”,只是因為是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不意遇上了風浪,所以毛了手腳,加上未曾預備方針,遇了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遮了,所以就沒有依傍。再一種人是乘客中鼓動造反的人,比喻當時的革命派,污衊他們都是些“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英雄”。宣揚如果依了他們,“這船覆得更快了”。還有一些肆意搜刮乘客的“下等水手”,則是指那些不顧封建王朝大局、恣意為非作惡的統治階級爪牙。作者對他們也很反感,視為罪人。究竟怎樣才能挽救這隻行將覆滅的大船呢?作者認為:唯一的辦法是給它送去一個“最準的”外國方向盤,即採取一些西方文明而修補殘破的國家。
小說中所寫的人物和事件有些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的。如玉賢指毓賢,剛弼指剛毅,張宮保(有時寫作莊宮保)為張曜,姚雲松為姚松雲,王子謹為王子展,申東造為杜秉國,柳小惠為楊少和,史鈞甫為施少卿等,或載其事而更其姓名,又或存姓改名、存名更姓。黑妞、白妞為當時實有之伎人,白妞一名小玉,於明湖居奏伎,傾動一時,有“紅妝柳敬亭”之稱。廢濟陽以下民埝,乃光緒十五年(1889)實事,當時作者正在山東測量黃河,親見其慘狀。正如作者所自言:“野史者,補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諸子虛,事須征諸實在。”(第13回原評)
《老殘遊記》的藝術成就在晚清小說里是比較突出的。特別在語言運用方面更有其獨特成就。如在寫景方面能做到自然逼真,有鮮明的色彩。書中千佛山的景致,桃花山的月夜,都明淨、清新。在寫王小玉唱大鼓時,作者更運用烘托手法和一連串生動而貼切的比喻,繪聲繪色的描摹出來,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覺。所以魯迅稱讚它“敘景狀物,時有可觀”(《中國小說史略》)。
劉鶚還曾寫有《老殘遊記》續集,作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之間。據劉大紳說,共有14回,今殘存9回。1934年在《人間世》半月刊上發表4回,次年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6回的單行本。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老殘遊記資料》收錄了後3回。續集前6回,雖然也有對官僚子弟肆意蹂躪婦女惡行的揭露,但主要的是通過泰山斗姥宮尼姑逸雲的戀愛故事及其內心深入細微的思想活動,以及赤龍子的言談行徑,宣傳了體真悟道的妙理。後 3回則是描寫老殘游地獄,以寓其懲惡勸善之旨。此外還殘存《外編》4700餘字,寫於光緒三十一年以後。
除《老殘遊記》外,劉鶚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術》,治河著作《歷代黃河變遷圖考》、《治河七說》、《治河續說》,醫學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鐵雲藏龜》、《鐵雲藏陶》、《鐵雲泥封》,詩歌創作《鐵雲詩存》。1980年齊魯書社出版了《鐵雲詩存》,其詩清新俊逸,功力頗深,反映了他的一些行蹤和思想感情。
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