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各說
中國自宋朝以來就有“四大書院”的說法,但是究竟哪四所書院可以稱得上“四大”,則各有各的見解。
普遍認可為應天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
1、宋末馬端臨《文獻通考》中《學校考》宋朝 四大書院說:
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徂徠書院。
此說法沒有爭議。范成大《驂鸞錄》和清代全祖望均贊同,朱熹《石鼓書院記》:“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天下四大書院的來源最早是宋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卷47,並指出嵩陽後來無聞,後來的歷史學家皆以《文獻通考》為據。
2、北宋 六大書院說:
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
(中華民國時期盛朗西、陳登原《中國書院制度》)
3、北宋 八大書院說:
應天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徂徠書院
(南宋詩人范成大推舉,民國陳登原《國史舊聞》)
應天書院
書院介紹
 四大書院之首-應天書院
四大書院之首-應天書院應天書院起源之早,規模之大,持續之久,人才之多,居古代四大書院之首。所以,《宋史》記載:“宋朝興學,始於商丘”。1998年國家郵電部在商丘舉辦了四大書院郵票首發儀式。
應天府書院即應天書院、睢陽書院,其前身為南都學舍,為五代後晉時的商丘人楊愨創辦,位於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國家4A級風景區商丘古城南湖畔,為中國古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正式賜額為應天書院,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應天書院改為府學,為應天府書院,慶曆三年(1043年)改為南京(北宋陪都,今河南商丘)國子監,為北宋最高學府。北宋初書院多設于山林勝地,唯應天書院設於繁華鬧市,人才輩出。隨著晏殊、范仲淹等的加入,應天書院逐漸發展為北宋最具影響力的書院,是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個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被尊為北宋四大書院之首。
創辦原因
 應天府書院
應天府書院第一,北宋科舉取士規模日益擴大,而宋初官學卻長期處於低迷不振的狀態。士人求學需求很大,卻苦無其所,在這種情況下,書院應運而生,起到了填補官學空白的作用,為廣大士子提供了讀書求學的場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術,鼓勵民間辦學。宋初提倡文治,但國家一時又無力大量創辦官學,故朝廷對書院給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贊助。像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都得到朝廷賜書、賜匾額、賜學田和獎勵辦學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這些支持無疑是促進宋初書院興盛的直接動因之一。
第三,佛教禪林制度的影響。佛教出於僻世遁俗、潛心修行的宗旨,多選擇環境僻靜優美的山林建立寺廟,五代及宋初的書院也大多建於山林名勝之中。佛教禪林集藏經、講經、研經於一體,也對書院教學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如:書院的講會制度就是借鑑了佛教僧講和俗講的講經方式,書院教學的講義和語錄等形式,也是來源於佛教禪林制度。
第四,印刷術的套用,使書籍的製作與手寫本相比,變得極為便利,是促成宋代書院興旺發展的重要基礎。書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眾都可以擁有的,才有可能使書院擁有豐富的藏書,並真正成為面向社會的教學研究場所。
書院簡史
後晉始創
唐哀宗天佑四年(907)唐朝滅亡,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分裂時期,官學遭受破壞、庠序失教,中原地區開始出現一批私人創辦書院,應天府書院由此而生。
 書院鳥瞰圖
書院鳥瞰圖書院歷史最早追溯到五代的後晉,楊愨在歸德軍將軍趙直扶助下聚眾講學,後來他的學生戚同文繼續辦學,應天府書院的前身就是當時歸德軍的南都學舍趙直為其築室聚徒。
北宋立國初期,急需人才,實行開科取士,睢陽學舍的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登第者達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遠千里而至宋州求學者絡繹不絕,出現了“遠近學者皆歸之”的盛況,睢陽學舍逐漸形成了一個學術文化交流與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後,學校一度關閉。
北宋盛世
宋真宗時,追念宋太祖應天順時,開創宋朝,1005年將其發跡之處宋州(今商丘)改名應天府。1008年,當地人曹誠“請以金三百萬建學於先生(楊愨)之廬”,在其舊址建築院舍150間,藏書1500卷,並願以學捨入官,並請令戚同文之孫戚舜賓主院,以曹誠為助教,經由應天府知府上報朝廷,受到宋真宗讚賞,翌年將該書院正式賜額為“應天府書院”。
學化書院
書院得到官方承認,成為宋代較早的一所官學化書院。時人稱:“州郡置學始於此”,天下學校“視此而興”。1043年,宋仁宗下旨將應天書院改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之一。後該書院經應天知府、文學家晏殊等人加以擴展。范仲淹曾受教於此,及後曾在書院任教,盛極一時,與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合稱中國四大書院。
應天府的辦學模式,令當地書院風氣大盛。李覯先在南城創辦了盱江書院,求學人數曾達1000多人;杜子野在宜黃興辦鹿岡書院,曾鞏在臨川辦起了興魯書院,並親自製訂校規並任教,還聘請歐陽修、王安石等名人教授生徒。
幾番廢立
明朝嘉靖十年(1531),御史蔡璦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學改建,而沿用舊名,重建書院,但萬曆七年(1579),宰相張居正下令拆毀天下書院,應天書院遂廢。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歸德知府重建“范文正公講院”又名“文正書院”于歸德府東,以紀念范仲淹掌教應天府學,講學育士。他效法范仲淹的精神,親自執書講學,一時培育了許多人才。
順治十五年(1658),符應琦重修講堂,集諸士而課之。清乾隆十三年(1748) 知府陳錫格又重修應天府書院,光緒二十七年(1901),舉國廢科舉,興學校,詔令各省的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的書院改為中學堂。因此,書院改為“歸德府中學堂”(簡稱歸德中學)。
再煥生機
2003年河南省政府批准應天書院在宋代原址附近進行修復,並被列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點旅遊工程項目,景區規劃占地121.6畝,總建築面積4116.8平方米,道路占地2523.4平方米。工程委託河南大學古建築研究院設計,整個書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為影壁、牌樓、大門及東西側門,前講堂及東西側門、明倫堂及東西配房、藏書樓及東西側門,饌堂、教官宅、崇聖殿、東西偏房、魁星樓及東西廊房。2004年2月應天書院修復工程開始一期工程建設。2005年底主體工程崇聖殿竣工,2006年應天書院的大門、圍牆、道路等工程完成。2007年10月1日正式對遊客開放。2009年8月應天書院二期工程開建,主要是講堂等復原工程。應天書院修建全部完成後,將展現北宋時期的文化、教育、科學、知識等內容,增加遊客對北宋歷史文化的全面了解,豐富商丘古城旅遊區古文化建築觀光游和學術學習游的內涵,增強古城旅遊區對中國傳統文化愛好者、專家和文化學者的吸引力,提升商丘古城旅遊區的品位和影響力。
應天書院,又名睢陽書院、南京書院。宋真宗正式賜書並親自題寫應天府書院,位於商丘市睢陽區商丘古城南,因為商丘在唐供稱為宋州睢陽郡,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為南京,為當時四京之一。商丘瀕臨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輻輳,自古以來,一直為江淮屏障,一方都會。古代書院多設于山林,唯應天書院立於繁華鬧市,歷來人才輩出,千年來,培養俊傑數不勝數。應天書院位於商丘古城之南,其前身是後晉時楊愨所辦的私學,後經其學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發展,北宋政權開科取士,應天書院人才輩出,百餘名學子在科舉中及第的竟多達五六十人。文人、士子不遠千里而至宋州(今商丘)求學者絡繹不絕,出現了“遠近學者皆歸之”的盛況,其中就有那位吟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應天書院逐漸形成了一個學術文化交流與教育中心。
 應天書院正門
應天書院正門宋真宗時,因追念太祖自立為帝,應天順時,將宋太祖趙匡胤發跡之處宋州(今商丘)於1006年改為應天府,1014年又升為南京,處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正式將該書院賜額為“應天府書院”。時人稱“州郡治學始於此”,天下書院“視此而興”,應天書院開創了古代興學的先例,成為古代書院典範,後世稱為“慶曆興學”。宋仁宗時,慶曆三年(即l043年)將應天書院這一府學改為南京國子監,使之成為北宋的最高學府之一,相當於現在的社會科學院,與東京國子監同為宋朝最高學府。後該書院在曹誠等人尤其是應天知府、著名文學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擴展。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學家晏殊出任應天知府,聘請著名學者王洙為書院“說書”,王洙博學多才,應天府書院在他主持下“其名聲著天下”。仁宗景祐二年(1035),應天府書院改為府學,成為皇家認可的公辦書院,晏殊又聘請因守孝服喪而退居南京(今商丘)的范仲淹執教,范仲淹年輕時在應天書院求學,後又在應天書院任教,可以說應天書院成就了范仲淹,也因范仲淹而名聲更甚。任教期間,范仲淹撰寫《南京書院提名記》。當時的應天府書院,是中州的第一大學府,顯赫幾世。據《宋史》記載:“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晏殊)始。”從大中祥符以後的二十餘年間,應天府書院的學生“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台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現存有大成殿、明倫堂、月芽池等建築。原大成殿內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倫堂為學堂。這兩座建築均為歇山式建築。大成殿為祭孔之地,明倫堂為應試地。
書院地位
應天書院是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個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被尊為 四大書院之首。
宋仁宗慶曆年三年(1043),擔任宋廷參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貢舉、擇官長”等十項改革主張,取胡瑗蘇湖教法改革當時教育系統,當時應天府已升格為南京國子監,先行實施改革,一改當時崇尚辭賦的浮淺學風,重經義、重時務、重實際。
范仲淹執教應天府書院時,經常教導學生要“從德”,而不能僅以科舉仕進作為求學的最終目的。在他提出的“為學之序”中,學、問、思、辨四者也是最後落實到“行”上。後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講院碑記》,建藏書樓,回顧范仲淹的講學生涯。
在范仲淹主講該書院的過程中,率先明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匡扶“道統”的書院(學校)教育宗旨,並以此確立了培養“以天下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動了宋初學術、書院(學校)學風朝經世致用方面的轉變;後來又通過“慶曆興學”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勵了這些成就,進一步推動了北宋書院的發展,明確了學術、大師在書院中的重要作用和歷史地位。
嶽麓書院
書院介紹
嶽麓書院位於湖南長沙南嶽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嶽麓山腳,是中國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書院。現為長沙市文化旅遊主要景點之一。
歷史變遷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嶽麓書院始建於北宋初期。北宋開寶六年(973),朱洞以尚書出任潭州太守,鑒於長沙嶽麓山抱黃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靜環境,接受了劉鰲的建議,在原有僧人興辦的學校基礎上創建了嶽麓書院。初創的書院分有“講堂五間,齋舍五十二間”,其中“講堂”是老師講學道的場所,“齋堂”則是學生平時讀書學習兼有住宿的場所。嶽麓書院的這種中開講堂、東西序列齋舍的格局一直流傳至今。初設講堂5間,齋室52間。宋太宗鹹平二年(999),李允則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繼續擴建書院的規模,增設了藏書樓、“禮殿”(又稱“孔子堂”),並“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一方面積極取得了朝廷對嶽麓興學的支持,以促進書院的更大發展。鹹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賜書嶽麓書院,其中有《釋文》、《義疏》、《史記》、《玉篇》、《唐韻》等經書。當時書院學生正式定額六十餘人,奠定了書院的基本格局。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經學家周式擔任山長主持嶽麓書院後,書院得到迅速的發展,學生定額愈百人,周式本人還得到宋真宗的召見和鼓勵。,賜“嶽麓書院”題額,於是“書院稱聞天下,鼓簡登堂者不絕”,到南宋的乾道年間,嶽麓書院達到鼎盛時期。
湖湘學派
著名理學家張栻主持嶽麓書院,他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為辦學的指導思想。在教學方面,提出“循序漸進”、“博約相須”、“學思並進”、“知行互發”、“慎思審擇”等原則;在學術研究方面,強調“傳道”、“求仁”、“率性立命”。從而培養出一批如吳獵、趙方、游九言、陳琦等經世之才的優秀學生,湖湘學派多數學者也在嶽麓書院學習過。一時間,大批遊學的士子前來書院研習理學問難論辯,有的還“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當時的嶽麓書院成為全國聞名的傳習理學的基地。南宋淳熙七年(1180),張栻去世後,朱熹、真德秀等人對嶽麓書院的辦學和傳播理學,也表現出極大的熱忱。朱熹還將《白鹿洞書院教條》人微言輕正式的學規,頒於嶽麓書院。,朱熹曾兩次來此講學,當時學生達千人,從而使嶽麓書院有“瀟湘洙泗”之譽,幾與孔子在家鄉講學的地方並稱。從元、明至清初,由於戰亂,嶽麓書院曾兩度遭到焚毀,後來雖然得以重建和恢復,已不復舊觀。清初。書院被禁。後康熙為了表彰理學,放寬書院政策。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書“學達性天”匾額,並以十三經、二十一史、經書講義等遣送至嶽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書“道南正脈”匾額送至嶽麓山,嶽麓書院又得以復興。復興後的麓書院,除了對齋舍屢加擴建外,其書院性質也由民辦而逐漸演化為官辦。乾隆十九年(1754),曠敏本被聘為嶽麓書院山長,任職約三年,後出任石鼓書院山長,因學問精湛,出類拔萃,倍受時人稱頌,士子爭以出其門下為幸。隨著乾嘉考據學的興起,嶽麓書院往往由從事詁經考史的著名漢學家主持,學習的內容也由理學轉向經史考證,特別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間,更以“群經教授諸子”。此後羅典任山長,“唯以治經論文,啟誘後進”。道光年間巡撫吳榮光在嶽麓書院增設“湘水校經堂”,專以研習漢學為主。嶽麓書院的最後一任山長是王先謙,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經學家。清代的嶽麓書院,集聚了一代常識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師,培養出諸如王夫之、陶樹、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國藩、郭嵩濤、李元度、唐才常、沈藎、楊昌濟等著名的湖湘學者。
千年學府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議的呼聲中,延續了近千年的嶽麓書院正式改為湖南高等學堂。爾後相繼改為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湖南工業專門學校,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至今,歷經千年,弦歌不絕,故世稱“千年學府”。嶽麓書院自創立伊始,即以其辦學和傳播學術文化而聞名於世。書院大門橫匾“嶽麓書院”四個大字,兩邊對聯“惟楚有才,於斯為盛”。講堂正中懸清乾隆御書“道南正脈”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節”四個高1.6米、寬1.2米大字。左右兩廊有清歐陽正煥所書“整齊嚴肅”石刻。講堂屏風正向刊張村撰《嶽麓書院記》。麓書院占地面積21000平方米,現存建築大部分為明清遺物,主體建築有頭門、二門、講堂、半學齋、教學齋、百泉軒、御書樓、湘水校經堂、文廟等,分為講學、藏書、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連線,合為整體,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建築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
嵩陽書院
書院介紹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嵩陽書院,位於河南省登封市區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極峰,面對雙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陽而得名嵩陽書院。創建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時,時稱嵩陽寺,至唐代改為嵩陽觀,到五代時周代改建為太室書院。宋代理學的“洛學”創世人程顥、程頤兄弟都曾在嵩陽書院講學,此後,嵩陽書院成為宋代理學的發源地之一。明末書院毀於兵燹,清代康熙時重建。嵩陽書院經歷代多次增建修補,規模逐漸形成,布局日趨嚴整。書院的建制,古樸雅致,大方不俗。
書院學制
嵩陽書院學制,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它始於唐朝,興盛於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興學堂以後書院制才被廢除。教學特點:嵩陽書院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經過近千年的衡讀發展,積累了豐厚的教學經驗,其特點主要是:1、書院既是教育教學的機關,又是學術研究的機關,實行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2、書院盛行講會制度,允許不同學派,不同觀點進行講會,開展爭辯。3、書院的教學,實行“門戶開放”,有教無類,不受地域限制。4、書院以學生個人讀書鑽研為主,十分注重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並採用問難論式。注意啟發學生的思維能力。5、書院內的師生關係融洽,感情深厚。書院的名師,不僅以淵博的知訓教育學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氣節感染學生。
名家輩出
嵩陽書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顆明珠,中國古代的高等學府。宋初,國內太平,文風四起,儒生經五代久亂之後,都喜歡在山林中找個安靜的地方聚眾講學。登封是堯、舜、禹、周公等曾經居住過的地方。據記載,先後在嵩陽書院講學的有范仲淹、司馬光、程顥、程頤、楊時、朱熹、李綱、范純仁等二十四人,司馬光的巨著《資治通鑑》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陽書院和崇福宮完成的。號稱“二程”的程頤,程顥在嵩陽書院講學10餘年,對學生一團和氣,平易近人,講學鮮感,通俗易懂,宣道勸儀,循循善誘。學生虛來實歸,皆都獲益,有“如沐春風”之感。康熙辛卯年,全省在開封選拔舉人,錄取名額一縣不足一人,僅登封就中了五個。名儒景冬,就這於嵩陽書院,中進士後,曾九任御史。嵩陽書院正是擁有了得天獨厚的師資條件,聲名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為北宋影響最大的書院之一。
書院珍寶
院內的漢封將軍柏人稱“稀世珍寶”。嵩陽書院內原有古柏三株,西漢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劉徹游嵩岳時,見柏樹高大茂盛,遂封為“大將軍”,“二將軍”和“三將軍”。大將軍柏樹高12米,圍粗5.4米,樹身斜臥,樹冠濃密寬厚,猶如一柄大傘遮掩晴空。二將軍柏樹高18.2米,圍粗12.54米,雖然樹皮斑駁,老態龍鍾,卻生機旺盛,虬枝挺拔。樹幹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門庭過道,樹洞中可容五、六人。兩根彎曲如翼的龐然大枝,左右伸張,形若雄鷹展翅,金雞欲飛。每當山風吹起,枝葉搖動,如響環佩,猶聞絲竹之音。三將軍柏毀於明末。關於將軍柏樹齡一直是個神秘的話題。該樹從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趙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陽有周柏,閱世三千歲”的讚美詩句。經林學專家鑑定,將軍柏為原始柏,樹齡有4500年,是中國現存最古最大的柏樹。細心的遊人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二將軍柏比大將軍柏大得多,為什麼被封為“第二”呢?這裡有個“先入為主”的傳說,動人的傳說,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潑墨揮毫,賦詩讚頌,更留給人們以啟示。巍巍將軍柏,給嵩陽書院增添了歷史的滄桑感和濃郁的感染力。門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稱。全稱為《大唐嵩陽觀紀聖德盛應以頌碑》,唐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寬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內容主要敘述嵩陽觀道士孫太沖為唐玄宗李隆基煉丹九轉的故事。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額徐浩的八分隸書。字態端正,剛柔適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隸書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噸,僅碑帽就有10多噸重,古時,人們是怎樣將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千百年來,凡到嵩陽書院的遊人都要提及這個問題。在民間,“智立唐碑”這個充滿智慧的傳說故事,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們,成為品賞大唐碑的重要內容之一。嵩陽書院在中國歷史上以理學著稱於世,以文化瞻富,景觀奇特名揚古今。山巒環拱、溪水長流、松柏參天、環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紀故宮銘而文明。書院主要文物有西漢的“將軍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千年道場
嵩陽書院在歷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場所,但時間最長,最有名氣的是作為儒教以聖地之後,嵩陽書院初建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為嵩陽寺,為佛教活動場所,僧待多達數百人。隋煬帝大業年間(605——618年),更名為嵩陽觀,為道教活動場所。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名為嵩陽書院,以後一直是歷代名人講授經典的教育場所。明末書院毀於兵火,歷經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時期,學田1750多畝,生徒達數百人,藏書達2000多冊。清代末年,廢除科舉制度,設立學堂,經歷千餘年的書院教育走完了這的歷程。但是,書院作為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永遠載入史冊。嵩陽書院在古代並不是單純的指一個院落而言,而是由一個主體院落和周圍多個單體建築群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較廣闊。大至而言,建築共分五進院落,由南向北,依次為大門,先聖殿,講堂,道統祠和藏書樓,除我們看到的嵩陽書院建築外,屬於書院的建築物,比較有名的還有位於嵩陽書院東北逍遙谷疊石溪中的天光雲影亭、觀瀾亭、川上亭和位於太室山虎頭峰西麓的嵩陽書院別墅-君子亭;書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嶺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築。
世界文化遺產
嵩陽書院因其獨特的儒學教育建築性質,被稱為研究中國古代書院建築、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標本”。2006年12月5日,嵩山古建築群,包括嵩陽書院作為河南省唯一一處獨立項目被國家文物局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10年3月9日,嵩山歷史建築群是2010年國務院確定的中國唯一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2010年8月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將嵩陽書院等登封一批建築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白鹿洞書院
書院介紹
白鹿洞書院為宋代 四大書院之首,且有“海內書院第一之稱”。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廬山五老峰南麓後屏山下(星子縣白鹿鎮境內),西有左翼山,南有卓爾山,三山環台,一水(貫道溪)中流,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全院山地面積為3000畝,建築面積為3800平方米。山環水合,幽靜清邃 ,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書院的變遷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書院“始於唐、盛於宋,沿於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初為唐代貞元元年(785年)洛陽人李渤與其兄隱居讀書之處。李渤養一白鹿,出入跟隨,人稱之白鹿先生。後李渤為江州刺史,於隱居舊址建台,引流植花,號為白鹿洞,其實並沒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懷抱,貌如洞狀而已,白鹿洞四山環合,俯視似洞,因此而名。唐末兵亂,高雅之士來此讀書。南唐開元年間,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講學,稱為“廬山園學”。宋初擴建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並稱四大書院。南宋時著名的理學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軍,到白鹿洞書院察看遺址,請孝宗批准,籌款建屋,徵集圖書,聘請名師、廣集生徒,親任洞主,親自講學,並制定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等五條教規,即有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白鹿洞書院教條》不但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而且成為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樣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至此,白鹿洞書院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譽為“海內書院第一”,“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它與嶽麓書院一樣,成為宋代傳習理學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書院被毀於戰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維修為正統元年(1436),以後還有成化、弘治、嘉靖、萬曆年間的維修。
進入清代,白鹿洞書院仍有多次維修,辦學不斷。19世紀末,中國政治、經濟發生急劇的變化,出現了教育改革的熱潮。光緒24年(1898年)清帝下令變法,改書院為學堂。白鹿洞書院於光緒二十九年停辦,洞田歸南康府(今星子)中學堂管理。宣統二年(1910),白鹿洞書院改為江西高等林業學堂。自宋至清的700年間,白鹿洞書院一直是中國宋、明理學的中心學府,陸象山、王陽明等都曾在此講學,書院殿閣巍峨,亭榭錯落,師生雲集,儼如學城。國民黨時期,蔣介石準備要南昌中正大學接管白鹿洞書院,但未實現。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對白鹿洞書院進行保護和維修。1959年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979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二級自然保護區,同年設定作為學術研究機構的白鹿洞書院建置;1990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書院管理委員會。現在,白鹿洞書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學、學術研究、旅遊接待、林園建設五位一體的綜合管理體制。1928年,胡適來到白鹿洞書院,並對其讚不絕口。胡適盛讚白鹿洞有兩個原因,一是“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書院,是中國書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親定的《白鹿洞規》“簡要明白,遂成為後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在他的《廬山遊記》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論斷:“廬山有三處史跡代表三大趨勢:一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代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三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白鹿洞風光
白鹿洞書院的自然風光極為毓秀,四山環台,古木蒼穹,溪水古橋,別有洞天,現已成為文化旅遊的佳鏡。院內松柏交翠,花草爭芳,環境幽靜秀麗。館內藏品反映了廬山歷史文化的輝煌,有當地出土和及從外地蒐集的古代青銅器和歷代陶瓷,有唐宋著名書法家顏真卿、柳公權、米芾、黃庭堅等在廬山的手書碑拓,有明清著名書畫家唐寅、鄭板橋、朱耷(八大山人)的字畫捲軸,最珍貴的則是《五百羅漢羅圖》,血書《華嚴經》和水晶佛珠,皆屬國家一級文物珍品。白鹿洞書院,在儒家理學思想的指導下,憑藉廬山這塊風水寶地,並依靠歷代文人學者和熱心教育者們的精心耕耘,獲得了一種精深文博的厚實,區別於廟堂式的州、府、縣學,令人嚮往、探索和追求,這正是它一千餘年來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緣由。白鹿油書院現存在建築群沿貫道溪自西向東串聯式而築,由書院門樓、紫陽書院、白鹿書院、延賓館等建築群落組成。建築體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磚木結構,屋頂均為人字形硬山頂,頗具清雅淡泊之氣。
石鼓書院
簡介
石鼓書院位於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陽市石鼓區,海拔69米,面積4000平方米。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石鼓書院始建於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歷史。書院主要建築有武侯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七賢祠、合江亭、禹碑亭、敬業堂、欞星門、朱陵洞等。蒸水出環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橫其前,三水匯合,浩浩蕩蕩直下洞庭。而石鼓正當其中,橫截江流,秦然若素。“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錦繡華”、“朱陵洞內詩千首”、“青草橋頭酒百家”三景集聚於此。
石鼓書院立有高約兩米石鼓。晉時庚仲初《觀石鼓書》云:“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則載:“具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經,鼓鳴則有兵革之事。”石鼓山峻峭挺拔,風景奇異。
 湖南衡陽石鼓書院
湖南衡陽石鼓書院名城衡陽人文薈萃,石鼓文脈綿延千年。石鼓書院是一座歷經唐、宋、元、明、清、民國六朝的千年學府,書院屢經擴建修葺,蘇軾、周敦頤、朱熹、張栻、程洵 、鄭向、湛若水、葉釗、鄒守益、茅坤、曠敏本 、趙大洲、林學易 、王敬所、蔡汝南、胡東山、李同野、羅近隱、王闓運、曾熙等人在此執教,在衡陽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鄒統魯、朱炳如、伍定相、曾朝節、陳宗契、王夫之、曾國藩、彭玉麟、彭述、楊度、齊白石等一大批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名人。諸葛亮、羅含、酈道元、齊映、宇文炫、杜甫、呂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范成大、辛棄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講學授徒,或賦詩作記,或題壁刻碑,或尋幽攬勝,其狀蔚為壯觀。
作為湖湘文化的重要發祥地,石鼓書院曾鼎盛數年,在中國書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比較高的地位。正所謂“石出蒸湘攻錯玉,鼓響衡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書院在衡陽保衛戰中毀於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陽市政府重修石鼓書院。
石鼓之名一說,石鼓四面憑虛,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所載:“山勢青圓,正類其鼓,山體純石無土,故以狀得名。” 另一說,是因它三面環水,水浪花擊石,其聲如鼓。晉時諛仲初《觀石鼓詩》云:“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從《水經注》來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載於史冊,但當時並沒有書院,山北面有一石洞,名為“朱陵後洞”,《水經注》上說“有石鼓六尺,湘水所經,鼓鳴,則有兵革之事”,意思是說如果在“朱陵後洞”內聽到湘江水的鳴叫,就會發生戰爭;《瀟湘聽雨錄》記載:此洞為“靈洞”、“真仙遺蹟”,在此祈禱能求子、除病。
三國時期,建安20年(215年)武侯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長沙、桂陽三郡軍賦。因此,後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武侯廟”(據《徐霞客遊記》記載),後被遷移至石鼓山上李忠節祠旁,改名為“武侯祠”【祠內有張南軒書《武侯祠記》(楷書體書),此碑在抗日戰爭時期流失】。
唐貞觀時期(公元627-650年)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東岸西溪間為遊覽勝地,題“東崖”、“西溪”四字,刻於東西岸壁上;天寶年(742~755)間,著名道士董奉先在“朱陵後洞”棲息,修煉九華丹,杜甫《憶苦行》詩中有“更憶衡陽董鍊師”之句;懶殘和尚常來洞棲息,又名朱陵仙洞;“詩聖”杜甫大曆4年(769)3月中旬和大曆5年(770)夏兩度到達衡州城,每次都在石鼓山下停泊上岸和離開,曾在此留詩數首。當杜甫第二次離開衡州城,便病故於耒水旁的方田驛(今耒陽市高爐鄉龍王廟),時年59歲。德宗貞元3年(787),宰相齊映貶到衡州任刺史,在山之東面建一涼亭,取名為“合江亭”。順宗永貞元年(805)大文豪韓愈由廣東至湖北,途徑衡州,齊映請韓愈為此亭寫下著名的《合江亭序》“紅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後人建“綠淨閣”以此為紀念韓愈。地以人傳,石鼓名聲大振,成為後世文人騷客“朝聖”之地。憲宗元和年間(806-820),有“唐代八大詩人之一”美譽的衡州刺史呂溫,任期間又對合江亭進行擴建裝修;衡陽秀才(唐朝,秀才為最高榮譽,相當於現在“院士”)李寬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為“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在此悉心讀書,為石鼓書院之雛型。刺史呂溫曾訪之,並作《同恭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日記其事。
宋代太平興國2年(978),宋太宗趙匡義為賜 “石鼓書院 ”匾額和學田(朱熹的《石鼓書院記》:“始唐元和年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敕額”。《國朝石鼓志》卷一事跡篇:“案文獻通考賜額在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與朱子記國初者合”);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書院內開堂講學、廣招弟子,使石鼓書院成為正式的書院。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擔任集賢殿校理之職的劉沆,在衡州任知府。這時,他將石鼓書院的故事上報給皇帝,宋仁宗閱後,便賜額“石鼓書院”。由於石鼓書院“獨享”兩度被宋朝皇帝“賜額”的殊榮,而步入石鼓書院的“鼎盛”時期,成為當時與睢陽(又名應天府書院)、嶽麓、白鹿洞齊名的全國著名的 四大書院。當時全國許多名流都至此講學;如文學家蘇軾、理學鼻祖周敦頤等……。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學大師朱熹、張栻在此講學,朱熹作《石鼓書院記》;張栻在亭中立碑,親書韓愈《合江亭》詩和《石鼓書院記》,後人將此鐫製成石碑,置於石鼓書院內,名曰“三絕碑”。仁宗慶曆4年(1044)石鼓書院成為衡州路的官辦學府,有正式教授1人,主要“以經術教導”學生。度宗鹹淳10年(1274年)正月,湖南提刑、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駐衡州時,作詩《合江亭》:“天上名鶉尾,人間說虎頭。春風千萬曲,合水兩三洲。……”;諄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一作疇)就原址建屋數間,榜以鼓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繼成,奉先聖先師之像,集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藏其中。請朱嘉作記,誡諸生勿為科舉功名所亂,而要辨明義利,有志“為己之學”。時戴溪為山長,與諸生講《論語》,有《石鼓論語問答》3卷。七年林田井學教授兼山長凡三年,“補葺經創”,鼎新書院,並刊大字本《尚書全解》40卷。南宋開慶元年(1259),書院毀於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長李訪“掃地更新”,“盡復舊觀”,增闢園圃,仰高樓,取明德新民文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再聞,士風作振”。提刑黃斡又置田35畝,“以贍生徒”。宋末著名音樂家郭沔曾寄居住石鼓山上,他泛舟於湘江上,創作出“瀟湘水雲(霧)”這首著名的琴曲。
元朝,繼續辦學。然其田於至元十九年(1292)為靈岩寺僧強占,經鄧大白、王復、康莊、程敬直等歷任山長長達62年爭訟,才得歸還。元末又毀於兵火。
明清時石鼓書院不斷擴大,明永樂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書院以待旅遊學者,設禮殿祭祀孔子,乾張祠祭祀韓愈、張拭。天順、弘治年間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葉釗為山長,講聖賢身心之學、道德之首,剖晰疑義、闡發幽微“時學者翕然雲從”。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湛若水至書院講論“體認”之學,理學家、教育家王守仁的傳人鄒守益亦來大倡“良知”之說。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書院為朱熹、張栻、湛若水、鄒守益“過氏之地”,乃重整書院,訂立規約,以學文敦行、辨聲慎習、等倫常、識仁體訓士,刊《說經札記》、《衡汀間辨》、《太極問答》等,“忘倦”達4年(1549-1552)。又請趙大洲、皮鹿門等“海內名公”講學其中,諸士環聽,“宛然一鄒魯洙泗之夙也。”。著名地理學家徐弘祖在其《徐霞客遊記》中對石鼓的景色有詳細描述;萬曆四十的(1612)巡撫記事,觀察鄧雲霄大修書院,以“鑄士陶昆”、建有講堂、敬義堂、回瀾堂、大規模、仰高樓、砥柱中流坊、欞星門、風雩、淪浪、禹碑、合江諸亭、其他“殿祠號舍,罔不完葺”,規模極一時之盛,崇禎十五年(1642)提學高世泰修葺。青年時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寫詩詞頌揚石鼓書院。明朝末年,書院再次毀於兵火。
清世祖順治14年(1657)經略大臣洪承疇,將石鼓書院作為軍事指揮所。同年偏沅巡撫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請重建石鼓書院,衡陽縣知縣余天溥具體負責修復工程。此時,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觀樓、會講堂、忠節祠、七賢祠等建築。石鼓書院為清政府允許恢復的這家書院,這一時期,書院科舉化,石鼓書院成為傳授舉業、培養科舉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張奇勳擴建號舍20餘間,“拔衡士之雋者肄業其中,每月兩試之,士風稱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鳴捐俸“增其所未備”、“督率師徒援古證今,析疑問難”其中。時七賢祠、仰高、大觀二樓,敬業堂、留待軒、浩然台、合江亭及東西齋房等、“日日髹、丹碧上聳、煥然巨觀”。山長多一時之選,如陳正雅、余廷松、林學易、易廷彥、羅瑛、皆湖南名進士,然所援多為科舉之業。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書院改為衡陽官立中學堂,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改為湖南南路師範學堂;民國時期,相繼改為“衡郡女子職業學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湖南三師),後由於石鼓山無法滿足新型學校要求,學校被遷移至金鰲山;此時,石鼓書院便成為供人遊覽、祈祀的風景文化名勝。
1944年7月,石鼓書院原有的樓、閣、亭、祠等建築物,在震驚中外的衡陽保衛戰中被於日軍焚毀。故址內還有唐、明、清碑刻多處。
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來衡陽視察時,要求恢復衡陽的名勝古蹟,諸如石鼓書院、回雁峰等。當時的市委市政府限於歷史條件,僅培植了樹木花圃,建以亭榭,在廢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園,無法恢復當時的建築和陳列。
1998年,國家郵政部發行“古代書院”即宋代四大書院郵票時,事先曾來石鼓書院實地考察,終因只見山石、不見書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陽書院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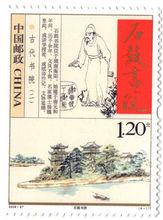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2009年,石鼓書院特種郵票首發式在湖南省衡陽市石鼓書院廣場舉行。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發行的“古代書院二(一為古代四大書院:應天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特種郵票共有4枚,分別為湖南的石鼓書院、江蘇的安定書院、江西的鵝湖書院、海南的東坡書院,每枚郵票面值1.20元,由當代中國著名的國畫大師範曾和著名畫家鄒玉利設計,以國畫形式表現。
山長們
石鼓書院位於衡陽市石鼓區石鼓山,海拔69米,相傳山上有石鼓,高六尺,能發出鼓聲,故得其名。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所載:“山勢青圓,正類其鼓,山體純石無土,故以狀得名。”另一說,是因它三面環水,水浪花擊石,其聲如鼓。晉時瘐闡《觀石鼓》詩云:“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從《水經注》來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已載於史冊。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開此處讀書堂。”石鼓書院歷唐、宋、元、明、清各代,至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改設石鼓高等學堂為止,延續了一千餘年。期間,它始終以藏書之豐、學風之盛、設備之全、經費之足、管理之嚴、成就之大,在中國教育史和書院發展史上享有比較高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脈”的美譽。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寬族裔李士真“援寬故事,請於郡守,願以私財”,在李寬辦學舊址上對石鼓書院進行首次重建。史載,宋朝皇帝曾兩次給石鼓書院賜額。一次是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這在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和朱熹的《石鼓書院記》中有錄;一次是仁宗景祐二年(1035),仁宗允集賢殿校理劉沆之請,詔賜“石鼓書院”匾額及學田5頃,使石鼓書院聲名大振,遂與睢陽、白鹿洞、嶽麓三書院並稱為“天下四大書院。”石鼓書院首任山長李寬、後任山長李士真同祀石鼓七賢祠,與韓愈、周敦頤、朱熹、張栻、黃乾並稱石鼓七賢。
梁章鉅《退庵隨筆》卷六記:“掌書院講習者謂之山長,山長亦稱院長,亦稱山主。”五代時蔣維東隱居衡岳講學,受業者稱蔣為山長(見《荊湘近事》)。至宋相沿為習,書院益多。元代書院,亦置山長,講學之外,並總領院務。清乾隆時改為院長,清末仍名山長。對其人選,明代多以品望為主,沒有地域限制。清代雖強調品行、學問,然而多主張選擇本地人士。自南宋以來,石鼓書院歷代延聘了數十位山長,由於屢遭戰亂,兵火連綿,現在能夠查找到有名有姓的有40餘位。
南宋時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大儒朱熹的《石鼓書院記》。在這篇帶綱領性的歷史文獻中,朱熹對書院辦學的指導思想、教學內容、教育重點、教學方法作了具體闡述。尤其是他倡導的將義理之學、修身之道作為書院的辦學宗旨,以達到“明道義正人心”教育目的,不僅為當時全國各書院所效法,而且對元、明、清歷代辦學都有深刻的影響。山長留名者有戴溪、程洵、李訪。戴溪在孝宗淳熙五年(1178)中省試第一,累官至權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十二年(1185),石鼓書院得以恢復重建,戴溪任山長,與諸生講《論語》,有《石鼓論語問答》三卷。程洵為朱熹門人,潛心理學,是程朱學派的重要學者。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始出任衡陽主簿。十四年又暫代石鼓書院山長,以宣揚朱子張子之學為要務,一時“士友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晦庵之門”(清康熙《衡州府志》)。在衡期間留有題詠石鼓詩若干首,並編纂首部《石鼓書院志》(後散失)。南宋開慶元年(1259),石鼓書院毀於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命山長李訪“盡復舊觀”,取明德新民文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再聞,士風作振。宋王朝南遷後,較為著名的書院為石鼓、白鹿洞、嶽麓、象山等,嵩陽因戰亂宋末時廢毀,及至明中期嘉靖年由登封知縣候泰重建才得以恢復書院。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一,統治者基本上不學無術,仇視漢族文化,書院基本上處於政府監控之下。例外的是,石鼓書院與全國其他書院遭際不一樣,是少有的受統治者重視的書院,還獲贈學田。歷任石鼓書院山長有鄧大任、王復、康莊、程敬直、李宥孫、金文海、朱仁仲、張珪等,但就跟元代本身一樣,這些名士也只是客串了一把山長,未能有多大作為,因此,正史、野史中都很難查找到他們的資料。
明清兩代,衡陽地方官員對於石鼓書院有著一種特別的情結,這也是石鼓書院得以興盛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元末兵燹後,自明代永樂年間起,經過衡州知府史中、翁世資、何珣及湖廣憲副沈慶等人70多年的努力,書院終於規制大備,沉寂多年的石鼓書院又再次興盛起來。正德四年(1509),葉釗為山長,講聖賢身心之學、道德之首,剖晰疑義,闡發幽微,“時學者翕然雲從”。王大韶青少年時期求學於石鼓書院,致仕後“重返母校”,主講石鼓書院,並參與編纂、重校首部《石鼓書院志》,為後世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有關書院史料。其他知名山長有周詔、李明安等。到了清代,山長陳正雅、吳炯、宋薊齡、曠敏本、林學易、李振南、羅廷彥、王光國、余廷燦、李繼聖、劉高閣、譚鵬宵、張學尹、常大湘、劉祖煥、蔣琦齡、鄒焌傑、馮俊、鄧傳密、李揚華、左斌、江昱、祝松雲、莫重坤、曾熙等,基本上都是進士、舉人出身,才高八斗,學貫古今,官場歷練多年,卓然湖湘名士,主觀上要為桑梓造福,客觀上保證了教育質量,石鼓書院“宛然一鄒魯洙泗之夙也”。
比山長更牛的是山斗,也就是泰山、北斗的合稱,猶言泰斗。鄒守益是明代大儒王守仁的高足,正德六年(1511)中進士第一,授翰林院編修,累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中講學石鼓,著《教言》25篇(又稱《語石鼓諸生二十五篇》),對識性、求實、時習、篤行、慎獨、戒懼、格物、致知等作了精闢的闡述,成為諸生向學的至理名言。四方從游者踵至,被諸生尊為書院“山斗”。曠敏本和林學易都是衡山縣人,都是進士出身,都是石鼓書院歷史上很有作為的山長。曠敏本乾隆十九年(1754)被聘為嶽麓書院山長,任職約三年,後出任石鼓書院山長,因學問精湛,出類拔萃,倍受時人稱頌,士子爭以出其門下為幸。林學易幼年受知於學使,有“國士”之稱。乾隆二十六年(1761)聘為石鼓書院山長,連續執掌書院達15年之久。末代山長(1894~1902)曾熙是衡陽縣石市人,光緒進士,累任提學使,不久返湘,主講石鼓書院,後任湖南教育學會會長、南路優級師範學堂監督。
石鼓書院素稱人才薈萃之地,講學風氣甚濃。歷代名師大儒,如宋代的朱熹、張栻、鄭向、黃乾,元代的偰玉立、奚漢伯顏、李處巽、陳淞年,明代的湛若水、蔣信、羅洪先、趙貞吉、茅坤、李渭、羅近溪、甘公亮、蔡汝楠、劉堯誨、王萬善,清代的王敔、潘宗洛、吳時來、余廷燦、劉良弼、江恂等,都相繼來這裡登台傳道,使石鼓成為遠至京師近至衡永郴桂士子們嚮往和雲集的學府,成為湖湘地區引人矚目的儒學傳播基地,並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古代“講學式”書院的楷模,對湖湘文化的演變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石鼓書院概貌
石鼓書院經過近十次的重修,在修葺的過程中,儘量保持其原貌,現在的石鼓書院主要是由禹碑亭、武侯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合江亭、朱陵洞組成。
始入石鼓書院,穿過大門,走過長廊,映入眼帘的是禹碑亭。禹碑亭亭柱上題著一副對聯:“蝌蚪成點通,天地衍大文”,此聯為中國現代著名書法家史穆所題,在禹碑亭中央放置著一塊禹碑,為蝌蚪文所做,禹碑為大禹治水功成在南嶽衡山岣嶁峰所刻,最早見於東漢趙曄所撰《吳越春秋》,其後史乘屢有記載。衡陽石鼓山禹碑亭始建於明萬曆九年(1581),位於石鼓山南面。
明代楊慎為禹碑作釋文亦置於此。
穿過禹碑亭,來到石鼓書院二門前,只見篆書對聯“名修千佛上;至味五經中”於門上,石鼓山與道教文化有頗深淵源,後建立石鼓書院以“四書五經”作為正統教育教材,這幅對聯是對石鼓書院的真實寫照。
透過二門,看到眼前有兩個祠堂,位居其右的為“武侯祠”,位於左的為“李忠節公祠”,武侯祠和李忠節公祠與石鼓書院都沒有很多聯繫,但是由於這兩位英雄的事跡都發生在石鼓山,遂將其移至石鼓書院。
武侯祠為紀念諸葛亮而建。武侯即諸葛亮(181—234),因其曾封武鄉侯,故世稱武侯。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劉備任荊州牧,諸葛亮以軍師中郎將駐臨然即今衡陽,督辦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軍賦,相傳住在石鼓山上。後來人們在臨然驛旁建武侯祠以供祀享。宋代重修石鼓書院時,將武侯祠移至石鼓山。南宋理學家張栻曾作《武侯祠記》,並親筆勒石立碑。
祠堂門上范鶴年題有對聯“心遠地自偏,問草廬是耶非耶,此處想見當日;江流石不轉,睹秋水來者逝者,伊人宛在中央”,上聯武侯猶憶劉備“三顧茅廬”,拜訪賢才,下聯武侯觀以前實景,感慨萬千。
李忠節公祠為紀念李忠節的高風亮節而建。李忠節公名李芾,字叔章,南宋衡州人。南宋德佑元年,元軍將犯,李芾臨危受命,任潭州(今長沙)知州兼湖南安撫使,率領軍民抗擊元軍三月有餘,城破,舉家殉國。元代在衡州城南金鰲山李帶故宅建李忠節公祠,配祀李芾部將沈忠和衡陽縣令穆演祖,清代移建石鼓山。元代宋本和清代陳沆先後有記。清同治年間(1862—1864)重修石鼓書院時,彭玉麟(時任兵部右侍郎)為李忠節公祠題聯,讚揚了李忠節鐵骨錚錚,為民族大義的犧牲精神。
穿過兩祠堂,大觀樓躍入眼帘,在大觀樓內,你一眼便可以望到“書院七賢”畫像依次排列,這是他們這一群文人雅士的貢獻才有今天的石鼓書院。大觀樓內放置著各地名人為其做的詩詞和書畫。
參觀完大觀樓,便是合江亭。
中國創建最早的書院之一
石鼓書院是中國四大書院創建最早,並具有確切史志記載的書院。書院制度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自唐至清未存在了一千多年。唐時書院從《全唐詩》中考證有十一所,從地方史志中有記為十七所(以陳元暉《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和王鏡第著《書院通證》及周書舲著《書院制度之研究》三文所列十七所為準)。兩者都有載的僅三所:為衡陽李寬中秀書院〈石鼓書院〉、南溪的南溪書院、永濟的費君書院。
《全唐詩》十一所書院:
李泌書院(南嶽衡山鄴侯書院),第四郎新修書,趙氏昆季書院,杜中丞書院,費君書院,李寬中秀才書院,南溪書院,李群玉書院,田將軍書院,子侄書院,沈彬進士學院
地方史志註明為唐代設定十七所書院:
麗正書院,張九宗書院,石鼓書院,皇寮書院,松州書院,青山書院,瀛洲書院,景星書院,義門書院,鰲峰書院,韋宙書院(南嶽衡山),盧潘書院(南嶽衡山),杜陵書院(耒陽),明道書院,梧桐書院,桂岩書院。
石鼓書院七賢
創院始祖李寬、哲學與文學大家韓愈、李士真、理學鼻祖周敦頤、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東南三賢”之一——張栻、黃斡。
石鼓書院八景
石鼓書院八景:“東岩曉日,西豀夜蟾,綠淨蒸風,窪樽殘雪,江閣書聲,釣合晚唱,棧道枯藤,合江凝碧。”
徂徠書院
北宋書院之徂徠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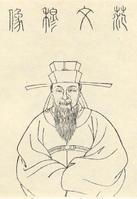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南宋宰相范成大《驂鸞錄》首舉徂徠書院,在歷史上,范成大最早的提出了古代四大書院之說:
“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中國古代四大書院的說法,即起源於此。
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曾言:“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
在古代,泰山徂徠書院,曾在中國書院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泰山學派,毓毓文風
徂徠書院的創始人孫復、石介二人是著名的古文家、教育家,也是宋代理學的先驅。
山東徂徠書院,開啟了宋代古文運動的序幕,代表了儒家的一種積極入世的文化,流動著儒家文化的風骨,它在齊魯文化中,應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山東徂徠書院,不僅對於中國古代書院史的考察,而且對於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研究,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徂徠書院也成為泰山文化史上富有理性光輝的篇章。
徂徠書院的創始人孫復、石介二人以儒家理學精神為先導,培養了一批富有成就的人才,樹立了一代嚴謹學風,形成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泰山學派”, 一時,泰山徂徠書院門生弟子云集,著名的有姜潛、劉牧、張洞、李蘊、祖擇之、杜默、張續、李常、李堂、徐遁等人。金代的党懷英、清代的趙國麟都曾讀書於此。徂徠山上,古蹟眾多。據初步普查,今存寺廟3處,碑碣54塊,摩崖刻石113處,古樹名木千餘株。《詩經》、《史記》對此山有多處記載,歷史名人多有題詠,民間傳說更是數不勝數。
吳王闔閭、孔子、漢武帝、漢光武帝、唐代偉大詩人 李白曾親自登臨,司馬遷也曾到達此處,汶河沿岸是春秋時魯國人才輩出之處。
大師鼎立、交輝相應:孫復、石介、胡瑗
宋代理學大師朱熹曾說:“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胡瑗)、泰山孫明復(孫復)、石守道(石介)三人。”
朱熹所說的以上三個人,就是和泰山徂徠書院有緊密聯繫的當時著名的學者孫復、石介和胡瑗。也就是,當時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鐵肩擔道義·徂徠之風,流傳千載
當時,以宋初三先生(石介、孫復、胡瑗 )為代表的泰山學派摧垮了楊億、劉筠為首的西崑體,促進了宋代古文運動的發展,石介遂成為一代古文運動的先驅。
石介一生,儒家積極進取的思想始終占主導地位。排斥道佛,標舉儒家正統思想。主張文章必須為儒家的道統服務,為現實服務,極力抨擊宋初浮華的文風,指責楊億的西崑體是“蠹傷聖人之道。”
石介的文學成就對後人影響很大,歐陽修、蘇軾、劉概都對他甚為讚揚。
石介有強烈的民本思想。他在《根本策》一文中說:“國家就是百姓,有百姓就有天下,否則天下就名存實亡。善於治理國家的人,一定重視百姓,因為百姓是國家的根本。”
民族的沉思、國民的反省
石介一生,可以說是“鐵肩擔道義”、盪氣迴腸、驚悚跌宕的悲劇一生,悲劇來源於他的性情剛烈、嫉惡如仇,也有人批評他個性過於“躁急”,即政治上不夠成熟。
但是,作為一名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一旦過於“成熟”,就必然大大減弱其思想上的鋒芒。對此,我們是否更應該激賞那些“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堅定豪邁和熱血沸騰呢?
畏畏縮縮、油腔滑調的政治成熟顯得太過齷齪,我們是否在靈魂深處,缺少了石介所代表的這一類士大夫所具有的氣魄和血性呢?
我們族群中的大多數,是不是那種唯利是圖、曲意逢迎、上媚下陷,迎合著權貴和低俗的社會需求的一群?是不是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激情不再?是不是那種為民請命、甘灑熱血的豪情亦被蕩滌的乾乾淨淨? ?
沉思吧,吾之民族!吾之國民!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馮玉祥—洗心亭題詞,警示後人上世紀30年代,愛國將領馮玉祥隱居泰安,曾在泰山普照寺西北五賢祠(孫復、石介、胡瑗、宋燾、趙國麟)居住,馮將軍景仰前賢品德學問,曾照《宋史》本傳立石介、孫復碑。
同時,為進一步表示敬重,馮將軍又邀請石、宋、趙三賢后人會見,當時三姓後人去了百餘人,馮將軍握著石介後人石景謙的手與之交談良久,並贈與禮品。
泰山五賢祠分東西兩院,東院為祠,西院為講書堂。祠後石崖上有題刻“講書台”、“授經台”、“千秋道岸”、“能使魯人皆好學”等,多少讓人看出些儒家學府當年的影子。
五賢祠前溪畔有石亭,額書“洗心亭”,四面皆為清代人題聯,似也沒什麼佳句。
馮玉祥在“洗心亭”內題的標語:“你忘了沒有,東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有硬骨頭的人應當去拚命奪回來!”看了讓人血涌心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