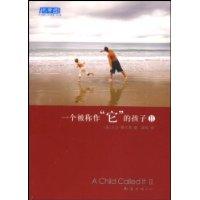作品信息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頁碼:291 頁碼
·出版日:2008年
·ISBN:9787544234375
·條碼:9787544234375
·版次:1版
·裝幀:平裝
·開本:32市場價:¥25.00
編輯推薦
一本讓千百萬重獲生活信心的書。雄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5年!媽媽天天打他、餓他、逼他喝氨水,將他的胳膊燙得皮開肉綻,在他肚子上扎出一個大洞……在無邊的凌辱虐待中,他依然對未來充滿希望。
所以,你要笑著活下去!美國三屆總統里根、布希、柯林頓熱情讚揚。
內容簡介
本書講述了大衛·佩爾澤早年的親身經歷: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裡,他在精神和肉體上都遭到母親的殘酷虐待,幾乎每一天,他都受到嚴重威脅,多次瀕臨絕境。然而,強烈的求生願望和永不屈服的內心給了他生存的動力,他最後終於戰勝了遠比自己強大百倍的對手。
正如《心靈雞湯》的作者傑克·坎菲爾所說:“大衛·佩爾澤並沒有過分渲染他生命受到威脅的重重困境,而是著重描寫他永不屈服的決心和意志,這才是鼓舞我們所有人的真髓。”本書故事讓人看到,不管生命中的逆流看起來有多強大,心靈深處最強烈、最有力的激情永遠在燃燒,它鼓勵人們挑戰精神極限,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本書出版13年以來,始終高居美國亞馬遜網站暢銷書排行榜前列,大衛·佩爾澤本人也接連受到美國總統里根、布希和柯林頓的熱情讚揚。本書成了一本真正幫助千百萬人重獲生活信心的書。
作者簡介
大衛·佩爾澤,童年時代曾遭到母親殘酷虐待,是20世紀美國加州歷史上最嚴重的三起虐待兒童案中惟一存活下來的人。他的自傳體三部曲《一個被稱作“它”的孩子》、《迷失的男孩》、《一個名叫大衛的男人》長居各大暢銷書排行榜,在美國、英國、日本等地均創造了暢銷的奇蹟,被普遍被譽為“最激勵人的書”。
大衛講述的是色調灰暗的真實故事,但同時也是關於人類的希望與救贖乃至最終獲得愛與接受的故事。他希望通過自身的親身經歷和心靈之旅告訴人們這樣一個真理:即使在最黑暗的夜空中,依然有星光在閃爍。
目錄
一個被稱作“它”的孩子
1逃離苦海
2幸福時光
3壞孩子
4飢餓折磨
5意外事故
6父親離家的日子
7主禱文
尾聲
迷失的男孩
1出逃
2天使
3判決
4新生
5漂離
6抗拒
7母愛
8疏遠
9歸來
10掙脫
尾聲
虐待兒童問題展望
關於收養家庭的一些看法
關於本書作者
媒體評論
大衛不屈不撓的精神始終激勵著我們:不管命運之路多么曲折,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能力活得更好。讀過這本書的人,他的心靈必將得到鼓舞和振奮。
——《心靈雞湯》作者傑克·坎菲爾
書摘插圖
一 逃離苦海
一九七三年三月五日,加利福尼亞州達里鎮。我起晚了。我一定得及時把盤子洗好,不然就沒有早飯吃了。因為昨天晚上就沒吃上晚飯,所以今天早上無論如何也不能再讓肚子空著了。母親正在屋子裡來回走動,不住口地呵斥兄弟們。我聽見她從門廳里冬冬冬地向廚房走來。我又把手放在滾燙的洗碗水裡。太晚了,她看到我的手並沒有放在水裡。
啪地一聲,她一拳打在我臉上;我應聲倒在地上。我知道最好不要站著不動,聽任她下手打我。她的硬心腸我非常熟悉。她會認為這是我在向她挑釁,那意味著,她要打個沒完,更糟的是,不叫我吃早飯。我重新站直身軀,當她在我耳邊大喊大叫的時候,我躲避著她的目光。
我裝做怯怯的樣子,不管她說什麼威嚇的話,我都點著頭。我心裡念叨著:“只要叫我吃上早飯就成。願意打我就打吧,可是別不給我飯吃。”又是一巴掌,我的腦袋一下子磕在磚砌的爐台上。我裝做屈服的樣子,叫眼淚從面頰上流下來。她好像已經心滿意足,威風凜凜地走出廚房。我數著她的腳步,在我確認她已經走遠以後,才長噓了一口氣。我演的戲成功了。母親愛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但是我從來沒有叫她摧毀我的生存意志。
我把盤子洗好,又做了其他一些雜務。我得到的回報是吃上了早餐——我的一個兄弟吃剩下的麥片粥。今天吃的是幸福牌麥片,剩下的半碗牛奶里只有不多一點麥片。但我還是狼吞虎咽地把碗裡的東西吃完了,我怕母親中途變卦。這種事以前發生過。她喜歡把食物當做懲罰我的武器。她不會把吃剩的東西倒在垃圾桶里,因為知道我會再把殘湯剩水從垃圾桶里拾出來。我對付她的一些花招,她都了如指掌。
幾分鐘以後,我已經坐在我們家那輛老舊的家庭轎車裡。因為今天做的家務事太多,我肯定要遲到,所以我可以乘上母親開的車去上學。平常日子,我總是走路上學。走到學校正好開始上課,我沒有時間從別的孩子的午飯盒裡偷偷拿出一點吃的東西來。
母親先叫我的大哥下車,留下我聽她訓話。她對我講,她已經為我安排好明天的計畫:她要把我送到她的兄弟那裡,以後就叫丹恩舅舅“養活我”。她告訴我這個計畫本意是想嚇唬我。我也就裝做非常害怕的樣子,好像真被她的話嚇著了似的。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雖然丹恩舅舅性格執拗,卻不會像母親這樣虐待我。
汽車還沒有停穩,我就從車裡跳出去。母親把我叫回來,原來我把我的裝著午餐的皺巴巴的袋子落在車上了。我的午餐在過去三年中從來沒有變過樣,總是兩份塗花生醬的三明治和幾根胡蘿蔔。在我還沒有從車廂里跳出來以前,她說:“就說……就說你的頭磕在門上了。”接著,她用一種對我講話時很少用過的聲音說:“希望你一天順順噹噹的。”我看了一眼她紅腫的眼睛;她的眼神呆滯,仍然沒有從昨天晚上的宿醉中完全醒過來。一度光澤閃閃的漂亮頭髮如今已經成了亂糟糟的一個個小團。像往日一樣,她臉上沒有化妝。她的身軀過分肥胖,這她自己也有覺察。在她的整個形象里,這已經成了她的典型特徵了。
因為到校太晚,我不得不首先到教務處去報到。頭髮灰白的秘書看著我笑了笑,算是打招呼。過了一會兒,學校的女護士走出來把我帶到她的辦公室里,對我進行了一次例行檢查。她首先檢查了我的臉和胳膊。“你眼睛上面的那塊傷是怎么回事?”
我怯生生地點著頭說:“噢,我撞在門廳的門上了……不小心。”
她又笑了笑,從櫃櫥頂層取下一個硬皮紙夾來。她翻了幾頁,俯身給我看,“上星期一你就這么說過一回了,還記得嗎?”
我連忙改口:“是我去玩壘球的時候被球棒打傷的。純粹是偶然的。”偶然碰傷!不管什麼我都應該這么解釋。但我是瞞不過護士的。她責備了我一頓,我不得不告訴她實話。每次受人盤問,最終我總是老老實實說出真情來,儘管我覺得我應該給我媽媽打掩護。
護士告訴我,說實話不會有什麼問題。她叫我把衣服脫掉。從去年開始,我就反反覆覆地一次次脫衣服,我立刻照她說的做了。我的長袖襯衫像一塊瑞士乾酪,到處是洞。這件襯衫我穿了快兩年了。母親叫我每天都穿這件衣服,這也是她污辱我的一個手段。我的褲子一點也不比襯衫好,兩隻鞋前面都已經開了口,腳趾可以自由自在地從口子裡伸出來。當我只穿著內衣內褲站著的時候,護士把我身上的疤瘌和傷痕——記在硬皮本里。她又數了一下我臉上的劃痕,看看有沒有過去她忽略沒看到的。她做得一絲不苟。這以後,她叫我張開嘴,看了看我被撞在爐台上磕崩了邊的門牙。她在紙上又寫了幾句什麼。在她繼續查看我身體的時候,她發現我的肚皮上有一個疤痕,“這是她把你扎傷的地方嗎?”
“是的,老師……啊,不是。”我在心中告誡自己:我又做錯了,不該說實話。護士一定發現了我目光中的憂慮。她把硬皮紙夾放下,抱住了我。“上帝啊,”我心裡說,“她多么暖和啊。”我不想叫她放開我,想永遠待在她的懷抱里。我緊緊閉上眼睛,有那么一小會兒,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她拍了拍我的腦袋。她的手碰到了今天早上母親打出的腫包,我縮了一下。爾後,護士放開我,離開了這間屋子。我很快就穿好了衣服。她不知道,無論做什麼事,我都不耽擱一點時間,這已經是我的習慣了。
幾分鐘以後,護士同校長漢森先生,還有另外兩個老師——摩斯小姐和齊格勒先生,一齊走進來。漢森校長對我的事知道得很清楚,因為我被他叫到辦公室的次數比任何學生都多。護士向校長匯報她檢查我身體時發現的一處處傷痕。校長翻看了一下她的記錄,然後,把我的下巴抬了起來。我不敢直視他的目光,這不僅是長年同母親打交道養成的習慣,也因為我不想把一切都向他坦白。有一次,大約一年前,他曾經因為我身上的傷疤,把母親找到學校談過話。當時他還不清楚我家裡的真實情況,只知道我是個問題兒童,有偷嘴吃的習慣。第二天我到學校去,他發現母親因此又狠打了我一頓,從此就再也不找母親來學校了。
漢森先生怒氣沖沖地說,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聽了他的話,幾乎嚇掉了魂。“他又要找母親談話了!”我的腦子裡突然響起了這句刺耳的話,一下子精神崩潰,放聲大哭起來。我像篩子一樣瑟瑟發抖,像個嬰兒似的喃喃乞求漢森先生,千萬別給母親打電話。“求求您啦,”我嗚咽地說,“今天別打!您不知道今天是星期五嗎?”
漢森校長叫我放心,說他不會給母親打電話。他叫我回到班上去上課。因為耽擱了很長時間,已經錯過了班級集會,所以我直接去上伍德渥斯太太的語文課。今天要考美國各州和各州首府的拼寫,可我並沒有準備好。過去我一直是個學習優秀的學生,但是最近幾個月里,我對生活中所有的事都沒有勁頭做了,就連借做功課來逃避悲慘生活也放棄了。
我一進教室,所有同學就對我做鬼臉,發出一片噓聲。代課老師,一個年輕婦女,雙手在臉前扇動,她聞不慣我身上的氣味。她伸長胳膊,站得遠遠的遞給我試卷。但是走到我的位子——我的座位在教室最後,緊挨著敞開的窗戶——以前,就有人來叫我到校長辦公室去。全班同學沖我大聲喊叫,我已經成了被五年級拋棄的一件廢品了。
我向教務處跑去,眨眼的工夫已經跑進屋子裡。因為母親昨天跟我玩的那個“把戲”,我的嗓子不只乾燥,而且疼得要命。秘書把我領到教員休息室。她把門打開以後,過了一會兒我才看清屋子裡的陣勢。在我面前,圍著一張圓桌,坐著我的年級主任齊格勒先生、數學老師摩絲小姐、學校護士、校長漢森先生,以及一位警官。我兩條腿僵在那裡,一步也邁不動。我不知道該趕快跑開還是等著屋頂塌下來。校長漢森招手叫我進去,秘書在我身後關上了房門。我在桌子的一頭坐下,拚命解釋我這一天沒有偷東西吃。一張張皺著眉頭的臉露出了笑容。我並不知道這些人是冒著失去公職的危險來搭救我的。
警官向我解釋為什麼校長漢森找他來。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警官叫我談一談我母親的事。我搖頭,不肯說。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我的秘密,我知道我是無法再為她掩飾的。一個溫柔的聲音在安慰我,我知道這是摩絲小姐。她對我說,我把事情說出來,什麼關係也沒有。我深吸了一口氣,絞了絞手,吞吞吐吐地把母親和我的事說給他們聽。後來護士叫我站起來,給警察看我的胸上的傷疤。我立刻說,這只是個意外。事實確實如此,母親從來沒想到真用尖東西扎我。我一邊說一邊哭。我告訴他們,母親處罰我是因為我不聽話。我哀求他們不要管我的事。我覺得心裡黏糊糊的,非常難受——這么多年來,誰也沒幫上我什麼忙。
幾分鐘以後,我被吩咐坐到外間的屋子裡。關門的時候,我看到屋子裡的人都在看著我,搖頭嘆氣。我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看著秘書打字。好像過了很久很久,漢森校長才把我叫回屋子裡。摩絲小姐和齊格勒先生離開了屋子。他們的樣子看起來比較高興,但又有些焦慮。摩絲小姐跪下來把我抱在懷裡。她頭髮上的香水味,我想我是永遠忘不掉的。她放開我,轉過身去,不叫我看見她在落淚。我這時真的感到憂慮了。漢森校長從食堂里給我拿來裝著午餐的托盤。“我的上帝,怎么都到吃午飯的時候了?”我問自己。
我狼吞虎咽地吃起來,連滋味也沒嘗出來。托盤裡的東西一眨眼就被我吃光了。校長馬上又給我拿來一盒甜點,囑咐我不要吃得太快。我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甚至猜測,同母親已經分開的父親來接我了。但是我知道,這只不過是奇思異想而已。警察詢問我的住址和電話號碼。“果然是這樣,”我對自己說,“要把我送回地獄去了!她這次可要往死里整我了。”
警官又在拍紙簿上寫了一點什麼,校長漢森和學校的護士在旁邊看著。不久他就把拍紙簿合上,對校長說,他需要的材料已經齊全了。我抬起頭,看著校長,他的臉上冒著汗。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胃正在蠕動,要趕快去洗手間嘔吐。
漢森先生打開房門,所有吃過飯正在午休的教員都睜大眼睛望著我。我感到羞愧難當。“他們都知道了,”我對自己說,“他們知道母親的事了,知道了真實的情況。”知道我並不是個壞孩子,這是非常重要的。我需要別人喜歡我,愛我。
我走過大廳。摩絲小姐在哭泣,齊格勒先生正用一隻胳膊摟著她。我聽到摩絲小姐吸溜鼻子的聲音。她又抱了我一下,然後很快地轉過身子。齊格勒先生同我握了握手。“做一個好孩子。”他說。
“是的,老師,我會努力的。”這是所有我能說的了。
學校的護士無言地站在校長漢森身旁。大家都跟我告別。我知道現在就要去監獄了。“這樣也好,”我想,“在監獄裡,至少我不會再挨她打了。”警官和我走到外面的院子,經過食堂。我看見幾個同班同學在玩丟球遊戲。他們中有的人停下玩球,衝著我喊:“大衛完蛋了!大衛完蛋了!”警察摸了摸我的肩膀,叫我別聽他們胡說八道。
當他把汽車開向大街,離開托瑪斯·愛迪生國小的時候,我看到有幾個孩子好像因為我離校而感到憂慮。被帶走以前,齊格勒先生對我說,他會把實情告訴我的同學,讓他們知道真實情況。我多么希望,他們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壞孩子以後,能再同他們一起在班裡上課啊!要是這個願望能夠實現,什麼代價我都肯付出。
幾分鐘以後,我們的汽車已經到了達里鎮警察局。我預料母親有可能也在警察局,所以不想下車。警官打開車門,輕輕地拉著我的胳膊,把我拖下車,帶進一間大辦公室。屋子裡沒有別的人。警官在角落裡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用打字機打了幾頁字。我一邊慢慢地吃甜點,一邊看著他打字。這次我吃得很慢,儘量品嘗點心的滋味。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能吃到這種美食。
已經過了下午一點鐘,這時警官打完了他的檔案。他又問我家裡的電話號碼。
“為什麼要我家的電話?”我帶著哭腔說。
“我得給你母親打個電話,大衛。”他語氣溫和地說。
“不要打!”我用命令的口氣說,“把我送回學校去吧。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嗎?一定不能叫她知道我把事情說出來了。”
警官又給了我一塊點心,用來撫慰我。然後他慢慢地撥動電話機:7—5—6—2—4—6—0。我站起身,走到他身邊,看著黑色的轉盤在電話機上轉動。我繃直了身子,想聽到電話的另一端是否響起了鈴聲。母親在接電話,她的聲音把我嚇壞了。警官揮手叫我站開些,他深吸了一口氣,開口說:“佩爾澤太太,我是達里警察局的警官史密斯。你的兒子大衛今天不回家了。今後他將由桑·馬提奧青少年收容所監護。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可以給他們打電話。”警官把聽筒放下,沖我笑了笑。“你看,一點也不困難,是不是?”他問我。但是,從他臉上的表情看,他說這句話更像是安慰自己,而不是安慰我。
汽車開了幾英里以後,就上了二八○高速公路,向達里鎮郊外駛去。我朝右邊看了看,見路邊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公路。”在我們駛出城區以後,他輕鬆地笑起來:“大衛·佩爾澤,你自由了。”
“什麼?”我問,緊緊攥著得到的唯一的食物,“我不懂。你不是把我送到一個什麼監獄去嗎?”
他又笑了笑,輕輕地搖了一下我的肩膀,說:“不是送你去監獄,大衛。你一點也不用擔心。我對你講的是實話,以後你母親再也不會傷害你了。”
我把身體向後靠了靠。陽光晃到了眼睛,我把頭歪了歪,一顆淚珠從面頰上滾落下來。
“我自由了嗎?”
二 幸福時光
在我開始受母親虐待以前,我的家稱得上是六十年代的一出電視劇《幸福家庭》的翻版。我們弟兄三個。爸爸媽媽是完美無缺的家長。不論孩子們提出什麼願望,他們都滿懷關愛地予以滿足。
我們住在一幢帶有兩間臥室的樸素房屋裡,位於達里鎮一個“良好”的居民區。我記得,透過房子起居間向外凸出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室外晴朗的天空,以及金門橋上亮堂堂的橘色塔樓和遠處舊金山的美麗輪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