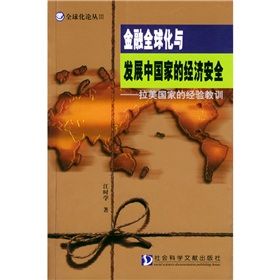作者簡介
江時學,1955年9月出於江蘇吳江。1980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同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工作。現任該所副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拉丁美洲系主任、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副總主任。曾在加拿大約克大學、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進修;多次赴巴西、智利、泰國、韓國、日本、美國、英國和丹麥等地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和講學。主要科研成果包括:《拉美發展械式研究》(1996)、《拉美國家的經濟改革》(主編,1998)、《拉美與東亞發展械式比較研究》(主編,2001)、《2002-200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主編,20030)、《阿根延危機反思》(主編,2003)。目錄
前 言第一章 金融全球化時代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安全
第一節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
第二節 金融全球化的由來及其動力
第三節 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安全
小 結
第二章 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第一節 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方案
第二節 IMF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小 結
第三章 金融全球化時代的資本管制
第一節 對資本管制的爭論
第二節 托賓稅與智利的資本管制
小 結
第四章 金融全球化與金融自由化
第一節 “金融壓抑”、“金融深化”與金融自由化的理論分析
第二節 拉美的兩次金融自由化
第三節 拉美金融自由化的利弊得失
小 結
第五章 金融全球化時代的匯率制度選擇
第一節 拉美國家的匯率制度
第二節 美元化與“超國家貨幣”
第三節 拉美三國的美元化
小 結
第六章 利用外資與經濟發展
第一節 拉美國家利用外資的形式
第二節 從“引擎”到“桎梏”
第三節 債務問題的出路
小 結
第七章 金融全球化與資本項目開放
第一節 資本項目開放的利弊得失
第二節 拉美國家開放資本項目的經驗教訓
小 結
第八章 墨西哥金融危機
第一節 金融危機前的墨西哥經濟
第二節 墨西哥金融危機的根源
第三節 墨西哥金融危機中的政治因素
第四節 墨西哥為什麼能在較短時間內克服危機
小 結
第九章 巴西貨幣危機
第一節 從“經濟奇蹟”到“雷亞爾計畫”
第二節 從“雷亞爾計畫”到貨幣危機
小 結
第十章 阿根廷債務危機
第一節 阿根廷經濟的百年興衰
第二節 阿根廷危機的根源
第三節 阿根廷危機的“探戈效應”
前言
前言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其《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寫道:讓我們玩這樣一種文字遊戲:一個人說出一個詞或短語,另一個人把他聽到後頭腦中的第一個反應回答出
來。如果你對一個見識廣的國際銀行家、金融官員或經濟學家說“金融危機”,他肯定會回答:“拉美”。
確實,最近一二十年,拉美經濟經常蒙受各種危機的沉重打擊。
·80年代初,拉美爆發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這一“雙重危機”使該地區在80年代陷入了所謂“失去的十年”。
·1994年12月,墨西哥遇到了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這一危機被視為“新興市場時代”的第一次金融危機。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傳染效應”對拉美國家的衝擊不大。正當人們彈冠相慶時,巴西卻於1999年初爆發了貨幣危機。
·2002年新年伊始,世界上的兩種貨幣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在歐洲,歐元正式進入流通領域,人們喜形於色,對前景充滿了希望。而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大規模的騷亂和激烈的政局動盪迫使政府放棄了比索盯住美元的貨幣局匯率制度,國內外投資者對阿根廷的估心急劇下降。
·2002年年中,由於受到阿根廷危機的“探戈效應”的影響,烏拉圭和巴西出現了金融動盪。
拉美經濟為什麼經常遇到危機?
毋庸贅述,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就內因而言,拉美國家在實施金融自由化、開放資本項目、管理匯率制度以及利用外資等方面,有許多失誤和偏差。但這些失誤和偏差是在金融全球化趨勢加快發展的大背景下出現的。拉美國家在轉換髮展模式的過程中,沒有將金融全球化拒之於門外,而是積極參與這一進程。因此,金融全球化對拉美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換言之,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缺陷以及國際資本的無序流動這些重要的“外因”與拉美國家的失誤結合在一起,使該地區經常面臨各種危機的打擊。
眾所周知,中國在加入WTO後,與國際資本市場和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繫越來越密切。因此,中國有必要從其他開發中國家那裡獲得一些有益的借鑑。本書力圖從金融全球化的視角出發,探討拉美國家在應對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訓和成敗得失。
本書共十章,分別探討十個問題。
第一章描述了與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有關的若干現象,闡述了金融全球化的動力及其影響,並探討了經濟安全的有關概念。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開發中國家經常遇到金融危機,國際社會希望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呼聲不斷上升,同時也希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減少金融風險和“拯救”危機國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當然也有許多人對IMF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本書第二章分析了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人們越來越注意到,開發中國家在經濟領域中遇到的各種危機,與巨額國際資本在全球範圍內隨意流動密切相關。有沒有必要對國際資本流動加以必要的管制?能否實施“托賓稅”?智利推行的資本管制措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短期資本的流人?第三章回答了上述問題。
為了參與金融全球化,開發中國家必須首先改革國內金融體系。第四章首先從理論上闡述了開發中國家實施金融自由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爾後論述了拉美金融自由化的具體做法及其成效。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貶值並非必然會導致金融危機。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開發中國家遇到的一些金融危機,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9年的巴西貨幣危機,甚至還應該包括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其“導火線”都是貶值。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在金融全球化時代,選擇一種具有靈活性的匯率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第五章論述了拉美國家匯率制度的變化,並探討了三個拉美國家的美元化“試驗”。
精彩書摘
上述機構和組織為提高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健度和增強風險意識做出了貢獻。然而,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上述制度安排的局限性日益明顯,因此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東亞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國際金融體系面臨的問題,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第一,國際貨幣體系在匯率制度和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上的“無序”,與巨額國際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資本流
動)之間的矛盾,導致世界上主要貨幣的匯率大幅度波動。第二,以自由化為基礎的國際金融市場得不到有效的監管,從而進一步加劇了短期資本流動的破壞性。
事實上,早在1995年,即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的翌年,在加拿大東部城市哈利法克斯召開的7國首腦會議就為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提出了5點建議:IMF應該強化對成員國的監督,對不願意調整政策的國家發出“坦率的告誡”。IMF應該確定成員國公布其經濟數據和金融數據的標準。IMF應該使成員國在面臨危機時能夠快速地得到援助。十國集團(即“巴黎俱樂部”)成員國政府和其他一些國家的政府應該使它們向IMF提供的資金翻一番。十國集團應該提出一些預防和解決金融危機的方法。
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社會更加關心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並採取了一些行動。例如,1999年9月26日,參加世界銀行和IMF年會的有關國家的代表經過磋商,決定成立20國集團。這一舉措被認為是為改革國際金融體制邁出的重要一步。
已開發國家也很關心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尤其在1998年下半年,西方已開發國家出現了一種被媒體稱為“金融外交”的動態。例如,1998年9月14日美國總統柯林頓提出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和解決東亞金融危機的方案後,英國首相布萊爾於9月21日提出了以強化監管、提供緊急援助、管理資本流動和增加國際金融信息的透明度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方案。9月25日,法國駐IMF執行董事提出了基本上能反映所有歐盟成員國意見的改革方案。法國總統席哈克甚至致函其他6個主要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呼籲已開發國家率先採取措施,努力增強國際金融體制的穩定性。許多觀察家認為,已開發國家之所以關注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主要是因為它們越來越認識到,國際金融形勢穩定與否,與它們自身的經濟狀況密切相關。而且,對國際金融體系的關注,還能改善其國際形象和提升其國際地位。
必須指出的是,金融自由化在推動“金融深化”的過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銀行部門的脆弱性。聯合國拉美經委會在評價拉美的金融自由化時指出,“金融自由化的目的就是要結
束‘金融壓抑’,因此,隨著改革的推進,國內利率自然就會上升。利率大幅度攀升導致國內利率大大高於國際利率。這對於那些無法從國際資本市場上獲得資金的小企業來說,是一個非
常嚴重的問題。此外,就整個國民經濟而言,更為嚴重的問題就是金融自由化為銀行部門帶來了問題。在改革以前,由於政府對利率和信貸配置施加影響,本國的銀行常常難以對長期信貸風險做出評估。當大量外資的流人導致信貸的供給增加時,銀行的風險也隨之擴大。如果這些國家借的是外國貨幣,那么問題會變得更加嚴重,因為資本流向的逆轉會造成貨幣貶值,從而使債務負擔變得更加沉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也表明,金融自由化與銀行危機的頻繁爆發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3) “布雷迪計畫”。該計畫是美國在1989年3月提出來的,其核心仍然是削減債務。然而,它與“貝克計畫”相比有一些進步之處:除鼓勵債務國繼續實行以增長為目標的經濟調整和敦促商業銀行加快削減債務的步伐外,還要求債權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做出更大的努力。這一要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債權國政府應制定出鼓勵商業銀行參與削減債務計畫的具體措施。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以及債權國政府應向債務國提供資金,以削減更多的債務。IMF應採取更加靈活的政策,向那些尚未同商業銀行達成協定的債務國提供信貸,以幫助其進行結構性調整。
“布雷迪計畫”也有其內在缺陷。首先,它所籌措的300億美元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債務危機。根據二級市場上拉美債務的折扣價格,這些資金只能為拉美國家減少13%~14%的本金
和利息。然而,增加“布雷迪計畫”的資金,亦即促使包括國際金融多邊機構和債權國政府在內的官方債權者承擔更多的風險,顯然是十分困難的。其原因有二:IMF和世界銀行的傳統職能,是為其成員國實施公共發展項目和改善國際收支狀況提供資金。如果它們將更多的資金用於削減債務,那么其傳統職能必將受到損害,參與削減債務的風險亦會影響其正常的放款業務。IMF和世界銀行的資金主要來自債權國政府,如果它們為削減債務提供更多的資金,那么由此而帶來的風險或損失最終仍將由債權國政府承擔。此外,由於各債權國政府的自身利益不同,加之本國財政收入有限,它們都不願將削減債務計畫可能招致的風險或損失轉移到自己頭上。其次。“布雷迪計畫”缺乏協調和獎懲措施,因為這個計畫是以自願為基礎的,而債權銀行又不願看到自己的債權受到損失。因此,在數項減債協定中,道義上的說服和債權國政府的壓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4)“債務與股權互換”。這是一種將債務轉化成資本的嘗試,因而常被稱做“債務資本化”。它的基本程式是:投資者(即債務購買人)首先在二級市場上以打折扣的價格購買一筆債
務,然後在債務國中央銀行將債款兌換成債務國貨幣,就地進行投資。債務價格的折扣主要視債務國資信而定。以1987年11月為例,哥倫比亞l美元債務的價格為72~76美分,智利為50—53美分,委內瑞拉為49~53美分,墨西哥為48~52美分,巴西為37~41美分,阿根廷為33—37美分,厄瓜多為31—34美分。
債務資本化使債權人、債務人和投資者三方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可圖。從表面上看,由於債務在二級市場上打折扣出售,債權人必然要蒙受損失。但是,債權人可收回部分債款,加速
資金周轉,減少債務糾紛和縮小債務國“倒賬”的可能性。債務國得到的好處是:減輕債務負擔,吸引新的投資,以本國貨幣“償付”外債,從而緩和了外匯匱乏的緊張局面。至於投資者,他不僅可以通過買賣債務的差價獲利,而且還能在用債務進行投資時享受一些優惠和好處。
相比之下,在參與“債務與股權互換”的三者之間,債權人以低價出售其債權的意願尤為重要。開始實行這種嘗試性措施時,債權人方面只有歐洲和日本的少數小銀行參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大銀行仍然指望債務國能夠按期償還債務。隨著債務國經濟形勢的惡化,一些大的債權銀行也不得不面對債務國基本喪失償債能力的嚴峻現實,在“債務與股權互換”方面變袖手旁觀為積極參與。
1983年12月阿方辛的上台象徵著“還政於民”的民主化浪潮出現在阿根廷。但這並不意味著政治穩定就一勞永逸了。一方面,軍人並不甘心留在軍營里,而是多次發動未遂政變;另一方面,經濟形勢難以好轉,黨派鬥爭不斷加劇。這一切終於迫使阿方辛於1989年提前5個月下台。他在辭職演說中說,他只能用他自己的犧牲來減輕人民的犧牲四。
事實上,阿根廷的“民主化”道路始終不平坦。例如,當90年代末阿根廷經濟出現衰退跡象時,“經濟問題政治化”趨向愈益嚴重。“經濟問題政治化”是指政府的任何經濟政策的
出台或付諸實施,都受到黨派之爭的影響或制約。此外,“經濟問題政治化”還與同一政黨內的分歧與不和聯繫在一起。例如,現總統杜阿爾德與前總統梅內姆均屬正義黨,杜阿爾德甚至還在梅內姆當政期間任副總統。正義黨是阿根廷的第一大黨,曾多次執政(見專欄10—1)。按理說,在國家陷入危機後,這兩人應該同心同德,共渡難關,但梅內姆在2002年1月9日接受智利《商報》的採訪時說,杜阿爾德總統“不稱職”。梅內姆還批評杜阿爾德的經濟政策是“極其壞的”,認為新政府放棄1比索兌1美元的兌換計畫將導致經濟不穩定,“使阿根廷在世界經濟中的參與迅速消失,使阿根廷自我封閉,也會使阿根廷倒退40年”。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阿根廷的政治制度中有一種黨內“相互殘殺”(cannibalism)的傳統。梅內姆貶低杜阿爾德的目的無非是要使自己在2003年的大選中處於一種有利的地位。
(6)必須選擇一種富有靈活性的匯率制度。在全球化時代,由於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聯繫越來越密切,而匯率是這一聯繫的“紐帶”,因此,選擇一種合適的匯率制度,實施恰當的匯率政策,已成為經濟開放條件下決策者必須要考慮的重要課題。拉美國家的經驗表明,浮動匯率制不是十全十美,固定匯率制也不是一無是處。鑒於國際資本流動的速度越來越快,開發中國家應該選擇一種富有靈活性的匯率,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匯率風險”。
(7)提高財政部門的穩健度同樣有助於維護經濟安全。90年代以來開發中國家遇到的歷次金融危機和銀行危機都與金融部門中的各種問題和弊端有關,因此,人們在談論經濟安全時,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問題上。但巴西貨幣危機和阿根廷債務危機則表明,維繫財政部門的穩健度同樣是十分重要的。
在金融全球化時代,開發中國家之所以有必要提高財政部門的穩健度,主要是因為:第一,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兩者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第二,財政安全是經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在理論上,正如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所揭示的那樣,避免貨幣危機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實施恰如其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確保國民經濟的基本面正常運轉,以維繫投資者和公眾對本國貨幣的信心。
(8)正確處理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之間的“三難選擇”。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拉美的現實中,蒙代爾和克魯格曼的“三難選擇”都是成立的。在金融全球化趨勢不斷加
快的條件下,資本流動越來越自由,因此拉美國家在制定獨立的貨幣政策和穩定匯率時常常面臨著困難的抉擇。智利等國的經驗表明,在一定條件下,資本管制有助於避免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之間的衝突。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資本管制的效果會減弱。如果匯率頻繁地波動,而且波動幅度大,就會破壞以穩定國內價格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可見,決策者必須根據不同時期的資本流量、國際收支的狀況以及通貨膨脹壓力的大小來制定相應的政策。要高度重視和正確處理利率與匯率之間的關係。用提高利率的手段來吸引外資和維繫匯率穩定的做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9)政治穩定是維繫經濟安全的必要條件之一。一方面,外資總是希望東道國的政局保持穩定,以便獲得更好的收益;另一方面,在金融全球化時代,資本流動的速度不斷加快,任何一種影響政局穩定的“導火線”都會導致外資溜之大吉。因此,只有保持政治穩定,政府才能專心致志地實施各項改革政策,才能強化本國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才能使經濟改革在良好的外部環境中順利推進。
(10)必須改革國際金融體系。隨著金融全球化趨勢的加快發展,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一些缺陷越來越明顯。因此,國際社會和有關方面應該加強合作和協調,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金融架構。
在減少金融風險和規避金融危機方面,應該發揮國際、區域和國別三個層面的積極作用。在國際層面上,IMF無疑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首先,IMF應該高舉反對“金融霸權”的大旗,更好地為廣大開發中國家服務。其次,它應該在建立新的國際金融架構時主動地協調各方利益。第三,在向陷入危機的開發中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時,IMF應該根據不同受援國的不同情況,提出一個附加條件較少的“藥方”。第四,為了使開發中國家更好地避免危機,IMF應該設計出一整套更加切實可行的“預警”指標體系,並在規範國際資本流動方面制定一些有效的條例。
**
總而言之,開發中國家不能將金融全球化拒之於門外。當然,搭上金融全球化之列車並不意味著開發中國家自然而然地就能到達繁榮富強的“理想之國”。但開發中國家的“決策者與
其說是期望著退回到不太動盪的過去(但過去不如現在繁榮),還不如別無選擇地學會如何面對全球金融市場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