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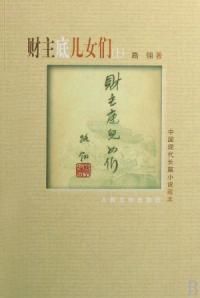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完成於一九四五年,是這個時期出現的篇幅最長的長篇小說之一。 這部小說以江南一家大地主大資本家家庭的風流雲散為中心,力圖反映「一·二八」以後的十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提出在這個動亂的時代中青年知識分子的道路問題。
結構
小說分兩部。小說分兩部。第一部結構雖稍凌亂,但線索仍很分明,從「一·二八」寫到「七·七」事變前,故事中心是蘇州頭等富戶蔣捷三一家在內外多種力量衝擊下分崩離析的過程,穿插交錯地描寫在上海、南京、蘇州的將家兒女的活動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 第二部結構則完整緊密,線索更加清晰,從「七·七」事變寫到蘇德戰爭爆發,集中描寫蔣家的小兒子蔣純祖在大動亂中經歷的曲折生活道路,也穿插描寫蔣家其他兒女在抗戰後方過著平庸麻木的生活。第二部結構則完整緊密,線索更加清晰,從「七·七」事變寫到蘇德戰爭爆發,集中描寫蔣家的小兒子蔣純祖在大動亂中經歷的曲折生活道路,也穿插描寫蔣家其他兒女在抗戰後方過著平庸麻木的生活。
人物
小說寫了七十幾個人物,除蔣家兒女及其親友外,還寫了士兵、軍官、演員、教員等許多人物。小說寫了七十幾個人物,除蔣家兒女及其親友外,還寫了士兵、軍官、演員、教員等許多人物。 叛黨後的陳獨秀和投敵前的汪精衛也在作品中出現。叛黨後的陳獨秀和投敵前的汪精衛也在作品中出現。 作者把財主的兒女,即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放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時代裡加以刻劃,表現他們的思想面貌,挖掘他們的內心世界。作者把財主的兒女,即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放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時代里加以刻劃,表現他們的思想面貌,挖掘他們的內心世界。 作者說:「我所檢討,並且批判、肯定的,是我們中國底知識分子們底某幾種物質的、精神的世界。這是要牽涉到中國底複雜的生活的;在這種生活裡面,又正激盪著民族解放戰爭底偉大的風景。」作者說:「我所檢討,並且批判、肯定的,是我們中國底知識分子們底某幾種物質的、精神的世界。這是要牽涉到中國底複雜的生活的;在這種生活裡面,又正激盪著民族解放戰爭底偉大的風景。」
情節
蔣捷三是蘇州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在京滬沿線許多地方擁有龐大的房地產,而在蘇州的那座巨大的、園林式的豪宅里也收藏著不少的珠寶和古玩。蔣捷三有四個女兒:蔣淑珍、蔣淑華、蔣淑援、蔣淑菊,還有三個兒子:蔣蔚祖、蔣少祖和蔣純祖。他們有的已經成家,有的還在念中學。表面看來,蔣家的人們都聰明、俊秀,而且溫柔多情,相互親愛,其實骨子裡都十分自私和傲慢。在這些子女中,蔣少祖最受人們的矚目。
蔣少祖16歲便離家到上海讀書,在接受了當時的新思想薰陶之後,他與父親決裂,成為蔣家叛逆的兒子。當時,他還只是個單純的青年,在還沒有明白什麼是政治之前,就身不由己地捲入了政治活動,並由此養成了對政治的興趣和雄心。大學畢業後,他和朋友們一起辦報紙,後來,環境變得有些灰暗,他就跑到日本,在濃厚的憂鬱中,他與同學陳景惠結了婚。然而,婚後他又覺得陳景惠雖然樸素而善良,卻並不能理解他對事業的渴望,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惱。
九一八事變的前半年,蔣少祖回到上海,把家庭生活的破碎的幻想拋開,開始了他的活動,接近了社會民主黨,想努力成為一個政治家。但他覺得社會民主黨里的人都很平庸,難有什麼大的作為,而他自己則需要激烈、自由和優秀的個人英雄主義。一二八抗戰剛剛爆發時,他頗興奮了一陣,熱情地希望在戰爭里能夠有所成就,但很快就發現無法達到目的,加之看到了戰爭中的一些混亂、投機、出賣,熱情很快就被澆滅。他看不起所有的人,認為自己是一個自由的、單獨地為理想奮鬥的人。為了擺脫內心的孤獨,他與年輕熱情的女郎發生了暖昧關係,導致女郎懷孕。在家庭和社會的強大壓力下,女郎被迫殺死了剛剛誕生的嬰兒。蔣少祖開始也感到內疚,但很快,自私和傲慢在心中占了上風,他覺得自己其實也沒什麼責任。
蔣少祖在上海與金融界和政府官員往來,擴大自己的社交圈子,成為報刊主筆,在社會上日益擴大了知名度,受到許多人的賞識。他逐漸覺得與周圍的環境越來越和諧,年輕時的激烈真是幼稚得可笑。他開始精明地計算金錢。在發覺兄弟姐妹們正在紐印父親龐大的家產時,他匆匆趕回蘇州,與父親和解,並得到一筆可觀的財產。
蔣蔚祖的精明厲害的妻子首先發難,強行奪取了蔣家大部分家產,引起蔣家兒女激烈的反應,一場財產爭奪戰拉開了帳幕。結果蔣捷三被氣死,蔣蔚祖被逼瘋後跳入長江,而蔣家兒女間相互親愛的面紗也被撕得粉碎。他們瓜分了財產,各自暴露出赤裸裸的自私面目。久病而孤高的蔣淑華經受不起這個沉重的打擊,迅速衰弱死去。
正在讀中學的、不知世事的蔣純祖目睹這一切,精神上十分痛苦,他覺得家裡的一切都代表著陰暗和苦悶。他憎惡所處的苦悶的現實生活,一度產生了毀滅的、孤獨的、悲涼的思想,甚至想到自殺。這時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民族戰爭的空前熱烈的氣氛拯救了蔣純祖,重新激動起他年輕的心。就在蔣少祖等人紛紛撤離南京退往漢口的時候,蔣純祖卻前往上海,到上海前線做後勤工作。
上海陷落了,中國軍隊開始了江淮平原上前所未有的大潰退,日軍步步遏進,局面一片混亂。蔣純祖和一切熟悉的人們失去了聯絡,疾速地向著南京逃亡,然後又精疲力竭地裹挾在無盡的難民和車輛中逃出南京,沿江向上游逃竄。他加入了一個散兵團伙,目睹了人民的苦難。
蔣純祖的哥哥和姐姐們仍舊過著平庸、沉悶、無聊的生活,他們只關心著自己的一點利益,對國家大事卻抱著輕蔑和麻木不仁的態度。聽到蔣淑華丈夫已經戰死的訊息後,蔣淑暖和蔣少祖居然為了推卸對孤兒的撫養責任發生了爭吵。蔣純祖大失所望,他與哥哥姐姐們精神上的裂痕越來越大,而這些人對蔣純祖的“浮躁”也越來越不滿。
蔣純祖進入了一個救亡團體,他漸漸熟悉了武漢,熟悉了他周圍的人們。他先是加入了一個合唱隊,繼而又投身於一個演劇隊,出發到重慶去做抗日宣傳。不過,蔣純祖雖然參加了抗日活動,但他只關心一件事,就是希望在目前的新的一切里成為英雄,享受光榮,所以他仍舊擺脫不掉失望與苦悶。他試圖通過戀愛來獲取安慰,與演劇隊女演員高韻發生了性關係,結果只是陷入更深的苦惱和恐懼。
不久,演劇隊解散,蔣純祖決定到鄉下去,到朋友辦的一所國小去教書,做些實際的工作。但他很快又失望了。儘管他擔任了校長,對包圍在學校周圍的濃重的黑暗的社會空氣仍然毫無辦法。他試圖以高傲來抵抗當地鄙吝的土紳的壓迫,然而也只能是勉強掙扎。他得了重病,在無助中尋求同校女教師萬同華的愛情的撫慰,又出於傲慢而與她分手。他身心疲憊地回到重慶,發現蔣少祖已經成為一個擁有土地莊園的官僚地主,過起了“性本愛丘山”的疏懶的生活。在兄弟間相互交換了鄙視之後,蔣純祖終於又離開重慶,掙扎著到鄉下,死在萬同華的懷抱里。
目錄
第一部
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
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
第9章第10章第11章第12章
第13章第14章第15章
第二部
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
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
第9章第10章第11章第12章
第13章第14章第15章第16章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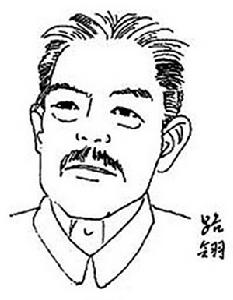 《財主底兒女們》作者
《財主底兒女們》作者《財主底兒女們》名列世紀百強第14。
作者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興,江蘇南京人。生於江蘇省南京市。他的生父本姓趙,但早亡,路翎改隨母親的姓氏。兩歲時,路翎隨母親改嫁給當時國民政府經濟部的一個小職員。由於與繼父關係不融洽,加上家境窘困,路翎童年時起就常常感到精神上的壓抑,變得敏感內向,有些神經質,內心情感特別豐富,經常到文學作品中去尋找安慰,並由此閱讀了許多中外名著。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隨家人輾轉到重慶。 1940年以路翎為筆名在胡風主持的《七月》、《希望》、《呼吸》等雜誌上發表作品。
有短篇小說集《青春的祝福》、《求愛》等,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蝸牛在荊棘上》,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等。 建國後在南京大學執教,1950年後在北京青年藝術劇院,中國劇協創作室工作。
建國後在南京大學執教,1950年後在北京青年藝術劇院,中國劇協創作室工作。 因受胡風錯桉牽連入獄,「文革」結束後恢復名譽。因受胡風錯桉牽連入獄,「文革」結束後恢復名譽。
創作
有這樣一些作家,凌空出世時,尚值青春年少,青春的意氣、膽氣,佐以洋溢的才情、激情,筆之所之,塗抹下大片大片的絢爛,逗引出文壇陣陣驚呼。現代文壇將永遠記得,張愛玲22歲發表了《金鎖記》,曹禺18歲開始構思《雷雨》,路翎17歲動筆創作《財主底兒女們》……
年輕的心沒有羈縻,初次創作長篇的筆更是不懂得節制。事與事,人與人,擁塞在一起,思想撞思想,行動碰行動,言語擠言語,《財主底兒女們》於是就有了80萬字的浩大規模。也因了作者的年輕,這80萬字建構正如同小說中許多人物的思維,充滿混亂,深烙痛苦,稍帶著病態與瘋狂。整體而言,它沒有一以貫之的事件、人物,乃至思想,除了作者恣意潑灑的青春與生命,除了作者追求的,“光明、鬥爭的交響和青春的世界底強烈的歡樂”(《題記》)。按著平常思路企圖從《財主底兒女們》中發現主題的人們往往會失敗:躁動的青春情緒才是這部小說無主題的主題。從局部看,我們可以在每一個人物的思想和行為的背後感到作者的不安痙攣著的執筆的手,卻道不出人物為什麼這樣或那樣想和做。每每,人物心理一激一宕,一蹙一舒,疾推疾進,猛收猛轉,顯得那樣的不可理喻,卻又如此地接近生活和生命的原始狀態。或許正是“無章法”造就了這個作品的奇特與生動:它蕪雜,因為它年輕;它充滿活力,也因為它年輕。
時代背景
小說從“一·二八”寫到“七·七”事變前,故事中心是蘇州頭等富戶蔣捷三一家在內外多種力量衝擊下分崩離析的過程,穿插交錯地描寫在上海、南京、蘇州的將家兒女的活動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
人物形象
小說塑造了王熙鳳式的人物金素痕,以這個人物為中心在蔣家內部掀起一場驚心動魄的爭奪財產繼承權的鬥爭,寫得有聲有色。但是,小說在不少方面,特別是在描寫知識分子道路方面,很大程度上又背離了現實主義。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大批知識分子到工農民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不斷改造自己,由投身民族解放鬥爭而走上同工農結合的大道。
《財主底兒女們》中塑造金素痕時,把她放在同蔣捷三爭奪財產的舞台上,並夾雜著同丈夫蔣蔚祖情感搏鬥,這樣她的潑辣、野蠻、強悍、與陰毒就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而塑造王桂英這樣一個小女子時,作家把她置於對她影響最大的也就是同蔣少祖的情感糾葛時來描寫她,特別是當她有了私生子而被人唾罵時將她內心的掙扎痛苦推向高潮。更不用說在自己的妻子和父親的爭鬥下以致被逼瘋的蔣蔚祖了。在這種關乎人物命運的矛盾衝突中塑造人物,從而形成“強烈的內心衝突和銳角式的情緒波折”的心理藝術。而在這一過程中,人物的意識、潛意識都聚將上來,共同決定著人物的命運走向。也可以說,他作品中的意識與無意識都是共同表現了“人物精神底來龍去向”。
《財主底兒女們》這部以描述知識分子道路為主要內容的長篇小說,卻不是努力反映這個客觀實際,而把具有濃厚個人主義思想的蔣純祖作為當代英雄加以歌頌,鼓吹蔣純祖的道路,其實這條道路是一條脫離廣大民眾,脫離鬥爭實際的歧路。作者說:“我不想隱瞞,我所構想為對象的,是那些蔣純祖們。對於他們,這個蔣純祖是舉起了他底整個的生命在呼喚著。”
小說中的蔣純祖是財主蔣捷三的第三個兒子,抗戰爆發後脫離令人窒息的家庭走向社會。作者以巨大的篇幅描寫蔣純祖在抗戰中曲折的遭遇,用細膩的心理刻劃展現蔣純祖時刻在激盪的精神世界。在作者筆下,蔣純祖忠厚、善良、高貴,富有正義感和愛國心,“他憎惡他所處的苦悶的現實”,對邪惡勢力有一定反抗性,但是他又軟弱動搖,在壓迫加重時往往逃避,從混亂的前線逃到麻木的後方,從演劇隊轉到鄉村國小,又在農村惡勢力壓迫下逃回城市,終於在貧病交加和失戀的精神重壓下死去。如果作者用正確的觀點分析這個人物,自然能給讀者以啟發,但在小說中作者對這個人物同情多於批評,甚至讚揚他孤高自賞,仇視一切理論,實際上也就是肯定和歌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鼓吹拒絕黨的領導、脫離革命集體的個人奮鬥。
在《財主底兒女們》第三部竟然被蔣純祖的生命經歷填滿了的時候,一邊訝異於這種寫法的冒險,一邊不由得佩服了作者的聰明——作者必須,也只能扣住蔣純祖來寫,因為無疑地,作者本人最親近於蔣純祖。
蔣純祖的經歷(或者毋寧說路翎的設計)是奇異的,然而最後,竟然在那么多巨筆已經描摹過了鄉場中的孤獨靈魂之後,路翎又讓他的主人公走進鄉場去教書。他是立意要學習他的前輩呢還是相反?
路翎好寫大波瀾,蔣純祖勇猛如倪煥之,衝動如梅行素,絕望如蕭澗秋,革痼弊他最敢作敢當,遭慘敗時也是他跌得最重,這不能不歸因於蔣純祖的永遠是躁動不安著的靈魂。作者牽扯著他的主人公,讓他不停頓地拼殺,前進,讓他與環境作最徹底決絕的反抗,讓他大哭或大笑,突如其來地作各種決定,直至筋疲力盡。寫蔣純祖內心的狂濤巨瀾時,作者的筆觸也是癲狂的。他幾乎讓他的讀者無法忍受那些幾乎是無休止地翻來覆去的懷疑、驚惶、拷問、折磨,不無慘酷地盼望這一切快快完結。
《財主底兒女們》從整體上看,它時空跨度大,家庭與社會交錯縱橫,人物形象駁雜,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尖銳。為了爭奪上輩留下財產,蔣家兒女明爭暗搶、勾心鬥角、串聯傾軋,終於大打出手。在這爭奪過程中,又人人經受著喜怒哀樂的刺激,在情感上糾纏不清的疙瘩攪得他們自己也常處於無所措其手足的情境。作家在記敘他們不同思想、不同經歷變遷過程的同時,也不時在抒發出自己對這群蔣家兒女們生生死死苦樂的同情。尤其是蔣家小兒子蔣純祖在路翎筆下被描繪成在中國苦苦尋覓的克利斯朵夫。他血氣方剛、忠厚、善良、高貴、富有正義感與愛國之情。
他最憎恨的是他所處的苦悶的現實,具有不尋常的“雄心和夢想”,時刻想創造偉大的功績,獲得非凡的榮譽。但生活賜於他的卻是長期的流浪漂泊,沒有功建,未得“英雄”之稱。自以為自己追求崇高的生活,並為此不遺餘力,但結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沉淪墮落,懺悔不已,病態的狂亂直到毀滅。對於這個人物,作家除給他一個悲劇和給予一定的批判之外,始終都是以欣賞和讚美的筆調來描寫的。因此,在繁複的故事敘述中融合了較多的熱情成分,或抒發描寫對象的苦悶,悲觀、消沉、頹廢;或抒發作家對人物的讚美、欣賞、同情、惋惜。
路翎的蔣蔚祖卻並不十分複雜,他只是一味地戀著金素痕,終至瘋狂,瘋人相對來說好寫一些,情緒大起大落,行為可以乖張到極致。而同樣題材的作品少年人則往往是最難把握的,無論是高覺慧,周沖,還是祁瑞全,比起蔣純祖,都過於單純,清澈見底了。小說中描寫的其他幾個財主兒女,思想面貌和性格特點各不相同,共同之點都
是一事無成。蔣家大兒子蔣慰祖受家庭內部傾軋和妻子放浪的刺激成為瘋子,多次逃離家庭與乞丐為伍,最後燒毀住所,跳入長江,淹沒在波濤之中。這個形象對財主家庭是個尖銳的諷刺,寄託了作者對醜惡現實的憤懣,和對私有財產制的譴責,許多情節動人心弦,但結局卻是消極的。
蔣家的二兒子蔣少祖是個高級知識分子,較早脫離家庭參加抗日愛國活動,但並沒有從立場上思想上背叛財主家庭,抗日也只限於空談,後來成為新的地主、紳士和文化上的復古主義者。蔣少祖所走的道路是通向反動營壘的歧路,但作者對這個人物欣賞多於批判。小說通過這幾個主要人物形象,企圖解答“在目前這種生活里……,這個世界上,人們應當肯定,並且寶貴的,是什麼。”但作品的實際卻沒有得出正確的結論,給讀者的印象只能象小說描寫蔣純祖和他的同伴逃出石橋鎮時“……他們無路可走了。……他們不知道要到哪裡去。”但小說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上和強烈的時代氣氛中,通過一個封建家庭的崩潰及其兒女們的曲折生活道路這一側面,顯示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而且篇幅巨大,又出自一個青年作者之手,因此小說出版後受到進步文藝界的重視。
《財主的兒女們》里的人物形象蔣少祖,時而覺得自己高、偉大,時而覺得自己卑劣、渺小;時而狂熱、興奮,時而消沉、頹唐;時而講求實際,時而耽於幻想,時而是英雄的化身,可以完成一切,時而又覺得怯懦,什麼都無能為力。另一個人物金素痕,既有王熙鳳式的潑辣狠毒,又有暴發戶式的貪婪放肆,完全夠得上一個可怕的惡魔。然而,在丈夫蔣蔚祖逃亡失蹤後的那段時間裡,她又一反常態,痛器流涕,真誠地懺悔,熱切地思念自己的丈夫,這時,她完完全全又是一位溫柔的天使。
《財主底兒女們》中蔣少祖甚至直言“我信仰理性。”雖然作者並不贊同他的追求的和他的人生選擇,但對他那種理性的自我判斷和不盲從意識還是十分推崇的,從他的奮鬥中更可以看得出來。他孤獨高傲自命不凡,始終在探索自己的生活道路,又始終陷於苦悶迷惘幻滅中。他投身於民族解放的洪流,但終因看不到潛藏在人民身上的巨大力量而成為一個特立獨行者。清醒而迷亂,真實與虛偽,高傲與謙遜,悲天憫人與孤獨自私,緊緊纏繞在他身上,使他成為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性格複雜的典型。因此可以說,路翎的小說在心理分析上對理性世界的探索也是成就很大的。無論是清醒的,還是困惑的。他的小說中的人物,特別是那些知識們,都是一個個的探索者。曾有評論家稱其為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書,雖然有誇大其內容含量的成分,可是把《財主底兒女們》稱為知識分子的心靈史詩再恰當不過了。
神判處西緒福斯把巨石推向山頂,然而石頭由於自己的重量又從山頂滾落下來。這種重複而又無意義的勞動象徵了人生的某種荒誕。在我看來,路翎的著作也正是呈現的在時代的裹挾中各色人物苦苦掙扎的荒誕世界。
在路翎的文學世界中,各種人物就像煉獄中的鬼魂在瘋狂地掙扎、嚎叫和攫取自己或是他人的生命。這中間不但有金素痕那樣的殘酷與貪婪、蔣淑媛夫婦那樣的虛偽和狡猾,蔣慰祖那樣的怯弱與陰冷,蔣純祖那樣的猶疑與卑劣,也有他們靈魂深處的污穢中的潔白。在這裡,人性的光明與陰暗,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糾葛就像一張無形的網縛住了每一個人,讓他們在近乎宿命的格線中奔突和滾爬。在這張網中,每個人的靈魂都被撕裂了,那撕裂的各個部分之間有充滿了敵視、攻擊、齧咬和殘害,充滿了自我和他我的對話。正是在這種靈魂的鞭打中,顯出了靈魂的深。這是一群在歷史的漩渦中慢慢地蠕動著的人們,是被遺落在地獄深處飽受苦刑的鬼魂,他們傷害了別人,也摧殘了自己,他們的奮鬥與抗爭並沒有使他們逃出命運的手掌,
因為他們的內心裡有永遠也贖不清的罪過。金素痕利用了蔣慰祖的軟弱與善良騙取了蔣家大量的財富,滿足著自己的物慾和性慾的放縱,卻飽受了蔣慰祖給她施加在精神上的酷刑,想獲得別人的原諒和內心中的安寧而不能,最終失卻了她生命中最為寶貴的東西,蔣慰祖也成為她心靈深處的鬼影,永遠也抹煞不了。蔣少祖一次又一次的突圍,然而作為個人英雄的他終於因為自身的弱點和現實的冷酷成為歷史的殘渣,復歸到他所憎惡的傳統中去成為歷史的零餘者。那個蔣純祖在曠野的漂泊中和命運搏擊,青春的躁動和熱血的賁張,是他的靈魂負了那樣的重荷,展現出他靈魂深處的卑劣和高尚混融的境界。這林林總總的靈魂終於讓人們知道他們是現實中的正常人的靈魂,使人性自身在歷史中所呈現的狀態,是真的帶有血的蒸汽的靈魂,也會想到自身被歷史和現實扭曲後所形成的靈魂的病態,讓讀者發一身冷汗久久不能忘卻。
在這樣對於靈魂的殘酷審視和鞭打中,我也感到作者把自己也燒了進去,也淌了自己心靈深處的血淚。這是在心靈的煉獄中凝成的血淚的史詩,凝結了一個青年面對那個紛繁世界的感受,凝結了作者對人的生存自身境遇的生命體驗和情感體驗。它的文字中燃燒著青春的火焰,跳動著熱血奔流的脈搏,閃爍著人性的光芒。這是用任何或陳舊或時髦的問題和主義所不能涵蓋所不能分析的,它就是一個青年突入現實經歷了靈魂的浴血肉搏所呈現給人們的一部文學著作。
正是在這樣的著作中,我看到了在精神的煉獄中苦苦掙扎求索的作者的身影。
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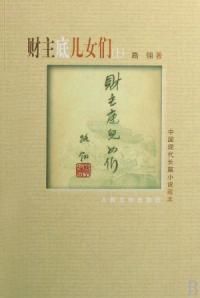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路翎是四十年代“七月派”小說家族的重要一員。在他的早期文學創作中,“原始的強力”作為一種樸素、強悍的衝動性力量和抗爭本能,一貫被視為其小說的基本特徵和終極追求。一九四八年,路翎的長篇巨著《財主底兒女們》由希望社將一、二兩部完整出版,這被胡風評價為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並認為《財主底兒女們》是一部可以冠以史詩名稱的小說。小說敘述了以蔣氏三兄弟等人為代表的青年知識分子在特定時代背景下所進行的酷烈思想鬥爭和血淋淋的人生搏斗,著力挖掘了“原始強力”在他們身上的寄興、表現、以及各自不同的成因與深層內涵。
1945年《財主底兒女們》上卷出版。這部曾被譽為「現代中國的百科全書」39的巨著,細緻而真實地刻畫了蔣蔚祖瘋狂的過程。正如馮雪峰所言,「瘋子發瘋的唯一理由,是以他自己的真實,恰恰碰撞著社會的真實。」40當個體的本真需求與社會的異化力量難以調和時,瘋狂也就成為一種必然。這種折射人類生存困境的精神狀態的產生與成長必然「和歷史的傳統、和現實的人生糾結得深」,從而使「整個現在中國歷史能夠顫動在這部史詩所創造的世界裡面」。41《財》中的蔣蔚祖作為一個富足家族中受著父親寵愛的長子,不用擔心物質貧困,傳統文化的根基使他善於從平凡的生活中挖掘出詩意,順天安命的性格使他有一種自得其樂的平和,他似乎具備了一切使幸福成為可能的條件。這種擺脫生存壓力後的瘋狂更深刻地反映了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的尖銳衝突。
無可否認,蔣蔚祖瘋狂的根本原因是其獨立意志的缺失所導致的不成熟狀態,以至在眾人眼中「好像蔣蔚祖是小孩子」。42然而,這種獨立意志的缺失正是傳統父權的結果。他唯有取消自己的獨立意志順應父權,才有可能獲得和平與安全。妻子的出現使他意識到愛情這種更為本真的需要,從而使他開始反抗父權。然而,獨立意志的缺失使得他無法承擔任何一種選擇所產生的責任,當他試圖倒向愛情的懷抱中時,親情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而導他試圖與親情和解時,愛情又促使他逃離。他於是只能不停地在二者之間奔走逃亡,陷入一種精神分裂。但這種意志發展的滯後並不必然導致瘋癲。他的發瘋,更主要的還是他淪為一種工具性存在,成為父親與妻子之間爭奪的戰利品。在這裡親情是扭曲了親情,愛情是扭曲了愛情。
父親試圖利用父權將兒子束縛在自己的膝下,並且不惜以禁閉的方式來達到這一目的;而妻子更是為了赤裸裸的物質利益利用他的愛情。在其他的人際關係中,這種異化更為嚴重。在蔣蔚祖的周圍,並沒有他所渴求的真正的理解與愛,有的只是用溫情掩蓋的物質利益的爭奪。姊妹與妻子為了財產,在父親屍骨未寒時,以愛情或親情的名義迫使他們有利於自己的表態,為此不惜給他致命的一擊。在這種赤裸裸的實用理性的支配下,人作為主體的意義消弭無形,異化為一種工具性存在。當蔣蔚祖無力順應這些社會認同中的任何一種時,他也就只剩瘋狂一條道路可走。然而,蔣蔚祖也正是以瘋狂洞穿著這個世界的虛偽與醜態,在癲狂中無所顧忌地批判這個不將人當成人的社會,否定了現存的理性與道德。正是在瘋狂中,蔣蔚祖以自己的本真對抗世界的異化,
以情感否定著工具理性與社會認同。路翎以一個靈魂的拷問者的姿態,不僅批判蔣蔚祖的軟弱,而且批判了使他瘋狂的病態社會。雖然蔣蔚祖的瘋狂與自殺並未指示出前進的方向,但他的瘋狂與自殺本身就出於對生存意義的嚴肅思考。「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判斷人值得生存與否,就是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43在整個生存的荒誕處境中,瘋狂與自殺一方面說明了生存的失敗,另一方面則彰顯著生存的意義與激情。
評析
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底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在這部不但是自戰爭以來,而且是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規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詩的名稱的長篇小說裡面,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識分子為輻射中心點的現代中國歷史底動態。然而,路翎所要的並不是歷史事變底紀錄,而是歷史事變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洶湧的波瀾和它們底來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靈在歷史運命這個無情的審判者前面搏鬥的經驗。真實性愈高的精神狀態(即使是,或者說尤其是向著未來的精神狀態),它底產生和成長就愈是和歷史的傳統、和現實的人生糾結得深,不能不達到所謂“牽起葫蘆根也動”的結果,那么,整個現在中國歷史能夠顫動在這部史詩所創造的世界裡面,就並不是不能理解的了。
在封建主義裡面生活了幾千年,在殖民地意識裡面生活了幾十年的中國人民,那精神上的積壓是沉重得可怕的,但無論沉重得怎樣可怕,還是一天一天覺醒了起來,一天一天挺立了起來;經過了無數的考驗以後,終於能夠悲壯地負起了這個解放自己的戰爭底重擔。人能夠概括地對這提出簡單的科學的說明,人更應該理解這裡面的浩瀚無際的、生命躍動的人生實相。在那中間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方面是最敏感的觸鬚,最易燃的火種,另一方面也是各種精神力量最集中的戰場,因而也就是最富於變化的、複雜萬端的機體。這種夾在錘和砧之間的存在,人能夠簡單地對它提出科學的分析和批判,但那裡面的層出不窮的變幻,如火如荼的衝激,鮮血淋漓的鬥爭,在走向未來的歷史路程上,卻有著多么大的教育的意義。
在這裡,作者和他底人物們一道置身在民族解放戰爭底偉大的風暴裡面,面對著這悲痛的然而偉大的現實,用著驚人的力量執行了全面的追求也就是全面的批判。說全面的,當然不應是現象底巨大懼收的羅列,而是把握住精神現象底若干主要的傾向,橫可以通向全體,直可以由過去通向未來的傾向。我們看到了封建主義底悲慘敗戰,兇惡的反撲,溫柔的嘆息,以及在偽裝下面再生了的醜惡的形狀,我們看到了殖民地性個人主義底各種形式,一直到被動物性主宰著的最原始的形式,一直到被教條主義武裝著的最現代的形式。在這中間掙扎著忠實而勇敢的年青的生靈們),雖然帶著錯誤甚至罪惡,但卻是兇猛地向過去搏鬥,悲壯地向未來突進。這一切,被自一·二八到蘇德戰爭底爆發這個偉大的時代所照耀,被莊嚴而又痛苦的民族大戰爭所激盪,被時代要求和戰爭要求鞭打著的這古國底各種生活觸手所糾纏。人沒有權利懷疑作者為什麼把舞台限在後方,
為什麼不正面地接觸到勞苦人民底世界,因為這不是作者要在這裡負起的任務,人卻應該感受得到,在這部史詩裡面所照耀的,正是勞苦人民底神聖的解放願望和他們底偉大的戰鬥目標。人更應感受得到,作者底一切努力一切爭鬥,正是為了和讀者們一道通向那個願望,突向那個目標。作者自己說,一切生命和藝術,都是達到未來的橋樑。正是這個把自己變成達到未來的橋樑或踏腳石的志願,才有可能產生了把七十個左右的人物底運命鏇轉在那個願望那個目標下面的磅大的氣魄。從這裡就可以理解作者所說的,他所追求的,“是光明、鬥爭的交響和青春的世界底強烈的歡樂”。是的,是“歡樂”。但可以把這換寫為“痛苦”,也可以把這換寫為“追求”。歡樂,痛苦,追求,這些原是“我們時代的熱情”(借用那個蔣純祖底用語)還沒有找出適當的表現語的那個passion所必有的含義。時代底passi0n產生了作者底passi0n和他底人物們底passi0n。作者說,
作為他底對象們底綜合性的人物,那個蔣純祖,是舉起了他底整個的生命在呼喚著,然而,人不難感到,作者自己更是舉起了他底整個的生命向他底人物們和讀者們在呼喚著的。原來,作者底對於生活的銳敏、感受力正是被燃燒似的熱情所推進,所培養,所升華的。沒有前者,人就只會飄浮,但沒有後者,人也只會匍伏而已罷。沒有前者,人當然不能突入生活,但沒有後者,人即使能多少突入生活,但突入之後就會可憐相地被那裂縫夾住“唯物的”腦袋,兩手無力地抓撲,更不用說能否獲得一種主動的衝激的精神了。不過,這些當是易於被人感受的,除非他是一段木頭,但人也許不易感受到貫串在這裡面的神經系統似的要素,作者底深邃的思想力量或者說堅強的思想要求罷。沒有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現實主義就沒有了起點,無從發生,但沒有熱情和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現實主義也就無從形成,成長,強固的。前者使教條主義狼狽地潰退,後者使客觀主義不能夠藏身。
但若就一部作品底創造過程說,這三者總是凝成了渾然一體的、向人生搏鬥的精神力,而這裡面的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的成份,開始是盡著引導的作用,中間是盡著生髮、堅持的作用,同時也受著被豐富被糾正的作用,最後就收穫了新的思想內容底果實。人會吃驚於這部史詩裡面的那些痛苦的境界,陰暗的境界,歡樂的境界,莊嚴的境界……,然而,如果沒有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這些固然無法產生,但如果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不是被一種深邃的思想力量或堅強的思想要求所武裝,作者又怎樣能夠把這些創造完成?又怎樣能夠在創造過程中間承受得起?正是和這種被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所武裝的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一同存在的,被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所擁抱所培養的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使作者從生活實際裡面引出了人生底悲、喜、追求、搏鬥積夢想,引出了而且創造了人生底詩。
正由於抱著了這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所以作者能夠創造出“光明、鬥爭的交響”。說交響,當然是在眾聲底和鳴中間始終有著一條主音在。人不難看到,被民族解放戰爭中間的時代要求和人民要求所照耀,被對於半封建半殖民地意識形態的痛烈的批判所伴奏,迴旋著前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底由反叛到敗北,由敗北到復古主義的歷程,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底在個人主義的重負和個性解放底強烈的渴望這中間的悲壯的搏戰。在那個蔣少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控訴:知識分子底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結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義所戰敗而走到復古主義的泥坑裡去。這是對於近幾十年的這種性格底各種類型的一個總的沉痛的憑弔。而在那個蔣純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號召:
走向和人民深刻結合的真正的個性解放,不但要和封建主義做殘酷的搏戰,而且要和身內的殘留的個人主義的成份以及身外的偽裝的個人主義的壓力做殘酷的搏戰。這是這一代千千萬萬的青年知識分子應該接受但卻大都不願誠實地接受,企圖用自欺欺人的抄小路的辦法迴避掉的命運。不用說,和一切真實的心靈一樣,作者是向著未來,為了未來的,所以他底熱情的形象到了以蔣純祖底傳記為主音的第二部,就更悽厲,更激盪,更痛苦,也更歡樂而莊嚴.在被丟掉了的初稿裡面,相當於蔣純祖的那個人物,是走上了比他更年青、更單純、也就能夠直線突進的,在這裡的少年陸明棟所走的路,但這裡的蔣純祖卻留在了後方,承受了痛苦的搏鬥,而且終於倒下了。這是,人物性格底內在要求不能不這樣,
作者自己的思想要求也不能不這樣。走向未來,當然有種種的路,那裡面也當然有直線突進的路,但直線突進的路並不能變為對於此時此地的負擔的逃避,而蔣純祖底性格更不是這樣的幸運兒。他得承受更大更大的痛苦的搏鬥,從他底搏鬥裡面展示出更深更廣的歷史的意義。一個蔣純祖底倒斃啟示了鍛鍊了無數的蔣純祖。就這樣,作者完成了他底史詩底構成和他底人物底經歷。在我們底文藝領野,矗立著魯迅的大旗。在今天,人會承認這面大旗,人更樂於自命是這面大旗底衛士,但人卻不願或不肯看見,多年以來(包括魯迅在生的時候),
雖然也有一些來自這個傳統的真誠的戰鬥,但卻有多少腐蝕這面大旗,淹沒這面大旗的烏煙瘴氣。什麼是魯迅精神?豈不就是生根在人民底要求裡面,一下鞭子一個抽搐的對於過去的襲擊,一個步子一印血痕的向著未來的突進?在這個意義上,不管由於時代不同的創作方法底怎樣不同,為了堅持並且發展魯迅底傳統,路翎是付出了他底努力的。自新文藝誕生以來,一直肯定著學習世界文學底戰鬥經驗。然而,雖然不能抹殺那努力下來的痕跡,但可悲的倒是太容易發現結構底模仿,主題底竊取,人物底抄襲……●世界文學底戰鬥經驗應該指的是,那些文藝巨人們雖然各各在時代底限制和思想底限制下面,但卻能用著最高的真誠向現實人生突進,把人生世界裡的真實提高成藝術世界裡的真實的,那一種戰鬥的路徑和戰鬥的能力。
那么,由於人類解放思想底武裝和我們偉大的時代底要求這些有利的條件而擺脫了他們底思想上的限制或苦惱,從戰鬥底需要出發,汲取甚至征服著幾個偉大的作家(特別是L·托爾斯泰)底現實主義,路翎也是付出了他底努力的。但作者是二十幾歲的青年,而且成長在生活在激盪一切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時期,所以他底搏鬥,人生上的和藝術上的搏鬥都燃燒在青春底熊熊的熱情火焰裡面。人如果能夠看出這灼人的青春底火焰的對於我們底人生、我們底文藝有著怎樣的寄與,人就能夠把作者自己所說的“失敗”和“弱點”只當作青春的熱情所應有的特點來理解的罷。所以,《財主底兒女們》是一首青春底詩,在這首詩裡面,激盪著時代底歡樂和痛苦,人民底潛力和追求,青年作家自己的痛哭和高歌!就暫用這幾節話當作對於這首詩和他底讀者們的祝福罷。
評價
這是一部心靈史。作者執著到幾乎頑固地潛入每一個人物的心靈深處,汲汲於探詢和描繪他們隱秘的內心苦惱,痛苦的生命創傷。在心靈的真實的悸動面前,非善即惡的傳統概念失色了。作者似乎只關心一個是非:真的還是假的。——你很難指責誰:蔣少祖虛偽嗎?他渴望懺悔的衝動是那樣熱烈,他憂國憂民的思考是那樣深沉,他是小說中作者著力描繪的最有頭腦的人,甚至於人們一再指責的他的復古,作者也未必對之抱有完全的反感。作者曾無限溫柔地描摹蔣少祖的感動:夕陽黯淡,大地肅穆,雲群舒捲,晚風輕拂,“祖先們底魂靈”神秘而莊嚴。金素痕無恥嗎?行為上顯然是的,但返歸到她的內心,作者為她的一舉一動都準備了辯護詞,把她看作“僅僅成為一個妻子和母親時”的女人,動情地述說她是如何害怕淒涼的未來,如何在蔣捷三靈前一空所思,哭泣如小孩,為了什麼突然地由天使變成魔鬼,瘋狂地攫奪蔣家的財產,等等,逼迫你恨她不得又憐她不得。這種寫法有時固有其是非含混之弊,但它赤裸裸的真實或許恰恰更接近文學的本來意義。“路翎所要的並不是歷史事變底紀錄,而是歷史事變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洶湧的波瀾和它們底來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靈在歷史運命這個無情的審判者前面搏鬥的經驗。”(胡風:《序》)把每一個人物當作一個獨特的世界,路翎成功於不落入任何窠臼,成功於沒有現成的思想框范他的人物,人物是鮮活的,這段歷史因而也是鮮活的。大概這正是年輕的好處:他忙著傾吐,忙著展呈,還來不及判斷,也顧不上(或者是沒有學會)下結論。
年輕還有一點好處,就是從一開始就站在了歷史的更高處。在同樣題材的繼承、延伸、開拓或變異中,新進作家的個性凸現得更其清晰和鮮明。
現代寫大家庭的作品多長於刻畫長子長孫,路翎的蔣蔚祖卻並不十分複雜,他只是一味地戀著金素痕,終至瘋狂,瘋人相對來說好寫一些,情緒大起大落,行為可以乖張到極致。而同樣題材的作品少年人則往往是最難把握的,無論是高覺慧,周沖,還是祁瑞全,比起蔣純祖,都過於單純,清澈見底了。在你發現《財主底兒女們》第三部竟然被蔣純祖的生命經歷填滿了的時候,一邊訝異於這種寫法的冒險,一邊不由得佩服了作者的聰明——作者必須,也只能扣住蔣純祖來寫,因為無疑地,作者本人最親近於蔣純祖。
蔣純祖的經歷(或者毋寧說路翎的設計)是奇異的,然而最後,竟然在那么多巨筆已經描摹過了鄉場中的孤獨靈魂之後,路翎又讓他的主人公走進鄉場去教書。他是立意要學習他的前輩呢還是相反?
讓知識者進入鄉場,是許多現代作家的一條習慣思路。遠離背景,一空依傍,對於荒蠻的民間,知識者敏感憂鬱的靈魂總能浮現得更清晰一些,就像曠野里一棵孤獨的樹。這些故事也有著相近的模式:青年知識者躲開都市,來到鄉間,或與愚民搏擊,或糾纏於無奈人間的明爭暗鬥,結果無不是一敗塗地,落荒而逃。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舉出《倪煥之》《虹》《二月》《夢之谷》《圍城》,《財主底兒女們》亦是其中重要一部。路翎好寫大波瀾,蔣純祖勇猛如倪煥之,衝動如梅行素,絕望如蕭澗秋,革痼弊他最敢作敢當,遭慘敗時也是他跌得最重,這不能不歸因於蔣純祖的永遠是躁動不安著的靈魂。
作者牽扯著他的主人公,讓他不停頓地拼殺,前進,讓他與環境作最徹底決絕的反抗,讓他大哭或大笑,突如其來地作各種決定,直至筋疲力盡。寫蔣純祖內心的狂濤巨瀾時,作者的筆觸也是癲狂的。他幾乎讓他的讀者無法忍受那些幾乎是無休止地翻來覆去的懷疑、驚惶、拷問、折磨,不無慘酷地盼望這一切快快完結。人們都說《財主底兒女們》受《倪煥之》影響極深,可能情節安排上是這樣。然而,《倪煥之》寫得穩健從容,是中年人講的故事,當倪煥之不堪心靈的重負,跌躓於地時,你會大吃一驚;《財主底兒女們》則緊張匆迫,是少年急不可待的表白,蔣純祖那顆“永遠沒有安定”的魂靈溘然飄逝的時候,你不由得長出了一口氣。
這就是少年人書寫的心靈史,一座雜草與鮮花並生的山崗,一首激昂熱情又時而顯出狂亂的“青春底詩”,《財主底兒女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