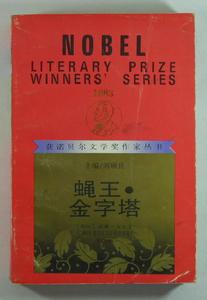 《蠅王-金字塔》
《蠅王-金字塔》威廉·戈爾丁(1911-1994)英國作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蠅王》、《繼承者》、《金字塔》、《自由墮落》、《看得見的黑暗》、《紙人》等。1983年作品《蠅王·金字塔》獲諾貝爾文學獎。
圖書簡介
 《蠅王-金字塔》
《蠅王-金字塔》作者:威廉·戈爾丁著;梁義華等譯
叢編項: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
裝幀項:精裝 21cm / 648頁
出版項:灕江出版社 / 1992
作者簡介
 威廉·戈爾丁
威廉·戈爾丁威廉·戈爾丁( William Golding, 1911~ 1994)英國小說家。生於英格蘭康沃爾郡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自小愛好文學。 1930年遵父命入牛津大學學習自然科學,兩年後轉攻文學。1934年發表了處女作——一本包括 29首小詩的詩集(麥克米倫當代詩叢之一)。1935年畢業於牛津大學,獲文學士學位,此後在一家小劇團里當過編導和演員。 1940年參加皇家海軍,親身投入了當時的戰爭。 1945年退役,到學校教授英國文學,並堅持業餘寫作。1954年發表了長篇小說《蠅王》,獲得巨大的聲譽。1955年成為皇家文學會成員。1961年獲牛津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辭去教職,專門從事寫作。
戈爾丁是個多產作家,繼《蠅王》之後,他發表的長篇小說有《繼承者》(1955)、《品契·馬丁)(1956)、《自由墮落》(1959)、《塔尖》(1964)、《金字塔》(1967)、《看得見的黑暗》(1979)、《航程祭典》(1980)、《紙人》(1984)、《近方位)(1987)、《巧語》(1995)等。其中《航行祭典》獲布克·麥克內爾圖書獎。此外,他還寫過劇本、散文和短篇小說,並於1982 年出版了文學評論集《活動的靶子》。
戈爾丁在西方被稱為“寓言編撰家”,他運用現實主義的敘述方法編寫寓言神話,承襲西方倫理學的傳統,著力表現“人心的黑暗”這一主題,表現出作家對人類未來的關切。由於他的小說“具有清晰的現實主義敘述技巧以及虛構故事的多樣性與普遍性,闡述了今日世界人類的狀況”,198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作品簡介
蠅王的故事其實很簡單,未來的一場戰爭毀掉了人類的和平。有一群孩子乘著飛機路過海上時發生了墜機事件並困在了一個荒島上。 最初孩子們齊心協力,共同應付隨之而來的種種困難。但由於對“野獸”的恐懼使孩子們漸漸分裂成兩派,代表理智與文明的一派與代表野性與原始的一派,最終爆發了兩派中的矛盾。
蠅王來源於希伯來語,原詞為Baalzebub(應該是這樣,又有說此詞出自阿拉伯語)。在英語中,“蠅王”則是糞便與醜惡之王(或污物之王),在《聖經》中,Baal被當作“萬惡之首”。在小說里,蠅王不只是象徵著醜惡的懸掛著的豬頭,更代表的是人性最深層的黑暗面,是無法避免的劣根性。
Golding是很典型的受戰爭影響後的文學家。他參加過海戰,參於過諾曼第登入,目睹戰爭的殘酷以及對人性的種種迫害與藐視。戰爭結束後這一代的文學家心中不免充滿了失望與沮喪,不可能要求他們是溫和且善良的,他們也無法寫出午後野餐或男女情感一類的作品。充斥他們內心的便是病態世界中人性的畸變,文明社會如何在人的原罪本性的改變下一步步走入墮落與毀滅。同時,他們又由於無法找到破解這一巨大難題的出路而頹廢不已,最終找不到緩和之點,只能以作品人物的死亡或消失來圓作品的結尾。
蠅王是一部很注重心理描寫的作品。在整十二章的線性敘述過程中,主要以理性派的眼光出發,以理性的態度(非完全性的)來評價與施行荒島生活中遇到的種種難題。拉爾夫是理性派自然的主角,全書也是他的觀念與角度看待問題。拉爾夫是一個海軍軍官的十二歲兒子,受過良好教育,溫文爾雅,始終相信只有文明社會的船來拯救他們,他們才能獲得通往文明社會的出路。於是在荒島生活中,他不僅樹立了“海螺”的權威性,建立起一個由大孩子領導的團隊,從而解決了住宿,食物以及求救問題. 他永遠都惦念著那冒出煙的求救信號。雖然在某些時候他的理性最終被本性所征服,但他最後痛苦的掉下眼淚,也代表了他是唯一一個在人性轉變的過程中還有理智的人物。
與之相對的則是代表野性的傑克,傑克是唱詩班的大孩子,有領導才能,雖然信奉基督但渾身充滿自然的力量。他從開始就睽視“海螺”的權威,企圖以力量當上至高無上的地位。他的野獸本性也充分的表現在對野豬的獵殺與屠宰上。他改編式的將唱詩的聖歌歌詞變為“殺野獸咯,割它喉嚨,放它血咯”。表現了一股震嚇的威力,最終當野性派戰勝理性派時,他就把拉爾夫當成了自己的獵物,瘋狂搜尋。並且要把曾經並肩作戰的同年齡朋友殺喉見血。
附庸著這兩派人物的,便是豬崽子與羅傑。豬崽子是個胖胖的且有哮喘病的男孩,戴著眼鏡,並且經常被人取笑。但拉爾夫以他的理性人格魅力讓豬崽子傾倒,於是豬崽子就成了拉爾夫身邊最貼近的人物。他時刻強調“海螺”的權威,強調著拉爾夫的求救理念。但他卻的確是個純理論家,最後也因"海螺"而慘死在海崖上。相對而言羅傑的篇幅則較少,但他兇惡殘忍的個性與行為卻讓人過目不忘,他幫凶式的鄶子手性格,讓人不寒而慄。很難想像他僅僅只是跟豬崽子一樣年紀的小男孩,卻狠狠的推倒大巨石,讓豬崽子摔死海崖。
西蒙則是引起事件高潮的關鍵人物。他有些懦弱且患有癲癇症。但他思想敏感,遇事總會以哲學的角度來看待問題。也只是他最初提出“也許,也許......野獸就在我們自己身上。” 雖然引來了孩子們的一致反對與嘲笑,但他的想法卻正好切入了事件的主題。也在他看到懸掛的豬頭從而隱約間見到蠅王對自己的話語,他似乎成了一個先知性的人物. 只是先知從來都是被遺棄的對象,蠅王也強烈的暗示了因為他的預言,也使得他死於非命。
在這裡必須提出,拉爾夫與傑克是之前一名英國著名兒童文學家的代表作中的人物。只是恰好相反的是,在那兒童文學中,他們倆是最要好的朋友,齊心協力,同甘共苦戰勝了許多困難。是人性“善”的表現。Golding應該就是為了諷刺在這病態世界中"善"的虛偽,從而寫出了"惡"的真正導向,那就是"野獸",就是人性的黑暗面,也就是“蠅王”。
Golding對人物的心理塑造採取了相當多的蒙太奇手法。從拉爾夫在沙灘上滿身大汗的行路到他思想跳躍到夏天時爽涼快樂的英式農場生活,也從傑克對海螺的念念不忘到他獵殺野豬時的思想劇烈動作。由於Golding出色的對心理進行了全方面的描寫,從而使人物更加立體化,讓人過目不忘。
在荒島文學的整個範疇中,自《魯賓遜飄流記》到《蠅王》,則是整個人類思想狀態的一種記敘過程。之前的荒島文學強調的是人的能動性,人與自然斗其樂無窮,並且在戰勝自然戰勝自己的同時實現自己的價值。然而二十世紀以來由於戰爭的迅速進化,遠距離武器的廣泛使用及巨大殺傷性武器的強烈摧毀性,使西安作家們沒有辦法再找到一種和諧平靜的解決方案。於是他們逃避到荒島上自己深思人類的劣根性與罪惡。然而他們找不出出路,只好讓荒島成為埋葬一切的總根源。雖然故事最後整個荒島被熊熊燃燒,但如果最後沒有象徵文明的大人們的出現,孩子們也恐怕沒辦法繼續生存下去。
作者十分強調了文明社會中的幾個標誌之物。比如大孩子們無論如何一定要衣服掩體,上廁所要定點去上不可污染水源,就連最小的孩子一開始也記得自己的家庭住址以及電話號碼。然而當獸性完全的征服人的理智之後,這些孩子們也變成了連自己名字都記不起來的野蠻人。
從暴風雨夜孩子們(包括拉爾夫)失手打死了西蒙之後,其實蠅王的本性就已經很清楚的表現給了讀者。雖然豬崽子辯解說著原由,但拉爾夫還是很痛苦的哭泣著自己的過失。人的本性是惡的,當蠅王降臨時,所有的理智都似乎敗給了仇恨與罪惡。不管結局理智派被解救這一機械降神手法到底代表了作者何種的意圖,仰或是他找不到解決途徑而無可奈何的一種自我安慰方法。但只要讀者仔細思考蠅王的本質與其來源,並將從中引申出的社會價值與人生理念運用於自我的哲學思維中,那么Golding這一本薄薄的小說也達到了它本有的目的。
啟示及意義
1983年,威廉·戈爾丁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聲稱,這是“因為他的小說用明晰的現實主義的敘述藝術和多樣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神話,闡明了當今世界人類的狀況。”這句話精確地詮釋出《蠅王》的藝術特點,那就是現實主義的描繪敘述和象徵體系的巧妙結合。小說比較典型地代表了戰後人們從那場曠古災難中引發的對人性思考,旨在呼籲正視“人自身的殘酷和貪婪的可悲事實”,醫治“人對自我本性的驚人的無知”,從而建立起足夠的對於人性惡的防範意識。戈爾丁向我們展示的是人類社會浩劫的一個縮影,至於導致災難的原因,他將其歸結為人性惡,正是人性惡導致了人類自身的不幸。“野獸”即是人性惡的象徵。正是由於人們總是不能正視自身的惡,於是悲劇才一次又一次地發生。以人們印象中“天真無邪”的孩子為主角,也許能更深刻地揭示出人性中最容易被掩蓋的和最深層的一面。男孩們在文明社會培養而成的現代民主意識在這個小島上短短的時間裡經歷了一個迅速衰落的過程,其根源就在於人性的墮落,就在於理性判斷和道德良知的分崩離析。
蘇格拉底說:“認識你自己”,至今仍是一句天啟式的至理名言。在人類發展史上,人類對自身的惡的認識的確是極不清楚的。而人要認識自己,最深刻的莫過於認識自己的人性,如哲學家黎鳴所說:“自知者莫過於知己之人性,自勝者莫過於克服自己人性的弱點、抑制自己人性中潛在的惡念。”
西方古代哲人,特別是宗教先知是明確的人性本惡的代表者,認為所有的人生來有罪,要用一生來懺悔、贖罪,只有篤信上帝,才能獲得靈魂的拯救,即原罪說。中國古代聖人主張人性善的觀點,孟子說:“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宋代王應麟在《三字經》中將其總結為:“人之初,性本善。”中國人與西方人在關於人性本善還是本惡的問題上持完全相反的觀點,這種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深刻地影響了中西方文化長期以來極其不同的發展道路和命運。
應當怎樣認識人性?哲學家告訴我們,人性在本來不可分的意義上統合以下三重屬性。即:
1.人性第一層:生物性,偏於惡;
2.人性第二層:社會性,善惡兼而有之;
3.人性第三層:精神性,偏於善。
人性本不可分而強以分,目的在於更準確地理解人性。但這三層屬性卻不是三一三十一的平均數,否則還是善惡難辨。我國學者黎鳴在他的哲學著作《人性的雙螺鏇》中,使用了一個帶有假設性的公理,即,越是歷史悠久的事物,其惰性越大,發生變化的可能性越小,而且這種惰性與它出現至今的時間成正比。黎鳴運用複雜的數學模型進行推導,結論是:
人性的90%偏向惡,只有10%偏向善!
這便是對人性善惡傾向的總估計,如果再用歷史比較的方法進行推理,這個結論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證明。也就是說,西方學者關於人性的認識基本上符合真實的人性,因此,他們對善的理解也是相應地真實而有效的。而中國古代聖人關於人性的認識則基本上是錯誤的,與真實的人性不相符,因此,他們關於善的觀點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空想,虛假、無效,而且“自欺欺人”。中國古代哲人帶頭在“認識自己”的道路上走偏了,所以中國文化在2000多年的發展中始終處於自相矛盾的狀態中,無法走出這個怪異的“局”。
人的生物性層次的惡,主要表現為惡的潛意識,任何人在這個層次上都具有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傾向,即任何人都自然地有作惡的潛在性或傾向性。在社會生活中只要人們缺乏外部的壓力,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就會變成顯在的可能性,從而產生真實的惡意識,乃至惡行為。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原惡”。人的社會性層次的惡,則主要表現為有意識的惡,以及表現為行為的惡,如詐欺、強姦、盜竊、搶劫、殺人等。《蠅王》就是對人性惡的最好的詮釋。拉爾夫身處邪惡的環境,他逐漸認識到,人類內心的惡在威脅著和吞噬著人性,自己和同伴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傑克和他領導的那幫孩子不斷作惡,形同走獸,但最終卻是這伙走獸摧垮併吞噬了每一個人,使孩子們喪失人性,與之為伍。人類內心中的原始衝動在光面堂皇的幌子下無限制地發展並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可,而它留給人們的就只有恐懼、敵意和仇視,生活於是演變成為一場無法無天的權力之爭。這就從開始表現的人的生物性層次的惡過渡到了社會性層次的惡。
在中國古代,甚至今天,說人性本惡,或人生來就自私是絕不會受歡迎的。楊朱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本來一語道破天機,但這樣的觀點遭2000年的唾罵,也決不會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墨子講“兼愛”,孟子斥之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中國人好講假話,好講漂亮話、好講面子,還要理直氣壯地講,其實早從孔孟時代就開始了。試想,在一個由原惡的人組成的社會中宣揚“克己復禮”、“清心寡欲”、“上智下愚”,會是個什麼樣的結局?只能是惡人當道,好人受氣,甚至有生命之憂。正如詩人北島所說:“卑鄙詩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一語道出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徵。聖人們被歷代中國人捧到了天上,頂禮膜拜兩千年,但正是由他們開創的文化只不過被統治者當作作惡的為所欲為的遮羞布而已。一直到現在還有人在鼓吹“新儒家”,要讓自己的孩子們繼續“讀經”,真是撞了南牆還死不回頭,沒救了。
在《蠅王》里,傑克有一個面具,它的寓意是,人之所以作惡而毫無顧忌,關鍵在於有一張“假”臉。人一旦帶上了面具,就有了狂歡的欲望,獸性就可以盡情地宣洩,而事實上掩蓋惡的又絕非僅僅只是面具,更可怕的還是善的藉口和理由,這種“面具之惡”比更對人類具有威脅性。小海島上發生的惡性事件,西蒙的被害,就是限制毀滅性衝動的人類文明被孩子們畫在臉上的面具所衝破的。人類的歷史上災難性事件,有幾個不是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希特勒的“衝鋒隊”、“黨衛軍”,文革的紅衛兵運動在作惡時不都是高喊著自己漂亮的口號嗎?可見,對人類威脅最大的還不完全是人們容易看到或體會到的人性惡,而是人在善的面具下所從事的惡。阻礙一個人進步的最大的敵人,往往是這個人自己,同理,阻礙一個文化發展的最大的敵人,往往是這個文化自身。其原因,就在於人們常常缺乏對自身的原惡的認識,普遍存在於一切人身上的人性的原惡。這是任何人從生到死都必須與之戰鬥的不可輕視的敵人。這就是《蠅王》帶給我們的最大的啟示。
發生在太平洋孤島上的這場未成年人之間文明與野蠻的鬥爭,不能被認為是虛擬的和無意義的。它是人類歷史的演繹,並且今後還會繼續演繹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