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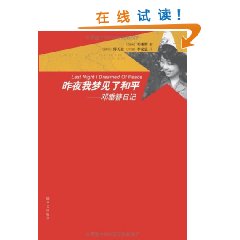 昨夜我夢見了和平
昨夜我夢見了和平一位戰死的越南女兵,她的日虻記錄著怎么的戰爭柔情?曾經的美國大兵為何最終決定讓這日記重見天日?
一部感動全人類的傾訴之書、和平之書。
編輯推薦
在一場戰鬥揭開序幕前,我與美軍一位士兵在戰壕中靜候,我們互相交談著自己曾經參加過的戰役。他講給我聽他剛參加過的120名美軍與一位越南女兵對抗的奇特的戰鬥:他的部隊在德普西邊的密林中發現許多棚子,就在那一瞬間,對方有一個人向他們開火,……為了抓活的,美軍向抗拒者呼籲投降,但得到的回應卻是更加猛烈的射向美軍的子彈,這是一位英雄無比的人物,雖然美軍武器裝備齊全,但卻經過一段不短時間的戰鬥才遏制了對方唯一的一名槍手。看到對方仍在開槍,美軍開始猛烈還擊並擊中了對方,當美軍來到那人倒下的地方時,才發現那是一位婦女,她是為了保衛一座醫院中的傷員,在她身旁只有一支CKC半自動步槍,一個裝著幾本小冊子的帆布包。
——摘自弗雷德給鄧垂簪母親的一封信
幾天后,她的遺體被當地的少數民族同胞發現,一粒子彈深深地穿過了她的前額。
——摘自該書英文版的序言
媒體推薦
“情感的劇情波瀾起伏,就像戰爭一樣殘酷迷人。”
——塞斯·麥當斯,《紐約時報》
作者簡介
鄧垂簪(1942-1970),生於越南河內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的文化薰陶。她畢業於河內醫科大學,愛好文學,偏愛越南詩歌和外國小說。1967年,鄧垂簪進入越南南方游擊隊活躍的廣義省,成為一名戰地醫生,在美軍炮火近在咫尺的威脅下,她卓越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深受戰友和當地人民愛戴。1970年6月,她在轉移途中中彈犧牲。這兩本日記記錄了鄧垂簪1968——1970年間的戰爭經歷與情感。美軍軍官弗雷德在繳獲的檔案資料中把它們保存下來,經過15年的歲月,終於送回到鄧垂簪的親人手中。日記的出版在全球引起轟動,人們爭相閱讀,為其中真摯的情感、真實的困惑和真正的勇氣而感動。這些日記不僅屬於鄧垂簪自己,也屬於每一個渴望真情、自由和幸福的人,不僅感動了殘酷戰火中的“他們”,也將感動生乾和平、長於和平,而追求生命意義的“我們”。
寫作背景
在美國陸軍第四師第三獨立旅所駐紮的德普縣,當年8月,當地10萬人口中,總共有大約一半以上的人口被驅趕到其他城鎮或難民營里。只有一號公路沿線的一些村落保存了下來。但幾乎每一個縣都成了美軍自由炮擊和轟炸的區域,老百姓都住在地洞或防空掩體裡,這些地洞同時也成為游擊隊的隱蔽所。許多村落都被燒毀或夷為平地,以防止游擊隊用來掩蔽。原野里遍布彈坑,附近的樹林也因為化學落葉劑而枯萎(在三個半月中,第三旅一共向德普縣和鄰近的地區發射了6.4萬發炮彈)。從4月到8月,越共部隊損失1857名,被俘566名(按該旅的統計數據)。但在上述幾個月的交火中,美軍也遭到重創,800多人的一個單位,共有120人死亡,490人受傷。
到了9月,俄勒岡州特遣部隊與其他幾個單位合一,組建為亞美利堅師團。從那時候到1971年11月,此單位一直在廣義省和廣信省一帶執行軍事行動。最後,亞美利堅師團成了美軍臭名遠揚的最差勁的一支部隊。這個師屬下的三個旅從未有效地相互配合過,其他的幾個單位也經常被調來調去。駐紮在德普縣的第十一陸軍輕步兵旅是一支最雜亂無章的部隊。它在上陣之前根本沒有經過什麼訓練,只有一小部分老兵和幾位士官,其他都是新兵。一開始,軍中的士氣本來就不高,隨著傷亡人數的猛增更是每況愈下。它在德普軍事基地的形勢由於內部種族衝突和服役軍人與職業軍人之間的矛盾而愈加惡化。科林·鮑威爾在1968年曾在第十一旅下屬的一個單位擔任過少校指揮官。他後來寫道,他在基地的每個夜晚都要把睡床搬來搬去更換位置,“一方面是提防越共的間諜跟蹤我,另外,也不排除軍營里會有人偷襲指揮官的可能”。1968年3月16日,第十一旅的一個排闖進了廣義省北部的山美村,把村裡的老人、婦女和小孩趕進一道渠溝里,開槍射殺了347人。一年多後,事件的真相才被揭露出來,這就是震驚世界的“美萊大屠殺”慘案。然而,第十一旅,就像整個亞美利堅師團一樣,陷入了一場與它們前任部隊無異的戰爭。游擊隊和北越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1969年初,他們相互配契約時向所有的美軍基地發起了進攻)。美軍密集的轟炸和炮擊也說明了這一點。
垂簪極其生動地描述了這場戰爭。她見證了噴氣式戰鬥機投擲炸彈,發射火箭的直升機射出一串串曳光彈,偵察機、直升機參加攻擊,還有美軍大規模的掃蕩。她記錄下了令樹葉枯萎的橙色落葉劑是如何使她和她的同伴們變得衰弱無力,以及一顆白色的磷彈是怎樣把一個青年烤焦的悲慘景象。她還看見那些被夷為平地的村莊,倖存下來的老百姓在廢墟旁徘徊,不願離開他們的家園。在一個執行任務的夜晚,她穿過公路,越過三面都被探照燈和照明彈照得雪亮的山坡,感覺仿佛正置身於一個舞台之中。另一個夜晚,她經過一個叫做“溪山”的地方,這裡是德普縣的稻米之鄉,但被美軍炮火控制,美軍巡邏嚴密,還安裝了電子監控系統。她在地下掩體中睡覺,曾經在齊胸深的水中度過一個夜晚,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1969年4月2日,美軍進攻鄧垂簪醫院附近的一個村莊,迫使傷員和幹部們不得不捨棄醫院。從那時起,她和她的同事們經常在不斷地轉移,無法為醫院找到一處安全的地點。有的地點遭到炮擊,有的地點被敵人發現。每一次轉移,大多數士兵和護士會帶著輕傷員先走,垂簪和一些護士則留下照顧重傷員,直到他們帶著擔架回來接應。有一次,敵人來到附近,她只好和幾個護士把一個身材高大的、腿骨折的重傷員拖進地洞。還有一次,她只得扔下自己的背包逃跑,背包里裝著差不多她的全部私人用品。
1970年6月2日,她屯駐的蒼山野戰醫院遭到轟炸,5人喪生。當醫院在6月12日第二次遭到轟炸時,醫院領導班子判斷,後來的資料顯示他們的認定是正確的,有叛徒指出了他們的位置。第二天,除了3個婦女和5個重傷員留下以外,其他的人都撤離了。甚至連醫院的黨委書記也沒有和她們一起留下來。此後,垂簪每天在警戒時都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如果敵人進來,她怎能忍心捨棄傷員而獨自逃生。一個星期過去了,還是沒有人來接應她們。到了6月20日,當只剩下煮一頓飯的大米時,她禁不住自問,是否人們已經忘卻拋棄了她們,她不得不派兩名女護士出去求救。她的日記同時中斷在這裡。不久,美軍又折回來。幾天后,她的遺體被當地的少數民族同胞發現,一粒子彈深深地穿過了她的前額。
那些在本書出版之前讀到鄧垂簪日記的人,都認為她被她的戰友們遺忘了,她是為了保衛傷員而犧牲的。但根據最近才找到的美軍單位軍事行動分析報告,才揭開了事實的真相。她犧牲的時候,醫院已獲重新補給過,傷員也都已安全撤離。她是在與一名北越的戰士和其他兩個人走在一條羊腸小道上時中彈犧牲的,而不是因為被組織放棄而與傷員們一起犧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