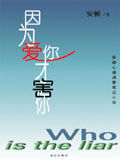作品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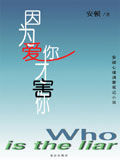 《因為愛你才害你》
《因為愛你才害你》《因為愛你才害你》圍繞著“安頓女性網”的建立講述了一個追尋說謊者的撲朔迷離的故事。本書是安頓計畫出版的系列“心理調查筆記小說”中的第一部。在這個系列作品中,安頓將以小說第一主人公的身份出現在每一個故事中,承擔調查者和講述者的功能。“心理調查筆記小說”有別於通常意義上的小說寫作,大量使用了犯罪學通常使用的“生平調查”方式,通過不同角色站在不同立場對同一事件或人物的描述來多側面地完善對一個故事的講述,給讀者帶來拼圖式的閱讀快感。安頓在成功創建了“口述實錄”文體10年後,首次提出“心理調查筆記小說”概念,引起了評論界、影視界和文學愛好者的廣泛關注。
作品簡介
主人公“安頓”創辦的“安頓女性網”遭到破壞,負責人嚴密失蹤。按照嚴密留下的蛛絲馬跡尋訪到每個與網站有關的人,大家講述的嚴密都不相同。這已經夠讓人生氣了。沒想到嚴密還給“安頓”的家人順手搞了點兒破壞。“安頓”得知嚴密將組織網友聚會,在聚會處堵截。接著,兩個人在街頭毆鬥,雙雙被公安局羈押。審訊過程中,“安頓”見到嚴密的丈夫高深,聽到關於嚴密身世的又一個版本。再然後,嚴密主動找到“安頓”,講述自己的經歷和對網站實施欺詐的動機。“安頓”因此放棄上法庭。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前半本書寫“誰騙了安頓”,就像小說的英文標題《誰是說謊者》;後半本書,寫騙子自述,也就是“我騙了安頓”。好比日常生活中兩個人的對話:“誰?”“我!”聽見這聲“我”,就算有結果。
作者簡介
安頓,原名張傑英,北京人。現為《北京青年報》編輯 、記者。自1995年8月起從事 有關“當代中國人情感狀態” 的個案調查。1997年6月6日起主持《北京青年報·青年周末》“人在旅途”版“口述實錄”欄目至今。
被西方記者稱為“中國第一位採訪情感隱秘的女記者”。
作品賞析
《因為愛你才害你》
序
“你知道嗎?我因為愛你,而恨你,因為對你又愛又恨,而忍不住想害你,讓你通過我,見識人生的慘烈。我覺得我能夠做到。我沒想到過,我會做不到。”
——摘自嚴密的來信
結識一個人,只需要一瞬間;了解一個人,也許需要一輩子。
我們習慣了說,某某是個什麼樣的人,似乎用一句話或者幾個詞語就能概括一個人了,然而實際上我們並不知道,有一種可能,這樣一句話或者幾個詞,完全與這個人沒有關係。他是誰?可能我們永遠都不知曉。我們了解的一切只不過是我們比較願意接受的、一個人的局部,或許是假象,或許是迫於某種情勢,他比較願意讓我們看到的一個小小的表面而已。
於是,有些人,可能一生都在致力於追尋某種真相,把每一個時刻追尋的結果拼合起來,形成一個不太清晰的面容,或者一個有無數線索卻找不到真正頭緒的事件。
我叫安頓,職業是記者,同時,我提供職業的心理諮詢和心理調查。很多人會在給我講述了一個漫長故事之後困惑地問我:“你說,他為什麼要這樣對我?”是啊,為什麼?每個人做一件事都會有動機,而這個動機的產生通常會和這個人的心理狀態和個人經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追蹤這個動機產生的原點,對一個人做儘可能詳細的生平調查,也不過就是為了能夠回答這個“為什麼”。
有時候,我能夠回答,有時候不能。但無論結果如何,我都能在這個追蹤的過程中獲得一些平時沒有機會聽到的真實故事——不同的人用時間描畫的人生脈絡。
時間的有情和無情都在於歷史的不可複製,無論一個社會的歷史,還是區區一個人。最後,也許連這個追尋的過程也被時間淹沒。接著,人們無奈而寬容地說:公道自在人心。
不這樣說,又能怎樣說呢?
人們會出於本能去相信對自己有利的一切以求皆大歡喜,也會出於規避風險的本能去相信來自生活某個角落的危險信號,但求自保。誰能說清楚哪一個是對的,哪一個又不是?每個人看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樣的,因此,一旦遇到一個和自己恰好不謀而合的人,我們會稱他為“知音”。
知音很少,人很孤單。
尋找知音很艱難,人很容易害怕孤單。
找到了知音,而後發現這是一個錯誤,人會很失望,或者還會憤怒,此後,漸漸的,人們失去了信任的方向。
什麼是真的?什麼不是?
這變成永遠的疑問,帶來永遠的彷徨。
我所經歷的一切,總是把我擱在追尋一個人和一件事的真相的半路上。
也許,對於一個熱衷於此的人來說,這樣的事情以後還會經常發生,就像“安頓心理調查筆記小說”總有機會繼續一樣。假如有一天,有人問:“安頓是誰?”我想我的回答會很簡單:“她可以是任何一個人,也可以誰都不是。”
作品評價
有意思的是故事的敘述過程,也就是“安頓”追尋嚴密真實身份的過程。有人說她是一個家庭幸福、父母和諧的好姑娘,有人說她是一個嚴重的抑鬱症患者;她一會兒有姐姐,一會兒是獨生女;有時候她是研究生畢業的高級白領,有時候她是掙扎在底層的小推銷員……嚴密到了故事的最後仍然在微笑:“你怎么知道我現在告訴你的一切就一定是真的?”故事到這裡結束了,恐怖的感覺卻無處不在了。一個人,一個你認識的人,你自以為了解的人,你可能會真心信任的人,她究竟是誰?她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能理直氣壯地回答嗎?這樣的問題不僅僅是在這個故事中惡狠狠地提出來,更重要的是它帶著咄咄逼人的氣息從故事裡走出來,直截了當地扔給你。你身邊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戴著面具、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你看見的、你信任的、你喜歡的、你厭惡的一個人,最終都可能只是這個人所扮演的角色之一罷了。包括你自己,你有幾張臉?哪一張是真的?這么一問自己,生活就變得殘酷起來,這本書就不能看了。
作品現實意義
這個故事讓我們想起一個已經死了好多年的人———福爾摩斯。福爾摩斯參與每一個案件的偵破過程,就像玩拼圖,把一個個線索拼接起來,最終追究到真相。他是多么幸運!而在現實中,可憐的是我們這些和“安頓”一樣的人———我們以為看見了“真相”,其實那不過是人家比較願意給你展示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