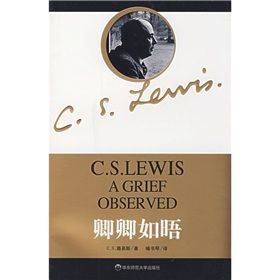編輯推薦
《卿卿如晤》問世以來,即以靈性而細膩的語言、真摯而強烈的情感吸引了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讀者,成為治療人們的心靈傷痛的一劑“恩典良藥”。有人說,這是迄今為止討論悲痛問題最好的一部作品。內容簡介
《卿卿如晤》是一篇悼亡手記。這是路易斯痛失愛妻之際,在那些“撕心裂肺、肝腸寸斷的午夜”里寫下的文字。
本書問世以來,即以靈性而細膩的語言、真摯而強烈的情感吸引了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讀者,成為治療人們的心靈傷痛的一劑“恩典良藥”。有人說,這是迄今為止討論悲痛問題最好的一部作品。
C.S.路易斯(1898—1963),是20世紀英國一位具有多方面天才的作家。他26歲即登牛津大學教席,被當代人譽為“最偉大的牛津人”。1954年他被劍橋大學聘為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英語文學教授,這個頭銜保持到他退休。
作者簡介
他在一生中,完成了三類很不相同的事業。他被稱為“三個C.S.路易斯”:一是傑出的牛津劍橋大學文學史家和批評家,代表作包括《牛津英國文學史·16世紀卷》。二是深受歡迎的科學幻想作家和兒童文學作家,代表作包括“《太空》三部曲”和“《納尼亞傳奇》七部曲”。三是通俗的基督教神學家和演說家,代表作包括《天路回歸》、《地獄來信》、《返璞歸真》、《四種愛》等等。他一生著書逾30部,有學術著作、小說、詩集、童話,他在全世界擁有龐大的支持者,時至今日,他的作品每年還在繼續吸引著成千上萬新的讀者。前言
當《卿卿如晤》冠以N.W.Clerk之名首次出版時,一位友人送我此書,我帶著極大的興趣,以旁觀者的角度讀完了它。那時,我的婚姻有好些年頭了,還有三個年少的孩子,因此,見路易斯為妻子的逝世如此悲慟,我雖然深表同情,但畢竟,這種不幸離我自己的經歷很遙遠。我無法有太深的感觸。許多年後,我先生過世,另一位友人再次送我《卿卿如晤》,我也再次捧起此書,期待著能獲得比第一次閱讀大得多的感動。部分內容深深觸動了我,但總體而言,我的居喪經歷和路易斯的大不一樣。當C.S.路易斯與喬伊·達韋曼(JoyDavidman)結婚時,喬伊尚纏綿病榻,路易斯很清楚自己娶的是一個身患癌症、奄奄一息的女人。即使後來她的病情意想不到地好轉,又捱過了數年的緩和期,但若與我這40年之久的婚姻相比,路易斯的婚姻之旅只能算淺嘗輒止。他應邀去赴婚姻的盛宴,但剛嘗了幾分樣品,筵席就無情地撤離了。
另外,對於路易斯,愛妻突如其來的失喪,導致他信心的極大衰退:“神在哪裡?……當你迫切需要她,而所有其他的救助都山窮水盡無濟於事時,你會發現什麼呢?一扇當著你的面砰然關閉的門。”但是,在走過漫長而美滿的婚姻之旅後配偶才過世,情形則大不一樣。在我先生彌留之際和離世之後的那段歲月,反而可能是我最深切地感受到神的存在和力量的時候。但這並不能抹去心中那份悲慟的感受。心愛之人的死亡是一種隔絕,但當兩人結婚後,就必須接受其中一方會先另一方而去這一事實。當C.S.路易斯與喬伊·達韋曼結為夫婦,她會先他而去,這早是意料之中的事,除非又飛來一場意外的橫禍。他伴著死亡對她的召喚邁入婚姻,並使這場婚姻成為愛、勇氣、自我犧牲的卓絕見證,與之相比,一個人經過了美滿的婚姻,享受了豐富的人生後,才壽終正寢,則是生老病死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在居喪的日子,讀《卿卿如晤》,讓我明白悲慟的每一種經歷都是獨特的,但又有某些基本的相似之處:如路易斯提到那種怪異的恐懼感、忍氣吞聲、健忘症。或許所有信徒都會像路易斯一樣,對那些將任何悲劇都說成是“願主旨成就”的人畏而遠之,好像慈愛的神是為著我們這些受造之物的好處,才會讓這些事發生。他無法忍受那些謊稱死亡對於一個信徒來說無足輕重的人。但我們大部分人都如此認為,無論我們的信心是否堅固。C.S.路易斯與我也一樣經歷了記憶失喪的恐懼。沒有一張照片能逼真地重現心愛之人的笑容。偶爾,瞥見一個在大街上行走的路人,一個活生生又蹦又跳的人,都會勾起我們一連串的真實回憶。但我們的記憶,雖然是那么地珍貴,卻像篩子篩糠一樣,不可避免地在遺漏,在流失……像路易斯一樣,我自8歲起也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在日記中一吐胸中塊壘再好不過了;這是一種消除自憐自艾、自我放縱和自我中心的方式。
當我們在日記里奮筆疾書時,是不太會顧慮到家人或朋友的。我很感激路易斯在他的日記里坦誠地展現了喪妻之慟。因為這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人類的悲慟之情是神所許可的,是正常的,也是合宜的。面對親人喪亡而產生的這種天然的情感反應,基督徒不應加以排斥。另外,路易斯提出了我們都會提的問題:當我們所愛之人死亡,他們去了哪裡?路易斯這樣寫道:“我向來都有信心為其他死者禱告,即使現在,仍有信心。然而,當我試著為H(在日記中他稱喬伊·達韋曼為H)禱告時,竟然躊躇不前。”我相當能夠體會這種感覺。所愛之人已那么深那么深地融為我們自己內在的一部分,我們無法旁觀者清,遠距離視之的。我們如何為已成為自己心靈的那一部分來禱告?我們沒有任何答案。教會對待死亡的態度仍然處於哥白尼之前的時期。描繪天堂和地獄的中世紀畫面還沒有被更現實或更溫馨的圖景來取代。
可能,對那些深信只有按他們的方式思考的基督徒才能得救上天堂的人,這種陳腐觀點已經足夠。但對我們大多數人,看到的並非是一個只關心他自己那一小群救贖子民的審判之神,而是一位有著更長闊高深的愛之神,我們對卒電有更大的渴求,我們更多需要的是信心的飛躍,相信那些因著神的愛而受造的人必不被丟棄。神的愛不會出爾反爾,創造之,又毀滅之。但喬伊·達韋曼現在在哪裡?或說,我的先生現在在哪裡?這一問題不是任何牧師、任何教會長老、任何神學家能夠用可證的事實及亟定的術語解答得了的。“不要給我談宗教的安慰。”路易斯寫道,“我會懷疑你根本不懂。”信仰所給予的真實安慰並不是精神鴉片般的愉悅感或舒適感,安慰一詞(com-fort)在拉丁語的真正含義是:大大加強力量。這是一種鼓勵生者繼續活下去的力量,一種相信無論喬伊需要什麼,或任何我們所愛之人亡故後需要什麼,都會得到那起初創造他們的大愛的悉心照料的力量。路易斯很明智地拒絕了那些虔誠告訴他喬伊現在處在平安之中且過得很喜樂的人。我們並不知道死後會發生什麼,但我揣測,我們所有人仍然還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這種學習並不容易。榮格說沒有疼痛就沒有生命的誕生,這話用在我們死後的生命上可能同樣屬實。重要的事情我們其實一無所知。因為它不是發生在信仰的領域,而是在愛的領域。
我也很感謝路易斯,有勇氣去呼喊、去懷疑、去在暴怒中與神抗爭。
這是健康的悲慟情緒中不常受鼓勵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如此成功的基督教護教大師,C.S.路易斯竟有勇氣承認,他也質疑過自己早先斬釘截鐵宣稱過的信仰,這於我們也無不裨益,這意味著,我們同樣也可以承認我們自己的懷疑、我們自己的憤怒、我們自己的創痛,知道這些也是靈命成長的一部分。
因此,路易斯也分享他自己的成長和自己的悟解:“喪偶並非婚姻之愛的中斷,而是婚姻諸多階段之一——就像蜜月一樣。我們需要的是在此階段也好好地、堅定地生活下去。”是的,在配偶死亡後,夫妻中剩下的那一方應當好好活下去,因為這本是我們的天職。
自從我先生過世後,我在書房和臥室里,掛了一些他的照片,四處都可看見它們,就如同他仍然健在,但這些照片只是肖像,不是偶像;只是記憶深處的一星點火花,而不是記憶本身。就像路易斯說的,有時它們不但不能促進回憶,反而會阻礙回憶。“一切事物的真相都具有偶像破壞的特質。”他寫道:“你塵世的愛人,即使在今生,也常常以其真實面目打碎你對她的純然想像。但你情願如此。你接納她,乃是接納她所有的任性、她所有的缺點以及她所有不盡人意的地方……正是真實的她,而非任何關於她的影像或記憶,才是我在其離世後還深深戀慕著的。”這一點比死者的魂兮歸來更為重要,雖然路易斯探討過這種可能性。
最後,在他日記最後一篇,一種對愛的篤定信靠和風麗日般撫平了心中的悲慟,這種愛,是他對喬伊的愛,也是喬伊對他的愛。這種愛,更是被神的大愛所完全充盈。
雖然沒有提供任何輕鬆或浪漫的安慰,但神對我們人類的情感的終極目的總歸還是愛。閱讀《卿卿如晤》,你將感受到的不僅是C.S.路易斯的悲慟,更是他對愛的理解,實際上,這種理解非常非常豐富。
瑪德雷娜·安格爾1988年8月於Crosswi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