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簡介
操、紹皆欲招安張繡,繡從賈計而降操,操不記舊怨。
曹令禰正為鼓吏以辱之。禰正平裸體擂鼓罵操。操撤禰往說劉表歸降。
劉表不殺禰正,使見黃祖,黃祖斬禰衡。
董承病,和太醫吉平密謀,董承家奴向操告密,操監禁董承、王子服等。曹操搜出了帶詔並義狀,欲獻帝立新君。
吉平撞階而死。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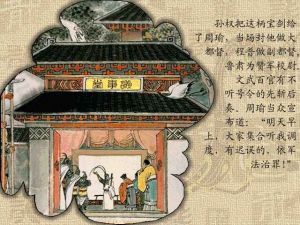 《三國演義》第二十三回
《三國演義》第二十三回卻說曹操欲斬劉岱、王忠。孔融諫曰:“二人本非劉備敵手,若斬之,恐失將士之心。”操乃免其死,黜罷爵祿。欲自起兵伐玄德。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也。可先使人招安張繡、劉表,然後再圖徐州。”操然其言,先遣劉曄往說張繡。曄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詡乃留曄於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繡命入。使者呈上書信。繡覽之,亦是招安之意。詡問來使曰:“近日興兵破曹操,勝負何如?”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今以將軍與荊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詡大笑曰:“汝可便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當面扯碎書,叱退來使。
張繡曰:“方今袁強曹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吾先與操有仇,安得相容?”詡曰:“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操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曹公王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焉。”繡從其言,請劉曄相見。曄盛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繡大喜,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繡見操,拜於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於心。”遂封繡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
操即命繡作書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升好結納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操問荀攸曰:“誰人可去?”攸曰:“孔文舉可當其任。”操然之。攸出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公可當此任否?”融曰:“吾友禰衡,字正平,其才十倍於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天子。”於是遂上表奏帝。其文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基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維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睹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嫉惡若仇;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詞,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系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制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台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腰裊,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如無可觀採,臣等受面欺之罪。”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禰衡仰天嘆曰:“天地雖闊,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衡曰:“願聞。”操曰:“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及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福將。安得無人?”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牆,徐晃可使屠豬殺狗;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於孔、顏。豈與俗子共論乎!”時止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遼曰:“此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彼自以為能,故令為鼓吏以辱之。”來日,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撾鼓。舊吏云:“撾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為《漁陽三撾》。音節殊妙,淵淵有金石聲。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著褲,顏色不變。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乃謂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污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
時孔融在坐,恐操殺衡,乃從容進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荊州為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扶挾而行;卻教手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之。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眾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何為而哭?”衡曰:“行於死柩之中,如何不哭?”眾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頭?”眾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汗刀!”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蜾蟲!”眾恨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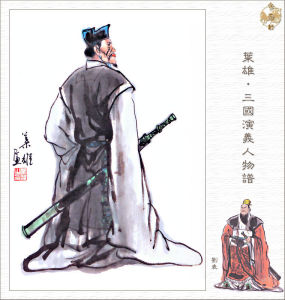 劉表
劉表衡至荊州,見劉表畢,雖頌德,實譏諷。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眾皆稱善。時袁紹亦遣使至。表問眾謀士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孟德又差禰衡在此,當從何便?”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將軍若欲有為,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將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御;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待將軍矣。”表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再作商議。”嵩曰:“君臣各有定分。嵩今事將軍,雖赴湯蹈火,一唯所命。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天子賜嵩一官,則嵩為天子之臣,不復為將軍死矣。”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主意。”
嵩辭表,到許都見操。操遂拜嵩為侍中,領零陵太守。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禰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操曰:“禰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遂遣韓嵩回荊州說劉表。
嵩回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耶!”欲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焉不負將軍!”蒯良曰:“嵩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劉表遂赦之。
人報黃祖斬了禰衡,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禰衡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為土木偶人耶!’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於鸚鵡洲邊。後人有詩嘆曰:“黃祖才非長者儔,禰衡珠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卻說曹操知禰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因不見劉表來降,便欲興兵問罪。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用兵江漢,是猶舍心腹而順手足也。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
且說董承自劉玄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建安五年,元旦朝賀,見曹操驕橫愈甚,感憤成疾。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醫乃洛陽人,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為吉平,當時名醫也。平到董承府用藥調治,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嘆,不敢動問。
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飲。飲至更余,承覺睏倦,就和衣而睡。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十二萬,從北殺來。曹操盡起許昌兵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若聚五家僮僕,可得千餘人。乘今夜府中大宴,慶賞元宵,將府圍住,突入殺之。不可失此機會!”承大喜,即喚家奴各人收拾兵器,自己披掛綽槍上馬,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二鼓,眾兵皆到。董承手提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劍剁去,隨手而倒。霎時覺來,乃南柯一夢,口中猶罵“操賊”不止。
吉平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驚懼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醫人,未嘗忘漢。某連日見國舅嗟嘆,不敢動問。恰才夢中之言,已見真情,幸勿相瞞。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承掩面而哭曰:“只恐汝非真心!”平遂咬下一指為誓。承乃取出衣帶詔,令平視之;且曰:“今之謀望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平曰:“不消諸公用心。操賊性命,只在某手中。”承問其故。平曰:“操賊常患頭風,痛入骨髓;才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救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時吉平辭歸。承心中暗喜,步入後堂,忽見家奴秦慶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慶童懷恨,夤夜將鐵鎖扭斷,跳牆而出,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操喚入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種輯、吳碩、馬騰五人在家主府中商議機密,必然是謀丞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著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見。”曹操藏匿慶童於府中,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尋。
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用藥。平自思曰:“此賊合休!”暗藏毒藥入府。操臥於床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教取藥罐,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已暗下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遲延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禮義: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為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操推藥潑地,磚皆迸裂。
操未及言,左右已將吉平執下。操曰:“吾豈有疾,特試汝耳!汝果有害我之心!”遂喚二十個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操坐於亭上,將平縛倒於地。吉平面不改容,略無懼怯。操笑曰:“量汝是個醫人,安敢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我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殺汝,豈獨我乎!”操再三磨問。平怒曰:“我自欲殺汝,安有人使我來?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打到兩個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階。操恐打死,無可對證,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
傳令次日設宴,請眾大臣飲酒。惟董承託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至。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為樂,我有一人,可為眾官醒酒。”教二十個獄卒:“與吾牽來!”須臾,只見一長枷釘著吉平,拖至階下。操曰:“眾官不知,此人連結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於地,以水噴面。吉平甦醒,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人。與汝共七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覷,如坐針氈。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
眾官席散,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只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操曰:“白絹中寫著何事?”子服等皆隱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迴避了眾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將四人拿住監禁。
次日,帶領眾人徑投董承家探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不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曰:“國舅知吉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須臾,二十獄卒推吉平至階下。吉平大罵:“曹操逆賊!”操指謂承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拿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因問平曰:“誰使汝來藥我?可速招出!”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視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為誓,誓殺國賊!”操教取刀來,就階下截去其九指,曰:“一發截了,教你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罵賊!”操令割其舌。平曰:“且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供招。可釋吾縛。”操曰:“釋之何礙?”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闕拜曰:“臣不能為國家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階而死。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詩曰:“漢朝無起色,醫國有稱平;立誓除奸黨,捐軀報聖明。極刑詞愈烈,慘死氣如生。十指淋漓處,千秋仰異名。”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即當誅之!”操曰:“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誰敢誅之?”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抵賴乎?”即喚左右拿下,命從人直入董承臥房內,搜出衣帶詔並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輩安敢如此!”遂命:“將董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休教走脫一個。”操回府以詔狀示眾謀士商議,要廢獻帝,更立新君。正是:數行丹詔成虛望,一紙盟書惹禍殃。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賞析
本章死去的兩位人物,禰衡和吉平,可以說是古代文士或者說古代知識分子中兩個群體的代表,吉平很明顯,是忠誠之士,傳統儒家教育,對於忠義兩字看的很重,尤其是各朝各代的統治者為了自身需要,更是講究這個忠字,這在後期達到了顛峰,正所謂君君臣臣,君為臣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地步。當然,這說的是在傳統宣傳上如此,但是要做到就很難了,所謂忠臣義士,並不是那么好當的,要用生命作為代價。但是也就是因為不好當,才引得眾人的仰慕。
所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知道所做的事有難度還選擇前進,這才能稱之為英雄,忠臣義士並不是凡人所能做到了,所以中國古代一直對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能人所不能”的這些忠臣義士而仰慕之。三國演義或者說歷代的傳說在刻畫了關羽,諸葛亮,劉備等人的同時也塑造了吉平等忠臣義士。在三國之中,雖然作者有所傾向,但是對於忠臣則無關立場,都是加以讚頌的,如許貢三門客,張任,審配,沮授他們所忠於的對象並不是作者所認為的明主,但是對於他們本人,即便站在主角的對立面,演義都給予高度評價,古代知識分子雖然不一定做的到忠義,但是大都希望能做到。
而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還有一種代表,或者說一種傾向,就是做狂士,便是禰衡這樣的人,則是和正統的儒家教育截然相反的。儒家小則自身講究修身,大則講究治國平天下,說的是入世,以禮為重,從傳統的儒家教義上,狂士這樣的人自然不是儒家所贊同的,但是,偏偏就是眾多的士大夫推崇狂士。春秋中文社區http://bbs.cqzg.cn
假若硬要說狂士的起源,則一般說的是以李莊為代表的道家學派,尤其是後者,莊子的逍遙是很得士大夫的欣賞,由此進化而來黃老學說在漢初也頗有市場,在東漢末年,更是形成了太平道等道教的起源,可知那時老莊思想的盛行了。
而且,儒家早期也和狂士頗有淵源,孔丘所遇楚狂人,在被人批評的同時,也被日後的許多正宗的儒家學徒所欣賞讚頌。
中國的士大夫往往有兩條路,一條是入世,正所謂做忠臣義士,但是這並不好做,假若是太平盛世喊喊口號那還罷了,可要到了亂世或者戰場上,判斷你的忠義之心的機會就多了,若是假忠義,那就要被訂在歷史的恥辱柱。人人都想做英雄,但是到了關鍵時刻,才知道是否真是英雄。不過幸好還有出世做狂士隱士這條路,當年老莊那或許確實是崇尚個人自由,但是到了後世,真正的老莊傳人早就去深山學楚狂做野人了,那所謂的狂士沽名釣譽的多,嘴裡喊著自由,心裡卻想著富貴榮華。不用做事,只需縱情,便有莫大的名聲,比起忠臣義士付出的少的多,名聲卻大的多,何樂而不為呢?
當然,這些狂士隱士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一定要高門大族,或者得到這些世族所認可的人才能做到,你小老百姓想做狂士,門都沒有,而且狂士隱士也是超越法俗之外的,你看禰衡那般做,若是其他人依法也是死罪了,但是就是因為他是名士,則只好暗害之,即便如此,還要落得罵名。為何呢?這中國的士大夫心中哪個不想做超越法俗的狂士,不要什麼心血,便可以為所欲為,無論外面是否改朝換代,無論百姓水深苦熱,只須呤幾句歪詩,發幾聲無用的憂嘆,便能獲得莫大名聲呢!其實從本質上,中國的士大夫眼裡並沒有皇帝,上天,只有自己,只要自己能逍遙自在,哪管王朝更替,百姓死活,路易十四說的我死之後,哪管他洪水滔天,用在這些沽名釣譽的狂士上最為適合。
所以不管各代皇朝再講忠義二者,也抵不過文士骨子裡的那點狂意,你看狂士最盛行的魏晉,士族最盛行的時期,誰還講那君君臣臣。各朝各代費盡心計,培養出那些忠臣義士,為攬狂瀾而拋頭顱,灑熱血,而那些狂士只需動動嘴皮子做做秀,便太平時做狂士,戰亂時做隱士,等得換了天下,再出來繼續享受那名士的名聲便可了,正是送死你去,背黑鍋你去,享樂我來,受苦你去,名聲我來。
所以各朝要亡時,便是出狂士隱士最多的時候,而或許也是忠臣義士最多的時候,只是前者興許能安然痛快的活著罵著,後者則要流盡了血。
回評
毛宗崗批三國
禰衡、孔融、楊修三人才同,而其品則有不同。楊修事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猶與操周鏇者也;禰衡則不事操,而並不屑與操周鏇者也。三人皆為操所殺。而三人之中,惟衡最剛;故三人之死,亦惟衡獨蚤。操自負奸雄,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而禰衡鄙夷傲睨,視若無物,非膽勇過人,安能如此?生前既罵曹操,死後又罵王敦,至今鸚鵡洲英靈不泯,豈得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或謂罵操如陳琳而不殺之,何以獨忌禰正平乎?操之出使正平於諸侯者,以正平恃才而狂,欲使人磨折他一番,挫其銳氣,然後用之耳;不虞黃祖之遽殺之也。先儒有<代曹操責黃祖書>,備言此意。予曰:不然。為此說者,未知禰、陳兩人之優劣也。禰衡罵操以口,陳琳罵操以筆。雖同一罵,而衡之罵操,自罵者也;琳之罵操,代人罵者也。夫自罵之與代人罵,則有間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使操用之以射人,則其代操罵敵,亦猶是也。陳琳罵操,而終於事操;禰衡罵操,則必不事操。代人罵者可降,自罵者斷不降,此操之所以不殺琳而必殺衡歟!
為劉表計者,既知曹操使禰衡之意,便不當使衡見黃祖,當仍令衡還許都,方是高曹操一頭地。今操借刀於表,表復借刀於祖,是與操一般見識,終在曹操術中耳。
董承元宵一夢,何其快心;奈此夢不應,可為惋惜。雖然,天地夢藪也,古今夢緣也,人生夢魂也。漢之變而為三國,三國之變而為晉,猶之蕉耳,鹿耳,蝴蝶耳,邯鄲與南柯耳。事之真者,何必非夢?則事之夢者,何必非真?夢如董承,直謂之真焉可矣。嘗讀<曇花記>,見冥王坐勘曹操,拷之問之,打之罵之。或曰:此後人慾泄其憤,無聊之極思耳。予曰:不然,理應如是,不可謂之戲也。古來缺陷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補之者:一曰鄧伯道父子團圓;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興楚國;一曰燕太子克復秦仇;一曰王明妃再入漢關;一曰侯夫人生逢煬帝;一曰岳武穆寸斬秦檜;一曰南霽雲立滅賀蘭。斯皆以天數俯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然則董承劍起,曹操頭落,忠魂所結,竟當作如是觀。
上醫醫國,其吉平之謂乎?若吉平者,不愧為太醫矣。以其藥醫曹操之頭風,是毒藥也;以其孳醫獻帝之心病,是良樂也。人謂其誤以詐病為真病,不得謂之知病;我謂其能以毒藥為良藥,斯真謂之知醫。惜乎其藥不行耳。欲生人則生之,欲殺人則殺之,能生人是良醫,能殺人亦是良醫。獨怪今之醫家,心則華陀救周泰之心,藥則吉平毒曹操之藥,殺人而猶執生人之方,生人而適作殺人之孽,吾不知其醫術居何等也。
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閱至此,掀髯稱快,當滿引一大白。禰衡鼓擊三撾,令人泣下;吉平血流九指,令人呲裂。閱至此,慷慨悲懷,又當滿引一大白。
此回起處,正是曹操欲攻劉備,卻因招安表、繡,放下劉備,忽然接入董承。及董承事露,而首人不知有劉備;至搜出義狀,而曹操始知與承同謀者之有劉備,於是下文攻劉備,更不容緩矣。然則此回雖無劉備之事,而實劉備傳中一大關目也。
李贄總評
人誰不死,如禰正平之死可謂不死矣。何也?口所欲言無不言之,一無所趨避,乃是活人也。若夫口欲言而不言,心不欲言而言之,皆怕死耳。斯人也,亦何嘗不死也乎哉!其生時先已死矣。誰能如我正平,死時尚不死也。
吉平真聖人,是大聖人,是佛,是活佛。誰謂其僅醫人乎?此真醫國手也。恨操賊惡貫當盈,故使慶童敗乃公事耳。此天實為之,於人何尤哉?
鍾敬伯總評
想稱生原具英雄氣、骯髒骨,故心一慧口快,把老瞞半生豪強,一旦盡掃。然則漁陽三撾,亦可當鳴鼓而攻也。
操惡貫盈,其病已入膏肓。若吉平醫國手用一貼毒藥斷送了他,則沉疴立起矣。誰使慶童作鬼,老奸作病,流毒更甚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