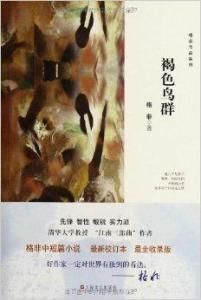內容介紹
80年代文學新潮叢書之一,選編了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王蒙的《來勁》、格非的《褐色鳥群》等小說
作者簡介
格非即 劉勇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
劉勇,男,筆名“格非”,生於1964年,江蘇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200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並於同年調入清華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幟》、《塞壬的歌聲》、《小說敘事面面觀》、《小說講稿》等。他的中篇小說《褐色鳥群》曾被視為當代中國最玄奧的一篇小說,是人們談論“先鋒文學”時必提的作品。
讀者評論
《褐色鳥群》注定是一篇你讀過就難以忘卻的小說,當然不止因為它不好懂。這部小說曾號稱當代中國最費解的一篇小說,但卻很好看。
從最外在的方面說,《褐色鳥群》帶給我的首先是語言上的快感。“眼下,季節這條大船似乎已經擱淺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樣更替。我蟄居在一個被人稱作‘水邊’的地域,寫一部類似聖約翰預言的書。”格非的語言從容而詩意,浸泡著豐富的回憶,勾起人的懷舊情緒。我的周圍仿佛彌散升騰起茶色的煙霧,氤氳著歌謠湖畔的水汽。而當這樣的語言與這篇小說里撲朔迷離的敘事相遇時,語言就顯得格外神秘,扣人心弦。“我想把它獻給我從前的戀人。她在三十歲生日的燭光晚會上過於激動,患腦血栓,不幸逝世。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這裡的語言是詭異的,當故事還沒有展開,當“我”還沒有與“棋”相遇之時,語言已經為後面的敘事營造了絕好的氛圍。對於一個看似沒有邏輯的混亂的故事而言,也許,只有這樣詩意而充滿黑色幽默的語言,才能拽著讀者,陪文中的“我”走到故事的末尾。
而當我們進入到故事本身時,我們發現,世界在被格非一點點顛復著。小說發表於1988年,而“我”講述的1992年到“歌謠湖畔”再遇穿栗樹色靴子的女人的“回憶”,屬於未來的時間。小說開頭所寫的“我”與“棋”的第一次相遇則是比1992年還要靠後的未來。小說的結尾,寫到:“不知過去了幾個寒暑春秋”,這樣時間漫延到了更加不可知的地方。我們的時間被顛復了,回憶與現實,現在與未來,交錯在“我”與“棋”混亂的敘述里,混成一潭。而當故事展開之後,我們發現,每一個故事都是前後兩層的,不同的敘述視角在重複中交織著,以《羅生門》式的敘述方式,共同編織成一個故事。令人費解的是,所有我們前面已知的事實,到後面都會被顛復,最終構成一串類似埃舍爾怪圈的系列圓圈。這一點評家們都有論及,郭寶亮將之比喻為俄羅斯套娃式結構。圓圈概括起來有三重:第一個圓圈,許多年前“我”蟄居在一個叫“水邊”的地方,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叫“棋”的少女來到我的公寓,她說與“我”認識多年,我與她講了一段我與一個穿栗樹色靴子的女人的往事;小說的最後,“我”看到棋又來到“我”的公寓,但是她說她從來沒有見過“我”。第二個圓圈,許多年前“我”從城裡追蹤穿栗樹色靴子的女人來到郊外;許多年之後我又遇見那個女人,她說她從十歲起就沒有進過城。第三個圓圈,“我”在追蹤穿栗樹色靴子的女人的路上遇到的事與女人和“我”講述的她丈夫遇到的事之間構成相似與矛盾。這三個圓圈之間存在相互否定(矛盾)與肯定(相似)的多重關係。存在還是不存在?在這裡,一切都難以確定。而故事的細微之處,前後矛盾就更多。比如“我”自稱自己蟄居在“水邊”,而棋則說“我”是住在“鋸木廠旁邊的臭水溝”;“我”跟蹤穿栗樹色靴子的女人到斷橋,看到她從橋上過去,而橋邊“提馬燈的老頭”則否認女人從這橋上經過;更詭異的是,後來這個女人稱當時在橋邊的是她的丈夫;穿栗樹色靴子的女人的丈夫淹死在糞池裡,而“我”卻看見棺材裡男人的屍體似乎動了一下,而且真切地看見,那個屍體抬起右手解開了上衣領口的一個扣子……倘若我們可以《羅生門》中不同人的講述歸因於在一個罪案中對自身利益的保護,那么《褐色鳥群》中不同的敘述則顯得荒誕得突兀——我們找不到原因,找不到動機,到小說的最後,都分不清黑白真假。
這樣的敘事是完全符合先鋒小說的特質的——在敘事的迷宮中自由穿行,去找尋人物內心的奧秘和意識的流動。而格非的這篇小說尤甚。季紅真先生認為《褐色鳥群》“由於過於抽象而喪失了敘事的本性,成為一種形式的哲學。”格非的確是在放縱著自己的文字,任它們在存在與虛無的混亂中衝擊讀者的意識,來完成自己的哲學思考,但是格非並沒有忘記敘事的本性,只是《褐色鳥群》中的敘事,遵循了格非設定的哲學邏輯。格非明顯受到了薩特等一撥人的影響。按照存在主義,所謂時間、空間和因果性、規定性、個體性、結構性,都是人在與世界接觸時主動存在的產物,是人的存在狀態的反映,屬於“自為存在”的性質,但這些都不屬於與人無關的“自在存在”。《褐色鳥群》的敘事,就是在“自為存在”向“自在存在”的轉換中,完成對存在與虛無的終極叩問。陳曉明論述得相當精闢:“格非把關於形而上的時間、實在、幻想、現實、永恆、重現等的哲學本體論的思考,與重複性的敘述結構結合在一起。‘存在還是不存在?’這個本源性的問題隨著敘事的進展無邊無際地漫延開來,所有的存在都立即為另一種存在所代替,在回憶與歷史之間,在幻想與現實之間,沒有一個絕對權威的存在,存在僅僅意味著不存在。”我認為,格非想要描繪的,是他眼中的存在與虛無混雜著的荒誕世間,而他將這世界的荒誕,濃縮在了一個關於“性、夢幻與感覺”這些人類最神秘領域的故事裡。
其實在我們每個人的潛意識裡,我們都在質疑著這個世界的真實性,都在痛恨著這個世界的荒謬,只是我們沒有發覺。而當我們在格非的故事中完全迷失了支配著的所謂“邏輯”月“定式”,迷失了時間與空間時,我們獲得的也許是對這世界最真實的感悟,這就是閱讀快感的由來吧,雖變態,但真實。
編輯推薦
這本《褐色鳥群》收錄了格非1986~1993年上半年發表在各雜誌上的文章,計有《追憶烏攸先生》、《迷舟》、《陷阱》、《褐色鳥群》等14篇,25萬字,代表了格非創作從起步到發展的歷程。從1990年代以來,格非中短篇小說選集以各種形式、在不同出版社先後出版過,計有七八種,但現在市場上已難尋覓。
目錄
變與不變(代序言)
追憶烏攸先生
迷舟
陷阱
褐色鳥群
沒有人看見草生長
大年
青昔
風琴
蚌殼
夜郎之行
背景
唿哨
傻瓜的詩篇
錦瑟
格非中短篇小說年表
序言
變與不變
《江南三部曲》問世之後,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和我商量,計畫將我以前的作品也重新編輯出版,包括三部長篇小說《敵人》、《邊緣》、《欲望的旗幟》和全部中短篇小說(分為三輯:取名《褐色鳥群》、《雨季的感覺》、《蒙娜麗莎的微笑》)。除了《戒指花》、《不過是垃圾》、《蒙娜麗莎的微笑》等作品寫於2000年之後,這些作品中的絕大部分都是上個世紀的舊作。編訂、翻閱這些舊作,雖說敝帚自珍,但多少有點陌生感了,也時時驚異於自己寫作在幾十年間的變化。
以前常有一種看法,以為作家的變與不變,主要是源於時代本身的急劇變化。列夫·托爾斯泰,詹姆斯·喬伊斯,威廉·福克納,納博科夫等等,都是如此。即以喬伊斯而論,若拿《都柏林人》跟《尤利西斯》比較一下,似乎有點讓人不敢相信這兩部作品出於同一個人之手。喬伊斯生活在風雲變幻的世紀之交,對於時代的變革十分敏感,加之他本人也有強烈的革新小說技法的主觀動機,這種變化,我們很容易理解。順便說一句,就算沒有後期的《尤利西斯》等現代主義作品,喬伊斯也是世界一流作家。他的《都柏林人》在文學史上也形成了一個小傳統。美國當代年輕作家耶茨所繼承的,正是這個傳統。至於納博科夫,他一生輾轉於俄國的聖彼得堡和德國、法國、美國之間,生活動盪不寧,需時時適應新的地理和文化環境,小說風格不斷出現變化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有不怎么愛變的作家。卡夫卡、霍桑、海明威等作家相對穩定,寫作風格沒有出現過劇烈的變化和調整。海明威是一個特例,儘管他的人生經歷也很複雜,但一生只寫一個主題,居然也寫成了世界級的大師。雷蒙德·卡佛是海明威的追隨者,和我們生活於同一個時代,也不怎么愛變。
說到中國現代作家,魯迅就可以算得上文風不斷變化的代表。從《懷舊》這樣的文言小說,到《狂人日記》,再到《吶喊·彷徨》和《野草》,一直在變。若不是去世較早,他往後的小說會有什麼變化,今天已不好妄加猜測了。汪曾祺的例子也比較特別。我們所熟悉的汪曾祺,是寫出過《受戒》、《大淖記事》、《故里三陳》以及大量優美小品的那位作家。可汪先生寫作《受戒》的那一年,他已經是60歲了。每念及此,總要無來由地為他老人家捏把汗:假如他活得與魯迅先生一樣長,也許《沙家浜》就要算他的代表作了。在中國現代作家中,也有不那么愛變的人。張愛玲可以算一個,在不變方面,完全可以和海明威相媲美。看她的《小團圓》,不用說語言和基本修辭方法,就連題材、情感、觀念也都沒有什麼變化。
有時候會對古典作家心生羨慕。變與不變,似乎是職業寫作出現以來才會有的苦惱。對於那些一生只寫一部作品的小說家(比如曹雪芹)而言,想變都沒有機會,倒也踏實。安心於茅廬高臥,省了多少六出祁山的左衝右突!但轉念一想,也不盡然。古代作家寫作的大宗不是小說,而是文章和詩詞,其實變化也是始終存在吧,否則就不會有“庾信文章老更成”這樣著名的感慨了。
格 非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