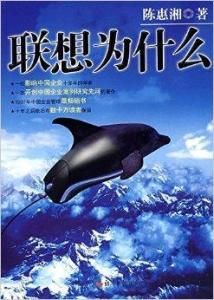內容簡介
陳惠湘的第一本企業研究著作,也是他案例研究的開端。本書是一本中國人寫中國企業的哈佛式案例分析力作。是1997年中國企業管理最暢銷書。本書主要內容為睜大你的眼睛,選擇未來需要勇氣,確定“你別選擇”的目標,拿鏡子照照自己,謀事在人,穿新鞋走新路,生命在於運動,承擔責任光榮。
目錄
再版序
序
第一章 睜大你的眼睛
第二章 謀事在人
第三章 穿新鞋走新路
第四章 生命在於運動
第五章 承擔責任光榮
……
編輯推薦
 聯想為什麼
聯想為什麼一位影響中國企業十多年的學者;一本開創中國企業案例研究先河的著作;1997年中國企業管理最暢銷書;十年之後依舊有數十萬讀者的保留。
《聯想為什麼》是陳惠湘的第一本企業研究著作,也是他案例研究的開端;一本中國人寫中國企業的哈佛式案例分析力作。
什麼是企業戰略?企業戰略就是你要乾什麼行當,要乾到多大,錢和人往哪兒投。
中國缺人才嗎?中國缺伯樂嗎?中國缺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機制嗎?
人才的標準首先是信譽。信譽不僅僅是品德,還有能力。
人才的訓練和培養永遠是“賽馬中識別好馬”。
小企業銷售看得見的貨物,大企業把看得見的貨物和看不見的貨物一同銷售出去,正如同麥當勞既銷售漢堡包,也銷售微笑。
脫離投入只談產出是不合理的。脫離產出只談投入人也是不合理的。離開責任就談不上激勵,離開激勵也談不上責任。
文摘
一、辦公司就是辦人
從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有三個時間段我們感到了人才的珍貴,這三個階段我們都產生過如饑似渴的感覺。
第一個時期是20世紀50年代,我們向蘇聯送去了大批留學生,今天五六十歲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有相當一批人是從蘇聯學成歸國的。我們的武器製造專家包括核子彈的設計者,我們的電子工業企業家,多數是在蘇聯學習的。1949年以前中國打了幾十年仗,無暇顧及科學和經濟。1949年以後,由於物資匱乏、科技落後,於是我們提出個“大幹快上建設社會主義”,農業成立了合作社希望多產糧食,工業提出大煉鋼鐵,國防工業圍繞著核子彈的研究展開。中國人當時的任務,一是保衛自己,二是養活自己,具有遠見卓識的政府為了實現這兩個目的,把一批批熱血青年送出去,然後又一批批接回來安排到重要的部門和企業。儘管20世紀60年代我們走過一段令生產力發展停滯的彎路,但是50年代的這批人才對我們當時以至後來的發展功不可沒。沒有這批人,我們一定連今天這樣的科學與經濟的基礎都不具備。
第二個階段是1979年至1985年間,中國誕生了許多的鄉鎮企業,面朝黃土屁股朝天種了一輩子莊稼的農民一旦成為企業老闆之後,他們對知識的敬重遠比有知識的城裡人高得多。他們知道自己沒文化,沒文化就搞不出好商品。於是他們寧願全村人集資蓋上別墅一樣的小樓,買上轎車,開出城裡人想都不敢想的薪水數字,然後學著劉備三清諸葛亮的樣子,畢恭畢敬站在一個又一個城裡知識分子的家門口,為貧窮的鄉村請去一個又一個能人。那時候城裡人才多,多到很多企業、研究所無所謂張三李四被挖走。直到鄉鎮企業的產品大舉進入城市,已經衝擊到那些被挖走人才的企業時,城裡人似乎才醒悟過來。應該說改革開放之後,對知識、對人才的尊重以至對人性的尊重,是由我們目不識丁的農民弟兄帶的頭。
第三個階段是從1990年開始,大量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合資企業要實現本土化策略,要為“以夷制夷”而大量招聘中國人。在美國,一個一般的工人年薪也要在10000多美元以上,在中國1000美元月薪就可以讓外企的門前排起一隊全部博士學位的長隊。中國的企業開始恐慌,開始尋求各種方法留住人才但收效甚微。在北京已經出現了數家獵頭公司,專以介紹人才為業務內容。獵頭公司受那些進人中國的外國企業和沒進人中國的外國企業委託,專門負責從中國的企業中物色人才,一旦找到目標便會開出無法抗拒的條件,把一個箇中17qA~l送到外國企業中去。我的一位同事的妹夫,原先在一家電腦公司從事軟體開發,他是從農村考大學進到城裡的,從沒想過要出國。但是有一天,有人告訴他,他可以全家去新加坡,定居手續、工作、生活一切自有安排,於是他就去了。中國少了一個人才,新加坡又多了一個華人。今天在北京的外國電腦企業中,確有一些企業在執行著一種規定,凡是從聯想集團到這些企業求職的人,可以不按程式考試,工資職務一律從優,優到收入可以超出這個人在聯想的一倍甚至更多。曾經有一個人說了一段充滿智慧的話,他說人人都認為人才值錢,其實是錢值錢。有錢的外企不缺人才,缺人才的中國企業其實缺錢。從作為商品的勞動力這個角度看,我認為他們的話也對。
一部美國歷史生動地表明人才之珍貴。二戰勝利,美國做的事情是把德國的核子彈研究專家、把德國的猶太人送往美國。今天支撐著美國科技的中堅力量是那些並不出生在美國的美國人。1995年間,聯想集團一個技術考察團去美國參加一年一度的拉斯維加斯世界計算機博覽會。聯想集團考察團在博覽會之餘去參觀了一家規模不大的美國軟體公司。這家公司里有幾位4年前還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工作的年輕的中國人,他們與聯想集團考察團中一些年輕專家是過去的同事或者朋友。談話中了解到,去了美國的這幾位研究人員此刻已擁有所在公司的上市股票,按市值計算也基本接近百萬富翁。
的確,從馬斯洛人的需求層次論來判斷,今天我們能夠滿足人才需求的能力是有限的,與我們的競爭對手比甚至是可憐的。這就是我們目前的處境。我們必須擺脫這種困境。在與中國企業相比擁有絕對數量和絕對質量人才的聯想集團,總裁柳傳志已經在大聲疾呼未來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但我們社會上這種呼聲依然不夠強烈。我們真的不是有經驗的海員,我們不知道老鼠上岸意味著什麼。假如有一天,絕大部分中國本土一流的人才都去了外企,由這些人組成的企業與我們自己的企業展開競爭,結果會是怎樣?這種假設並非危言聳聽。北京已經有上千家外資企業,按每家企業平均50名員工計算,至少已經有5萬名中國人才在打外國工。還有上海呢,還有廣東呢。我記得曾經有一個統計,據說每培養一名大學生,國家要有上萬元的經費補貼。在中國今天有沒有10萬名以上的研究生打外國工?有沒有50萬名以上的大學生打外國工?如果有,每個人僅算國家貼入教育經費1萬元,那就等於我們花了近百億元人民幣培養出來的人才,如今正在外國企業直接與我們中國企業競爭。這就是20世紀90年代在我們這個國家隨處可聞的聲音,我們聽懂了嗎?
有人說,因為我們貧窮所以留不住人才。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家貧出孝子”,關鍵是我們缺乏這樣的意識。我們貧窮的農民弟兄曾經做出過榜樣,曾經全村人勒緊褲腰帶對人才頂禮膜拜,“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中國的人才並非都見錢眼開,更多的時候套用一句歌詞,屬於“我要的不多,無非是一點點溫柔感受”那種人。“士為知己者死”,我們從現在起就該警醒,就該為人才創造哪怕是“一點點溫柔感受”。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我們已經有一批企業家看到這一點,他們在用各種方法發現人才。在北京頗有市場的中南抽油煙機的老闆許為平先生,曾在價格昂貴的北京飯店常年租用了兩個房間,開設了一個人才交流中心。他的人才交流中心其實沒有註冊,他用了一些方法使得那些需要人才的單位樂於在他那裡登記,不必交任何費用。他用了另外一些方法使那些需要謀職的各種人也在他那裡登記,也不必交任何費用。所有登記求職的名單每周都會送到抽油煙機企業老闆那裡,由他優先選擇。用這樣的方法,一年下來他自己物色到幾十名人才,給別的企業推薦了數十名人才。
一家廣東的企業在北京登報,以年薪50萬招聘廠長,承受力不強的北京人當時如同經歷一次炸彈爆炸。幾年過去,在報紙上登廣告以年薪幾十萬招聘人才的事已經不那么令人驚奇了。在北京的獵頭公司里,隨便調出一份求職者名單,你便會發現80%以上的求職者自己開出的月薪要求都在萬元以上。但是另外一面,從傳統國營企業縮減定員被辭退的員工,即便是四五百元的月薪要求也很難找到工作。
競爭終於讓中國人承認勞動力是商品。
後記
一本書、一個人、一個企業和一個民族
一、貴在認真
很久以前就想寫一本關於聯想的書。
1989年8月2日,是我正式到聯想集團上班的第一天。在此之前,我在電子工業部下屬的另一家企業工作了將近10年。工作之餘涉及到文學創作並且加入了作家協會。但是,想寫一本關於聯想的書與寫作本身沒有絲毫的聯繫,最初完完全全是出於一種激動。我在聯想的第一位經理名叫郭為,是一位比我年輕3歲的MBA碩士生,我在本書之中有多處提到他,此刻郭為已榮任聯想集團的副總裁。我到聯想集團工作4個月後接替郭為出任公共關係部的經理,並且在這期間創作了“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的廣告語,協助郭為主持了1989年至1990年上半年公司的多項重大活動。其中包括公司由原來的中科院計算所公司改名為聯想集團的宣傳工程,包括聯想微機上市以及聯想集團第一篇關於管理文化《大船結構管理思想及管理模式科學性》的文章撰寫,還有管理幹部培訓等等。1990年5月,我再次接替郭為主持集團辦公室的領導工作,策劃實施了1990年至1991年兩年問聯想集團所有的企業形象推廣工作。而郭為則以助理總裁的職務主持了全國各地十幾家分公司的管理工作。由於工作的關係常常能夠有機會與柳傳志總裁、李勤常務副總裁在一起討論工作,接受指示,對聯想的激動就時時鼓舞著我。在此期間,寫一本關於聯想的書,這種願望在心裡就時時涌動著。這裡面的原因大概是我在傳統的國營企業有過較長時問的工作經歷,過去工作過的企業與聯想集團相比,後者確實更顯得生機勃勃。1978年至1980年間,我在北京市物資局化輕公司的一個易燃易爆劇毒品倉庫做庫工。倉庫位於懷柔水庫西南的一個小山坳里,有二十幾位與我年齡相仿的年輕人。白天大多時間閒得無事,年輕人在一起便絞盡腦汁想各種各樣的花招兒做各種各樣的惡作劇,以打發多餘的精力而顯得充實。譬如到相隔三四公里的果園偷摘蘋果,或者到同樣距離的公社衛生院找稍稍漂亮一些的年輕女護士山南海北聊天……我在所有這些活動中屬於既不踴躍也不消極的一類人。平平淡淡的日子過了兩年之後,一個極偶然的機會促使我調回城裡,到電子部所屬的那家工廠工作。有30多年歷史的這家工廠是我國生產石英諧振器的第一大廠,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第一枚飛彈都有這個廠的功勞,工廠會議室四周牆壁懸掛的錦旗向所有人證明了它的榮耀。我在廠里的設計所做過技工,不久便去做專職的廠工會宣傳幹事,然後做廠里宣傳教育處的宣傳幹事。工作任務是每年在報紙上發表20篇關於工廠業績的新聞。這個任務我基本上可以用10天的時間完成,因為1篇稿件可以在20家報紙發表。這使得我每年有大約300天的時間不知道乾什麼。於是就一邊讀書、一邊創作和一邊談戀愛。讀書是在現今的首都師範大學,當時叫北京師範學院。讀夜大中文系,一讀5年。剛開始廠里不批准,學費不予報銷,占用的工作時間不準假,寧願我在廠里無所事事也不能去學中文。於是我就寫信告狀,一直告到當時的中央書記處宋任窮處,終於把學費和上學時間一攬子解決了,在廠里工人的眼光里我看到對英雄一般的敬慕。文學創作是從十幾歲就有的愛好,寫的書比讀的書多,能夠發表的作品只有寫出來的1%。仗著分母大、分子小但發表作品的絕對數量依然不太少,於是就由我的老師、著名作家韓少華做介紹人,多少有些僥倖混入的感覺加人了北京作家協會。一直到1988年,忽然發覺幾乎所有的生活都是馬馬虎虎的,工作沒認真過,創作沒認真過,讀書也沒認真過。惟有談戀愛、做父親比較認真,戀愛一年就結婚,結婚一年就做父親。看起來匆匆忙忙,但品味一下還算認真。知道自己缺乏認真的時候已經28歲。29歲到聯想工作,發現還有如此認真的企業,還有如此認真的人們,拿工作當自已的生命看。這是聯想最初給我的印象。當然我本人也義不容辭地認真起來,這時候又發現認真以後自己原本有那么多的創造力和熱情。
在聯想,我有過兩次挨柳傳志批評。一次是1990年的北京計算機展覽交易會,我是聯想展覽團的負責人,我們在這次展覽會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簽訂的契約逾千萬元,列大會所有參展單位成交額第一名。我很興奮,專門指定有人天天統計契約金額,每天閉展前電話通知公司。有一天,報來的訊息說當日契約金額達到500萬元。我不敢相信,叫人繼續核實,回答還是500 萬元。於是我就把這個好訊息匯報給柳傳志。第二天柳總親自到展覽館核實,結果證明契約金額離500萬元相差甚遠。為此,他怒氣沖沖回到公司,幾乎是把我痛罵一頓,罵我“謊報軍情”。這是我職業生活里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受到的痛責。儘管柳傳志當時的表現怒氣沖沖,但我非常非常感激他。因為從那一刻起,我對於“認真”的理解又有了新的進步。第二次是 1991年7月,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北京市新技術開發試驗區和《經濟日報》聯合舉辦“聯想走向世界”報告會。按照報告會的設計方案,我們希望請一位長期關心我們的中央領導屆時能夠出席。我的部下與這位領導的秘書進行了確認,領導答應可以出席。但我忽略了應該叮囑部下了解這位領導在這個時間段里的日程安排,以至於當我們把報告會時間定好以及所有的會議邀請發出之後,才知道這位領導在報告會舉辦當天恰好在外地考察工作。這件事柳傳志並沒直接批評我,因為我母親身患癌症處於彌留之際。但是這次無言的批評依然令我難以忘記。認真的聯想,認真的柳傳志,認真的所有其他聯想人,進入到這樣一個到處寫滿認真的環境之後,我也認真r。這對我是極為珍貴的。通過這種認真,我能夠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價值。
儘管寫書的願望始終如一,但是我沒有寫。沒有勇氣。我知道我對企業的本質了解膚淺,對我們的國家了解膚淺,對世界經濟的了解膚淺。我必須認真地生活過,使這些膚淺有了一定的改變,然後才可能真切地寫出一些於人有益的感受。這樣的滋味實在很痛苦。感情時時衝動著,使你按捺不住地要奮筆疾書。理智卻不斷提醒你不能倉促和草率。能夠忍耐這種痛苦對人實實在在是一個磨鍊。
1991年,我決定離開聯想。離開聯想的心情很複雜,但原因很簡單。在聯想工作了兩年之後,我希望自己能夠有從事經營的機會,能夠有創業的體驗。在我看來這十分重要。思想會有如此之大變化,連我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因為僅僅在1989年的時候,我內心強烈的願望還是要當一名作家,作為企業人並不是我的最終歸宿。時隔兩年,我對企業已經產生了一種難以遏制的激動。坦率地說,沒有聯想的影響,我不會有這樣的變化。
……
三、不僅僅是關於聯想
我的搭檔張華濱先生時時會有一些怪論。有一次他說企業是怎么回事呢?就好比時鐘,員工址秒針,所以不斷地走;中層主管是分針,員工走一圈,他就走一小格;企業的最高管理者是時針,人家走了若干圈若干格,他就走一格。
這比方我一直記著。
還有一次他又說,這人才培養的事兒也是木桶原理。你不能讓他在單項指標上拚命長,長得越高越是個細高挑兒,風一吹就折了。要有些綜合營養。
這比方我也記著。我覺得這些例子都生動也都有用。
同樣,我幾乎是以一種等待審判的心情在等待著這本書的結果。儘管我知道當書稿變成鉛字到達讀者手中的時候,遺憾已經不可避免。但我希望這遺憾儘可能少一些。我希望這本書有用。為了這一點,我著力在書中更多地表現民族性、思考和行為研究三個特點。
關於民族性的問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貿易保護。但這並不是我的出發點,儘管我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們的國家應該一面是改革開放而同時也要進行必要的貿易保護。就像美國、日本、韓國一樣,雖然它們已經很發達、很強大,但它們的貿易保護依然隨處可見。開放的目的是使我們富強而不是使別人富強,世界各國經濟的這種民族性(也可認為是利己性)是自然而然的。我們當然也犯不著羞羞答答的。雖然這是我對貿易保護的觀點,但我在本書中依然是從中國企業如何參與國際競爭,如何提高自身素質出發,所謂民族性的體現也基本在此。我在書里涉及到外國著名企業對中國市場強力滲透的部分,包括外國文化強力滲透的部分,更多的目的並非指責別人,而是希望我們自己能夠做得更好。我想指責別人是沒有意義的,人家強大人家能夠滲透進來,這隻說明我們虛弱。我們如果拒絕與強手競爭,那我們會永遠虛弱。唯一的出路是我們研究別人,研究自己,使自己也強大起來,別無選擇。因此,我在本書中論及的所有問題中都無一例外地把中國企業放在與外國企業競爭這樣一種環境中來進行判斷,而並非就事論事地說某一件事應該怎么樣。在我看來,判斷一個企業如何,必須結合生存發展對它的要求是什麼,否則結論就會失之偏頗。而對企業的要求應該全部來自於競爭。所以,我在本書的五個章節里,就企業戰略、觀念、創新、人才和激勵五個方面的論述,源於管理理論的思考遠遠少於競爭實際情況的思考。
有人認為,20世紀末的這幾年,民族性會是中國人日益被關注的問題。我同意這個說法,但我覺得民族性不僅僅是對中國,對全世界都會是一個日益被關注的問題。事實上是我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已經落後於發達的國家。我們現在稍加留意就會發現,早已爆發的日美貿易摩擦、歐美貿易摩擦實質上都源起於美國、日本、德國對20世紀本國地位的競爭。因為所謂民族性,在今天這個信息日益發達的時代,除去經濟與文化的體現,還能夠有別的什麼內容呢?當有一天,我們中國人真的像本書描寫的那樣,開德國車、喝法國酒、抽美國煙、用日本電器,通過英特耐特欣賞美國的娛樂節目,我們的民族性還能在哪裡體現呢?人類社會在19世紀甚至20世紀前半葉之前,多數是用武力體現民族性,即所謂強權政治。但是,在今天以後,體現民族性的途徑只有經濟的崛起。日本和德國的例子生動地說明這一點。“亞洲四小龍 ”的例子也說明這一點。所以,我們的民族性首先是中國經濟的富強,這是根本的。
關於思考的問題,應該說本書大量涉及的都是聯想集團的事例,這使得這本書始終有一種風險,那就是寫成一本純粹介紹聯想集團業績的書籍。儘管這樣的結果對社會依然是有益的,但我以為這種作用還是比較表面的。我自己就常常有一種感覺,如果有一本書是說某個企業優秀到什麼程度,當然我也會覺得很好,但總不如從“為什麼”的角度去闡述更令我激動。聯想集團有太多令我激動的東西,這使得我有可能僅僅是為聯想寫一本書而不能是為社會寫一本關於聯想的書。當寫完最後一章時,我才感到鬆了一口氣。因為有那么一些思考,我想這本書已經不僅僅是為聯想而寫的了。
關於行為研究的問題,我以為當前我們國家理論科學的研究和行為科學的研究與國際社會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差距表現在我們對行為科學的研究遠遠落後於社會發展的需要。我曾經認為,中國有很好的經濟學家,但中國缺乏甚至沒有很好的管理學家。這樣的現實離我們要躋身國際經濟舞台的要求相距太遠。今天我依然保留這個看法。我們在行為科學研究上的狀態始終不能得到良好的改善,這是很令人擔心的。所以,我在本書里的思考基本上都圍繞著企業的實際情況進行。這樣做雖然可能有些拘泥,但我想也許會實用一些。
我要感謝我的恩師韓少華先生為本書作序。在過去的10多年裡,韓先生和其夫人馮玉英女士對我的愛護已遠遠超出一般的師生關係。
還有很多很多朋友。我想我對他們最好的報答只有今後認真地生活。
本書寫作完成不幾日便是國慶節。“十·一”的那天晚上,天空下細雨,應兒子的請求,我開車帶著一家人從長安街的東頭向西頭駛去。天安門廣場依舊華燈齊放,人群涌動。雨夜絲毫沒有擋住這個古老都市節日的燦爛。也就在那一刻,我再一次強烈地感到我們今天所背負的沉重以及搏擊的希望。
1996年10月於北京西郊
(再版時,略有刪改)
作者簡介
陳惠湘,1960年出生。致力於中國企業經營管理實證研究近20年。曾擔任聯想集團高級經理、國內某大型投資集團總裁,目前擔任北京豐收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和國內某知名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後著有《聯想為什麼》、《中國企業批判》、《企業團隊修煉》、《登頂之舞》、《邊走邊想》等書,在業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被譽為對中國企業界影響範圍最大與影響時間最長的“中國企業實證研究第一人”。
序言
在過去的兩年里,有朋友不斷鼓勵我應該再版自己過去的老書。我始終缺乏勇氣,甚至出版社方面也缺乏勇氣。缺乏勇氣的一個原因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中國企業的進步很大,一本寫於那個時期的《聯想為什麼》對今天的企業是否還有價值?缺乏勇氣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這本書是我第一本企業研究著作,它代表著那個時間我對企業的認識,處處表現出幼稚。直到前一段,山東的一位企業家朋友跟我說,他自己辦企業開竅是因為當時讀了我的幾本書,包括《聯想為什麼》。我知道這樣的誇獎有溢美成分,我也知道其實他是在學習聯想、學習柳傳志,我只不過沾光了。當年我曾借用王蒙先生早年一篇隨筆里的一句話自嘲自己:“一隻蒼蠅叮在駿馬的身上,因此它也一日千里了”。我得益於聯想。儘管如此,山東這位企業家朋友的話仍舊不失為一種鼓勵。而最終下決心再版此書需要感謝河北旭陽焦化集團的董事長楊雪崗先生。他領導的企業在2007年銷售規模接近百億。他委託我領導的諮詢公司為旭陽集團作諮詢,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課題是研究聯想從30億到100億的過程中都面對了哪些問題以及解決之道。
這使得我最終有了再版此書的自信。因為,1997年之前的聯想實踐對於今天大量的中小企業或許依舊有一些啟發。在此書再版之時,我想向讀者坦誠說明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聯想為什麼》這本書當年完全是我個人行為而並非企業工作。最初的寫作動機是因為我和柳總的工作討論。當時我建議聯想的媒介宣傳工作要有些改變,要告訴社會聯想之所以能夠不斷進步的深層次原因,也就是要講為什麼。柳總不同意我的主張。其中一條理由就是柳總認為我們自己也沒有把不斷進步的規律搞清楚,不能為了要宣傳為什麼而去亂說。建議被否掉之後我仍然不甘心。於是,1996年有差不多10個月時間的節假日以及平時的晚上,始終在思考、在寫作。最初沒想過要寫書,更沒想過出版。或許文人緣故,一不小心就寫成書了。動筆之前和過程中,沒有人知道此事。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寫完、寫好,先把話說出去最後事情做不好,那就很尷尬。也因此,當這本書將要出版時,我被柳總在聯想高級經理會議上批評為無組織、無紀律、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並且也因此離開聯想去辦諮詢公司。後來有記者撰文推測說我不寫書就不會離開聯想,不離開聯想就不會損失可能上千萬人民幣的期權收益。但我始終感激聯想,感激柳總和很多其他同事,因為我得到很多。這本書的首發式很排場,來了數百人,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搞的。我在首發式上講了十幾分鐘話。其中談到共產黨在延安時,有大批知識分子從國民黨統治區投奔那裡,靈與肉都經受了洗禮。而我在聯想有類似的個人感覺。十多年了,現在我愈加覺得聯想賦予我太多。
第二個需要說明的問題是《聯想為什麼》出版之後,我自己最為珍惜的事情是由於出了名,我有機會在過去的10年裡訪問逾300家中國企業和近百家跨國公司。這成為我後來繼續研究企業的基石。有一次接受電視台採訪,對方問我出名最大的好處是什麼。我說最大的好處是老師多了。每個企業都是你的老師,幾百個老師教你,只要你不弱智、不偷懶,一定會學到些東西。我知道,這是《聯想為什麼》帶給我的最大財富。世界有聯想,而聯想不代表世界。但是,聯想給了我去認識世界的機會。
需要說明的第三個問題是我對中國企業管理研究的認識。我一直認為,企業管理科學最基本的原則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這也是所有套用科學的根本特徵。企業管理研究似乎應該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案例研究,諸如有關GE、沃爾瑪、豐田、三星之類,也包括《聯想為什麼》。第二個層次是實證研究。它是要從眾多而非單個企業的實踐中去發現規律,從而讓社會分享,例如《基業長青》之類,德魯克則是這個領域的泰斗。第三個層次是理論研究。它的任務是要把已經發現的規律變成方法與工具,例如泰羅、西蒙等。中國的企業管理研究是十分落後的,而中國企業的管理實踐是十分豐富的。例如聯想、華為、平安保險、海爾等等。改革開放近30年,一大批中國企業已經積累了足夠多的管理經驗。遺憾的是研究方面則十分蒼白。案例研究方面,我們已經有了一些成果,但同時充斥著太多企業廣告書。實證研究層次幾乎空白。惟一讓人安慰的是專業很有建樹的曾鳴教授、彭劍鋒教授這樣一些學者,要么去了企業任職,要么辦了諮詢公司。我很尊敬他們。我猜測他們正在進行某種挑戰。對於長期在象牙塔里享受人們尊敬的學者而言,他們為自己的挑戰要放棄很多值得留戀的東西。而在理論研究層次上,中國的那些商學院今天還完全沒有我們自己系統成型的東西。這就是我們企業管理研究的現狀。這樣的狀況-9中國企業國際化的要求,與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要求相距甚遠。
這次,出版社將我在不同時期的四本書集合出版。我理解首先是給那些支持我的讀者們提供一個系統閱讀的可能。其次是表明出版方對企業管理研究的一種認識-9態度。《聯想為什麼》是這些著作中的第一本,也是我的案例研究開端,而寫作於2005年的《登頂之舞》則是我走訪數百家企業之後寫成的實證研究著作。一頭一尾,我十多年的研究都在其中。也因此,《聯想為什麼》此次再版時,內容方面我不作任何修改,以保持那個時期的真實,包括我自己的真實。
是為序!
陳惠湘
2007年12月於北京靜心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