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晚清歷史全景式畫卷、史詩巨著《慈禧全傳》之二。辛酉政變之後的政局,百廢待興,珠簾之後,年青的太后,有著怎樣的政治手腕,居然逐步邁向權力之顛?高陽的小說,妙在文字天成,妙在細處刻畫入木三分,其中關於中興人傑之一的彭玉麟的描繪,尤其令人一贊三嘆。
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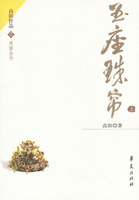 玉座珠簾
玉座珠簾本書內容: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深夜。
涼師正陽門東的兵部街,由南口來了一騎快馬,聽那轡鈴叮噹,便知是外省的折差到了。果然,那騎快馬,越過兵部衙門,直奔各省駐京提塘宮的公所。到了門前,驀地里把馬一勒,馬上那人被掀了下來,一頂三品亮藍頂子的紅纓涼帽,滾落在一邊,那人掙扎著爬起身,踉踉蹌蹌走了兩步,還未踏進門檻,一歪身又倒下去,口中直吐白味。
公所里的人認得他,是江寧來的折差,娃何,是個把總。何把總原是曾九帥的親兵,打一次勝仗使升一次,積功升到三品的參將,但無缺可補,依舊只好當那在他做把總時就當起的折差。……
作者簡介
高陽,台灣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許晏駢,字雁水,筆名郡望、吏魚,出生於錢塘望族大學未畢業,入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當了空軍軍官。1948年隨軍赴台灣。曾任國民黨軍隊參謀總長王叔銘的秘書。退伍後任台灣《中華日報》主編,還一度出任《中央日報》特約主筆。高陽擅長於史實考據,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僅在於評史述史,更重要是將其史學知識用於創作歷史小說。1962年,高陽受邀於聯合報副刊連載《李娃》,此部作品不但一鳴驚人,也成了高陽歷史小說創作的濫觴,爾後發表的《慈禧全傳》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紅頂商人》、《燈火樓台》,更確立他當代首席歷史小說家的地位一生著作一共有90餘部,約105冊。高陽的歷史小說不僅注重歷史氛圍的營造,情節跌宕,旨在傳神,寫人物時抓住特徵,寥寥數語,境界全出。
目錄
飛騎捷報
金陵血戰
初議修園
將帥不和
歌舞昇平
宮廷暗鬥
人小得志
翦除悍將
賢王被黜
弟為兄援
重贊綸扉
蒙古狀元
痛失干城
曾侯剿捻
樞臣督師
帝師大拜
深宮親情
淮軍代興
劉鮑爭功
新舊水火
驅虎驚龍
吳棠督川
魯軍東剿
金戈紅粉
彌河大捷
兩淮風雨
京畿震動
春明燈市
八旗秀色
天子多情
御賜綠頂
合肥人相
湘陰入覲
曾侯陛見
歲幕宋情
殺機初動
籌辦大婚
私議出京
第負君恩
書摘插圖
玉座珠簾(上)
飛騎捷報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深夜。
京師正陽門東的兵部街,由南口來了一騎快馬,聽那轡鈴叮噹,便知多外省的折差到了。果然,那騎快馬,越過兵部衙門,直奔各省駐京提塘官的公所。到了門前,驀地里把馬一勒,唏凚凚一聲長嘶,馬上那人被掀了下來,一頂三品亮藍頂子的紅纓涼帽,滾落在一邊,那人掙扎著爬起身,踉踉蹌蹌走了兩步,還未踏進門檻,一歪身又倒了下去,口中直吐白沫。
公所里的人認得他,是江寧來的折差,姓何,是個把總。何把總原是曾九帥的親兵,打一次勝仗保升一次,積功升到三品的參將,但無缺可補,依舊只好當那在他做把總時就當起的折差。
一看這樣熱天,長途賓士,人已昏倒,大家七手八腳把他抬了進,一面撬牙關,把整瓶的“諸葛行軍散”,往他嘴裡倒,一面把折包從他的汗水濕透了的背上卸下來。江蘇的提塘官,拆開包裹,照例看一看兵部所頒的“勘合”,然後順手一揭,看到油紙包外的“傳票”,不由得大吃一驚。
傳票上蓋著陝甘總督的紫色大印,寫明是陝甘總督楊岳斌、兵部侍郎彭玉麟、浙江巡撫曾國荃,會銜由江寧拜發。拜折的日期是六月十六,卻又用核桃大的字特別批明:“八百里加緊飛奏,嚴限六月二十日到京。”
那提塘官趕緊取出一個銀表來看了看,長短針都指在洋字的十一上,只差幾分鐘,一交午夜子時,便算違限,軍法從事,不是當耍的事!怪不得何把總不顧性命地狂奔趕遞。
現在責任落到自己頭上了!一想到“八百里加緊”那五個字,提塘官猛然省悟,失聲喊道:“莫不是江寧克復了?”
這一喊,驚動了別省的幾個提塘官,圍攏來一看,個個又驚又喜。驛遞是有一定規矩的,最緊急的用“六百里加緊”,限於奏報督撫、將軍、學政,在任病故,以及失守或者光復城池,不得濫用。現在江寧軍次負責水師的楊、彭二人,以及攻城的曾九帥,聯銜會奏,可知不是出了什麼大將陣亡的意外。而且,破例用“八百里加緊”,剋期到京,則不是江寧克復,不必如此嚴限。
“快遞進去吧!”有人說道:“江寧到此,兩千四百四十五里,三伏天氣,四天工夫趕到,簡直是玩兒命!可不能在你那裡耽誤了。”
“是,是!我馬上進宮去遞。”江蘇的提塘官拱拱手說:“這位何總爺,拜託各位照看。真虧他!”說完,他匆匆穿戴整齊,出門上馬,往西而去。
照規矩,緊急軍報遞外奏事處,轉內奏事處,徑上御前。這樣層層轉折,奏摺到安德海手裡,已經是清晨兩點鐘了。
“什麼?‘八百里加緊’!那兒聽見過這個名目,可不是新鮮事兒嗎?”
見安德海有不信之意,內奏事處太監不能不正色說明:“我也問過外奏事處,沒有錯兒!江蘇的提塘官親口說的,還說江寧來的折差,為了趕限期,累得脫力了,從馬上摔了下來,昏倒在那兒。”
說得有憑有據,不由人不信,但安德海仍在沉吟著。天氣太熱,慈禧太后睡得晚,天色微明,又得起身,準備召見軍機,也就只有這夜靜更深,稍微涼快的時候才能睡兩三個時辰。突然請駕,擾了她的好夢,說不定又得挨罵。
內奏事處的太監有些著急,他不肯接那個黃匣子,自己的責任未了,而這個延誤的責任,萬萬擔當不起,所以催促著說:“你把匣子接過去吧!”等把黃匣交了出去,他又加了一句:“快往裡送,別耽誤了!”
安德海正在不痛快,恰好發泄到他身上,“耽誤不耽誤,是我的事兒!”他偏著頭把微爆的那雙金魚眼一瞪,神情象個潑辣的小媳婦,“你管得著么?”
“我告訴你的可是好話!這裡面說不定就是兩宮太后日夜盼望的好訊息。要耽誤了,你就不用打算要腦袋了!”安德海又驚又喜:“什麼?你說,這是江寧克復的捷報?”
“我可沒有這么說。反正是頭等緊要的奏摺。”
“何必呢?”安德海馬上換了副前倨後恭的神色,陪著笑說:“二哥,咱們哥兒倆還動真的嗎?有訊息,透那么一點半點過來,有好處,咱們二一添作五。”
一則是不敢得罪安德海,再則也希望報喜獲賞,奏事處的太監,把根據奏摺傳遞遲速的等次,判斷必是奏捷的道理,約略告訴了他。
“慢著!”安德海倒又細心了,“怎么不是兩江總督出面奏報?別是曾國藩出了缺了?”
“曾國藩在安慶,又不在江寧。再說,曾國藩出缺,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報,與陝甘總督楊岳斌何乾哪?”
“對,對!一點都不錯。”
於是,內奏事處的太監,由西二長街出月華門回去。安德海命小太監依舊關好敷華門,繞著四壁繪滿了紅樓夢故事的迴廊,到了長春宮後殿,喚起坐更的太監,輕輕叩了兩下門。
等宮女開了門,安德海低聲說道:“得要請駕,有緊要奏摺非馬上回明不可。”
那宮女也是面有難色,但安德海已是長春宮的首領太監,正管著她,他的話就是命令,不敢不依,只好硬著頭皮去喚醒了慈禧太后。
“跟主子回話,安德海說有緊要奏摺,叫奴才來請駕。”
“人呢?”
慈禧太后剛問得一聲,安德海便在外面大聲答道:“奴才有天大喜事,跟主子回奏。”
一聽這話,慈禧太后睡意全消,卻不作表示,先吩咐:
“拿冰茶來喝!”
等宮女把一盞出自太醫院特擬的方子,用祛暑清火、補中益氣的藥材,加上蜂蜜香料所調製的冰鎮藥茶捧了來,她好整以暇地啜飲著。其實她急於想知道那個好訊息,卻有意作自我的克制,臨大事必須鎮靜沉著,她此刻正在磨練著自己。
喝完了冰茶,由宮女伺候著洗了臉,她才吩咐: “傳小安子!”
安德海應召進入寢殿,望著坐在梳妝檯前的慈禧太后,把個黃匣子高舉過頂,直挺挺地跪了下去,低著頭說道:“主子大喜!江寧克復了!”
“你怎么知道?”
冷冷的一句話,把安德海問得一愣,好在他會隨機應變,笑嘻嘻地答道:“主子洪福齊天,奴才猜也猜到了。”
“猜得不對,掌你的嘴。打開吧!”
於是安德海打開黃匣,取出奏折,拆除油紙。夾板上一條黃絲繩挽著,結成一個龍頭,只輕輕一扯,就鬆了開來,從夾板中取出黃紙包封,裡面是三黃一白四道奏摺。
黃的是照例的請安折,兩宮太后和皇帝每人一份,慈禧太后丟在一邊,只看白摺子。看不到兩行,嘴角便有笑意了。
安德海便悄悄退了出去,輕輕拍了兩下手掌,等召來所有的太監、宮女,才又重新進屋,一跪上奏:“請主子升座,奴才們給主子叩賀大喜!”
慈禧太后沒有理他,只這樣吩咐:“你到‘那邊’去看看,如果醒了,就說請在養心殿見面。”
“喳!”
“還有,派人通知值班的軍機章京,去告訴六爺,說江寧有訊息來了!”
安德海答應著飛奔而去。慈安太后住在東六宮的鐘粹宮,繞道坤寧宮折入東一長街,第一座宮殿就是,原叫他看一看,他卻叩開了宮門,自作主張告訴那裡的總管太監,說有緊要奏摺,請慈安太后駕臨養心殿見面。
兩三年來一直如此,凡事以“西邊”為主,“東邊”成了聽召。慈安太后不敢怠慢,但梳洗穿戴,也得好一會工夫,及至到了養心殿,天色已明,皇帝已上書房,慈禧太后也等了一會了。
先在西暖閣見過了禮,慈禧太后很平靜地說:“我念江寧來的奏摺你聽。”接著朗聲念了其中最要緊的一段:
“十五日李臣典地道告成,十六日午刻發火,沖開二十餘丈,當經朱洪章、劉連捷、伍維壽、張詩日、熊登武、陳壽武、蕭孚泗、彭毓橘、蕭慶衍,率各大隊從倒口搶入城內。悍賊數千死護倒口,排列逆眾數萬,舍死抗拒。經朱洪章、劉連捷,從中路大呼衝殺,奮不顧身,鏖戰三時之久,賊乃大潰……。”
念到這裡,慈安太后打斷她的話,急急問道:“妹妹,是奏報江寧克復了嗎?”
“才克復了外城。不過外城一破,想來內城一定也破了。”
這是應該高興的絕大喜事,但慈安太后深深地嘆了口氣,忽然傷感了,卻又不肯讓眼淚流落,只拿著一塊繡花絹帕,不住揉眼睛、擦鼻子。這個舉動,把伺候的太監們,弄得驚疑不定,但誰也不敢去探問。站得遠些的便竊竊私議,長春宮傳來的訊息不確,江寧來的奏摺,怕不是什麼好事,否則,“東邊”何以傷心呢?
慈禧太后是了解她所以傷心的原因的,必是由這個捷報想到了先帝。十一年的皇帝,幾乎沒有一天不是在內憂外患之中。由得病到駕崩,雖說是溺於酒色所,但那種深夜驚醒,起身看各省的軍報,不是這裡兵敗,便是那裡失守,儘是些令人心悸的訊息,加以要餉要錢,急如星火,這樣的日子,也真虧他挨了過去。
“唉!可憐!”慈安太后終於抒發了她的感慨,“盼望了多少年,等把訊息盼到了,他人又不在了!”
“過去的,過去了!姐姐,今天有許多大事要辦,你別傷心了!”
就這一句話,把慈安太后的心境,暫且移轉。她的傷感來得驟然,去得也快,歡喜讚嘆地說:“皇天不負苦心人,曾國荃到底立了大功,也真虧他!”
慈禧太后的想法有些不同,她認為江寧的克復,不應該遲到現在。曾國荃早就下了決心,要達直搗金陵的殊勛。四月里李鴻章收復常州,朝命進軍江寧會剿,李鴻章遷延不進,理由是兵士過勞,須得休息,其實是不願去分曾國荃的功。倘或沒有這些打算,會師夾攻,江寧早就該拿下來了。
“看這樣子,仗打得很兇!可不知道人死得多不多?”
“那還少得了嗎?”
“咳!”慈安太后又憂形於色地,“仗是打勝了,收拾地方,安撫百姓,以後這副擔子還重得很吶!”
這又與慈禧太后的看法不盡相同,但一時也無法跟她細談,此刻要召見細談的是軍機大臣。
“叫起吧!”她說了這一句,便即站起身來,略停一停,等慈安太后走到她旁邊,才一起緩步到了東暖閣,升上御座。
全班軍機大臣,恭王、文祥、寶鋆、李棠階、曹毓瑛早就在軍機處待命,喜訊雖好,苦於未見原奏,不知其詳,內城破了沒有?洪秀全雖已於四月下旬,服毒自殺,他的兒子,被“擁立繼位”的洪福瑱,可曾擒獲?尤其是偽“忠王”李秀成,此人雄才大略,不可一世,如果他漏網了,太平天國便不算全滅。
大家正這樣談論著,寶鋆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天該遞如意吧?”
“啊呀!這倒忘了。”恭王說,“趕快派人去辦。”
這是多少年來的規矩,凡是國家有大喜慶,臣下照例要向皇帝遞如意,象今天這種日子,如意是非遞不可的。
就在這時候,軍機處的“蘇拉”來稟報:兩宮太后已臨御養心殿,傳旨即刻進見。時間倉促,即使象恭王那樣,府里有現成的如意,也來不及取用,只好作罷。
如意雖不遞,頌聖之詞不可少,所以一到養心殿東暖閣,恭王首先稱賀。兩宮太后自然也有一番嘉慰之詞,然後把原奏發了下來。殿廷之上,不便傳觀,由寶鋆大聲念了一遍,殿中君臣,殿外的侍衛、太監,一個個含著笑容,凝神靜聽。
由於慈安太后不明白江寧的地勢,於是籍隸江陰的曹毓瑛,作了一番“進講”。他為兩宮太后指陳,曾國荃奏摺內所稱的“外城”,就是明朝洪武年間所建的都城。原有十三個城門,本朝封閉其四,剩下正陽、通濟、聚寶、三山、石城、儀鳳、神策、太平、朝陽等九門,用火藥轟開的倒口,是在太平門,正當玄武湖東南。再往東去,就是鐘山,洪軍在此築了兩個石壘,稱為“天保城”、“地保城”。這年春天,曾國荃奪下“天保城”,江寧合圍之勢已成,五月間再奪下“地保城”,則江寧的克復,不過遲早間而已。
“那么內城呢?”慈安太后又問。
“內城就是明太祖的紫禁城,本朝改為駐防城,那是不相干的!外城周圍九十六里,城基是花崗石,城牆是特製的巨磚,外面再塗上用石灰和江米飯搗成的漿,堅固無比,這一破了外城,江寧就算克復了。”曹毓瑛以他在軍機處多年的經驗,復又指出:“想必就在這一兩天,曾國藩還有奏摺來,那時候克復江寧的詳情,就全都知道了。”
“那么,”慈禧太后問道:“咱們眼前該怎么辦呢?”
“當然是先下個嘉慰的上諭。論功行賞,總要等曾國藩把名單開了來,才好擬議。”恭王這樣答奏。
“好!馬上寫旨來看了,讓江寧的折差帶回去。”
於是曹毓瑛先退了出去,擬寫諭旨,除了對曾國荃所部不滿五萬,在兩年的工夫中,將江寧城外的“賊壘”,悉數蕩平,現在復於“炎風烈日之中,死亡枕藉之餘”,力克堅城,歸功於曾國藩的調度有方,曾國荃及各將士的踴躍用命,表示建此奇勳,異常欣慰以外,特別許下諾言:“此次立功諸臣將偽城攻破,巨憝就擒,即行漏沛恩施,同膺懋賞。”寫完送進殿去,先交恭王看過,然後呈上御案,兩宮太后一字未動,原文照發。
“江寧克復,差不多就算大功告成了。” 慈禧太后看著恭王說道:“這幾年的軍餉,全是各省自籌。現在要辦善後,可不能再叫地方上自己籌款了,戶部該有個打算!”
“臣已經打算過了。”恭王答道:“偽逆這幾年搜括得不少,外間傳言,金銀如海,只要破了他的偽府,辦理善後的款項,自有著落。”
“怕不能這么打算吧?”慈禧太后疑惑地。
“現在只好先這么打算。”恭王極快地回答,語氣顯得很硬,“戶部跟內務府,每個月都是窮打算,京里的開銷也大,還得想辦法省!”
內務府只管支應宮廷的用度,說內務府還要節省,等於要求宮廷支用,還要撙節。慈禧太后已不止一次聽得安德海報告,說長春宮向內務府要東西要錢,恭王難得有痛痛快快撥付的時候。她雖也知道,恭王不是肅順,並非有意跟她為難,但是,他也並不見得如何尊崇太后!
最使她耿耿於懷的是,上個月裡,有個名叫賈鐸的御史,上了個摺子,說風聞有太監演戲,一賞千金,並且用庫存的綢緞,裁製戲衣,請速行禁止,以期防微杜漸。這是那裡的話?自從國喪孝服滿了,每月初一十五在漱芳齋唱唱戲是有的,何至於“一賞千金”?既然演戲,就得要行頭,不能象道光年間那樣,戲台上不管帝王將相,還是才子佳人,都穿的是破破爛爛的行頭,身上東一片,西一片,滿台搖晃,簡直就是花子打架,那又何必唱戲?因此,慈禧太后覺得賈鐸是吹毛求疵,非常不滿,但恭王卻回護著他,不能不下個否認的批諭。
這些回憶加在一起,愈覺恭王剛才說的話刺耳。不過在今天這樣的日子,那份不快很容易掩沒,對恭王的芥蒂也不難容忍,所以還附和著他說:“是啊,該省的一定要省。大亂一平,那就要‘百廢俱舉’了,處處都要花錢。而況捻匪還在鬧,軍費也少不了的。”
聽得慈禧太后如此明理,軍機大臣們無不心悅誠服。退出養心殿後,又到軍機處集議,把曾國荃的原奏,重新細細研究,得出一個相同的看法:曾軍圍城已久,糧道久絕,城內餓死的人,不知其數,卻拚死頑抗,鬥志不衰。而曾軍在炎暑烈日下,圍攻四十餘日,死亡枕藉,艱苦萬狀,則一破城以後,必然是一場窮砍猛殺的惡鬥,地方糜爛,難以善後。
因此,這個捷報對執掌國柄的軍機大臣來說,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但無論如何,這是開國以來第一場大征伐,也是第一場大功勳。乾隆朝的“十全武功”,固然膛乎其後,就是康熙朝的平三藩之亂,論規模、論艱難,也都不如。戡平這場大亂,自然要數曾國藩的功勞第一,真值得封一個王。
可是沒有人肯作此倡議。
這時外面也已經得到訊息了,起初還將信將疑,等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退值回家,紛紛都來打聽,正式證實有此捷報,於是奔走相告,傳遍九城。這天晚上從王公府第到蓬門篳竇,在納涼閒談時,無不以此作為話題。
當然,對此捷報的想法,因人而異。流寓在京的江南人,念切桑梓,自然欣喜若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