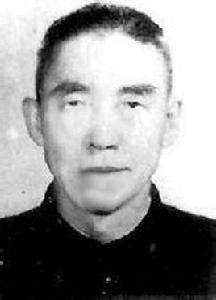個人簡介
汪維恆,原名汪益增,又名汪微痕。浙江諸暨牌頭寺下張汪家人。同文公學畢業。1913年在杭州浙江一中學習,1921年畢業於北洋政府北京軍需學校第四期,被派往浙江慈谿縣浙軍,先後任營、團軍需官。1924年初,經張秋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與楊眉山等同為寧波地區最早的四名共產黨員。1925年,經組織決定,汪維恆跨黨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任共青團寧波地委書記。同年九月返諸,與陳兆龍、金城、宣俠父和弟弟汪益堃等組成第一屆中國共產黨諸暨縣委員會,汪維恆為縣委委員,組織部長。1928年5月,受命潛伏國民黨軍需界二十餘年,歷任國民黨中央軍校、中央軍校洛陽分校任科長,參加過淞滬抗戰。抗戰時期,任胡宗南部軍需工作,又任國民黨軍政部第一軍需局少將局長,與弟弟汪益堃積極為八路軍提供軍需物資。內戰爆發,任南京聯勤總部副司令兼經理署副署長,他多次為黨中央提供重要情報。1948年,以台灣第十補給區少將副司令兼供應局局長身份潛伏台灣。1949年4月,接到組織通知,撤離台灣,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上海市銀行董事長,派人日夜監護財政局系統,為人民保護好一大筆財產,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情報和軍需物資,為解放後財政局系統的軍事接管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解放後,汪維恆歷任上海直接稅局副局長、地政局局長、房地產管理局局長等職,並當選為市一至五屆人民代表和市人民委員會委員。十年動亂時,被“四人幫”陷害關進監獄,含冤而死。
人物生平
汪維恆(1896-1971), 浙江諸暨人。1924年(民國13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後受黨組織委派,在浙江台州、黃岩、寧波、諸暨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擔任特派員、諸暨縣委委員、共青團寧波地委書記等職務。
1927年(民國16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堅持地下鬥爭。1928年(民國17年)秋,諸暨地下黨機關遭破壞,經中共諸暨縣委負責人金城、張以民的同意,他走避南京,從而失去與黨的聯繫。
汪在南京、西安先後擔任過國民黨中央軍需學校中校科長、78師上校軍需主任、西安軍政部第一軍需局少將局長。1937年(民國26年),國共合作抗日,他與中共方面建立了聯繫,利用職務便利為八路軍提供經費和軍需物資。1943年(民國32年)春,在重慶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的秘密接見,得到周恩來的鼓勵和讚揚。解放戰爭期間,擔任台灣供應局局長,上海市財政局局長,曾為掩護、營救、資助中共幹部做了許多工作。
解放後,汪當選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屆人民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委員,歷任上海市直接稅局、地政局、房地產管理局副局長、局長等職務。
1949年8月,汪維恆任上海市地政局局長,在加強土地管理、清理土地積案、進行土地登記、整頓地價、擬訂土地管理行政法規、開徵地價稅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2年9月,地政局與公共房屋管理處合併,改組成立上海市房地產管理局,汪任副局長。1952年12月,任局長。任職期間,他以無黨派人士身份自覺接受黨的領導,與班子成員坦誠相見,合作共事,認真貫徹市政府提出的“為生產、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房管工作方針;在修理養護中,他強調“舉手之勞”的主動服務精神,深入房修工地和里弄,傾聽住戶意見,擬訂房修行政管理法規;在管理上,遵照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多次調整公房、私房管理體制,精簡機構,下放管理許可權,開展住房交換,挖掘房屋潛力,合理調配使用房屋,緩解生產和居住用房的供需矛盾。
1957年5月,汪列席市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並在大會上就當時的房屋供需矛盾、修繕力量不足、租金偏低、以租難以養房等問題作了如實匯報,呼籲各方予以支持。1962年,市房地產管理局向市政府呈送《健全和加強市房屋調整委員會組織機構》專題報告,很快得到市政府的批准,汪維恆受任為房調會委員,對大力挖掘房屋潛力,緩解房屋供需矛盾等重要問題的研討和決策,發揮重要作用。他還為爭取台灣回歸祖國曾做了許多有益工作。
汪維恆於1971年1月,遭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致死。1979年1月,得到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並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恢復中共黨籍,黨齡從1924年(民國13年)1月起算。
人物經歷
一、潛伏敵營
汪維恆,1896年生於浙江省諸暨縣牌頭鎮汪家村一個破落地主家庭。1917年在諸暨縣漁山國小擔任國小教師。1918年,為了接受維新思想,求學於上海法文翻譯學校。1919年,他投筆從戎,赴北京軍需軍官學校學習。1921年他作為軍需軍官學校第四屆畢業生,被派往浙江慈谿縣浙軍,先後任營、團軍需官。
在寧波,汪維恆認識了共產黨人張秋人,兩人談得頗為投機,從此書信來往,汪維恆從張那裡真正開始接觸革命思想。張秋人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區委員會委員,受派到寧波地區進行宣傳活動,也是浙江諸暨縣人,與汪維恆同樣畢業於同文公學,時任湖南衡陽師範學校英文教員。
1924年,汪維恆與楊眉山、周天僇、許漢城四人經張秋人介紹,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是寧波地區最早的4位黨員。1925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組織決定派汪維恆跨黨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汪維恆所在的浙軍回響廣州國民政府的號召發動起義,但被北洋軍閥的軍隊擊敗。此後他脫離浙軍,回到家鄉諸暨。1927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提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委任他為浙江台州區黨務特派員,到台州、黃岩、臨海、溫嶺各縣整頓國民黨黨務,改組國民黨縣黨部。這些工作,當時都是半公開的。同時,他帶著更秘密的任務,發展共產黨組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中的共產黨員和左派分子大都犧牲或逃亡,中共寧波地委調任汪維恆為寧波地委團委書記,後調往故鄉諸暨縣任中共縣委組織部長,以縣城區國小教師作為職業掩護。國小校實際上是地下縣委機關。1928年5月,諸暨縣委積極準備發動暴動。不料,該校一位黨員教師邊世民練習使用手槍時不慎誤殺了其妻,從而暴露了準備暴動的計畫。諸暨縣委立即決定:各負責人員迅速撤離、走避。汪維恆遵照縣委書記金城(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指示,去南京利用原軍需軍官學校的關係,打入國民黨軍需界,潛伏下來,等待組織來人聯繫。誰知道這一等就是十幾年,汪維恆為了堅持自己革命到底的決心,改名“維恆”。
那時,白區一片恐怖,地下組織全遭破壞,人員不是被捕、被殺,就是走避,始終沒有黨組織來找過他,最後連縣委書記金城自己也逃了出去。由於大革命時期沒有黨證,一旦與組織失去聯繫就無法證明黨員身份。汪維恆的黨籍問題後來成了他一輩子的心病。
1928年9月,汪維恆到了南京,找到了過去在第四軍需軍官學校任經理處長、時任國民黨中央軍校經理處長的陳良。陳良一向欣賞汪維恆的正直,當即安排他在國民黨軍需署經理法規研究所學習,三個月結業後先後被派往中央軍校總部、中央軍校洛陽分校任少校軍需科長,隨國民黨87師參加了淞滬抗日戰役。由於汪維恆為人清廉,工作出色,聲望逐步上升。當時屬抗日派的胡宗南要陳良推薦一位清廉有為的軍需軍官,陳良就推薦了他。胡對他也極為欣賞,讓他隨同轉戰河南、西安,建立後勤基地。
潛伏在國民黨軍需界,尋找等待黨組織的同時,汪維恆利用職務之便,在南京、洛陽、商丘等地救助、轉移走避的地下黨員,包括金城、金堅、金劍鳴、金丁永、壽松濤、駱子釧、潘念之、張以明、許漢城、邱培書、陳老太、何竟華、鍾子逸、祝子韓、陳葵南、何咀英、馬乃松、華林、周天傻等人。汪維恆在西安國民黨中央軍校第七分校訓練900餘名軍需幹部和會計幹部,派往各部隊實行軍需獨立。其中300餘名共產黨員和愛國青年是從西安國民黨集中營中以參加軍需實習班、研究班學習為名營救出獄。
1938年8月,經李克農同志首肯,中共南京諜報機關的史永(原名沙文威,後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找到汪維恆,問他是否願意為黨做事。汪維恆當即爽快地答應了。自此汪維恆與黨組織重新接上了關係,但也產生了誤會:汪維恆以為他等了這么多年,黨終於來找他了;而史永並不知道汪維恆受命潛伏的歷史。這個歷史誤會一直到解放後史永在北京向金城了解情況時才解開。
1942年,在國民黨西北軍需局局長任上的汪維恆和弟弟汪益堃,又重新填寫了入黨申請書,由八路軍紅岩辦事處主任錢之光送交黨組織。(後因形勢危急,紅岩辦事處匆忙撤退,錢之光不得已而將申請書銷毀。)
1943年,蔣介石違反國共合作協定,秘密策劃剿共。7月間,他密令胡宗南部準備襲擊八路軍控制的陝甘寧邊區南部的突出地帶,汪維恆得到訊息,見情況危急,便與汪益堃藉故趕到重慶,與錢之光聯繫。錢之光當即派車將他們秘密接到紅岩嘴,去見周恩來、林彪、伍雲甫,及時匯報西北各省國民黨軍隊的兵力、裝備、布防和調動以及胡宗南部進行封鎖的情況,之後仍從原路返回。後來蔣介石發現八路軍已經察覺他的企圖,便沒有貿然行動,計畫未能實施,延緩了國共合作的破裂。
1946年汪維恆任南京聯勤總部副司令兼經理署副署長時,史永特意從上海調往南京配合他工作。汪維恆將他所掌握的幾乎所有的重要戰役、國民黨軍隊調動、武器彈藥、軍隊運輸補給等情報,通過史永源源不斷傳至黨中央。大別山戰役時,蔣介石得知劉伯承大軍已渡過黃河,緊急召集最高級軍事會議,經過激烈爭議最後決定,由非蔣嫡系的白崇禧任總指揮,率二十萬大軍向劉鄧大軍發動總攻擊。負責後勤的汪維恆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他將蔣軍部隊數量、裝備以及進攻路線。出動日期等全部計畫速報史永轉至黨中央。1948年,遼瀋戰役前夕,汪維恆借赴河北、東北考察軍需配製及供應情況為名收集情報。其中有河北、東北各地國民黨部隊番號、長官姓名、兵員人數及駐地布防等。回來後交給史永同志,由上海局劉人壽領導的電台發出。遼瀋戰役結束後,從殲敵人數,捕獲將領和戰況總匯來看與所提情報如出一轍。
二、臨解放受命赴台
1948年6月,陳誠將汪維恆調往台灣出任台灣第十補給區少將副司令兼供應局局長,為國民黨軍隊退守台灣作後勤供應的準備。
陳誠沒有想到,在國民黨軍需界供職已二十年的少將汪維恆竟是中共老黨員。
汪維恆的潛伏生涯一晃已過去二十年。如今曙光在前,突然接到了赴台任命,汪維恆陷入了深思。他知道,一旦去了台灣,全家很可能就回不來了,他將繼續潛伏下去;而此時國軍敗退台灣已是大勢所趨,國軍退守台灣後的軍事部署、武器配備、後勤基地等軍事動向對解放軍尤為重要。因此,他毅然決然攜全家赴台上任,不計個人得失,為解放事業作出必要的犧牲。在飛往台北之前,他與史永進行了聯繫,報告了他的決定。史永向中共情報機關匯報後通知他:同意汪維恆赴台,但一旦接到新的命令,應立即撤離台灣。同時為了配合他的行動,中共情報機關派遣地下黨員許漢城同往台北,以印刷廠廠長名義往返台灣與大陸之間遞送情報。許漢城是位外表極其普通的中年人,與汪維恆同時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又是浙江諸暨同鄉,他們的往來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汪維恆到台灣後,不時將台灣的軍事情報——部隊換防、武器配備、美軍顧問團活動情況,通過許漢城送回大陸;另一方面他也在等待密令,等待時機,準備隨時返回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潛伏生活,他一直期盼新中國的成立,尤其盼望能親自迎接解放,這種心情常人是難以體味到的。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短短几個月間,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解放軍渡長江,克南京,挺進杭州,勢如破竹,對上海形成了包圍圈。汪維恆預感到最後的暴風雨即將來臨,他和家庭將面臨著考驗。每天半夜他都緊張地收聽新華社廣播,了解形勢新動向,準備一旦接到密令立即撤離台灣。
三、接密令返滬
1949年春,汪維恆突然接到史永的一封信,信里有一首盼故友回歸的詩,意思是:迅速撤離台灣,返滬迎解放。汪維恆又激動又發愁,激動的是終於等到了盼望已久的通知;愁的是無以為藉口返回大陸。
幸而天無絕人之路,台灣省供應局因局勢變化宣告解散,汪維恆的上司陳誠也在醫院養病。他乘機打電話向陳誠告別,稱母患病要回大陸探望。陳聽後勸他不要“冒險”,遂又派夫人前來極力勸阻,坦言大陸局勢危急,切勿冒險行事。為了避免引起懷疑,汪維恆將全家留在了台北,於1949年4月毅然隻身飛回大陸。實際上全家離台的準備工作早就悄然就緒,一旦接通知他將立即撤離。
1949年5月初,汪維恆家人乘坐一班返滬的船,有驚無險地回到了上海。
四、力勸陳良“勿做敗局的殉葬人”
汪維恆回到上海,陳誠挽留未果便宣布他為駐滬淞滬區補給區副司令。此時他的老上級陳良已任上海市代市長。陳良見到汪維恆很高興,致電陳誠要留汪維恆在身邊,並推薦他在原職以外再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銀行董事長。
此時汪維恆已無法與在南京的聯絡員史永取得聯繫。於是他利用職務之便,自行開始了迎接解放的準備工作。召集舊部張興國、林安庭、何其偉、樓翔等人,對財政局所有檔案、倉庫進行盤查、造冊,安全封存日偽檔案;同時阻止大量的資金繼續外流。
與此同時,他還要應對殘留的國民黨軍政要員。湯恩伯要求撥巨款修固上海四郊的防禦工事,準備頑抗。汪維恆力勸陳良:“勿做敗局的殉葬人!”陳良聽取勸告,以財政空虛為名,沒有撥款。谷正綱和方治勸陳良提取上海銀行存款換美金帶走。汪維恆說:“這是谷和方的流亡資本,而你將落個盜取公款的罪名。”陳聽後當即撕掉取款手令。特務頭子毛森和陶一珊脅迫陳良將上海市府各局的檔案、賬冊全部燒毀。汪維恆曉以大義:“這種行為會引起全體市民的恐慌,不利戰爭有害人民。”陳良聽後反而下令市政府各單位“必須保全財物賬冊,不得銷毀”,並限時造冊備查。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一套《徵收房捐依據圖》。它標出了上海市區每條街、巷,每棟房屋面積、結構的詳細圖表。其數量之龐大,若被毀壞,數百名測繪員花幾年時間也難以重新製作。由於它關係到上海未來的市政建設,所以汪維恆派專人嚴加保管,日夜守護,為穩定上海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陳良不僅是汪維恆的老上司而且是老朋友,關係非同一般,對汪維恆幾乎是言聽計從,所以汪維恆一直在策反陳良。他說,陳良大革命時期也曾加入過共產黨,經勸說陳雖已動心,但由於擔心後果最終還是離開了。
1949年5月27日,汪維恆以“投誠”形式率員在財政局向軍管會代表顧準、謝祝柯和朱如言交接。交接時汪維恆要求與顧準單獨談談。他們走進局長辦公室關上門,當汪維恆告訴顧準,他是1924年入黨的中共地下黨員時,顧準當場驚呆了。看著眼前這位五十多歲的國民黨少將,竟然黨齡比自己還長十幾年。他緩緩拿起話筒,撥通了副市長潘漢年的電話。經過確認並聆聽了指示,顧準錯愕的臉方鬆弛下來。掛上電話,顧準緊緊握住汪維恆的手,激動地說“太好了!太好了!”走出辦公室後,交接儀式仍按原計畫進行,在眾目睽睽之下上演了國民黨財政局長向解放軍軍代表顧準交接的一齣好戲。隨後顧準派專車送汪維恆去見潘漢年。汪維恆將他從台灣帶回的軍事情報以及美軍顧問團活動情報等,親自呈交給潘漢年同志。
五、反貪腐被蔣緯國告狀
汪維恆的正直、清廉在國民黨時期就出了名。他耳聞目睹了舊政權的覆滅與貪腐密切相連,因而將剷除貪腐視為自己的使命,把造福於民作為一生奮鬥的目標。
汪維恆是個注重儀表卻不追求時髦的人。他的個子不高,約1米70左右,平頭,粗眉大眼,站立挺直,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與其長年在軍隊工作有關。他不抽菸不飲酒而且禁止子女抽菸飲酒。解放前他歷任國民黨的軍需局長、聯勤司令、供應局長、財政局長:解放後歷任稅務局長、地政局長及房地產管理局局長,一生與錢和權打交道,卻從不為己謀私利。
八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政界一些高官自詡抗戰有功,居功自傲,借權謀利,貪污之風逐漸盛行。汪維恆當時已是國民黨軍需界的重要人物,以他的為人決難容忍,在反貪腐鬥爭中他得罪了不少國民黨高官,因此兩度遭到撤職,幾近入獄。
最具諷刺的一出“狀告”汪維恆的鬧劇,是蔣緯國導演的。
1945年汪維恆接到線報,國民黨34集團軍某師虛報軍餉。他得知後立即下令查扣。實是胡宗南部隊一師師長挪用軍餉做生意,自製劣質軍鞋濫竽充數。時任一師連長的蔣緯國與師長沆瀣一氣,利用其特殊身份,密報蔣介石,反誣家父扣壓、貪污軍餉,發給士兵的軍鞋質量很差。蔣介石輕信其言,不問青紅皂白立即批令,撤職查辦汪維恆,但遭到何應欽堅決反對。何應欽是蔣介石的嫡系大將,他認為應先搞清來龍去脈再下定論。不得已,蔣介石怒召汪維恆以及一師師長和軍需主任。面對不明底細的蔣介石,汪維恆據實匯報了事件經過,並將34集團軍賬冊全部呈上。經軍政部一一審核,證明絲毫不差。蔣介石無奈地取消了對汪維恆的撤查令,復將一師師長查處。
自此,汪維恆在國民黨軍需界更是名聲大振,然而經歷了這樣的遭遇,又知道了事件的背景,汪維恆毅然辭職,不久乘飛機離開西安去南京。沒有料到,胡宗南親自到機場送行以示歉意。汪維恆因不告而別主動向他致歉,說: “在胡司令領導下工作八年,未能幫助胡司令解決生活困難,深為內疚。”胡宗南也說:“我在此也不會長久的。”胡宗南是蔣介石黃埔軍校中有名的戰將,抗戰時期蔣介石派給他的任務總是最艱巨的。
此外,汪維恆查處的大案還有:緝獲衛立煌長官部私運布匹;緝獲蔣鼎文行營私藏大批軍服;緝獲傅作義的西安辦事處套購大批軍布;揭發閻錫山辦事處賄賂案;沒收山西幫“通誠晉”走私軍服案等。
汪維恆培養了數以千計的軍需人才,同樣以清廉不斷要求和教育他們。1938年,胡宗南將西北軍官訓練班改成中央軍校第7分校軍需經理訓練班。汪維恆當時是黃埔軍校第7分校的經理處長,同時也是第34集團軍、第8戰區副長官部經理處長兼戰乾4團經理處長以及西北第一軍需局局長,由他主持第7分校軍需經理訓練班的培訓任務。除了常規經理課程外,他特別開設了清廉課,將之列入教學大綱。他命訓育主任魏予珍收集歷代清廉操守的古聖賢、道德高尚的愛民清吏的案例編寫成教材。由他和魏親自授課,並在升旗時講評。同時,發動學員搞牆報宣傳清廉。所以他培養出的部下很少有貪腐的。
汪維恆權掌西北五省軍需供應時,逢年過節家門口車水馬龍,送禮人絡繹不絕,但均遭他回絕。後來大家都知道了他的秉性,便鮮有人再送禮來。不過有次白崇禧派人送來禮物,汪維恆卻收下了。他說:“白崇禧非老蔣嫡系,擔心軍需物資遭剋扣,收下禮物方安其心,尤其(當時)白崇禧(的部隊)在抗日第一線。”
然而,清廉的汪維恆並不受軍界高層的歡迎,反而受到排擠,直至1948年脫離軍界時依然是個少將。
解放後汪維恆任上海市房地產管理局局長(副市長級),他也從不利用職權為自己和我們搞特殊待遇。組織上分配給汪維恆東湖路近淮海路的某處洋房,被汪維恆拒絕了。後又分配淮海路某處居住面積達180平方米的一套公寓,汪維恆說:“要這么大幹什麼!”最後要了一套淮海路居住面積88平方米的公寓。
六、家庭情況
汪維恆兄弟姐妹四人,他是老大,父親早亡,母親一直由父親贍養。他對弟妹的關懷也無微不至,對弟弟汪益堃尤為情深。夫人是個國小音樂教師。
1925年,汪益堃由汪維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兄弟二人一同為開闢抗戰後勤基地轉戰西北,並為黨提供了重要的軍事情報。
1942年,汪益堃剛升為少將,一次他從蘭州去新疆,原可以乘民航班機,但他急於返回,執意乘軍用飛機。飛臨甘肅省六盤山烏鞘嶺上空時,天氣突變,飛沙走石,飛行員視線受阻,飛機撞在山坡上,機毀人亡。為了悼念汪益堃,汪維恆在光禿禿的烏鞘嶺上為汪益堃立了衣冠冢,並建立了一所益堃國小。同時還在甘肅酒泉天祝(藏族自治縣)安遠鎮另建立了一所益望國小。
汪益堃留下了三女二子,長女汪晶芝、次女汪玉芝、三女汪渝芝,長子汪而夫(有媒體誤報導為汪維恆之子)、次子汪嶺夫(名取自烏鞘嶺)。汪維恆毅然挑起了撫養汪益堃遺孤的擔子,同時將抗戰時期汪益堃托人代養的次女和三女也千方百計地尋了回來。
汪維恆共有六個孩子:長女汪晶予、長子子汪伯羊、次女汪放予、次子汪仲遠、三子汪雁峰和四子汪小流。
七、恢復黨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始,上海市房地局黨委為了保護當時作為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汪維恆,讓他在家休息。但以他性格,非但不會呆在家裡,而且依然堅持每天上午上半天班,說:“去看看‘大字報’,了解民眾的意見和想法。”然而,他回來後常常一言不發,眉頭緊鎖,心事重重。一次,他道出箇中原委:“‘大字報’揭發了許多(黨內)的事,如果事情屬實,問題就太嚴重了。”後來,全國颳起了一陣“經濟風”,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長兼局黨委書記朱道南(《大浪淘沙》的作者)數次遭批鬥,汪維恆痛心地說:“朱局長代我受過。”
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汪維恆已經預感到衝擊波,即便在此艱難時刻,他想到的依舊是如何去保護他人。當得知有人企圖搶占陳修良(原浙江省省長沙文漢之妻、浙江省委宣傳部長)母親陳老太的住房時,他專門指示:不得動她的房子。汪維恆說:“大革命時期陳老太為黨做了許多工作,多次幫助和掩護過地下共產黨員,我們不能忘恩。”
1968年的一天,汪維恆像往常一樣去上班,從此再也沒有回家。汪維恆被安上“特務”、“叛徒”的罪名並冠以“台灣派回來的總特務頭子”,先後關押在哈密路上海公安學校內和上海龍華監獄。
1971年1月30日,汪維恆含冤去世。
汪維恆一直以共產黨員身份做地下工作。然而解放後他才知道,自己的黨籍並沒有恢復,而他和弟弟汪益堃重填的入黨申請書因當時紅岩辦事處撤退匆忙而銷毀。汪維恆雖然心裡因此很苦惱,但始終沒有放棄要恢復共產黨員身份的心愿。
“四人幫”倒台後中央撥亂反正,不僅為汪維恆平反昭雪,而且恢復了他夢寐以求的黨籍。
汪維恆去世8年以後,1979年3月終獲平反昭雪,中共上海市基本建設委員會黨組批准通告:“為汪維恆同志舉行骨灰安放儀式。汪維恆同志深受林彪四人幫修正主義路線殘酷迫害,1971年1月30日致死。為汪維恆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特預定1979年3月26日下午在上海市龍華革命公墓大廳舉行骨灰安放儀式。”參加安放儀式的人群擠滿了內、外院和路道,中央領導及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和汪維恆工作過的諸暨、寧波等地都送了花圈,骨灰存放在龍華烈士陵園。
由於汪維恆的情報系統是潘漢年領導的,受“潘楊冤案”影響黨籍一直無法落實,1982年,潘漢年得到平反,198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84)組建字1027號發文《關於恢復汪維恆同志黨籍的請示》的批示:“恢復汪維恆黨籍。黨齡自1924年1月算起。”
2001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發文《關於汪維恆同志骨灰存放意見的函》指出,本著實是求是,特事特辦的原則,妥善處理汪維恆同志骨灰存放的特殊問題,將汪維恆同志骨灰從三廳(局級廳)轉至一廳(部級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