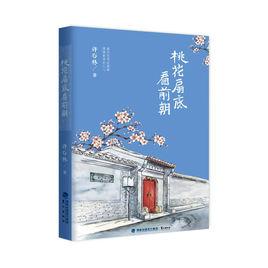編輯推薦
1周有光霍松林 馮其庸 葉嘉瑩 尚長榮鮑鵬山傾情推薦
2文章以短小精悍見稱,文筆以嬉笑怒罵為長;談的是前朝舊事,看似“食古不化”,諷喻的是如今世道人心,有道下筆情深。
3太上有立德,古之人不余欺,只有人倫大防才能阻止社會墮落;社會總在變化發展之中,走上正道,還在眾人戮力躬行。
4許石林先生談吃、說戲、鼓琴、交遊、經史雜家無所不能、無所不觀,刀子嘴,菩薩心;其人亦灑脫:穿長衫,戴墨鏡,抽菸斗,喜飲食,此其性情之所鍾。
 桃花扇底看前朝
桃花扇底看前朝 桃花扇底看前朝
桃花扇底看前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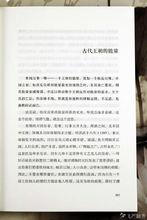 桃花扇底看前朝
桃花扇底看前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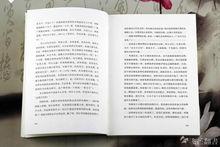 桃花扇底看前朝
桃花扇底看前朝內容推薦
本書作者,遊刃於歷史人物掌故之中,上到帝王,下至文官武將、黎民百姓,皆不在話下;小到個人慎獨功夫,大到社會建制,提筆即成;嬉笑怒罵間,舊社會的三綱五常鋼骨、社會情狀,躍然紙上。在調侃古人“冥頑不靈”的字裡行間,亦戲說著先賢金石之言,勸善之意。
莫說今人士大夫式的勸善教化以言志載道太過冬烘,抹殺學人進德彰賢的現代意義;更不能單以一個“舊”字將古人宣揚的德行義理淪為阻礙個性解放、現代文明進步的眾矢之的。作者將憂世之心,化作崇古之文、笑罵之筆,其中自有深情。
作者簡介
 桃花扇底看前朝
桃花扇底看前朝許石林,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傳媒大學客座教授、深圳市雜文學會會長、深圳市烹飪協會名譽會長、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中華吟誦學會理事、中國古琴學會專業委員會會員。
主要著作:《損品新三國》《尚食志》《文字是藥做的》《飲食的隱情》
本書目錄
朝臣待漏五更寒
003古代王朝的能量
008成王敗寇的真正含義
013黃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
026王道本乎人情
030古代帝王下詔罪己
034宋仁宗的飲食
037美食背後
040“設官求人,非人求官”
043諫諍猶如擠粉刺
048清末軍機處的那些事兒
052顧命大臣的命運
056一輩子就為了得一個好死
061當官要隨時準備說:我不幹了!
064古代官員退休生活
068古代法官嫖娼的事兒
073古代醫患之間
077“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081古代官員自殺
086古代打老虎
090拿什麼警誡官員最有效
功名富貴皆春夢
099所謂琴心——減少苟活的理由
105古代弔民伐罪
110“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
114“君子愛人以德”
117“里有喪,不巷歌”
120“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124古代士大夫遇沮則退
128要臉的和不要臉的
132“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136守禮者無敵
140懲罰的藝術
144十歲小孩兒的風度
147“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150“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153量小非君子
156心肺肝膽
160生正逢時
163遊必有方
167“聲色勢利怒愛昏其智矣”
170“謹慎應酬無懊惱,耐煩做事好商量”
173那些很極端的孝
白雲蒼狗一笑中
179史上最無恥的“帶路黨”
186見官員被殺死為何不救
192科場案和假文憑
197宋朝人的元宵節如此好玩
201古代飲酒之厄
205天下官民相互體恤
208古代賑災的故事
212古代秘書
216古代城管的那些事兒
220胥吏思維的毒瘤
223古代為什麼嚴重鄙視役隸
227中國古人為啥不和演員計較
232古代優伶身份卑賤卻心向尊貴
237古代的騙子
241古代官員迷信風水
245古代人如何對待“怪力亂神”
249古代如何阻止謠言
254古代枉法的案例
258清代海南的一宗強姦案
媒體評論
許石林的學問好,讀了不少書,還沒有冬烘氣,文字恣肆而能收斂自如。今天多少所謂學者教授,除了會寫“論文”,一句有意味有趣味有人味的話都說不出來。更重要的是,許石林有價值觀,他的文章不違背天理——要知道,今天多少名流作家,舞文弄墨,專門違逆天道壞人心術!
——鮑鵬山
許老師的書可以淺嘗,可以精讀。廣見聞,知風俗,是淺嘗。而貫徹始終的民胞物與之情懷,存亡續絕之心聲,春風化雨之教化,才是許老師文章感人之所在。
——楚狂兒(旅日學者)
就所謂文人的德行和格調來說,許石林是深圳文人中最有學識、最低調、最不裝者。
——高小龍(導演)
部分章節
下筆情深
鄒金燦
一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親近與否,取決於其性情,有深情者自能近之,無深情者即使雅好傳統文化,亦難體察箇中幽微之處。
許石林先生深情。在他絕大多數的文章里,尤其是談論古人言行之作,他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進德彰賢。這聽起來很冬烘,似乎頭巾氣十足,然而裡面所涉及的德行,是人之大端,不可糊塗。現在很多人看不得正襟危坐地說道理的文章,時勢如此,許先生在寫作時也不得不進行權變,他將“進德彰賢”這一用心,溶在平易近人的文字里,如鹽入水,人受其味而不覺有東西進入腹中。
讀許石林先生的文章,容易被各種生動的比喻吸引,又或是對其嬉笑怒罵的姿態印象深刻。在我看來,這些東西都不是最應注目之處。“天下文章出桐城”,桐城文章強調義法。所謂“義”,是《周易》說的“言有物”;所謂法,是《周易》說的“言有序”。今人寫東西,於義於法都顯得茫昧。要而言之,許先生書中的各種比喻也好,嬉笑怒罵的姿態也罷,都屬於“言有序”,而他的“進德彰賢”之心,才是言中之物,就像水裡的鹽一樣。古人寫作技巧極高,但並不以“言有序”為能事,他們不去高談什麼寫作技巧,寫作是“辭達而已”。言有物,才是古人最看重的,因為無論你是反對還是贊成作者,都要基於作者的“鹽”來發論。
在古人看來,要窺得作者用意,是講究眼光的一件事。譬如讀《莊子》,入眼就不得不慎重。清末大儒王先謙在《莊子集解》的自序里,這樣評價《莊子》里的各種狂言怪語:“此豈欲後人之行其言者哉,嫉時焉爾。”意思是說,莊子的狂怪,皆因憂世而發,並不希望後人模仿。王先謙可謂是莊子的異代知音。《莊子》成書於衰世,裡面的言論多因憂憤而生,因此往往正言反說。後人讀《莊子》,若不能體察其憂世深情,就容易對那些非賢非聖的言論不得要領,甚至走火入魔。
當然了,許先生的書並非像《莊子》那樣走激詭之路。但他在文章里大談古人的好,篇幅之大,舉目皆是。這似乎給人“食古不化”的印象。其實,許先生自有深情。他服膺顧亭林,亭林先生主張“文須有益於天下”。許先生躬行顧氏之言,將憂世之心,化為崇古之文、笑罵之筆,實際上是希望對今日的人心出一分匡扶之力。
在現實生活中,許先生並不泥古,比如他與一群朋友相聚,當大家都將某人批駁得一無是處時,他會直言不諱地說出那個人的可貴之處;當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讚揚某人時,他則會告訴大家那個人有哪些不足之處。他無意標新立異,只是論人衡事自有進退的標尺,不會被大流裹挾,這個標尺就是人的德行。李白有言:“古人今人若流水。”若將時間線拉長看,今天的人也會成為古人。然而人分今古,美德卻不分今古,前人的嘉言懿行,在任何時候都值得後人心慕手追。這就是先賢崇古的精神所在。
有人說:“古代專制、黑暗,你談這些有什麼意義?”幾乎每一個崇古之人,都會面臨類似的詰難,許先生應該也不例外。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首先,古代是否真如你想像中的那么專制、黑暗,本身就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其次,正如錢穆先生所說,天下“無數百年不敗之政治,亦無數百年不壞之制度”,再好的制度也會有壞的時候,所謂久必生弊,需要不斷損益,不可能一勞永逸。最後,今人所沾沾自喜的現代政治制度,若不是由賢人君子施行,非但弊端叢生,而且更加“吃人”。
先儒論人,以美德與學問為高,目的是培育士君子,而士君子是良政美俗的基石。這是一種極其深邃的眼光,因為它直接指向人本身。許先生顯然領會了古人這一深意,他那些貌似為古代招魂的文字,其實是為玉成與勉勵今日的士君子而發。讀許氏書,如果認為他只是在緬懷古代,顯然將他讀淺了,至於將他的書當談助看,則更是辜負了他的深情。
所謂琴心——減少苟活的理由
春秋,樂官師曠先生是個瞎子。關於他的眼睛是如何瞎的,有三個版本,兩個版本說是他為了專注學音樂自己弄瞎的,弄瞎的手段:一是用艾熏瞎的;二是用針刺瞎的。第三個版本是他天生就是瞎的。我目前傾向相信他的眼睛天生就是瞎的——一個人能將自己的眼睛弄瞎,其心太狠、太毒,用今天的話說是個超級偏執狂,不合常理人情,不可取,這樣的偏執性格,不符合琴道人格。以如此狠的心,內心有那么大的光明,似不可信——師曠是一位內心有大光明的人,您不能說正因為眼睛瞎了才內心光明。
聖賢大都生於衰世、末世——師曠生活在春秋時晉悼公、晉平公時代,作為兩代晉公的宮廷樂官,隨侍晉國最高領導。他最初的職責就相當於一個肉體活人版的MP3,即晉公想聽音樂的話,不像您現在一按按鈕就可以聽了,他得讓樂師現場彈琴,跟今天播放MP3一樣,這種樂師的職務,後來有一個名字:琴待召。
師曠作為一個宮廷樂師,他的地位遠比一般奏樂供人娛樂的樂人高得多。晉公有重大的外事活動,一般都請師曠先生一起出席。即外賓和晉公談論國事,晉公旁邊坐著一個神色端莊和藹的瞎老頭。有一次,衛國靈公一行到晉國訪問,晉國在衛靈公訪問期間,舉行“衛文化周”。衛靈公身邊也帶了一個樂師名叫涓,即師涓先生。衛靈公一行去晉國的途中,路經濮河,在河邊休息時,夜晚月光照著河水,波光粼粼,薄霧籠罩其上,突然,隱隱約約有人唱歌,大家都覺得好聽。可是過後誰也記不住那個歌聲的旋律,只有師涓先生聽一遍就全記住了。在“衛文化周”開幕式上,衛靈公要顯示自己國家的文化軟實力,讓師涓當場彈奏那個從濮河邊聽到的樂聲,他想考驗晉國的人是否知道這個曲子。師涓老師調好琴弦,彈奏起來。在場的人都覺得這個琴音太好聽了,追星族們都準備好了讓師涓老師簽名了。這時候,坐在晉平公旁邊的師曠老師猛地一拍桌子,大聲說:“停下!別彈了!”
在場的兩國國君都很尷尬,晉平公覺得師曠這樣打斷客人彈琴很沒風度,是在忌妒人家吧?師曠徐徐道:“請問你這個曲子是從濮河上聽來的嗎?”師涓一聽,很窘。衛靈公大驚,只得承認。
師曠說:“這就對了——這是商紂王的宮廷樂師師延給紂王演奏的靡靡之音。武王伐紂,師延知道自己助紂為虐,其罪不免,就畏罪跳濮河自殺了。這個曲子盪人心智,如果任其流傳,久之則人心淫逸頹廢,國必亡。所以,它是不祥之樂,亡國之音,不能彈!”
晉平公客氣地打圓場:“現在早已不是商朝了嘛,無論如何也得讓貴賓演奏完整個曲子,曲不可不終嘛。”
師曠語氣溫和但堅決地說:“好的音樂使人振作,靡靡之音使人墮落,防微杜漸以修養身心,為什麼明知不好,還要聽完它呢?”
又有一次,晉平公舉行高級幹部大會,在會上說自己國家的建設成就,這也好,那也好,晉國的媒體上平時只有三種聲音:一是我們是最好的;二是別人都說我們最好;三是別的國家都忌妒我們最好。師曠老師聽晉平公這樣講話,就拿起身邊的一張琴,照著晉平公的方向用力扔了過去,晉平公講話脫稿,正在興頭上,突然感到一陣黑風撲面而來,嚇得哇哇大叫,摔倒在地,琴雖然沒打著他,但是把他驚著了。衛士衝上來就拿住了師曠。晉平公稍微安定了一下神色,厲聲問:“師曠!你要行刺寡人?”師曠兩隻胳膊被衛士抓著,坦然地說:“您是主公?真是您嗎?”晉平公說:“是寡人!你眼睛看不見,耳朵也不好使嗎?連寡人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師曠說:“啊!難道是老臣聽錯了?我剛才明明聽到不是您在講話呀!我聽到商紂王在台上胡吹冒撩大忽悠哩,怎么是您在講話?”
晉平公明白師曠老師的意思了。少頃,即擺擺手,散會了。
古云:“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就是說,不要將琴聲彈奏得太順隨人的欲望以娛樂人,而要用琴聲馴化人的性情,削弱人的一些不正當的天性和欲望,使其達到“正”的效果。當然,這個過程達到的效果微乎其微,不是說聽了一曲,流氓立刻不流氓了,貪官立即不貪了,沒那么神。正因為沒那么神,所以才要強調和堅持。跟減肥似的,你要堅持才有效果。
現在,古琴一下子熱起來了!熱得人都有點不習慣,熱得跟得了流行感冒一樣,熱得讓人想起誰寫的那句話:“花說開就開了,嘩地,像潑婦一樣。”
但是,真正懂得琴理、明曉琴道的人還是很少的。所謂琴道,無非就是“存天理,滅人慾”而已。有關這個,可以看我先前的小作《天理》,此不贅述。
琴和琴人之尊貴,說到底是琴人要心中多存一些“不”,即世俗要你這也能做,那也能做,這也能搞掂,那也能搞掂,而琴教你“不”做這,“不”做那。你不要試圖用琴影響他人,你只需用琴管住自己即可,所謂理一人之性情,以理天下之性情。人都把自己管好,社會才能好。別扯得太遠,別企圖代表別人,比如有個網站吹牛,說中國不怕跟美國打仗,大不了中國豁出去死幾千萬人,而美國最怕死他們自己的人。這就是瞎扯——你只能說你自己願意去死,或者跟你一樣有這種想法的人願意去死,你沒權力安排別人去死。什麼是淫邪?這就是需要禁止的淫邪。
琴不娛樂他人,只調和自己身心。為什麼說琴人難覓知音?就是因為琴只對自己彈,對二三好友彈,不娛樂他人,不取媚他人。
正因為琴者知音難覓,一旦得到知音,簡直可以說是生死知音,簡直就是琴者自己的另一個複製品。這就是為什麼伯牙子期,個讀書人和一個樵夫能因琴而結生死之交。
鄒忌您是知道的,就是那個長得很帥,但是跟城北徐公一比就覺得自己還是不夠帥的齊國人。鄒忌年輕的時候學了一身本事,他想當官有所作為,造福國家,可是,那時候還沒有後來的選材察舉制,更沒有發明科舉制,他如何才能找到一個機會被齊王賞識呢?
機會總是留給有所準備的人。鄒忌會彈琴,齊王也會彈琴。鄒忌自薦說自己的琴彈得好,希望能為齊王彈琴。他以這個名義進入宮廷,成為齊王的一名琴師。有一天,齊王自己正在彈琴,鄒忌大膽,推門就走了進去。齊王見了很不高興,說:寡人沒叫你來呀!
鄒忌說:大王您的琴彈得好!
齊王心情不錯,問:你說說,好在哪兒?
這一問,給了鄒帥哥一個機會,他朗聲回答:您彈琴,大弦渾厚溫和,這是明君氣象;小弦清廉幹練,這是丞相諸臣奉公能幹;您按弦按得果斷而深,放得舒展而輕鬆,這好比國家政令寬嚴得當;音量大小適中,無不正之音的干擾,如天下四時協調,沒有亂象。
齊王聽了,很高興:小鄒啊!沒想到你還如此懂音律!
鄒忌說:我不但懂音律,其實我還懂治理國家哩。
齊王不高興:說你胖你就喘,年輕人,要學會謙虛!
鄒忌說:大王,治理國家就像彈琴一樣嘛。
鄒忌藉助琴理說治國之道,很快就得到了齊王的賞識,三個月後,鄒忌當了齊國的相。後來的事實證明,鄒忌是古時一代良相。鄒忌其實生在一個好時代,他遇到了喜歡琴的齊王。
琴道在於“不”,琴人在於有所不為;有所不為,無過放棄生命。有關琴人故事,近世最動人心魄的是四川的裴鐵俠與沈氏——裴鐵俠與沈氏夫婦家藏唐代一大一小兩張雷威制琴,因號“雙雷”。1949年,社會形勢激變,作為舊式讀書人的裴鐵俠,覺得自己是屬於另一時代的人,不該活在新的時代。加上兒女命運連遭變故,更添憂懼。於是,夫婦摔碎雙雷琴,將琴之金徽收集到一起,留下遺書:“二琴同歸天上,金徽留作葬費”,雙雙自殺身亡。裴鐵俠夫婦讓人想起王國維以身殉那個化他的文化,經此世變,義無再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