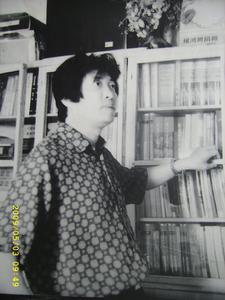基本概述
姓名
文浪,
概況
 1999於沔陽
1999於沔陽1989年在公安派出所辭去公職。1990年6月4日去湖北省作家協會文藝部工作。1991年奔赴深圳,曾在香港明星出版社、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做過編輯、記者。1995,1996為湖北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1990年代登上中國文壇。全國十大實力派作家之一。
詳情
人物簡歷
文浪,男,沔陽土著。原名王華生、王文浪。1989年以“文學浪潮”之意定其筆名。發表小說《黑感覺》、《驪歌》、《舊事新年》之後。於1989年末在彭場水陸派出所辭職。1990年在湖北省作家協會文藝部工作,負責電視專題片與撰寫企業報告文學,後為省文學院創作員。1991年去南方發展,不久返回湖北,專事文學創作。
1999至2009,對文學表示沉默。隱居十年,故名“布衣·默”,。2001年創辦文學雜誌《潮流》,任社長、主編。主張當代性,探索性,藝術性。關照人的新生存困境。反對文學的虛偽和操縱,以及強加的“反藝術”和“反美學“。其文學觀念為:文學是全人類的痛苦。文學的權力是解除人的鎖鏈。2011年8月9日在武漢成立“九號攜帶者”影視原創小組。著有影視劇本《非常暗殺》。
發表論著
1990年代發表《浮生獨白》,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著名評論家王乾在《語言的碎片與狀態的洪流》(《大家》1995年1期)中評論這部小說從“哲學/欲望,東方/西方,古典/現代”這三重困惑中,表現了價值失范之後的文化衝突。其敘述手段是與喬伊斯,與《尤利西斯》,與普魯斯特,與弗洛伊德,與現代派聯繫一起的,並且還體現在建構“元小說”的雙重品格上。敘述時放棄固定價值視角,包括帶有終極關懷意義的人文主義理想(《新狀態的多種可能》,《小說月報》1996年2期)。 其後發表系列中篇小說,如《呼嘯》、《孤獨之狼》、《流水》等,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熱議與廣泛評介。著名評論家陳曉明(中國社科院博導)、張頤武(北京大學博導)、葛紅兵(上海大學博導)、張鈞(東北師大博導)、昌切(武漢大學博導)、樊星(武漢大學博導)等紛紛撰文評論。著名評論家李運摶(華南師大博導)在《中國當代小說五十年》(大學教材)中作為一種文學流派辟有專版評註。
1996年4月,《鐘山》、《大家》、《作家》、《山花》與《人民日報》、《作家報》、《新聞出版報》、《中國青年報》以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召開“聯網四重奏”年會,決定在同一時間內推出一個作家的不同新作。認為這“不僅影響到本世紀文學的興衰,而且還關係到21世紀文學的繁榮”。文浪與全國著名作家韓東、東西、張梅、魯羊、須蘭、邱華棟、李馮、丁天等被推舉參加。全國許多報刊均已報導和轉載。文浪發表於四大名刊的作品是:
《別夢依稀》(《鐘山》1996年6期)
《遙望》(《大家》1996年6期)
《有一種欲望像飛》(《作家》1996年11期)
《殺人的垃圾》(《山花》1996年11期》
著名評論家李俟認為:《有一種欲望像飛》表現的“陷入理性的重壓與陷入欲望的輕盈”,是對“欲望時代的末日審判”。《別夢依稀》是“穿越夢境的叢林,是歷史、現實和未來的自我曲折再現”;《殺人的垃圾》展現了垃圾(物質的,精神的)制度和大眾生活構成的“環境垃圾”;而《遙望》在“描繪被圍困的時代圖景和在這種生存情境中突圍”的悲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1997年以後,發表小說《女人不是樹葉》、《趕驢板車的人》、《一邊說笑話,一邊過日子》、《麻木·偽鈔·花蝴蝶》、《斷蘆葦》等。1995年出版小說集《浮生獨白》(北京)。著有《文浪文集》八部:
《浮生獨白》(中短篇小說集)
《有一種欲望像飛》(中短篇小說集)
《夢幻空花》(長篇小說)
《呼嘯》(中短篇小說集)
《末路繁華》(長篇小說)
《情人’1989》(散文集)
《紙花》(散文集)
《病中雜念》(隨筆集)
文浪部分作品目錄
《孤獨之狼》(中篇小說)
《浮生獨白》(中篇小說)
《流水》(中篇小說)
《冷月》(短篇小說)
《別夢依稀》(中篇小說)
《呼嘯》(中篇小說)
《驪歌》(短篇小說)
《黑感覺》(短篇小說)
《名落孫山》(中篇小說)
《喪家犬》(短篇小說)
《舊事新年》(短篇小說)
《遙望》(中篇小說)
《老屋,樹,稻穗和草料》(中篇小說)
《麻木·偽鈔·花蝴蝶》(短篇小說)
《殺人的垃圾》(短篇小說)
《有一種欲望像飛》(短篇小說)
《麻臉》(短篇小說)
《女人不是樹葉》(短篇小說)
《斷蘆葦》(中篇小說)
《黃昏前的狂潮》(短篇小說)
《趕驢板車的人》(短篇小說)
《記敘那件並沒有撒謊的事情》(中篇小說)
《黑雨傘》(短篇小說)
《病中吟》(中篇小說)
《夢幻空花》(長篇小說)
《末路繁華》(長篇小說)
《狂草大師的虛幻實境》(短篇小說)
《惡樹林》(短篇小說)
《非常暗殺》(30集電視劇劇本)
相關信息
訪談錄
采 訪 人:張鈞 (著名評論家、東北師範大學教授、文學博士)
被採訪人:文浪 (湖北省作家協會文學院專業作家)
張鈞:這次,我從東北來,採訪全國影響很大的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首先,請回顧一下你的創作。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寫小說的?
文浪:1982年寫第一篇小說《黑感覺》,《青年作家》來信要我修改。一個月以後,我又接到信函說,沒過終審,可投他刊。可我沒有立即寄出,而是關在抽屜里擱了九年才投《花溪》發表。
張鈞:你認為自己90年代之前與90年代之後的寫作有什麼區別?
文浪:90年代以前的作品比較故事化,這是批評家昌切的說法。90年代以後,除了幾篇“老實”外,其餘的都很“浪”。“老實”就是對人物、事件、典型形象的簡單鋪陳。情節集中,線索清晰,講述了一個鄉土故事。“不老實”就是打破了這些東西,敘述了一個生命的理念,或者一個新的生存困境。情節和話語的表述方式呈碎片狀。批評家陳曉明評論我的小說是以現代的或後現代的思緒來清理鄉土中國的記憶。
張鈞:小說寫到現在,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文浪:應該說寫作是愉悅之事,是剝離自己的魂靈,它可能比吸毒還要來勁。當然,我是指提升心靈。在思想繁複的年代裡,能夠描述困難的生存圖景,能夠感知或領悟生命歷史的能力,那還不來勁?因此,有的作家說,寫作就是手淫。另外,小說寫到此,我越來越對它產生懷疑,這是認識論吧。我們究竟怎樣才能完成對人的真正解析,以及對人和自然的解析;怎么寫,才叫真正的真實。
張鈞:你生於50年代末,但是批評界習慣上卻把你看成新生代作家,可就我的感覺, 你的寫作有新生代作家們所共有的一些東西,比如關於生命的主題、關於欲望的主題、敘述的碎片化、結構的迷亂特徵、對於經驗世界的超驗式變形轉換等等吧——但我認為這僅僅是一方面;另方面,我覺得你還有許多新生代作家所沒有的東西,就這個向題,你能夠自我解析一下嗎?
文浪:首先說新生代或晚生代,我是把它作為一個文學派別和一種新的思潮來認定的,也就是說不是完全依照作家的年齡來看的。新生代是一個流派,年齡只是一種參照。我不強調自己屬於什麼,這是批評界的事,我注意的是“傾聽”或“證實”。就新生代而言,有的評論家認為這一流派搗毀意識形態話活、啟蒙話語和詩性話語,“反諷”,不關心語言;另外,在泛“性”主義的背後,通過”性”這個唯一的引號進入世俗樂園。我想我不屬於這類,尤其是後面說的,世俗的,平庸的,猥瑣的。
張鈞:我覺得你的創作最大的特點是本色化和非本色化。這表面看起來很矛盾,實際上一點也不矛盾。如你在《孤獨之狼》、《流水》、《呼嘯》等作品裡表現的就是一種本色化的寫作傾向;這類作品,尤其《流水》中的敘述,是原生態的、樸素自然而有點悲涼的純真;而你在《浮生獨白》、《別夢依稀》等作品裡,則表現出一些本色化的特點,它們的敘述我以為是帶有某種誇飾色彩的,膨脹的,或者說先驗的,迷亂的。也許,這也是一種本色?
文浪;我想,這都屬於我,不過,你作了這樣的解析。本色化與非本色化的作品都是對沉寂深處的一種檢索。當然,本色化強調了荒野的原生態,非本色化的則注重了心靈的“真信切願”。
張鈞:現在,讓我們進入你的作品。我讀到你的第一篇作品,是發表在作家上的《有一種欲望像飛》。當時我的第一感覺就是一一恕我直言:有點不太舒服。帶著這種疑惑,我又讀了李俊先生髮表在《作家報》上的那篇名為《無望的突圍》的評論,覺得他說得有一定的道理。他說,小說表現了那種脫離理性的沉重而完全沉浸於欲望自我的輕盈,是一種“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人類在恢復這種自我的同時,也瀕臨毀滅的邊緣。於是,我恍然大悟。的確是那么回事,小說是寫出了這個東西,這從理論上講完全可以講得通。但是,我還是覺得有某種東西在作梗,那就是一種敘述上的感覺。我認為,小說無論你要講什麼,講得多么深刻,多么具有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悖論潛藏於其中,但感覺你的這篇小說,有一種理念的硬性擴張的味道,我想聽聽你自己對這篇小說的感覺。
文浪:《有一種欲望像飛》,主要是“飛”的過程,飛到哪裡去,飛到自己的內心(欲望)。通過這個過程來展示譚秋生等人向外膨脹的欲望。這種“飛”就是“擺脫了理性之後的那種心靈的飛翔”。我不知道你說的那種感覺,也許是技術問題吧。其實,整篇只是寫了兩個情節:一是譚秋生如何去武漢給香港過來的裸女群拍照,以品嘗女人的美麗;二是譚秋生失望後(欲望再次受到壓抑),回家在澡堂看到他的女友古小英的美麗嗣體時,不慎跌在水籠頭上。這兩件事都是生活的真突(素材在沔陽獲得的)。我只是想透過他的死,來表明非理性的東西最終受到理性的制裁,而且是“死”的制裁,以此來恢復理性的權力。按弗洛伊德的觀點,這種“自我”欲望是受了壓抑之後被扭曲的自我,既然非理性驅使他恢復了這個自我,那么,理性的東西就會對這種叛離的思想以壓制,並使之繼續扭曲,甚至死亡。不知你有沒有看過我寫的《殺人的垃圾》。主人翁王本橋的死表明他是在迎合理性時的身心輕安而死的。如果他認為現實是一種濁流的話,這種濁流就是環境。人要與環境達到和諧,如果主動進入環境,就會相安無事。王本橋的內心是有矛盾的,他在這種矛盾中而死。而《有一種欲望像飛》是樂極生悲。樂是釋放或者放逐的效果,悲是必然的最終的結果。
張鈞:關於《浮生獨白》,我也有類似的感覺。王乾先生髮在《大家》的上那篇評論,給子這篇小說很高的評價。他從語言景觀、文化關懷、敘述狀態、結構特徵等方面對小說進行了全方位的解讀,挺深刻的。不過,我覺得他在文章的最後,還是頗有微言的。他說:“在結束這篇評論之前,我想對文浪說的是艾略特的一句頗為悖逆的格言:詩不是表現感情,而是逃避感情;詩不是表現才華,而是逃避才華。小說呢,不是要表現語言,而是要逃避語言。 不是要表現狀態,而是要逃避狀態。這樣才會有新的語言、新的狀態。”我以為,王乾在這裡談得非常到位。的確,《浮生獨白》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作者的語言不透明,流動得過於緩慢,讓人感到壓抑。所以,我認為這篇小說從根本的意義上講,是反閱讀的。讀者閱讀的時候,總是處於一種無法進入的狀態一一至少,我的感受是這樣。
文浪:艾略特的話是一種哲學,物極必反。詩,如果把感情完全逃避掉了,那也不是詩了,那可能是口號。王乾先生的話準確而深刻。《大家》主編李巍先生也說過這類的話。反閱讀,不反解讀。我想這篇小說之所以難以閱讀,是“我”在敘述“我弟”,又以“我弟”來透視“我”的精神困境,是一種“跳來跳去”的敘述,轉換得太快太頻,因此難以卒讀。如果把夾雜的那些話語挑出來刪去,再補充一致性的敘述話語,那就不難讀了。但那樣徽,也許使小說蒼白無色。
張鈞:小說的反閱讀性還表現在作家對於敘述狀態的過於迷戀,作者,無疑是敘述的主宰,小說中所有人物的現實行動和內心活動,全部屈從於作家有著強烈主宰意識的敘述之流。從這點上講,小說與其說是小說人物的內心獨白還不如說是作家本人的內心獨白。從形而上到形而下,從理性到非理性,從內心活動到外部行動,從游移不定的夢幻式欲望的膨脹到無序的混沌世界,進行了一次高密度的話語轟炸,使得各種話語在相互摩擦中燃燒,在相互牴牾中抵消。在這個意義上講,小說的作者好像在這篇作品裡主要是以一種繁複生長的狀態來敘述來體驗,而所要表達的某種帶有隱喻色彩昀意味,則是次要的了,也就是說,敘述的話浯體驗上升到了本體論的意義上了。
文浪:就我的本意而言,我是想通過草、橋、岸的紛亂情愛所呈現的哲學世界觀,來呼籲道德重建。要說這就是隱嗡色彩的意味,好像那全部的獨自都是聽命於這個意味的。但實際情形並非合乎我的願望。真正說來,《浮生獨白》恐怕就是一個漂泊紅塵的人對身邊世界的獨特感受。你想想,一個時代,不可能所有的人說出的話全部相同,也就是說,所有的人對現實對人生的感悟都是不同的,甚至相去千里。而每個人都是一個世界,都反映的是現實問題。《浮生獨白》的全部人物的現實行動和內心都是被敘述人所控制的,形成了獨一無二的個人話語。
張鈞:不過,即使這樣,某種終極性的意味,還是從這種碎片化的敘述洪流中浮現了出來,比如理性與欲望的衝突、主人公岸的意識分裂和潛意識的無序混亂、鋪天蓋地而來的消費文化對於人類精神空間的擠壓等等。
文浪:我以為你所說的這些都是現實不能否認的,也是作品不能迴避的。我是照實說了罷了。
張鈞:在敘述話語的極端化膨脹方面,我認為《別夢依稀》比《浮生獨白》做得更甚,後者與前者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別夢依稀》給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語言的末路狂歡。這種狂歡的語言方式在當下的一批作家作品中也有程度不等的表現,比如莫言,他的頗有爭議的《豐乳肥臀》中的泥沙俱下的語言方式就是這樣。但是,你似乎比他走得更遠,似乎把這種東西推向了極致,它們就像一浪高過一浪的搖滾樂一樣,轟轟隆隆地滾過文本。這種癲狂似的語言,是為了更好地表達世紀末人類精神的癲狂狀態?
文浪: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變遷導致的生存和情感,都是通過主觀當下狀態來體現的,它首先向我體現的則是精神的癲狂。我甚至主觀的認為,在中國,一種舊的理論模式導引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為,在過去的年月里已經製造出許多的垃圾,精神的,物質的,然而,新的理論又製造了新的垃圾。我們希望社會有秩序地和諧地發展,而有秩序的事物總是不斷地遭受破壞,人們的內宇宙總是呈現著被破壞的廢墟,人們的精神總是焦躁不安。所以,《別夢依稀》呈現了這種狀態?另外,一個作家努力追尋的就是弘揚個性,作品應該打破主題表現的寓言模式,應該具有一種無限創新的意向和超越實驗文學的探索神話,融合對現實狀態的感情,對自我進行顛覆和消解。如果你承認新世紀交替之時的人類精神處於癲狂和荒亂的話,那么這種敘述語境就無可非議。正是這樣,《別夢依稀》試圖擺脫傳統文化語境的規範和束縛,用現代化心理流程取而代之。再說,這種書寫方式也是現變生活所賜予的,當下人接受信息的頻率,競爭的殘酷性,以及勞頓疲憊的懶散和想入非非,構成了《別夢依稀》錯亂的語境。
張鈞:除了狂歡的語言之流之外,小說的意象也像一場大雪一樣鋪天蓋地,你可以從任何一個地方開始閱讀,也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停下,它給你的都是同樣的怪誕,比如一個人瞬間就變成了一隻蒼蠅、汽車在空中飛翔、成群的動物與汽車賽跑、大學校園的學術活動如兒戲,審判可以隨心所欲、梧桐樹葉如蝗蟲般墜落遮天蔽日、尼姑們的武器則是裸露的雙乳,等等,種種怪異的意象符號在文章中恣肆亂竄,像夢魘一樣搞得世界如同末日。你似乎也在刨造一種世界未日的景象?
文浪:人類的進程已到20世紀末,諾查丹瑪斯預言1999年8月18日,太陽系排列成十字架,人類遭受滅頂之災。這預言給西方人帶來極大恐懼,而中國人多少沒有去過問這些, 只因經濟潮流和洪水猛獸問題而困惑,迷亂,彷徨,構成了當下的生存狀態。這是我寫作《別夢依稀》時的思考。同時,我回顧了1994年世界上發生的許多大事,比如蘇聯解體,中東和談,南非總統曼德拉獲勝,索馬里的難民,美國解決海地的問題,古巴的移民,毒品問題等,整個人類出現秩序混亂。加之,九十年代是一個各種主義風起雲湧的文化時代,各種思潮影響著文學的書寫方式,傳統的、古典的受到懷疑和挑戰,文學傳統和價值觀念應該解構或者被顛覆,應從新的角度去審視現有秩序。這種構想極大地左右了《別夢依稀》的命運。費爾巴哈說:我的感覺是主觀的,但它的基礎和成因是客觀的。
張鈞:語吾的任意跳躍、飛翔,給人一種危險感。這種語言方式表現的也是全人類思維的世紀末情態?
文浪:《別夢依稀》的語言不是那種傳統程式的,或說巴爾扎克式的,或者說原先書寫的那種集體習慣,它是由許多複雜的信息綜合而成,它是具有心理流程的東西。在這種書寫形式下,這種語言一直鼓勵和刺激我,誘惑我,但這決不是語言的遊戲。它似乎是那些人物失去了文化的,歷史的和心理的支撐,浮動出一種漂移的失去了信仰之後的恍惚狀態。這也是生活所形成的新的語言策略。
張鈞:所有這一切,都給人一種強烈的世界末日的預言色彩。所以,現在的存在似乎都是虛無的,而同時似乎也有某種渴求。馬飛、楊籬、康林等人雖然也在不安的煩躁之中,但也在渴求著某種東西。這也許就是這個世界的希望所在?所以,在小說結尾的地方,作者要露出一線曙光:“大約過了好多年,東方才出現曙光,火紅的太陽又一次從魔山的出頭冉冉升起。”
文浪;宇宙有沒有末日,我說不清楚,但是我的想像絕不是宇宙突然有一天全部黑暗和消失。我只是通過這篇小說,強調人的痛苦和掙扎。人類面臨著知識大爆炸和信息大爆炸的迷局,信息高速公路縮短了人類交流的距離,人們對原有的哲學和人類學又一次提出了質疑。有人認為宇宙與人類都有一個平行世界,也有人提出宇宙四季學,物質與反物質等等。人對自身的困惑和對人體生命的研究越來越趨於神秘化。對外太空是否存在著與人類相似的智慧生物,對神秘的宇宙飛行物,人類困惑不解。人類同時為自己製造出了許多麻煩,生與死,靈魂自救,精神家園等。但是人是有希望的,世界問題說到底是人的問題,既是人的問題,最終由人來解決。因此,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張鈞:魔山,可以說是這個世界的詩意象徵。它既黑暗又混亂,是當下文化垃圾的堆積場,同時也騷動著某種叛逆的情緒和思想,成為叛逆者們清理垃圾的戰場。當然,清理垃圾的人們如馬飛、康林等人現在還是被成群群的蒼蠅圍攻,尤其有權有勢的綠頭蠅常校長之流的攻擊。所以,魔山也可以說是人類困境的一個象徵。
文浪:魔山,是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也是人的精神中心。我時常有這種觀察和感覺,似乎每個人都在困境之中。我曾在武漢大學大大小小的山頭遊走之時,就看到那些教授和莘莘學子的心裡都像亂了似的。
張鉤:從修辭學的意義上講,《別夢依稀》是有某種獨特的意味,比如我前面已經提到了迷亂式的語言方式,另外還有旋轉式或者叫做魔方式結構、意象組合的隨意性、想像的超現實性,等等。
文浪:我以為生活是一個“圓”。幾乎每個事件都是有始有終,有頭有尾的。但是在這“始”和“終”裡面和“頭”與“尾”之間夾著其它與同一事件不相干的東西,它們混存其間,構成了敘事上(包括語言)的迷亂。另外,這一事件的“始終”與“頭尾”連線成一個“圓”後,在現實的旋轉中就產生了模糊的,跳躍的情形。這裡有“始”對“終”的追尋,有“尾”對“頭”的應答,構成了魔方式、立體式的結構。想像的,超現實的,絕不離開現實。意象的隨意組台,也絕不是斷線的風箏。
張鈞:在時空問題上,《別夢依稀》是逾時空的。這一點魯西西在她的評論文章《審判與邈離》中講得很透了。我在這裡要說的是,這種逾時空的時空處理方式,它所帶來的結果是讓人感到迷亂,瘋狂的人類無處可逃,特讓人絕望。讀你這篇小說給人的是某種恐懼感。
文浪:假如一個人含淚看世界,其情形就會產生重疊的影像。儘管這影像給事物以放大或誇張,但這仍不失為真實。《別夢依稀》原打算取名為《未來啟示錄》或《對未來一些年的基本預測》。人類的困境是主要問題,而掙扎與擺脫只是一種活動方式,光明是這種方式的一種結果。人,一出生就面臨困境。人是被現實壓抑的,虛假的現實不過是一種存在著的表象,因扭曲人而荒誕、怪異,甚至恐懼。
張鉤:就我個人而言,我似乎更為看重你的《流水》、《孤獨之狼》、《呼嘯》和後來的《遙望》這一類小說。比如《流水》,正像李運摶《顯示著一份獨異的敘述》一文中所言的那祥,“將現實與歷史糅合,以及故事性的明顯加強,使我們覺得這其實是篇有些怪異色彩的寫實主義小說。”因為故事是在原生態的基礎上展開的想像,所以更易被人接受,同時所要表達的某種意味也表達出來了,所以我認為《流水》雖然只敘述了一個小鎮上的一個茶館,但它的意境不見得不如《別夢依稀》闊大。
文浪:一種是願生態的真實,並且直接描述了那種真實,而且大多教人物都在我面前活靈活現,甚至有時在夢中和他們相會;一種是想像的真實,這兩者都來源於客觀實際。《流水》是對少年人生情感的搜尋。我說過,文學是一種痛苦,回顧歷史是一種隱痛,當我處理歷史生活時,這種隱痛叫我陣陣呻吟。
張鈞:你在《流水》中有兩句話:苦難是人生的老師,人生實際上是一場錘鍊。這兩句話與你的文學觀念:文學是全人類的痛苦一樣有某種相通之處。請你談談為什麼會形成這樣一種文學觀念。
文浪:這都來自我個人的生活閱歷和深切體驗。人生實際上是一場錘鍊,這實際上說明一個人並無先天的什麼,而是身處具體環境,靠後天的鍛鍊來完成自身的。同時我也認為苦難出真知。幼時在黃家口看別人打鐵,一塊在爐中燃燒的紅鐵(材料),師傅一錘,徒弟一錘,町叮噹當,經過反覆敲打也就是錘鍊,後來那塊鐵漸漸打成鐮刀(成品),還放到水裡做冷處理。文學是全人類的痛苦.這句話是我的文學觀念。這也是我對文學價值的基本認識。迄今為止,世界上沒有哪一部名垂千古的史詩不是反映人類痛苦的。荷馬、莎士比亞也好,《紅樓夢》、《狂人日記》也罷,一個作家不能放棄史學的嚴肅性和殘酷性,不能用極其無聊的寫作或者粉飾的東西迎合看客的心理。小說不是“政策形勢十生活事件”的模式,最起碼也不應是“小說形式的報告文學”,它應該是一種閃爍華光的痛苦。
張鉤:《流水》既是對於記憶中的故鄉的風俗畫的描繪,又是一種對於已逝的少年時代的追憶。這種描述和追憶是悲涼落寞的,情調是哀傷的,讓人心酸的。請問,你之所以這么寫除了因為你的文學觀念在起作用外,是否同你的某些早年體驗有關?那個少年因家貧讀不起書不得不到茶館裡當個跑堂的生存境遇,讓人心碎。
文浪:《流水》是純童年的東西。可以說。那個讀書的少年就是我,茶館是街坊上一個說書或唱皮影戲的場所。我現在回憶起來,覺得童年是我唯一的珍貴的可愛的人生。我的童年是在洪潮一個名曰黃家口的鄉下小鎮度過的,以後我工作和生活過的其他地方都超過不了這塊荒野的充滿世俗的原始之地。我覺得這地方很純,很靜。沒有欺詐,沒有巧取豪奪,沒有當下人的那種狡詐。我只喜歡少年時代,也就是12歲以前的生活圖景。之後,我多次到過上海、北京,深圳甚至香港,但這些都市給了我什麼情懷呢,總超越不了我腦海里的少年小鎮。
張鈞:曹麼姑的性無能和變態心理,寫得挺到位,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過嗎?
文浪:遇到過。曹麼姑的成形不是一個人,而是幾個人的揉合。在我的少年時代,生活的小集鎮,下放的農村都有。鑒於那些一說出來就讓人產生聯繫的緣故,因此迴避提及這些人物的真實姓名。
張鈞:孤獨,似乎是你小說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如前所談到的《別夢依稀》中有著某種深刻的孤獨情結之外,還有《孤獨之狼》。我認為,《孤獨之狼》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比較集中地表現了一種孤獨的人生情結。小說具體刻畫了鄉村中學教師呂少農這個人物。他有正義感、憤世嫉俗,對弱者有同情心,對苦難有著深刻的理解。這樣,他在這個污濁的世界上就必然地要孤立無援。他給人的感覺是悲愴的、孤獨的、絕望的。由於小說在敘述上的冷寂和透明,這樣呂少農這匹孤獨之狼在天地間悲嘯的形象就變得空濛和孤單。
文浪:人生告訴我,孤獨是最高境界。一個人的孤獨之心,你無法進入。孤獨也是一面鏡子。一次我在沙湖(沔陽的一個小鎮)看電影,外國的,名字已忘記。有個船員丟失了孩子, 要大家幫他出海尋找。海上驚濤駭浪,人們面有難色,一來是大風大浪,二來是人們覺得他的孩子很有可能被大海吞沒。這個人看著大家不願出海,就哭喪著臉說:你們不幫我,可你們還說是我的朋友吶!這時他才意識到原來朋友竟是這樣的,原來,人,是孤獨的,周圍是沒有人的。當然,精神孤獨,則更加可怕。呂少農身邊是學生和老師,但和他相去甚遠。至於你的那種空濛之感,這來自於品得很深的緣故。有一次黃昏散步,我的女友突然問我,天上有沒有鳥飛過?有。可是抬頭一看,沒有。但她說,有。她告訴我說,是影子。這個影子是什麼呢,是人的心靈。當時,我的心像被她洗了一遍。天上有鳥,飛過了。飛出了太陽系,又飛出了銀河系,而且是無聲無響的,這個東西就是孤獨。總統是世上最孤獨的人,然而更是一些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家。我讀過《甘地自傳》、《福澤渝吉自傳》等,這些人都是孤獨的,連這些書也是孤獨的。《孤獨之狼》是我把鄉村知識分子的生活拿出來給人們看。我認為他們和我的情感往事像一幅風俗畫。評論家樊星認為,呂少農孤獨得成了一個與塵囂對峙的隱士,或說高人野士。
張鈞:關於《呼嘯》,我覺得不像小說,更像一篇長長的抒請散文。小說基本上沒什麼故事情節,有的只是對於祖母的懷念和展示祖母的生活,以及祖母與浩浩蕩蕩的蘆葦林的關係,以及祖母晚年孤獨寂寞的生活。在語言上,也有成塊成塊的飄動感。
文浪:你說的飄動感最合我的心境。回憶狀態下,我眼前的是夕陽滾動著的蘆葦,那蘆葦的畫圖一片渾漠。渾漠是當時的境況,也是記憶的境況。你想一想,我的祖母回娘家去,她是南京人,我祖父就用一隻小船把祖母盪到南京去,在長江邊上要走三個多月。我曾經把這個事情說成是人類最偉大的愛情,它震撼著我的心靈。因此,語言呈現了這種古典浪漫的情調。我覺得《呼嘯》是世紀末的一種懷舊激流。由於語言的漂移(這是想像所造成的)而放射火花。在電腦前口述《呼嘯》時,我的沉靜完全顯示了蒼白冬日的那份淡漠,那副搖搖晃晃的已走了多少年之後的影子,忽然又掛在呼嘯的蘆葦上滾動。我想那是一種年月與歷史的影子,掀動我的情懷。
張均:《遙望》與《流水》和《孤獨之狼》都屬於那種寫實主義的敘述,敘述的透明度比較好。但這只是它們的共同點。而我在這時,要談的是不同的地方。我覺得,在經過《浮生獨白》和《別夢依稀》的迷亂敘述之後,《遙望》的敘述回歸到了《流水》等作品裡的迷亂敘述之流。而這“流”,卻比原來的深了,是一種深層的涌動。用你在小說開篇時的一句話來講,就是:靜水深流。水在深處流,暗暗地涌動著一種力量。然後爆發,然後瘋狂。
文浪:《遙望》表述“我”在精神、環境、經濟等諸多人生問題中陷入不能自救的困境,只好憑藉一個日本女人的情感作為支撐。這是一種心靈自救。1988年我辭去公職,想到中國南部去,可是那年秋季我卻到了上海,結識了日本京都的一名女子。我和她有幾年的通信,她曾來信叫我去日本留學。對於這種友情,我一直要寫一篇小說,原來的題目是《遠方沒有來信》,但始終寫不好。一直擱了好幾午,才寫成。可在“謀篇”時,不知怎么把這個人與日本兵庫縣地震聯繫一起,把她寫“死”了。我怕她怪我,《遙望》發表後,我一直不敢寄到日本去。
張鈞:傷感孤獨,這是我對《遙望》的又一感覺。那個叫做蓬生的敘述主人公在情感上是傷感的,尤其他同那名叫做松夏夕子的異國女子邂逅又分離之後,在人生和愛情上幾經波折,傷感的情緒就越發地濃,最後演變成了不可救的瘋狂。小說的敘述是痛苦而又浪漫的,浪漫而孤獨,孤獨而傷感。
文浪:這與實際生活有點相仿,傷感和惋惜難以避免。我甚至以為,傷感和孤獨是我從娘肚子裡帶來的。
張鈞:小說的敘述模式我認為是比較陳舊的:英雄/美女式。這種敘述模式再加上主人公蓬生面對的難題和困境是當下現實意義上的,或者說得具體一點是與當下的文藝團體的改革相聯繫的,這樣的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蔣子龍式的改革文學。如果換一種敘述模式,是否能好一點?
文浪:剛才我說過,我本想將《遙望》寫成純情似的東西的,回憶那時的生活,便拿來作了背景材料。事後,也有不少讀者感嘆道:這么好的情感和改革聯繫在一起多么不屑。甚至有很多讀者指責我把松夏夕子寫死了,要我寫《遙望》續篇,將松夏夕子寫活。從我的本意來說,這與改革無關,甚至我後悔不該把這么美好的情愛素材放在這個背景中來,哎呀,也是苦於某種因素噢。
張鈞:主人公蓬生面對異國女子松夏夕子既自卑又自傲的心理活動比較真實,這種心理情結在你的別的小說里好像有,比如《浮生獨白》和《別夢依稀》中我感覺就有。請問,你的這種敘述情結的產生是否與你在現實生活中的某種內心體驗有關?這種情結是很深刻的,它反映了某種人類生存的情感困境。
文浪:任何一部作品都與我的內心有關。甚至可以這樣說,這些作品都是寫的我。假若你要具體涉及人物,我就會推掉這種說法。
張鈞:能否談談你所受到的影響,我指的是文學上的影響,中國的和外國的。
文浪:中國的,應該說最早影響我,時問又最長的是魯迅。我從高中時就喜歡他。我想我的一生也是這樣。毛澤東說,讀點魯迅,毛澤東沒有說讀其他人。我很信奉毛澤東的這種經典評論。讀點魯迅和讀點孔子,和讀點《論語》是一同事。半部《論語》可治天下。這和讀聖經,佛經,誦經,日課如出一轍。外國的,我尤喜福樓拜、契科夫,莫泊桑。歐亨利讀過一些,後來就不讀了。至80年代初期,那是讀書最多最勤的時候。讀了大部分世界名著,比如,19世紀200種,20世紀有60種。我這指的是純文學方面的。可以說,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魯迅的《狂人日記》是我最叫好的巔峰之作。80年代中期主要看看普魯斯特,馬爾克斯、加謬等20世紀的。90年代都是讀西方政治、倫理,科技之類,倘若說有影響的話,都有影響,要說沒有影響的話,都沒影響。因為我不知道究竟是誰影響了我。
張鈞:你認為,你是否已經寫出了自己理想中的小說?你今後有何打算?
文浪:我想沒有一個作家認為自己以前的作品是不理想的廢品,至少不是完全這樣認為。人群中,我常常聽到有些喜歡我的一些小說,說我的另一些寫得不好,然而那些不好的東西卻被另一些人所鼓掌。世上本來就是一百人讀一百本書,也得出一百種見解。因此,我並不覺得寫出這些小說而後悔,因為我得到了一種實際的訓練。我將要寫出的一部100萬字的大書,寫出我理解世界的能力與經驗。假如我讀別人的書,幾乎沒有自己看不懂的。關鍵是如何解讀別人的心靈,比如尤利西斯,西方神學,佛學等。廟裡五百羅漢,我看他們的面孔,知道它們在想什麼,並可以嘗試揣摩他們曾經的人生和善惡。至於今後的長遠打算,一時還難以說定,我不能安排人生,人生是接受一種悄然的支配。
張鈞:好,今天就談到這裡。謝謝!(握手)
文浪:非常感謝你對我的作品的解讀和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