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內 容 簡 介建築和城市歷史遺產的概念在西方是如何產生、發展和完善的?它與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的關係如何,又怎樣因工業革命浪潮的衝擊而被正式認可?弗朗索瓦絲·蕭伊教授在本書中介紹了拉斯金、維奧萊\|勒\|杜克、西特、博托及里格爾等建築思想家在歷史遺產保護方面的重要理論建樹,為我們勾勒出西方思想史的一個重要層面的一幅歷史畫卷。在書中作者還提出了自己對世界範圍的“遺產崇拜”現象的解釋。本書可以作為西方藝術史及建築遺產保護方面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參考書。弗朗索瓦絲·蕭伊女士是建築與城市的形式和理論的歷史學家,巴黎第八大學教授。本書獲1995年法國國家遺產大獎。
圖書前言
為了紀念安德烈·沙泰爾 (André Chastel)我願在此向那些激勵我寫作此書的,其工作服務於遺產的人表示敬意,特別是雅克·烏萊(Jacques Houlet)、雷蒙·勒邁爾(Raymond Lemaire) 和米歇爾·帕朗(Michel Parent)。
另外要感謝為我友情閱讀手稿的亞歷山大· 梅利西諾(Alexandre Melissinos)、米歇爾· 勒比-薩爾達(Michel Rebut-Sarda)和讓-瑪麗·樊尚(Jean-Marie Vincent)。
告.讀.者
自《建築遺產的寓意》第一版1992年面世以來,已經七年。在這七年裡,建築及城市遺產的重要性不斷地在增長並被加強。
且這七年,不僅完全證實了我的見解,也深化了我在怎樣使遺產實踐更系統地面對城市化進程及城市問題方面的思考,而在我們這個正處在全球化道路上的社會裡,這些問題是不可分割的。
作為這一思考的結果,我又寫了一系列文章,拓寬了《建築遺產的寓意》開啟的人類學視野,值此書第三次印刷之際,我從它們中萃取出一個新的結論,並保留了這一章原來的標題“建造的能力”。
弗朗索瓦絲·蕭伊(Fran.oise Choay)
紀念物與歷史性紀念物
遺產*,這個文雅而非常古老的字眼,追本溯源,與一個根植於時間和空間之中的穩定社會所具有的家庭的、經濟的和法律的結構相聯繫。加上使它成為“遊牧式1”概念的各種定語(遺傳的、自然的、歷史的……)的修飾後,它如今已成為一個反響廣泛的新詞。
歷史遺產,這一表述指預留給尺度已擴展到全球的人類群體的愉悅的一筆財富,由不斷積累的多種多樣的物品構成:純藝術及工藝美術的作品和傑作,人類知識及技能的所有成果及產品,這些物品被共同的對歷史的從屬匯集起來。在我們這個變遷中的,從未停止對其現實的普遍存在和趨勢進行轉換的社會,“歷史遺產”成為大眾傳媒的關鍵字之一。它反過來有賴於一種制度及一種道德觀念。
辭彙經歷的詞意變換意味著事物的深度。歷史遺產及與其相聯繫的行為具有多層次的意義,這些意義的含混性及矛盾性連線並區分開了兩個世界及兩種世界圖景。
我們不應滿足於當今社會對歷史遺產的尊崇。這種現象還呼喚一種問題意識,因為它是社會狀況及所含問題的揭示者,雖被忽略然而卻能給人啟示。我的論述正是從這一角度開始的。
在歷史遺產浩瀚多樣的寶藏中,我選擇了與所有人及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最直接相關的範疇作為典型:建築遺產。我們以前稱之為歷史性紀念建築,但這兩種表述不再是同義詞。自20世紀60年代始,歷史性紀念建築,只不過是歸入的新物品的種類不斷增加,其所處時間和地理範圍不斷擴大的繼承物的一部分。
在1837年法國創立第一個歷史性紀念物委員會(Commission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之時,歷史性紀念建築的三個重要範疇是古代文化的遺存、中世紀的宗教建築及一些城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翌日,造冊登記的物品種類增加了十倍,然而它們的性質並沒有多大改變,仍主要與學術性建築的歷史及考古有關。此後,所有建造藝術的形式,無論是學術的還是民間的,城市的還是鄉村的,所有建築物的範疇,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有的,奢華的還是實用的,都被登記在新的名目之下:次要建築,來自義大利,指非紀念性的私有建築,通常在沒有建築師幫助的情況下建成;鄉土建築,來自英國,以區分出那些有顯著地區特徵的建築物;工廠、火車站、高爐煉鐵廠等工業建築,首先由英國人提出2。最後,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立的世界遺產“名錄”所顯示的,遺產的領域不再僅限於單個建築,還包括建築群,以及城市肌理:城市街區及鄰里、村莊、整個城市,甚至城市群3。
直到20世紀60年代,,幾乎沒有限制,只與考古研究的發現重合。就下限而言,則未逾越19世紀下半葉的界限。如今,比利時人奧爾塔
(Horta)的代表作人民宮(1896)在1968年的被毀感到遺憾,而法國人則是對巴爾塔(Baltard)的中央市場(Les Halles)1970年在來自整個法國及全世界的強烈抗議之下仍然被毀而難以釋懷。這些抗議的聲音儘管寶貴,與普遍的冷漠相比卻是一個微弱的少數。對於行政部門及大部分公眾而言,奉拿破崙三世(NapoléonⅢ)及奧斯曼(Haussmann)之命而建的這些輕巧的亭子,只不過具有瑣屑的功能,要列入紀念性建築還不夠格。另外,它們屬於一個以鑑賞力不佳著稱的時代。如今,奧斯曼的巴黎的一部分已被列級,並且,原則上今後是不可改變的。同樣,世紀之交的“現代風格”建築的簡潔特徵很快被同化為一種時髦並貶值。在法國吉馬爾(Guimard)、拉維羅特(Lavirote)及南西(Nancy)學派是這一風格的代表。
20世紀人們打開了遺產保護領域的大門,如今毫無疑問會將萊特(F.L.Wright) 的代表作東京帝國飯店(1915)列級並保護,它抵抗住了自然地震,卻於1968年被拆毀。佩雷(Perret) 的Esder工作室(1919),被拆毀於1968年;孟德爾頌在斯圖加特的Schocken大型商場(1924),被拆毀於1955年;路易斯·康(Louis Kahn)在費城的門診所(1954),被拆毀於1973年。在法國,最近一個負責“20世紀遺產”的委員會,尋求制定一些標準及一種分類方法,以不遺漏對任何有重要意義的歷史見證物的保護。建築師自己對他們代表作的關心也毫不遜色。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在活著的時候就開始著手保護他已實現的設計。其中11項被列級,14項被列入補充名單。他為薩伏伊別墅進行了多次整修,其造價比很多中世紀紀念性建築的整修更為昂貴。
最後,起初誕生於歐洲,並長期以它為擴散範圍的歷史性紀念建築的概念及與其相關的保護實踐,被傳播到了歐洲之外。在明治維新的大環境下,19世紀70年代見證了歷史性紀念建築的概念審慎地進入日本4:日本是一個堅持延續傳統的國家,它只按朝代來認識歷史,只以活的方式來對待古今藝術,並且只以照例的重建將其紀念性建築總是維護在新的狀態,它對西方的時間觀念的吸取表現在對於世界歷史的認識,對於博物館概念的接受,以及對作為過去的見證物的紀念性建築的保護上。
在同一時期,美國成為首批對自然遺產進行保護的國家之一。第二屆,1964年在威尼斯召開,迎來了三個非歐洲國家,突尼西亞、墨西哥及秘魯。十五年後,屬於五大洲的八十個國家簽署了《世界遺產公約》。
遺產財產在種類上、時間上及地理上的三重擴展,伴隨著其觀眾人數的指數式增長。
遺產的合奏及保護實踐的協奏並非沒有不和諧音。這些記錄也開始引發不安。它們會不會對保護對象產生破壞7?旅遊的負效應不只是在佛羅倫斯及威尼斯才能被感受到。京都的舊城一天比一天衰敗,在埃及需要關閉國王谷的使重大整治項目陷於癱瘓的行動等。創新的必要以及如何辯證地對待拆除也被論及,在世紀變遷過程中,正是這種創新和拆除使得新的紀念物替代了舊的。事實上,不用上溯到古代及中世紀,僅在法國就可找出數百個在17和18世紀以“美化”為由被毀,並被巴洛克式及古典式建築替代的哥德式教堂。皮埃爾·巴特(Pierre Patte),路易十五(Louis ⅩⅤ)的建築師,在其完善及美化巴黎的規劃中,極力主張“拆除8”所有哥德式建築。甚至古代的紀念性建築,即使是在古典時期建造的珍貴作品,當它們妨礙城市及國土現代化的項目時被毀棄的也不少,如波爾多市(Bordeaux)著名的監護宮(Palais de Tutele)9。
在法國,這些先例代表的建設性破壞及現代化的傳統成為不少議員反對國家建築師及歷史建築和保護區委員會(Commission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et de secteurs sauvegardés)觀點的盾牌及理由。正是在技術和社會進步,以及提高生活質量的名義下,尼姆劇院,一個在這個國家獨一無二的新古典建築群中的關鍵角色,已被一個多功能文化中心取代。在馬革里布(Maghreb)及近東,同樣的理由被用於證明在伊斯蘭教區的大拆除及破壞是正當的。在突尼西亞10,如同在敘利亞和伊朗,現代化的政治意願也借用了CIAM11及其明星們的思想體系。
在他們看來,建築師具有作為藝術家進行創造的權力。他們願意和他們的前輩一樣,標誌城市空間,而不是被放逐到城牆之外,或者在歷史性城市中,淪落到模仿的地步。他們回憶起,在過去,不同風格也曾共存、並置,在同一城市甚至同一建築中各放光彩。自羅馬風格時期到火焰哥德式或巴洛克式,建築的歷史可以從一部分重要的歐洲宗教建築中讀出,如夏特(Chartre)、奈維荷(Nevers)、埃克斯(Aix-en-Provence)、瓦朗斯(Valence)、托萊德(Tolède)的教堂。像巴黎這樣的城市的魅力來自於其建築及空間風格的多樣性,它們不應被毫不妥協的保護所凝固,而應是延續的,如羅浮宮的金字塔所體現的。
至於業主,強調自由處置自己財產的權利,主張由他們自己來選擇是從遺產中獲得快樂還是利潤。這些不同觀點的碰撞在法國導致了一項以公共利益為優先的立法。而在美國,對私有歷史遺產的使用限制侵害了公民的自由這樣的觀點還在占上風。
這些反面的不和諧音既強大又堅定,每天都有見證。但是,這些對遺產的持久的威脅,並不能阻止人們就對其保留和保護達成廣泛共識。為這一共識辯護的理由是遺產的科學的、美學的、記憶的、社會的、城市的價值。在一個工業發達的社會,遺產是這些價值的載體。一位美國人類學家論證了,以藝術旅遊活動作為媒介,建築遺產可成為聯結全球社會的一種紐帶12。
共識/爭論: 由相應的兩種觀點援引的推理及價值有待於一種審視和評判。過度增長:它可歸於一種政治策略;它的行為顯然具有經濟的尺度,並或許標誌著對當代城市規劃的平庸的一種對抗。然而這些對建築遺產的行為的解譯卻不足以解釋其超常的發展,它沒有發掘出其全部意義。
我所探究的正是這一意義之謎:從構建過程來考察建築遺產的語意範圍——它是難以理解的,既是冷冰凍的又是熱情洋溢的。為了便於形成一個定位的參照系,我將從時間上回溯,尋找源頭,但這不是記述一段歷史。我將論及一些具體的人物和標誌性事件,但用意不在於記流水賬。首先,需要事先至少說清楚作為全部遺產保護實踐前提的兩個術語的內涵及差別:紀念性建築及歷史性紀念建築。
我們先看一下,紀念性建築(monument)的含義是什麼?在法語中,這一術語的本意來自於拉丁文中的monumentum,它又來自於monere(告知,使憶起),與記憶相關。建造紀念性建築的目的的感情性質是實質性的,它並不是簡單地使人觀察,釋放一種中性的信息,而是通過情感激活一種生動的記憶。在這一基本意義上,我們稱為了回憶或者使後代回想起一些人物、事件、犧牲、傳說及信仰而由某個群體建造的所有人工物為紀念性建築。。它不僅通過情感的中介調動並參與記憶,其方式是喚醒過去,使其如在面前般活起來;而且,這個如施咒符般被調用和激活的過去,是為了至關重要的目的而被定位和選擇的,以使其能直接有助於維持和保留一個社團具有的種族的、宗教的、國家的、部落的或家庭的特徵。對於那些建設紀念性建築和從中接受訓誡的人來說,它是抵禦對存在的創傷的一種防衛,一種安全措施。紀念性建築通過體現時間的存在而使人安心、安寧、平靜。它保障了本源並平息了由開始的不確定性而產生的不安。通過消除熵,抵消由時間作用於所有自然及人工物體上的消融一切的力量,它試圖安撫由死亡及消逝帶來的焦慮。
與存在過的時代及記憶的關係,或者說它的人類學功能,構成了紀念性建築的本質。別的因素都是偶然的,因而是多樣的和變化的。我們已看到紀念性建築的目的是如此,其種類和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有陵墓、廟宇、柱廊、凱旋門、石碑、方尖碑、圖騰柱。
紀念性建築很像是一個豐富的文化世界。在其多樣的形式之下,它似乎存在於所有的大陸以及幾乎所有的社會,不管其有無文字。紀念性建築,根據不同情況,有的沒有銘文,有的則以惜墨如金的方式刻上銘文,有的則自由揮灑,甚至整個紀念物都覆蓋上了銘文。而這時候建築物已轉向其他的功能。
然而,紀念性建築原本意義上的作用,已逐漸在西方社會失去重要性,趨向於自我消逝。而這一字眼卻取得了其他含義。詞典的變化可以證明這一點。在1689年,菲勒蒂埃(Furetière)似乎已給這一術語考古學意義,而減弱了其記憶的價值:“過去的世紀裡,某些強大的權力和偉人留給我們的見證物,如埃及的金字塔、競技場,是埃及法老和羅馬共和時期的強盛的崇高紀念物。”又過了若干年,《法國科學院編大詞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恰當地將紀念性建築及其記憶功能放到現在的語境,但它的例子顯露出一種偏移,這次轉向美學的及聲譽的價值:“著名的,壯麗的,宏偉的,耐久的,光榮的紀念性建築。”13
這一演進一個世紀之後被卡特勒梅爾·德坎西(Quatremère de Quincy)所證實。他注意到“當套用到建築作品”時,這一辭彙“指一個建築物,或者被用於永遠紀念值得懷念的事物,或者以成為一個城市中美觀和宏偉的因素而被設計,建造和使用”,但他繼續指出“在這第二種方式中,紀念性建築的概念,與建築物的效果,而非其實體及用途關係更大,這種概念適合併可套用於所有類型的建築”14。
當然,1789年的大革命者沒有停止對紀念性建築的夢想,也沒有停止在紙上構思宏偉的大廈,以確立法國的新特性15。儘管這些工程實際上是用於後代的記憶,它們的演奏卻有更寬廣的音域。17世紀的字典中可覺察到的演變是不可逆轉的。“紀念性建築”自此表示著權力,崇高,美麗,它的目標清晰地指向表現某些重大的公總計劃,提升某些風格,或追求美學的敏感性。
今天,“紀念性建築”的詞義仍在發展之中。顯示技術力量的塔樓作為現代版的巨石陣所引發的驚嘆和震撼,替代了宏偉大廈的美所帶來的愉悅。而正是從這巨石陣上面,黑格爾在遠古東方民族那裡看到了藝術的開始。自此以後,紀念性建築無需藉助于思考,直接衝擊人們的注意力,可在瞬間被解譯,紀念性建築從古代作為記號的狀態被轉換成了信號的狀態。例如,賴特在倫敦的建築,南特的不列顛大廈,巴黎的德方斯拱門。
紀念性建築的紀念功能的逐漸消退,無疑是有原因的。我只舉出兩個,這兩個原因長期以來一直都在起作用,第一個原因在於西方社會自文藝復興以來對藝術的概念賦予的不斷提高的地位16。在此之前,紀念性建築的目的是提醒人們上帝的存在或其作為造物主的處境,要求它們的建造者的工作最為完美,更好地完成,最終有光線的傾瀉及豐富的裝飾效果。美,則不在考慮的問題之列。通過將美作為藝術的終極目的,從而給予美以自明性及地位,文藝復興將美與宗教和紀念的慶典完全結合起來。儘管阿爾伯蒂,作為第一個建築美學的理論家,虔誠地保留了紀念性建築的本原觀念,他卻開啟了用美的典型來替代紀念的典型的過程。
第二個原因在於人工記憶方式的傳播、完善及發展。柏拉圖把書寫看作是人類記憶的有害的變例17。在印刷術帶給寫作一種掌握記憶的前所未有的能力之前,紀念性建築在記憶上的支配地位從未遇到過挑戰。
目光敏銳的查爾斯·帕魯(Charles Perrault)高興地看到,隨著書籍的增多,給記憶以負荷的約束消失了:“如今……,我們幾乎不需要用心記什麼東西,因為它們通常都在我們自己閱讀的書里,當需要時就可求助於它,因而我們可以通過寫下過去的事而比從前依賴記憶中樞時更確切地援引它18”。他沉浸在作為文人的興高采烈中,卻沒想到,供博學者調遣的知識的驚人飛躍,帶給他們的是一種遺忘的實踐。而認知記憶的新補形術對有機記憶則是有害的。自18世紀末,“歷史”指這樣一個學科,在其中,總是得到更好的收集和保留的知識,為它提供了時代活的記憶的表象,儘管這知識替代了活的記憶並由此削弱了它的能量。然而,“只有當人們注視歷史時,它才能被構建起
來;而為了注視歷史,人們應置身歷史之外”19。這一定律精闢地說出了紀念性建築的兩個不同及相反的角色,表現在它作為能激活一段珍貴的過去及使觀者沉浸其中的帶隱喻性的客體的存在。
在帕魯的頌詞一個半世紀以後,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發表了被印刷術的發明判了死刑的紀念性建築的葬禮頌詞演說20。存儲過去的新模式的發明和完善證實了他這一對遠景的直覺:保存圖像及聲音的技術所形成的記憶能力,能夠以一種更具體的方式儲存及再現過去的事件,因為它們直接作用於感覺及敏感性,是更抽象、更非物質化的電子系統的“記憶”。
以攝影術為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承認這一“人類學上的新物件”的出現,既不會和油畫競爭,也不會否定或排斥油畫。“攝影的最基本的定位既不是藝術也不是通信,而是參照物”。它的出現因而像是一種以前沒有的補形術:它帶來了一種“新的證明方法”,“這種確定性是任何寫作都無法提供的”。這種證實的能力無疑是從使照相術“釋放出參照能力”的化學反應得到的。而且,這種化學反應同時使照相術具有重現的能力。因為有了鹵化銀的媒介作用,“消逝的存在的照片如星星的光芒般照射到我”。
巴特已經感知到並分析了攝影術的雙重性,即這一新的pharmakon(藥物)具有的雙面性。它的可在記憶的兩個層面發揮作用的獨特能力:即證明一段歷史的真實性和重現一段消逝的歷史。這裡不要混淆攝影作用於我們的兩種模式,巴特通過給它們起名而揭示出這兩種模式。照相(studium)指一種睿智的愛好,一種對外部的興趣,但同時也是一種情感。心醉神迷(L’extase),指使“等同某一時刻的文
字21”重新回到人們的意識中,它是一種誘導性的使人產生幻覺的運動,痴迷這個詞被多次用於形容它。不過,這種與存在和情感耦合的對攝影的痴迷與紀念性建築的咒語有同樣的性質。這樣人們就可理解《明室》(La Chambre claire)一書的斷言,即現代社會已放棄紀念碑,理由是攝影為一種適應我們這個個人主義時代的紀念碑的形式:私人社會的紀念碑。使每個人都能隱秘地回顧私人的或者是公共的逝去的事物,而這些事物構成了其特性。記憶的魔法從此可以更自由地完成,其代價是要對這些部分地保留著主體性的圖像付出適當的勞動。
另一方面,攝影有助於紀念性建築——信號的語義轉換,事實上,正是由於越來越多地通過它們的圖像的媒介,通過其在印刷品、電視及電影中的流通和擴散,這些信息才能被傳遞到當代社會。它們僅以被轉變為圖像,被轉變為沒有重量的複製品的方式成為符號,其中凝聚著它們的象徵價值,而這種象徵價值已以這種方式被與實用價值分離。所有的建築不管其用途如何,都可被“傳播”的新技術提升為紀念物。在此,它的功能是為一份原始的、脆弱的、易變的複製品的真實性提供合法的和權威的依據。在這一複製品上從此就寄託了其價值。真實的建築與它們的媒介表達或理想的圖像是否符合則無關緊要。羅浮宮的金字塔在建造之前就已存在,如今這一建築透明且熠熠生輝的形象出現在其設計圖和照片的複製品上,儘管實際上,它更像是某個商業性中心的入口,而它的不透明性遮蔽了從四方庭院向杜伊勒利宮及巴黎方向的透視。德方斯拱門的照片為它保留了一種具有象徵性的魅力,儘管現實中的大廈很粗糙,它容納的辦公空間使用不便。沒有誰能比未來的“大圖書館”的建築師更好地描述當今所謂紀念性建築的非現實感及其存在形式。在被問及這一建築如何與貝爾西(Bercy)的地段結合時,他回答“在10年或20年內,我們在這個地段能做出巴黎最漂亮的明信片22。”
在這種條件下,紀念性建築,就其本原意義而言,是否在所謂發達社會還扮演一定的角色?在保留用途的大量文化建築之外,除了作為對死者的紀念碑及最後幾次戰爭的軍人公墓,它們的狀況是否僅僅是從過去倖存下來?人們是否還在建新的紀念性建築?
紀念性建築,這裡有必要加上定語“追憶性的”,繼續習慣性地追求一種正統的和可笑的特徵。我們的時代建造的僅有的真正紀念性建築,不叫這個名字並異化為最不奇特且不具隱喻性的形式。它們喚起一種過去,它的分量,以及更多的是,它的恐怖使得不能將其寄託於單一的歷史記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凡爾登的戰場構成了一個先例,無邊無垠的大自然,被戰鬥所切割和扭曲,僅在此設定旅行的地標就已足夠,如設定十字形的路徑,以紀念現代歷史上人類的巨大災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華沙市中心的原樣重建,使人想起波蘭古老的國家特徵,又使人想起它的敵人滅絕種族的嗜血性。同樣,太人的記憶正是集中營本身,包括臨時房屋及瓦斯室成為了紀念物。只需要分散地進行一些整治及貼一些標籤就已足夠:人們從前在這裡的遭遇永不會被淡忘,死者及對他們的行刑者永遠在提醒來到德紹(Dachau)或者奧斯維辛(Auschwitz23)的人們。任何藝術的渲染都是不必要的,只需一個簡單的借喻的行動。真實的分量,與那些共同記憶中的事件密切相關的事實,在這裡比任何象徵都更有力。成為了紀念性建築的集中營,具有了珍貴紀念物的特質24。
但這些既是遺物又是遺物盒的巨大紀念物,依然是罕有的,正如它們從人類記憶喚醒的那些事實。對於這些歷史痕跡,重要的是選擇及知道如何指定。它們見證了生動的記憶與建造知識之間的分離。新的華沙市中心本身作為一個紀念物,僅僅因為它是一個複製品:它以某種由照片等媒介記錄的真實性,替代了被摧毀的城市。為了憶念的目的而從無到有被(ex nihilo)豎立起來的象徵性的紀念性建築,在我們已開發國家已入窮途末路。由於這些國家具有功能更強大的記憶方式,它們漸漸停止建造紀念性建築,而將對它們的熱情轉向歷史性紀念建築。
紀念性建築和歷史性紀念建築這兩個概念,今天經常被混淆,在仔細審視之下,它們即使不是反義的,也是相對的。首先,與紀念性建築在時間和空間中近乎普遍的存在相差很遠,歷史性紀念建築是一個有清楚時間記錄的西方的發明。我們已看到自19世紀下半葉這一概念已非常成功地傳播到歐洲之外。
但國際組織的研究報告顯示這種對這一概念的全球性的接受仍是表面的。歷史性紀念建築的語意在困難地拓展。這一概念與一種文化背景和一種世界觀是不可分的。進行歷史性紀念建築的保護實踐而不具備一種歷史的參照系,不賦予時間段一種特別的價值,不把藝術放在歷史之中,則將失去意義,正如演示茶道儀式而忽視日本人對自然的情感,神道及日本式的社會結構。在那種情況下,熱情會加大誤解,甚或掩飾實際所為。
另一個根本性的差別,由里格爾(A.Riegl)25於20世紀初闡
明:紀念性建築是一種精心的創造,其目的是被事先確定並一開始就實現了的,而歷史性紀念建築初始時卻不是人們有意為之,將其作為紀念性建築而創造的;它是事後由歷史學家和業餘愛好者的共識所形成的,這種共識將其從大量現存建築中選擇出來,而紀念性建築在這大量現存建築中只占一小部分。所有過去的物品都可被轉化為歷史見證物,而在最初,卻不必具有一種憶念的目的。反過來,我們知道,所有的人工製品都可被精心地投入一種憶念的功能。至於藝術帶來的愉悅,卻不是紀念性建築的排他的封地。
,歷史性紀念建築與活的記憶及與歷史時期之間維持著另外一種關係,或者它只是簡單地由知識的客體構成並被整合到時間的線性結構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它的認知價值將其無可挽回地擱置在過去,要么被擱置在一般的歷史,要么在特殊的藝術史之中。或者它可以額外地,作為藝術作品,迎合我們的藝術敏感性及我們的“藝術願望(kunstwollen)26”,在這種情況下具有一種顯著的差別。表面看來,保護這一概念對紀念性建築和歷史性紀念建築是對等的。然而,紀念性建築永遠被實際的歲月所摧殘。忘記、漠然及廢棄不用使得它們被荒廢及聽任坍塌。有意的27及經過商議的破壞也威脅著它們。其動因也許是想要消滅它們,也許相反,是為了逃避時間的作用或是完善它們的願望。第一種形式,出於消滅它們的動因,是消極的,也是最常被提及的:它出於政治、宗教及意識形態的原因,然而卻從反面證明了紀念性建築在保持種族及社會團體的特徵方面的實質性作用。第二種形式,積極的破壞也是普遍的,但引起的注意較少。它的表現方式有多種多樣:一種是某些民族特有的形成慣例的方式,如日本人並不像我們那樣,夢想把時間銘刻在他們的紀念性建築上,而是周期性地精確複製廟宇的原型而將較早的複製品毀棄。另一種是創造性的,在歐洲有許多例子可說明這種情況。為了擴大“真福的丹尼斯已駐500年”的聖殿,使其更輝煌,在12世紀30年代,敘熱(Suger)拆除了傳統上歸於達戈貝爾(Dagobert28)的卡羅琳娜式巴西利卡的一部分。基督教的最珍貴和最受尊崇的紀念性建築,羅馬的聖-彼得(Saint-Pierre)教堂,在其12個世紀的生涯之後,不是被居勒二世
(Julius Ⅱ)的一項決定給毀棄了?這一決定的目的是用一個宏偉的大廈將其取代,其壯麗和透視感足以喚起自康斯坦丁時期以來的教堂所取得的力量,並適應其教義的新改變。
反過來,由於歷史性紀念建築在被知識體系視為客觀並固化的整體中處於一個不可變動的和確定的位置,在這一知識體系的邏輯里,至少在理論上,它們需要得到一種無條件的保護。
保護歷史性紀念建築的計畫及其實施隨時間而演化,也不能將其與歷史性紀念建築這一概念的自身歷史分開。我們說歷史性紀念建築這一概念由西方發明,對這一發明的過程有良好的時間記錄。仍需要確定的是判定這一時間的標準。
一個新詞被收錄進詞典標誌著對一個其所指的物質或精神上的實體的正式承認。然而這一正式認可相對於其最初的套用和突然或經過長期醞釀而出現的援引,表現出一種時間上根據不同個例或多或少的延滯。“歷史性紀念建築”的表述,被法語詞典收入的時間不早於19世紀的下半葉。但它的套用在19世紀初即已普遍,這要歸功於基佐(Guizot),在1830年,當他剛就任內務部部長時,就創立了歷史性紀念建築督察的職位。我們還應上溯得更遠,這一辭彙無疑於1790年第一次出自L. A. 米蘭(L. A. Millin29)的筆下,當時的背景是法國大革命完善了歷史性紀念物的概念及與其相關的保護措施30(博物館、清點造冊、列級、重新利用)。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文物的破壞卻不應被低估。一批在大革命的委員會及聯盟內部與破壞主義鬥爭的人,在危險的緊急情況下,使對於藝術愛好者、建築師及啟蒙時期的學者來說共同的一些想法得以結晶。
這些文人自身是一種文化傳統的繼承者,這種文化傳統源自義大利15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及知識和精神上的偉大的人文革命。同樣,歷史性紀念建築的來源應該在表述它的術語產生之前尋找。為了追尋這一概念的起源,應該回溯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項目誕生的時刻,即僅僅因為某個建築是歷史見證或藝術作品而對其加以研究和保護的項目誕生的時刻。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在這兩個領域都位於前沿的阿爾伯蒂(Alberti),已經讚美了那些可同時重現我們的過去,確認建築師-藝術家的光榮及證實歷史學家的記載的建築31。
正如我所期望的,將歷史性建築遺產32置於對現代社會命運的反思的核心;隨之而來的,試圖評估在當今遺產保護行為之下的,默認的或被忽視的,動機、擔當、願望:一個如此的工程不能不回溯其根源。我們不能僅關注文化遺產這面鏡子,,而不事先尋求理解這一鏡子的宏偉而光滑的表面是如何由最早被稱為古物,後來被稱為歷史性紀念建築的碎片一點點熔鑄而成的。
這就是為何我要首先確定這一概念出現的時刻,並重新構建歷史性建築遺產逐漸創立的關鍵步驟的原因。其歷程從文藝復興的古典研究時期到這一概念被正式認可的時期,前一時期所有被選中的紀念性建築都無一例外是古代的,後一時期通過確立保護的法制化並將修復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學科,而將歷史性紀念建築的保護制度化。這一考古是必需的,但並不需要進行無窮無盡甚或大量的搜尋。
因而我並未系統發掘歷史的細節33以及每個歐洲國家與歷史性紀念建築及歷史遺產概念的關係的特殊性。我並未對文物保護法制化,及對文物修復的繁複世界過多著墨,也未能對此作出超出我的討論需要之外的全面闡述。我的例子通常是借用法國的,但這並不影響其典型性:作為一項歐洲的發明,歷史遺產在所有歐洲國家植根於一種同樣的思想觀念(mentalité),在它成為一項全球性制度的同時,它終將面對世界上所有面臨同樣問題,同樣緊迫性的國家。
一句話,我不願將歷史遺產的概念及其用途作為
圖書目錄
紀念物與歷史性紀念物 ........................................................003第一章 人文主義與古代紀念性建築 .................................001
希臘古典藝術及古代人文學術 .....................................................002
古代遺存及中世紀人文學術 .........................................................004
義大利15世紀的古典研究時期 ...................................................012
第二章 古物學者的時代:實際的紀念物及圖繪
的紀念物 ..............................................................026
國家古物 .........................................................................................031
哥德式 .............................................................................................033
圖像時代的來臨 .............................................................................037
啟蒙運動 .........................................................................................041
實際的保護與肖像式保護 .............................................................046
第三章 法國大革命 ..........................................................050
遺產的列級 .....................................................................................052
破壞主義及維護:解譯及副作用 .................................................057
價值 .................................................................................................063
第四章 歷史性紀念物被正式認可
的時期(1820—1960) ........................................068
歷史性紀念物的概念本身 .............................................................070
認知價值與藝術價值 .............................................................070
浪漫主義藝術的準備:畫意美,殘缺美及藝術崇拜 .........073
工業革命:劃分無法彌補損失的邊界 .................................075
虔誠的價值 .............................................................................078
實踐:立法和修復 .........................................................................081
法國歷史性紀念物立法的起源 .............................................082
作為學科的修復 .............................................................................085
關於修復的辯疑:拉斯金與維奧萊-勒-杜克 ..................087
法國及英國 .............................................................................091
小結 .................................................................................................094
拉斯金及維奧萊-勒-杜克之外:伽米奧·博托
(Camillo Boito) ......................................................................094
阿盧瓦·里格爾:一個主要的貢獻 ......................................097
第五章 城市遺產的發明 ...................................................103
紀念的作用 .....................................................................................107
歷史性的作用:預科教育的角色 .................................................109
歷史性的作用:博物館化的角色 .................................................115
歷史中的作用 .................................................................................117
第六章 文化產業時代的歷史遺產 .....................................124
從崇拜到產業 .................................................................................125
價值開發 .........................................................................................128
與當代生活的整合 .........................................................................134
負面效應 .........................................................................................139
策略性保護 .....................................................................................145
建造的能力 .........................................................................149
遺產之鏡:一種自戀行為 .............................................................150
遺產綜合症真實的決定因素 .........................................................156
走出自戀:被消除魔法的遺產之鏡 .............................................159
注釋 ...................................................................................164
附錄 ...................................................................................238
參考文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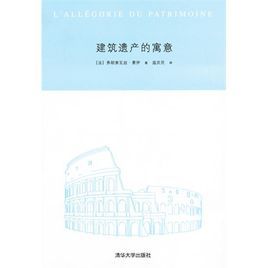 建築遺產的寓意
建築遺產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