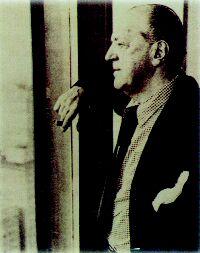
密斯
二十世紀只有很少的建築家達到這種最高的境界——崇高,建築巨匠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就是這極少中的一位。密斯是一位神秘主義建築家,他的建築遺產被許多迷所包圍,本文就是試圖從一個世界密斯研究所沒有涉及到的領域,尋找密斯的精神源泉。
2001年在紐約兩大美術館,分別舉辦了《密斯在美國(Mies in America)》和《密斯在柏林(Mies in Berlin)》的展覽,這是至今為止對密斯生涯中兩個重要時期的作品所進行的全面回顧。雖然密斯被人們並列為二十世紀三大建築巨匠之一(柯布西耶和萊特),但是密斯和其他兩位建築巨匠有著本質的區別。從表面上看,密斯酷愛鋼鐵和玻璃,那些用這兩種材料建造的摩天樓,被視為鋼鐵男性的象徵,縱觀密斯一生的作品有始終如一的堅持,那就對崇高性的表達。
崇高論
康德認為,崇高是一種“絕大”的“量”的概念。例如沙漠和星空,巨大的金字塔所具有的廣和大讓人感覺到他的崇高,還有火山所帶來的破壞力,咆哮的海,暴走的冰山都會讓人感覺自然的力所具有的崇高。然而康德認為前者是“數學性崇高”,而後者是“力學性崇高”,像北方浪漫主義那種敬畏自然,同時尋求人和自然高度統一的情感,是屬於“力學性崇高”。在《判斷力批判》一書中對“崇高”的論述大大影響了後世,所謂“崇高”,是指具有精神性價值的“高”為主題的表現。那種面對巨大的對象而產生的想像力,以及由於和理性相違產生的不協調所帶來的痛苦,然而超越這些痛苦產生新的理念,這個理念讓我們獲得超越理性的快感,這就是我們從“崇高”中獲得的精神產物。近代建築是由於密斯的努力,承接浪漫主義的精神,通過崇高性的建築使我們的精神和道德向上。
關於崇高性的表現,美國美術史家羅伯特?羅森勃拉姆(Robrt Rosenblum)把德國浪漫主義最高的代表畫家卡斯帕爾?達維德?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Friedrich1774-1840)的繪畫列為表現“自然性崇高”的藝術,而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巨匠和美術評論家紐曼(Barnett
Newman1905-1970)有名的“崇高與現在”的論文,則論述了自己的抽象繪畫理論,是從康德的崇高論出發,以及明顯受到C?D?弗里德里希影響而形成\\"抽象性崇高\\"的過程,那么本文試圖通過對密斯建築的考察,提出“崇高性建築”問題。
始終如一
密斯?凡德羅在很長的建築生涯中,有兩段時間的作品最為重要(這與他在柏林和美國這種地理上的位置無關),那就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最後的作品。
人們常常從密斯的作品中去分析和尋找現代主義的建築語言,例如使用什麼樣的材料,如何強調柱和梁的關係,怎樣讓玻璃幕牆後退讓出空間,牆和柱分離的手法等等。然而密斯在這些技術和表現還沒有具體化之前,即在1921年發表了對二十世紀建築帶來巨大衝擊性的設計--柏林腓特烈大街高層建築方案,以及1922年發表的玻璃摩天樓方案模型和同年發表的玻璃塔樓方案。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玻璃塔樓方案的尺寸,這是一幅用碳條繪製的巨幅素描,不是一般的那種建築效果圖,完全是一幅獨立的美術作品。說是玻璃塔樓,然而沒有任何細部表現,只有和周圍已存建築物的比例關係,那種粗獷的霸氣可以說貫穿著密斯的一生。在那之後密斯在美國紐約和芝加哥先後建造的摩天樓西格拉姆大廈(1954-1958),和IBM公司大廈(1967-1969)的氣概都有1922年那幅巨幅素描的影子,這說明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年輕的密斯的世界觀已經形成。 建築即信仰
密斯風格
建築行為不是要確立一種風格,密斯曾在1923年7月柏林出版的《創作》雜誌上發表文章,對一切美學的抽象理論、教條、形式主義進行過猛烈的抨擊,那么密斯崇尚什麼?
密斯認為建築是一種精神活動,這一點貫穿於他的一生,他在1930年《構築(Bauen)》一文中寫道:“我們必須設定新的價值,固定我們的終極目標,以便我們可以建立標準。因為正確的以及有意義的,對於任何時代來說—包括這個新的時代—是這樣的:給精神一個存在的機會。”這裡所說的“終極目標”就是密斯的信仰。
密斯說:“上帝存在於細部”,那么就是說“細部中上帝”,密斯所說的“上帝”就是他的信仰,那么怎樣的形式或造型能夠體現這種信仰?
埃森曼在為《密斯在美國》一書所撰寫的“密斯和不在場的成形”一文中指出,柯布西耶慣用的圓柱暗示了周圍空間無方向地自由流動伸展,而密斯的不鏽鋼十字形柱則在於含蓄地矢量化四周的“空”。埃森曼的觀點從結構上可以講的通,然而我認為,密斯的不鏽鋼十字形柱不是結構問題,也不是埃文斯(Robin Evans)所論證的,密斯所謂的結構並非工程意義上的結構,而是一種審美意義上的概念結構的說法,我認為密斯的十字形柱是一種信仰結構。
十字形柱的暗示
巴塞羅納國際博覽會德國館(1928-1929)是密斯的代表作,人們對整個主廳承重結構只有八根十字形斷面的鋼柱,所有大理石牆和玻璃隔斷背叛傳統結構關係,以及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流動空間印象深刻。然而這座建築對於密斯來說最重要的是創造了不鏽鋼十字形柱的結構,這個結構成為象徵密斯的符號,看到這個符號就讓我們聯想到密斯的一切,他就是密斯的信仰,即十字形柱是基督教信仰的暗示。
密斯崇尚的在歐洲中世紀基督信仰思想發展史上極其著名的神哲學家聖奧斯定(St.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說過:“在巡禮的狀態中活著”,那些和牆分離的十字形柱,為那些有著基督信仰的人創造了一種可以巡禮的環境,這就是十字形柱的暗示。
真正影響密斯的人
說到密斯的信仰必須返回到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浪漫主義思潮,當人們研究密斯的時候,常常積極地出現卡爾?弗里德里希?辛克爾(Karl Friedrich Shinkel 1784-1841)的名字,當然K?F?辛克爾是對密斯有過很大影響,但是由於研究者們多重視密斯建築形式的文脈,因此忽略了密斯建築的本質,即和這些建築有著精神傳承關係的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其實對密斯建築的崇高性有著絕對影響的,是和辛克爾同時代的畫家卡斯帕爾?達維德?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如果說辛克爾是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最大的建築家,那么弗里德里希則是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最大的畫家,然而真正左右密斯建築精神走向的則是弗里德里希。
浪漫主義繪畫:像一首聖歌
弗里德里希通過風景畫——從嚴格的意義上講,這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那種繪畫題材性的風景畫——表達了對大自然神性的憧憬,十字和十字架在他的繪畫中反覆出現,而且都是左右居中的位置。弗里德里希早期繪畫作品中多出現具象的哥德式教堂和十字架,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具象開始向暗示性手法演變。比如那些停泊在海上降下帆的船,裸露出十字形桅桿,以左右對稱的黑色松樹代替哥德式教堂,左右居中有極細十字框的正方形視窗,天空中出現十字光芒……,弗里德里希對光的精細控制,和表現純靜深遠的空間,好像一首聖歌蕩漾在被弗里德里希的繪畫完全俘虜的空間中。
弗里德里希在歐洲繪畫和精神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美術史家認為,弗里德里希那幅表現在崇山峻岭的風景中,遠山上有一個在十字架上受難的基督的繪畫“Riesengebirge的早上(1810-11)”,是第一位有基督教繪畫以來,通過繪畫把基督送回自然中去,強調大自然的神性戰勝人間的畫家。其實弗里德里希的浪漫主義繪畫不僅對二十世紀的藝術,還對二十世紀的社會政治產生過巨大影響,例如那幅1818年的“霧海上的流浪者”(The Wanderer above a Sea of Mists 1818),就是激發希特勒從政的刺激劑。弗里德里希對建築家密斯的影響,是浪漫主義思想在二十世紀建築界的延伸,因此了解密斯和弗里德里希繪畫的關係是解析密斯思想的關鍵。
窗的暗示
即使弗里德里希表現的是普通的日常風景,也有神秘的暗示。例如1805-06年的作品“弗里德里希畫室的窗”和1805年的“畫室的窗”,1822年同樣表現視窗的風景“窗邊之女”,畫面的正中都有兩扇窗戶,上面的窗戶都是有十字窗框的正方形窗,特別是1822年那幅畫中的十字窗框非常細,幾乎不起結構作用,特別奇怪的是,上面的窗戶沒有窗板,下面的窗戶有窗板。羅伯特?羅森勃拉姆的研究認為,上面的正方形窗戶是基督信仰的神聖空間,下面是世俗的窗戶,那個十字架就是基督信仰的暗示。
這些暗示影響了神秘主義抽象畫家蒙特里安(Piet Mondrian)、梵谷(Van Gogh)和墨西哥建築家巴拉乾(Luis Barrgan)等人。當我們理解了弗里德里希反覆表現具有十字特徵的物體真正的含意之後,就不難理解密斯十字形柱的由來,以及這一結構所具有的暗示功能。
浪漫主義繪畫的崇高性
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繪畫是孤傲與叛逆的象徵,浪漫主義者崇尚大自然,從中獲得崇高與力量,弗里德里希繪畫中的神秘色彩和光,這是他接近神秘自然的途徑,弗里德里希多表現夜晚的風景,它與夢一起暗示著潛意識中神秘的世界。他一生都在山林和海邊孤獨地漫步,1809年的“海邊的僧侶”在1810年的展覽會上對他贏得聲譽,這幅畫成為浪漫主義繪畫將光非物質化的傑作,表現了在沒有任何人工符號的景色中人所體會到的自然的崇高,根據X光透視攝影,弗里德里希在這幅畫中去掉了他的作品中通常出現的船舶,由於失去對象空間顯得更為神秘和空無,也然而弗里德里希本人絕對不會想到,這幅畫居然成為二十世紀“無對象繪畫”的原點。
弗里德里希的繪畫中還經常表現暗黑的歌特式大教堂、森林和教堂廢墟,對浪漫主義者來說,廢墟是人間內面的表象,浪漫主義繪畫喜歡暗黑美學和光,他們把非物質性作為表現對象。弗里德里希繪畫的精髓,既他自己所認為的那樣,藝術是表現肉眼所看不到的世界。
弗里德里希1813年所繪“山中的十字架和大教堂”,讓我們找到密斯建築的精神根源,在弗里德里希的繪畫中主體形象和周圍景觀在視覺上有著很大距離和對比,然而密斯的建築也和城市景觀距離極大,如果我們從遠處眺望有密斯建築的風景,就會發現由密斯設計的黑色大廈,就像哥特大教堂和城市的景觀一樣。密斯1922年的玻璃塔樓方案,有著強烈的哥特美學和受浪漫主義繪畫影響,密斯建築的崇高性使得他是浪漫主義精神在建築方面的繼承者。
密斯喜歡烏黑的鋼鐵材料,那是弗里德里希繪畫中暗黑的大教堂和森林,密斯喜歡透明的玻璃材料,那是弗里德里希繪畫中的光和冰。這樣我們現在再看弗里德里希大街高層建築方案上,還是在“自然性崇高”上都保持著一致。在密斯那裡,完成建築的過程是意志的表現,而建造建築的目的是表達一種信仰。
大理石壁的暗示
我們繼續分析弗里德里希的兩幅作品,會在密斯建築中獲得驚人的發現。1811-12年弗里德里希創作了“山中的十字架”,八年之後的1820年,構圖幾乎同樣的作品“森林中的十字架”出現,所不同的是原來中景森林之後的哥德式大教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天空中出現光的十字架,而原來前景的十字架上基督受難變成金色的光芒掛在十字架上。顯然弗里德里希有意識將基督信仰的表現退隱到自然表象的後邊。
當我們承認密斯的建築和弗里德里希的繪畫有著同一性時,就會在密斯設計的巴塞羅納德國館中有意外的收穫。密斯用許多花紋非常明顯的大理石來組合牆壁的表層,這些大理石牆面顯示著上下左右對稱構,成向十字為心的花紋模樣,然而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那些花紋有著明確的暗示,既隱藏的十字架。這再次印證了先前所說的,密斯意在創造一個可以巡禮的環境,這也是密斯建築崇高性的一個側面。
“祈”之回歸
1968年密斯的女兒曾問他最希望建造而沒有實現的建築是什麼時,密斯回答說:“教堂”。同年82歲的密斯完成了在他的祖國德國一生最後的作品“柏林新國家美術館”(1962-1968)。我曾在《黑色的沉默--密斯?凡德羅的新國家美術館》一文中專門描述過這件正方形的讚歌,正方形作為一種模數,是密斯建築設計的基礎。密斯為了托起主體建築,建造了一個一個長105米、寬110米的方形平台,而美術館烏黑沉重的大平屋頂尺寸為64.8米見方。也就是說,建築本身是在一塊大的正方形上,重疊著另一塊純淨的正方形,這正是俄羅斯構成主義巨匠馬列維奇(Malevich)的絕對主義繪畫“黑色的正方形”(1914-15)所創造的偶像原型。
密斯的名聲,從1929年設計巴塞羅納國際博覽會德國館開始,走過40年的人生,為他的祖國設計的新國家美術館,標誌著人生最後乃至最高的到達。和巴塞羅納的德國館相比,晚年的設計已經是在單純的造型中尋找到歸宿,他為新國家美術館設計的是一個幾乎不需要進行任何切割的巨大正方形。
密斯同樣崇尚絕對主義繪畫的崇高性,並試圖建造了一座絕對主義的殿堂,這座新國家美術館,與馬列維奇那件“黑色的正方形”作品在精神上有著認同關係。只不過密斯是把灰色的正方形地面當作畫布,如果我們的視角是從空中垂直看這座建築,就是一個黑色的正方形,最好的說明是這座建築的施工圖紙上再清楚不過地展示了正方形和邊緣的關係。然而真正的震撼不是來自從俯視的角度,而是當你走進這個美術館,只有八根柱子懸挑起來的巨大黑色正方形屋頂,蓋在所有人的頭頂上,形成巨大的壓迫感。
如果說藝術的本質是向原點的回歸,那么密斯是通過“新國家美術館”這件封筆作,回歸到絕對主義繪畫的偶像“黑色的正方形”所要表現的終極世界。當我們對弗里德里希的繪畫進行連續考察之後,會發現這位浪漫主義的頂級畫家一生的作品,是一個“祈”的人生旅程,那么作為浪漫主義文脈的繼承者密斯?凡德羅的建築,則是虔誠的“祈”之生涯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