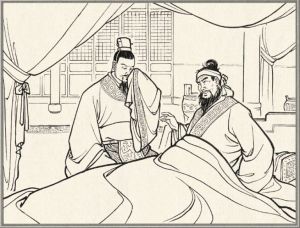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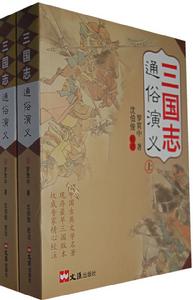 三國志
三國志表病篤,?國於備,顧謂曰:“我?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松之注引《魏書》
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松之注引《英雄記》
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亡?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松之注引《漢魏春秋》
有關劉表託孤(或是托國)的說法,大致有以上三種,全出自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用於不同的三本書。
說法
 劉備
劉備按《魏書》所記,劉表是在口頭上答應要把荊州讓給劉備來管理;《英雄記》的說法則是,劉表上書中央政府,推薦了劉備來做荊州刺史;據《漢魏春秋》的記載,又變成了劉備自己說的,劉表曾經有這么一個“托我以孤遺”意思,沒有了托國之說。
三種說法,綜合起來,便是兩種說法:“託孤”與“托國”。
分析
首先要明白,這“託孤”與“托國”不是一個概念,“託孤”的意思,就是將自己的後代交給一人來輔助,這名義上的君主還是自己家的;“托國”是將整個地方給託管一個人,這地方也就換了主人,其中也許包含了託孤,也許沒有託孤。總的說來,“托國”的範圍大些,影響大些,變化也大些。
劉表也許是托國又託孤,也許只是託孤,或許只是托國,現在已不能考證,我只是想談談這件事的幾種可能性。
第一種:史書誤記。
三種史書,三種說法,不禁讓人懷疑這史書的可靠性,史學家們所記的事,並不是自身的親身經歷,往往不是得自於第一手材料,即便是親眼所見,也有個“為君者諱”的說法,對於這道聽途說的事,不免會有些捕風捉影,以訛傳訛下,記錯了也有可能,因而也就有了三個版本的說法。
第二種:史書瞎記。
出於某種原因,為了彰顯某個君主“仁義”形象,或是在當時的崇高地位及人們對他的器重,而編出了許多的符合當時情形的故事來,只是為了給這位“封建正統”臉上多貼點金,多造些聲勢,減少負面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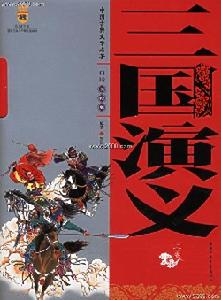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第三種:不然之言。
如裴松之所說,劉表夫妻一向喜歡的是劉琮,早就想著撇開劉琦,把荊州老大的這個位置給劉琮來做,怎么也輪不到劉備這個外人來,插一扛子,況且劉表對於劉備並不是很信任。
第四種:善意謊言。
劉備這樣說,當然是有目的的,劉表剛死,曹操又打了過來,荊州的局勢很不穩定,當地的士族中有一部份人既不喜歡曹操,又不喜歡繼任者劉琮,只得寄希望於劉備,為了拉攏這一部分人為己所用,也是為了給自己爭取更多的民心,以人為本的劉備,便說出這樣的話來,安定人心,也未嘗不是一個好方法。
第五種:有意試探。
劉備對荊州是有想法的,劉表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他就故意地布了了一個這樣的局,想讓劉備承認自己的真實意圖,正好下手,劉備當然不會上鉤,也就假意地辭讓掉了。
第六種:真心實意。
劉表確實知道自己的兩個兒子,實在是扶不上架,若要守住荊州這份基業,只能是靠頗得人心又頗有實力的劉備,學著前人陶謙般,有意要將荊州讓給劉備,這樣一來,即保存了自己的這份基業,後代的生活也有了保障。
第七種:時人套話。
三國時代,臨終前表示要把政權讓給別人的,不在少數,如先前的陶謙、孫策,及後來的劉備都有過這樣的說法,可見有其一定的流行性,有些是真讓,有些可能就是一種時尚性的套話,說了也就過了,沒有真正的意義。
第八種:以退為進。
劉表對劉備很不放心,怕自己死後,劉備奪了自己的地盤,說出這樣的話,是為了逼出劉備的實話,將劉備逼到了死角,讓他表明自己的心跡,從而沒有了退路,只得賣命效力。
第九種:君主權術。
這是一種帝王權術,為的是更好的讓屬下為自己賣命,也算是一種激勵,讓做臣子的更加感恩圖報,為自己的事業,盡心盡力,而無怨無悔,也是一種君主的用人之術,歷史上也常常出現。
第十種:無心失言。
也許酒喝多了,或是一時高興,可能是昏了頭,無意之中,劉表曾經說過這么一句話,他不當一回事,早就忘記了,劉備卻是牢牢的記住,還是放在了心上,不時的還拿出來跟人顯擺一下。
第十一種:病中胡言。
劉表這一病,病得還真不輕,沒過多久,便去世了,也就在生病的時候,他跟劉備講了這一番話,一個病人,神智也許不是很清楚,迷迷糊糊之中,也就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一些連自己都不知道的話,這也不能不說是不可能的。
第十二種:最後攤牌。
劉備這人是很難管得住的,既來管不住,那大家都把話給說開了,說明了,說穿了,大家都不要留有餘地,靜下心來,將所有的事都談明白,不用保留,大家放心,大家安心,總好過各自猜疑,互不信任。
歷史往往就是這樣的具有不可測性,在可能與可不能之間,說他有時,很難有充分的證據,說他無時,卻能找到很多的蛛絲馬跡,如迷霧般不可捉摸,如高山般不能縱觀全局,除了當事人外,誰也難以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切只能是猜測,合理的,不合理的,合情的,不合情的,但是否是真實的事實呢,沒人說得清,沒人道得明。
事實
劉表託孤於劉備確有其事。那後來為何在諸葛亮提出攻打劉琮取得荊州的謀略時,劉備又不同意呢?《三國志·先主傳》曰:“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占據荊益是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興復漢室的基本方針,對於這個方針,劉備以一個“善”字給予了肯定,並從而與諸葛亮“情好日密”。那么,面對著荊州垂手可得的機遇,劉備卻棄而不取,並發出“吾不忍”的感慨,為何?筆者認為其原因:一是劉備所特有的“義”德決定的;二是劉表對他深情厚意。義與情的結合,觸動了他的靈魂,由此而產生了思與行。
翻開史籍,不難看出,劉備的政治生涯始終貫穿著一個“義”字。他以“義”處事,以“義”立身,以“義”興國。公元207年,他三顧諸葛亮於隆中時,就曾說過“欲信大義於天下”。他也曾經表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其人的特點,《三國志》本傳有記:“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建安十三年,曹操大軍壓境,時值危機關頭的劉備還不忘“駐馬呼琮”,使得“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這些都是劉備素積“義”德的表現。
“義”根植於心,他針對“宜從表言”之規勸,明確表態:“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
對於劉備,諸葛亮認為他“信義著於四海”。習鑿齒評論說:“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們的主觀意識來自於客觀實際,又反作用於客觀實際。以此,我們似乎可以說劉備骨質里“義”的產生,乃“物”之所及,具體地說,他不忍攻琮取荊,是主觀“義”念決定的,這種“義”念基於劉表對他的深情厚意。那么,劉表是否對劉備有著至深的情義呢?下面諸多史籍記載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一,據《三國志·先主傳》載:“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
《三國志·劉表傳》亦說:“劉備奔表,表厚待之”。被曹操進擊處於危難之中的劉備投奔劉表後,劉表自郊迎之,這種行為比之於曹操,不能不使劉備感激。不僅如此,而且,劉表對於劉備“厚待之”,“益其兵”,劉備既受到上賓禮遇,又壯大了自己所領軍隊的力量,這與處處以自己為敵的曹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劉備並非草木,孰能無情。後雖因荊州豪傑的歸附,“表疑其心,陰御之”,但劉表畢竟只是因產生懷疑而陰御劉備,在公共場合劉表對劉備並無過分之舉。
二,據《三國志·先主傳》注引《英雄記》曰:“表病,上備領荊州剌史。”
三,《三國志·先主傳》注引《魏書》:“表病篤,托國於備”。
四,劉備投靠劉表後,服從劉表的安排,竭盡全力來鞏固劉表的政權,如駐防新野、火燒博望、說表襲許等。
五,建安十三年,劉備在曹操大軍壓境之急,還不忘兩件事,一是駐馬呼琮。二是“過辭表墓,遂涕泣而去。”
從上可以看出,劉備與劉表之間有著深情厚意,特別是託孤的情誼,否則,被曹操視為天下英雄的劉備,不會置《隆中對》中提出的“占據荊益”於不顧,摒棄諸葛亮的建議,而發出“不忍攻琮取荊”的感慨。
對於不攻琮取荊的原因,《三國志·先主傳》注引《漢魏春秋》記載劉備說:“劉荊州臨亡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
劉表與劉備既是同宗,在政治上又存在著某些契合點。據《後漢書·劉表傳》記載:“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而劉備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所以劉備在遭遇曹操所難,投奔劉表時,劉表“便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
在政治上,劉表雖無稱霸天下之志,但“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擁戴漢廷。《後漢書·劉表傳》載:“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
對於曹操,劉表視為政敵。建安六年,劉備投奔劉表,“(表)益其(備)兵,使屯新野”,其目的就是派兵去抵禦曹操的南侵。
而劉備呢,終表之世竭力抗曹。荊襄數年,處心維護劉表的利益,一生堅持興復漢室的事業。相比蔡瑁、蒯越等眾臣,劉表自然把希望寄於劉備,故臨終託孤與自己同宗且政見上有著某種切合的劉備不是沒有可能的。
據習鑿齒《襄陽耆舊記》記載:“表疾病,琦歸省疾。琦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後之意……遂遏於戶外,使不相見,琦流涕而去”。蔡瑁、張允的這些擔心不無道理,因為該史籍記曰:“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稱其類己。”《後漢書·劉表傳》亦說:“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對於劉琮,劉表有言,“吾兒不才”。既如此,那么,劉表政權中為什麼會出現廢嫡立庶的現象呢?對此,《三國志·諸葛亮傳》明言:“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後漢書·劉表傳》也有言:“琮娶其(劉表)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在前引《襄陽耆舊記》中更有言:“(表)為少子琮納後妻之侄,遂愛琮而惡琦。至蔡氏有寵,其弟蔡瑁,又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琮有善,雖小必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於內。允、瑁頌德於外,愛憎由之,而琦益疏,乃出為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伺其過闕,隨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忿怒之色日發,誚讓之言日至。而琮竟為嗣矣。”由此可知,劉表對於二子態度的變化及其廢嫡立庶,並非表之初意,而是在蔡瑁、張允和後妻等人的唆使下使然,其目的是以便於控制荊州政權。如果劉表父子相感,托繼嗣於劉琦,那么,蔡氏在荊州的既得利益就可能失去,這一點蔡瑁、張允等人是很清楚的,故要遏止劉琦省父,以防不測。他們也似乎看到了潛伏在劉表身上這種不測的陰影,聞到了劉表政治氣味的異常。若使劉琦繼嗣之位成為現實,那么,首要即擺脫蔡氏集團的羈絆,這種政治措施,對於一州之牧的劉表來說不是智所不逮,而這正是蔡瑁、張允所擔憂的。
而要擺脫蔡氏集團的政治陰影,就要另立輔佐大臣,培植反對力量,而劉表臨逝前的荊州政治集團,用他自己的話講:“諸將並零落”,唯有劉備,既與劉表同宗,在政治上又與劉表存在著共同點,更與蔡瑁有隙。從《三國志》記載“劉琦深器亮”並“去梯求計於亮”,“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等來看,劉琦與劉備、諸葛亮關係甚密。劉表不可能不無所聞。因此,臨終舉國託孤於劉備不是不可能的。
劉表雖無四方之志,但“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的思想還是存在的。受其影響,劉琮亦欲“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
然而,其身邊的文輔武將如蒯越、韓嵩、劉先、傅巽等多持異意。韓嵩、劉先就曾勸說劉表“舉州以附曹公”。韓嵩更勸“表遣子入質”。王粲也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傅巽在為劉琮分析了當時形勢後,勸說劉琮歸操,並強調“願將軍勿疑。”蔡瑁“少為魏武所親”,從前引《襄陽耆舊記》所載:“瑁、允恐其(劉琦)見(劉)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後之意”來看,蔡瑁似在揣度劉表要動搖蔡氏集團在荊州的利益和地位,故對劉表是懷有二心的。
對於降操,劉表是堅決反對的,據《三國志·劉表傳》記載:“(蒯越勸劉表降曹)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表)欲殺嵩。”“其(劉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
這種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不僅動搖了劉表集團抗曹的決心,而且還將危及其在荊州的利益。而劉備與曹操有隙,在與劉表相處的幾年中多有反操言行。對此,劉表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劉表託孤於劉備是必然的。
廢嫡立庶在封建社會雖屢見不鮮,但實乃違背封建禮制的事情,結果多遭人嗤鼻,世之抨擊。劉表亦然,陳壽在《三國志·劉表傳》中就有評論曰:“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蹙,社稷傾覆。”而蔡瑁呢,“魏武雖以故舊待之,而為時人所賤,責其助劉琮,譖劉琦故也。”
對於自己所為逆反道德規範的非禮之舉,作為一州之牧、知名當世、號為“八俊”之一的劉表不可能不明。加之後嗣者並非劉表初愛,故其臨終應天順禮,移情初愛,托後繼於劉琦似有可能,雖然這種可能並未出現,但面對著“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且“二子素不輯睦”的局面,劉表也要安排好後世,託孤於劉備,以企永保江漢間。
劉備一直視曹操為賊,他要恢復漢室,就要攘除叛逆,故有與董承合謀誅曹操之舉。而曹操呢,視劉備為天下英雄,“不擊必為後患”,於是,“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劉備投奔劉表後,做了許多有益於劉表的事情,表達了堅定的反操決心。這在當時劉表政治集團一片降曹聲中實屬可貴。對此,劉表自然耳聞目睹。
曹操進伐劉表,是要吞併其所轄荊州,剝奪其在荊州的地位和利益,這當然是劉表所不願看到的。因此,在抗擊曹操南侵這個問題上,劉表與劉備便有了共同的語言、形成了統一的思想。因此,面對內外形勢,為了各自的利益,劉表託孤於劉備就在情理之中了。
總之,無論從劉表政治集團所面臨的內外形勢、劉備與劉表的關係、劉備思想及言行等方面來看,劉表臨終託孤於劉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