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神話創世神話
 中國上古神話
中國上古神話中國古代的創世神話,以盤古故事最為著名: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藝文類聚》卷一引徐整<三五曆紀》)>
這是一則典型的卵生神話,認為宇宙是從一個卵中誕生出來的,這種看法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初民中普遍存在。卵生是一種普遍的生命現象,先民們由此構想宇宙也是破殼而生的。宇宙卵生神話對中國的陰陽太極觀念有極重要的影響。同時,宇宙生成的人格化、意志化過程也反映了先民對人類自身力量的堅定信念。
盤古不僅分開了天和地,同時也是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的締造者。另一則神話說他死後,呼吸變為風雲,聲音變為雷霆,兩眼變為日月,肢體變為山嶽,血液變為江河,發髭變為星辰,皮毛變為草木……。這種“垂死化身”的宇宙觀,暗喻了人和自然的相互對應關係。中國古代關於宇宙萬物的神話還有多種表達形態,如帝舜的妻子羲和生育了十個太陽,帝俊的妻子常羲生育了十二個月亮等。《山海經》中所記錄的燭龍之神,他的生理行為就直接引發了晝夜、四季等自然現象。這些都表明了先民對宇宙等自然現象積極探索的精神。
散失和演化
篡改塗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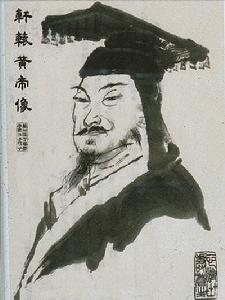 中國上古神話
中國上古神話中國古代神話的原始狀態是十分豐富多彩的,但經過歷史潮水的沖刷,如今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大多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這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中國古代神話之所以散失,除了它沒有受到文人的重視之外,神話的歷史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所謂神話歷史化,就是把神話看成是歷史傳說,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為人的祖神,並把神話故事當做史實看待,構成了一些虛幻的始祖以及它的發展譜系。這一文化現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現過。中國的神話歷史化,是史家、思想家們自覺或不自覺的行為。一般認為,古代神話形象經歷了從動物形、半人半獸形到人形這么一個發展過程。在正統的史家或儒家的典籍中,那種半人半獸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殺殆盡了,因為這種形象很難被納入歷史譜系之中,而且也違背了理性化的原則。此外,還有其他一些觸犯了理性化原則的神話,也都遭到刪削。如司馬遷所說:“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史記·五帝本紀》)相當一部分神話因此得不到史家的認可,因而沒有進入載籍。這些,我們已無從考察了。有些有幸被文人筆錄,但在此後的流傳過程中,又被無情地刪削。如《列女傳》古本所錄舜的神話中,有二女教舜服鳥工龍裳而從井廩之難中逃脫的情節,今本《列女傳》中就蕩然無存了。再如《淮南子》古本載嫦娥奔月神話時說嫦娥“託身於月,是為蟾蜍,而為月精”,今本《淮南子》亦不存。其原因可能都是“不雅馴”。
神話歷史化的另一個方法就是改造。即對神話進行歪曲的解釋,使其成為某種現實事件,從而成為構築遠古歷史的一塊基石。這種例子,在儒家傳統典籍中比比皆是,從《尚書》、《左傳》、《國語》,一直到《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都是如此,宋代羅泌所作《路史》是其集大成之作。改造的結果是使神話大量消亡,歷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譜系更加嚴密。比如《左傳·昭公十七年》載: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量度,夷民者也。
我國東方部族中很多是以鳥作為圖騰的,其中也必然流行著不少有關鳥的神話。而在這裡,這些有關圖騰鳥的神話則被改造為一系列的官名,並按照後世的社會官僚系統組織起來。
神話歷史化在春秋早期就已開始了,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繼承並發揚了這一傳統。孔子就曾說:“不語怪力亂神”,還直接參與了對神話的改造。據《尸子》(孫星衍輯本)卷下載,當子貢向孔子提及黃帝有四張面孔的神話時,孔子說:“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此謂之四面也。”四張面孔被解釋為四個人面朝四個方向,“黃帝四面”的神話就變成了一件有關治理天下的史實。另一則有關夔的神話,在孔子那裡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作為聖人的孔子對待神話的態度對後世文化有著重大的影響。
演變仙話
中國古代神話發展變化的另一條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為仙話的一個來源。仙話一般講述的是通過修煉或仙人導引,以達到長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在仙話中,我們能發現不少古代神話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是黃帝和西王母。《史記·封禪書》所記黃帝在荊山腳下鑄鼎,鼎成,有龍垂鬍髯在鼎上,迎他騎龍升天一事。這則故事有著明顯的仙話的痕跡。而黃帝戰勝蚩尤,在仙話中則被歸功於“九天玄女”“授(黃)帝以三官五意陰陽之略,……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廣博物志》卷九引《玄女法》)。同樣,竊藥奔月的嫦娥、操不死之藥的西王母,也是仙話中的重要人物。神話轉變為仙話是有限的,它一般集中在特定的幾個人物身上,且有類似於修煉、服藥、升天不死的情節。但仙話的文化意蘊要比神話淡薄得多,在仙話中,那些神話人物所蘊含的民族精神、審美品質,都被嚴重地削弱了。
古代神話對後世作家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正如馬克思所說“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在文學中,我們能看到神話精神的延續、光大。神話對文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文學創作的素材,一是直接影響文學創作的思維方式、表現手法、欣賞效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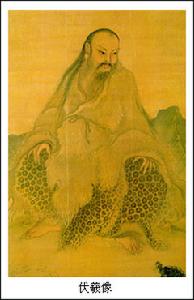 中國上古神話
中國上古神話中國神話以其廣博精深的意蘊,生動活潑的表現力,為後世文學奠定了基礎。神話除了被後人直接載錄之外,還為各類文學作品提供素材。在先秦散文中,《莊子》一書以“意出塵外,怪生筆端”、“縹緲奇變”(《藝概·文概》)著稱,《莊子》說理的精妙和文風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神話。如《逍遙遊》之鯤鵬變化,《應帝王》之“鑿破混沌”,這兩則神話為全文抹上了變幻奇詭的浪漫色彩。至於曹植採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創作了膾炙人口的《洛神賦》,更是利用神話素材進行的一次成功的創作。
用神話入詩的現象,在中國文學史上比比皆是,如《詩經·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種種神跡,楚辭《離騷》中各種神靈紛至沓來。此後的詩人,尤其是浪漫主義詩人常常以神話入詩,如李商隱《瑤池》詩云:“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就是對神話意象的妙用。小說、戲曲採用神話作素材的也很多,它主要是藉助於神話的奇特的想像,利用神話形象或神話情節進行再創作。如唐代李朝威的小說《柳毅》,創造了一個優美的愛情神話。
明清神魔小說對神話的採用和重塑,達到了此類文學的最高點,其代表作為《西遊記》,孫悟空、豬八戒以及他們的騰雲駕霧、七十二般變化成了中國文學中最有影響的故事之一。從孫悟空身上,我們不難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啟、“銅頭鐵額”的蚩尤、“與帝爭位”的刑天以及淮渦水怪無支祁的影響。此外,如《聊齋志異》、《鏡花緣》、《封神演義》、《紅樓夢》中也有不少發人深省的神話情節。可以說,古代神話作為素材,遍布在中國古典文學的每一個角落,它經文學家的發掘、改造,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發出光芒,使文學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
總體影響
意識含蘊
神話作為原始先民意識形態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先民對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著濃郁的情感因素。這些神話意象在歷史中固定下來,通過文化積澱,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並總是不失時機地通過各種形式,在後代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以上所述,主要採用了現代文學批評中原型理論。 也就是說,神話對於文學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它是文學家的素材,更為重要的是,那些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神話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讀者領入先民曾經有過的那種深厚的情感體驗之中,從而緩釋現實的壓力,超越平凡的世俗。神話作為原型的意義要比它作為素材的意義更為重要。當屈原在現實世界中屢遭打擊而悲苦無依的時候,他就毅然地轉向古老的神話:龍鳳結駟,巡遊天界,四方求女。是神話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從現實世界中超越出來,支持他的人格,撫慰他心靈的創傷。
同時,由《離騷》所抽象概括的某些意象,由於它深沉的神話背景和屈原創造性的提煉,而成為一種穩固的神話原型,在中國文學史上,在一代代作家的筆下傳遞。而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則不僅是將神話看作素材,而是當成全部的精神寄託,是對這個不公平的世界的厭棄和對神話感情、神話世界的皈依。 正如榮格所說的那樣,“一個用原始意象說話的人,是在同時用千萬個人的聲音說話。……它把我們個人的命運轉變為人類的命運,它在我們身上喚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這些力量,保證了人類能夠隨時擺脫危難,度過漫漫的長夜。”可以說,屈原、蒲松齡等作品都體現了神話原型的精髓和力量。
精神希翼
古代豐富多彩的神話,是遠古歷史的回音,它真實地記錄了華夏民族在它童年時代的瑰麗的幻想、頑強的抗爭以及步履蹣跚的足印。同樣,它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源頭,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及其特徵。首先,中國古代神話體現了深重的憂患意識。中華民族發源於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廣闊地域。而在3000年前,黃河流域除了不斷出現洪水和旱災以外,還分布著很多密林、灌木叢和沼澤地,其中繁衍著各種毒蛇猛獸,從《山海經》中那些能帶來災異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獸或半禽半獸的描述中,人們能了解到先民對生存環境的警懼之情。為了順利地生存和發展,先民們在滿懷希望中必須切實地體驗現實的艱難,並作不懈的努力。比如在女媧、羿和禹的神話中,無不以相當的份量描繪了人類的惡劣處境,神性主人公們都能正視現實的災難,並通過鍥而不捨的辛勤勞作和鬥爭,戰勝自然災難。神話特彆強調諸神不辭辛勞的現實精神,反映了先民對現實的苦難有著深刻的體驗。
其次,古代神話具有明確的厚生愛民意識。對百姓民眾生命的愛護和尊重,是中國文化的一貫精神,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69],就反映了這種思想。中國古代神話在展示人類惡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時,還為人類塑造了一些保護神,如前所說之女媧、后羿等。此外,還有一些神話形象如龍、鳳等,“見則天下安寧”,它們的出現給人帶來了祥瑞和安慰。重生意識還包括對個體生命的珍惜和對生命延續的渴望。
此外,《山海經》中“不死之國”、“不死民”、“不死之藥”的傳說,也說明了中國神話對人類生命珍視。古代神話還表現了自然和人之間的親和關係,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厚生意識。如主日月之神羲和,不但要職掌日月的出入,“以為晦明”,調和陰陽風雨,還要“敬授人時”,以利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再如春神句芒的到來,“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給人類帶來了美好的希望。這些都體現了人們對和自然和諧相處的願望,在本質上是對保護和發展生命的希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