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老舍的短篇小說一般採用單線結構,但《黑白李》卻採用了類似魯迅《藥》的雙線結構,在傳奇故事的外殼下,隱藏著革命文學的內容,構思非常獨特。
先讓我們略述第一條情節線--傳奇故事:
李氏兄弟二人,父母均已去世,兩人年齡相差5歲,相貌酷似。哥哥臉上有個黑痣,叫黑李,弟弟臉上無痣,便叫白李。黑李是個深受傳統道德觀念影響的舊式人物,受母親遺命,極力地維護家庭的和美,不管什麼事情都讓著弟弟,只要能保全兄弟之誼,即使是情人、家產和性命,他也在所不計。白李卻是個受到新思潮影響的現代青年,敢說敢為,不但勇於犧牲自己,也不吝犧牲他人,惟對哥哥,尚存一絲憐憫。白李計畫要辦一件大事,為了不連累哥哥,堅持要分家。黑李知道弟弟的這番心意後,悄悄地蝕掉臉上的黑痣,準備替代弟弟犧牲。不久,白李因組織洋車夫砸電車被當局通緝,黑李便冒充頂罪,替弟弟慨然赴死。白李逃脫追捕後,繼續從事他的“砸地獄的門”的事業。
黑李愛護弟弟,純出於傳統的考悌道德觀,沒有任何的社會和政治動機;他的勇於犧牲的精神力量來自傳統道德與基督獻身精神的融合,沒有上升到為革命或為大眾的層面。因此,長期以來,這篇作品往往被讀者和研究界看成是“李代桃僵”傳奇故事的現代翻版,並樂於對這兩個性格迥異的人物作道德判斷或價值判斷。《黑白李》問世不久,天津《益世報》在一篇介紹新創刊的《文學季刊》的文章中便對其進行了評論,文章雖然注意到了小說的“理論和故事”並重的特點,但注意力很快便轉到作品的傳奇外殼上,討論著作品中兩個不同性格人物的命運——黑李、白李誰該存,誰該亡?肯定了作家對“黑李犧牲”的描寫,並讚揚作“在技巧和意識上,都有著很明顯的力量”。
再讓我們看第二條情節線——革命內容:
白李參加革命組織後,擔負起組織洋車夫工人鬥爭的任務。他為了不連累哥哥,毅然與家庭斷絕關係。他有意識地接近家裡拉包月的車夫王五,啟發他的階級覺悟,和他交上了朋友。不久,北京市政交通方式發生變革,電車道竣工,電車將投入運營,洋車夫的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白李從哥哥那兒索取了一千元錢用作革命經費,通過王五把洋車夫組織起來,在電車公司出車的那天發起暴動,砸毀電車多輛。暴動遭到當局的殘酷鎮壓,工人被捕多人,白李潛逃,黑李被誤捕後,與參與暴動的工人一起被當局處決。白李僥倖脫逃,輾轉外地繼續從事革命工作。
如果能夠關注到這第二條情節線,那么,無論從作品的情節、人物、語言及與現實社會政治鬥爭的關係進行分析,我們都可以看出《黑白李》確實是在努力地向革命文學靠攏。
革命文學運動興起之初,成仿吾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曾為“革命文學”下過定義,他指出,革命文學應該具有三個要素,即:“階級意識”、“農工大眾的語言”和“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瞿秋白擔任左聯實際領導人之後,更加具體地指出,革命文學應該寫革命的“大事變”、勞動人民的鬥爭和地主資產階級的罪惡等題材;他反對當時一些作品中所流露的淺薄的人道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等傾向,認為"普洛大眾文藝的鬥爭任務,是要在思想上武裝民眾,意識上無產階級化"(《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
不管是以前期還是以後期革命文學的理論標準來衡量,《黑白李》都具備著入圍的資格。首先,它反映了一場重大的社會事件:
約摸五點多鐘吧,王五跑進來,跑得連褲子都濕了。"全——揍了!"他再也說不出話來。直喘了不知有多少工夫,他才緩過氣來,抄起茶壺對著嘴喝了一氣。"啊!全揍了!馬隊衝下來,我們才散。小馬六叫他們拿去了,看得真真的。我們吃虧沒有傢伙,專仗著磚頭哪行!小馬六要玩完。"
第二天早晨,報紙上登出——砸車暴徒首領李——當場被獲,一同被獲的還有一個學生,五個車夫。
其次,作品通過洋車夫王五的口述描寫了白李啟發動員洋車夫們參加鬥爭的過程:
四爺(指的是白李)年青,不拿我當個拉車的看。
四爺和我聊起來的時候,他就說,憑什麼人應當拉著人呢?他是為我們拉車的——天下的拉車的都算在一塊兒——抱不平。
四爺不管我的腿,可是管我的心;二爺是家長里短,可憐我的腿,可不管這兒。
你知道,電車道快修完了?電車一開,我們拉車的全玩完!這可不是為我自個兒發愁,是為大傢伙兒。
四爺明白這個;要不怎么我倆是朋友呢。四爺說:王五,想個辦法呀!我說:四爺,我就有一個主意,揍!四爺說:王五,這就對了!揍!一來二去,我們可就商量好了。
作品甚至流露出揚棄"淺薄的人道主義"的思想傾向:
他們哥兒倆的勁兒——心裡的勁兒——不一樣。二爺吧,一看天氣熱就多叫我歇會兒,四爺就不管這一套,多么熱的天也得拉著他飛跑。
他當然是不怕犧牲,也不怕別人犧牲,可是還不肯一聲不發的犧牲了哥哥——把黑李犧牲了並無濟於事。現在,電車的事來到眼前,連哥哥也顧不得了。
作品的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更保持著老舍一貫的京腔京韻和大眾口語的風格,與當時左翼中人歐化的語言不可同日而語。
寫作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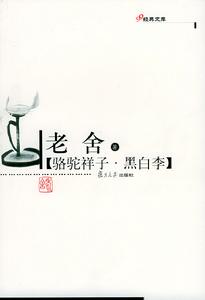 《黑白李》
《黑白李》《黑白李》反映的是一樁真實的歷史事件!
1929年10月22日,就在老舍創作《黑白李》的前4年,北平爆發了一場震驚全國的洋車夫"暴動"事件。
1929年10月22日,北平洋車夫在工會領導下,全城同時發動,砸毀電車數十輛,當即遭到國民黨軍警的殘酷鎮壓,工會被解散,工會領導悉數被捕,拘押洋車夫千餘,審判後驅逐800餘人,處決4人。
"參加暴動者至少有二萬五千人,參加的成分不只是人力車夫,還有工程隊,清道夫,溝工隊,大車夫……等等。武裝行動的地點,自西單牌樓,西門大街,天橋,東單,東四,北新橋,至西總布胡同等,簡直瀰漫了整個北京市。搗毀電車五十餘輛,打傷工賊走狗數人,與全北平市的警察,軍隊,憲兵肉搏七八小時(自下午1時至下午8時) ","此次鬥爭中,北平軍警屠殺工友四十餘人,殺傷數百人,拘捕一千六百餘人,審判結果,驅逐九百餘人出境,監禁數百人,使幾千個老幼窮人失去飯碗,凍餓至死。"
事發期間,老舍不在北京,甚至不在國內,他於1924年赴英,1930年春始從新加坡返國。回到北京時,他還能感受到這場數月前發生的事件對於北京平民社會的震撼,他還能從那些拉洋車的親朋近鄰的口述中聽到發生在這個期間的種種傳奇故事,他還能從新聞報刊觸摸到這場事件的餘波。不論是出自人道主義,出自社會責任心,或是出於政治敏感,老舍不可能不對這場事件有所反映,他在《黑白李》和其後的《駱駝祥子》中將這樁工潮納入視野幾乎是必然的。
老舍的《黑白李》雖然有意靠攏革命文學運動,但由於表現了一個"錯誤的事件"(出於單純經濟目的的破壞先進交通工具的"盲動"),描寫了一個"錯誤的人物"(國民黨改組派),而被政治意識極強的中國左中右翼文壇集體拋棄。
這不僅是老舍《黑白李》的悲劇,更是北平洋車夫們的悲劇。
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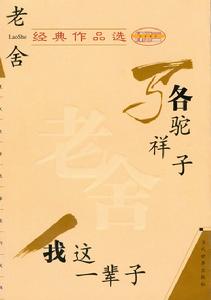 《黑白李》
《黑白李》1950年8月,老舍在《〈老舍選集〉自序》中這樣提到這篇作品:
在今天看起來,《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於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當時,那確足以證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變動。誠然,在內容上,我沒敢形容的白李怎樣的加入組織,怎樣的指導勞苦大眾,和怎樣的去領導鬥爭,而只用傳奇的筆法,去描寫黑李的死;可是,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該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不管怎么說吧,我總比當時那誣衊前進的戰士的人,說他們雖然幫助洋車夫造反,卻在洋車夫跑得不快的時候踢他兩腳的,稍微強一點了。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讀出老舍久藏於心中的抱怨:他在《黑白李》中努力地表現革命的思想,表現"革命"的事件和"革命"的人物,作品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自以為思想傾向是正確的;無論如何要比當年那些否定洋車夫暴動的人,比那些指責工人運動領導者的人要好得多。
老舍無法明白,《黑白李》之所以當年不為左翼文壇所重視,後來不得研究界的好評,最直接的原因應該是作品所表現的車夫"暴亂"事件的政治性質問題。
30年代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將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搬運到中國後,左翼中人無不以"政治-文藝"一元論者自居,機械地以"經濟-政治"的框架來規範文藝的主題、題材和人物。1932年,谷非(胡風)在《文學月報》1卷5-6期上發表《粉飾,歪曲,鐵一般的事實》,以上述理論橫掃《現代》雜誌,將其撰稿者統統歸於"第三種人",初顯"輿論一律"的霸氣;文中對杜衡《懷鄉病》的批判便是依據著"經濟-政治"的框架來濫加指責的。杜衡在小說中述說了一個農村個體船戶因汽車的競爭而破產,淪為劫車匪徒,終被捕殺的故事,表現近代資本主義的壓迫和中國農村的破產的社會場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然而,胡風卻判定作品的主題是表現"機械化和鄉民生活的衝突",指責作者"把這個悲劇的原因推到抽象的'機械'身上",嘲笑作者是"迷戀'自然'的機械憎惡者!"。
《黑白李》所表現的正是《懷鄉病》同類的題材,只是將場景從鄉村搬到了城市,船戶變成了洋車夫。無怪乎,左翼中人對它不屑一顧!
第一,白李是否"共產黨員",還應存疑。老舍在自述中僅提到曾在《大明湖》中寫過一個共產黨員,如果白李也是作為"共產黨員"來描寫的,他沒有必要隱瞞。第二,當年北平車夫"暴亂"事件的組織和領導者是國民黨改組派,共產黨並沒有介入當年的洋車夫暴動事件,這是不爭的事實。第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作品所反映的歷史事件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先進的生產方式取代舊的生產方式時所帶來的"人道主義危機",並不具有論者所指出的革命性質。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高度評價西方工業革命對東方世界的衝擊,他寫道:
"那些幾千年來沒有進步的國家,例如印度,都已經進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國現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今天英國發明的新機器,一年之內就會奪去中國千百萬工人的飯碗。這樣,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繫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作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裡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餘各國。"
此外,老舍在作品中用傳奇的筆法所描寫的是黑李,並不是白李。至於他為什麼說"黑李該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似乎應該從作品人物形象、人物關係的描寫入手,再進行深入的探索。
首先看哥哥黑李--黑李似乎完全不把自己的生命當回事兒,他活著的全部目的就是為弟弟"代死",他並不介意弟弟幹了些什麼,是殺人放火、打家劫舍,還是見義勇為、扶危濟困,全都不在乎。這樣的典型人物在中國現代文學人物長廊中是絕無僅有的。由於時代和所受教育的影響,我們這一代人難以理解這樣的典型人物的現實依據;但另一種文化環境中的學者卻不以為怪,台灣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董挽華在《中國五四傑出作品與基督教》中寫道:"受洗皈依耶穌基督的老舍……在其傑出作品裡活化基督的救贖,代死與犧牲"。讓我們定睛細看,真能清晰地從黑李身上看到耶穌的影子:耶穌來到世上的目的就是為人類贖罪,他自願地背上十字架,從死亡中得到永生;黑李一生也是除死之外別無所求,求仁得仁,功德圓滿!只有跨越時代和文化的軫域,才能理解老舍所說的"黑李該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的宗教意蘊。
黑李是基督式的典型人物,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他的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與所"代死"的對象沒有直接的關係;換言之,黑李的死並不能證明白李的有價值,正如耶穌的死並不是為了證明世人無罪一樣。老舍謹慎地把握著表現的"度",他讓黑李平靜滿足地死去,既沒有讓"看客"們看出了"悲壯劇",也沒有讓他們看了"滑稽劇":
毒花花的太陽,把路上的石子曬得燙腳,街上可是還擠滿了人。一輛敞車上坐著兩個人,手在背後捆著。土黃制服的巡警,灰色制服的兵,前後押著,刀光在陽光下發著冷氣。車越走越近了,兩個白招子隨著車輕輕地顫動。前面坐著的那個,閉著眼,額上有點汗,嘴唇微動,象是禱告呢。
這段描寫,幾乎是《四福音書》中基督赴死情景的翻版。
另外一個人物是弟弟白李——老舍把他當作"革命黨"進行摹畫,在這個人物身上,灌注了一些作家當時並不理解也不認同的思想觀念。諸如待人接物、愛情婚姻觀、親情友情等倫理道德層面的表現,作家完全採用對比的寫法,黑李這樣,白李就偏那樣,在此不贅。舉其大者,頗可以見出作家對他的主觀評判:
"他在大學還沒畢業,可是看起來比黑李精明著許多。他這個人,叫你一看,你就覺得他應當到處作領袖。每一句話,他不是領導著你走上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綁在斷頭台上。"
"他當然是不怕犧牲,也不怕別人犧牲,可是還不肯一聲不發的犧牲了哥哥——把黑李犧牲了並無濟於事。現在,電車的事來到眼前,連哥哥也顧不得了。"
這兩段議論深有文心,只要敢於正視,無須細加品味,作家的褒貶態度,一目了然。老舍在描摹白李時,並不想掩飾心中的厭惡感,他這樣寫道:"我忽而覺得是和一個頂熟識的人說話,忽而又象和個生人對坐著。"確實,30年代的老舍絕然沒有達到能理解白李這樣的"革命黨"的程度。
20、30年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然有著參與社會政治改革的熱情,但對於政黨的活動及方式普遍缺乏理解,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蘇聯政府拒之於國門之外的進步盲詩人愛羅先珂。他在中國居留期間曾發表《智識階級的使命》的演說,其中談到:
"我們沒有權利強迫別人為我們的理想而生死。無論這些理想有多么的高尚多么尊貴,我以為我們有為國家為社會為人類而犧牲自己的權利,卻沒有為同類的事情強迫別人去死的權利。"(愛羅先珂《智識階級的使命》,載晨報副刊1922年3月7日)
與愛羅先珂非常接近的魯迅當年也執著這種觀點,他信奉"我以我血薦軒轅",卻在《娜拉走後怎樣》中特彆強調:"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
從這種角度審視老舍的"把你綁在斷頭台上"之類的議論,作家對白李的態度是褒是貶,是讚賞還是批評,應該是很清楚的。
現實意義
《黑白李》並不能證實老舍當年對中國革命的認識有著根本的改變,只能證實其現實主義精神有所深化。這篇作品在白李性格塑造上的最大特點只是如實地表現了作家心目中的"革命黨"形象,能把想像中模糊存在著的這類人物清晰地搬到紙面上,這是作家的本事,不管"他"與實際的革命黨有多大的距離。
老舍不是個政治意識十分明晰的作家,他的道德觀念始終強於政治觀念,終其生也未有改變。他在《〈老舍選集〉自序》所透露出的抱怨,充分證實了他對主流文藝取捨文藝的政治標準的不理解,甫從美國歸來編選的這本選集,其選材標準便充分體現出認識上的模糊狀態,集中選了《黑白李》、《斷魂槍》、《月牙兒》、《上任》和《駱駝祥子》(節選)等5篇,選擇《黑白李》的理由是"說明我怎么受了革命文學理論的影響",而選擇後4篇的理由是它們都寫的是"苦人"。他始終不明白,無論他怎樣努力地靠攏和適應主流文藝,他的這些作品在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眼中充其量只能是"批判現實主義"的,距離"革命現實主義"的要求還差著十萬八千里。
這是老舍的悲劇,也是《黑白李》的悲劇。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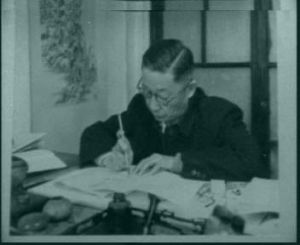 老舍
老舍老舍 (1899~1966) 現、當代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另有筆名絮青,鴻來、非我等。滿族,北京人。曾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 1918年北京師範學校畢業後任國小校長和中學教員。1924年赴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漢語講師,閱讀了大量英文作品,並從事小說創作, 1930年回國後任濟南齊魯大學、青島山東大學教授。抗日戰爭爆發後南下赴漢口和重慶。 1938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他被選為理事兼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日常工作。在創作上,以抗戰救國為主題,寫了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 1946年應邀赴美國講學1年,期滿後旅居美國從事創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應召回國,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等職。參加政治、社會、文化和對外友好交流等活動,注意對青年文學工作者的培養和輔導,曾因創作優秀話劇《龍鬚溝》而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棄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