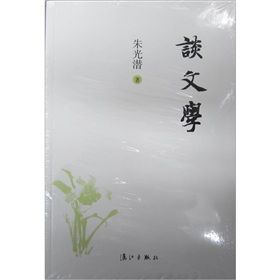內容簡介
《談文學》中所述皆為朱光潛先生多年“學習文藝的甘苦之言”,作 圖書封面
圖書封面作者簡介
朱光潛(1897-1986),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我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主要著作有《文藝心理學》、《悲劇心理學》、《西方美學史》、《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修養》、《談美》、《談論》、《談文學》等。目錄
序文學與人生
資稟與修養
文學的趣味
文學上的低級趣味(上):關於作品內容
文學上的低級趣味(下):關於作者態度
寫作練習
作文與運思
選擇與安排
咬文嚼字
散文的聲音節奏
文學與語文(上):內容、形式與表現
文學與語文(中):體裁與風格
文學與語文(下):文言、白話與歐化
作者與讀者
具體與抽象
情與辭
想像與寫實
精進的程式
談翻譯
精彩書摘
拉丁文中有一句名言:“詩人是天生的不是造作的。”這句話本有不可磨滅的真理,但是往往被不努力者授為口實。遲鈍人說,文學必須靠天才,我既沒有天才,就生來與文學無緣,縱然努力,也是無補費精神。聰明人說,我有天才,這就夠了,努力不但是多餘的,而且顯得天才還有缺陷,天才之所以為天才,正在他不費力而有過人的成就。這兩種心理都很普遍,誤人也很不淺。文學的門本是大開的。遲鈍者誤認為它關得很嚴密不敢去問津;聰明者誤認為自己生來就在門裡,用不著摸索。他們都同樣地懶怠下來,也同樣地被關在門外。從前有許多迷信和神秘色彩附麗在“天才”這個名詞上面,一般人以為天才是神靈的憑藉,與人力全無關係。近代學者有人說它是一種精神病,也有人說它是“長久的耐苦”。這個名詞似頗不易用科學解釋。我以為與其說“天才”,不如說“資稟”。資稟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只有程度上的等差,沒有絕對的分別,有人多得一點,有人少得一點。所謂“天才”不過是在資稟方面得天獨厚,並沒有什麼神奇。莎士比亞和你我相去雖不可以道里計,他所有的資稟你和我並非完全沒有,只是他有的多,我們有的少。若不然,他和我們在智慧型上就沒有共同點,我們也就無從了解他、欣賞他了。除白痴以外,人人都多少可以了解欣賞文學,也就多少具有文學所必需的資稟。不單是了解欣賞,創作也還是一理。文學是用語言文字表現思想情感的藝術,一個人只要有思想情感,只要能運用語言文字,也就具有創作文學所必需的資稟。
就資稟說,人人本都可以致力文學;不過資稟有高有低,每個人成為文學家的可能性和在文學上的成就也就有大有小。我們不能對於每件事都能登峰造極,有幾分欣賞和創作文學的能力,總比完全沒有好。要每個人都成為第一流文學家,這不但是不可能,而且也大可不必;要每個人都能欣賞文學,都能運用語言文字表現思想情感,這不但是很好的理想,而且是可以實現和應該實現的理想。一個人所應該考慮的,不是我究竟應否在文學上下一番功夫(這不成為問題,一個人不能欣賞文學,不能發表思想情感,無疑地算不得一個受教育的人),而是我究竟還是專門做文學家,還是只要一個受教育的人所應有的欣賞文學和表現思想情感的能力?
這第二個問題確值得考慮。如果只要有一個受教育的人所應有的欣賞文學和表現思想情感的能力,每個人只須經過相當的努力,都可以達到,不能拿沒有天才做藉口;如果要專門做文學家,他就要自問對文學是否有特優的資稟。近代心理學家研究資稟,常把普遍智力和特殊智力分開。普遍智力是施諸一切對象而都靈驗的,像一把同時可以打開許多種鎖的鑰匙;特殊智力是施諸某一種特殊對象而才靈驗的,像一把只能打開一種鎖的鑰匙。比如說,一個人的普遍智力高,無論讀書、處事或作戰、經商,都比低能人要強;可是讀書、處事、作戰、經商各需要一種特殊智力。儘管一個人件件都行,如果他的特殊智力在經商,他在經商方面的成就必比做其他事業都強。對於某一項有特殊智力,我們通常說那一項為“性之所近”。一個人如果要專門做文學家就非性近於文學不可。如果性不相近而勉強去做文學家,成功的固然並非絕對沒有,究竟是用違其才;不成功的卻居多數,那就是精力的浪費了。世間有許多人走錯門路,性不近於文學而強做文學家,耽誤了他們在別方面可以有為的才力,實在很可惜。“詩人是天生的不是造作的”這句話,對於這種人確是一個很好的當頭棒。
但是這句話終有語病。天生的資稟只是潛能,要潛能成為事實,不能不惜人力造作。好比花果的種子,天生就有一種資稟可以發芽成樹、開花結實,但是種子有很多不發芽成樹、開花結實的,因為缺乏人工的培養。種子能發芽成樹、開花結實,有一大半要靠人力,儘管它天資如何優良。人的資稟能否實現於學問事功的成就,也是如此。一個人縱然生來就有文學的特優資稟,如果他不下功夫修養,他必定是苗而不秀,華而不實。天才愈卓越,修養愈深厚,成就也就愈偉大。比如說李白、杜甫對於詩不能說是無天才,可是讀過他們詩集的人都知道這兩位大詩人所下的功夫。李白在人生哲學方面有道家的底子,在文學方面從《詩經》、《楚辭》直到齊梁體詩,他沒有不費苦心模擬過。杜詩無一字無來歷為世所共知。他自述經驗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西方大詩人像但丁、莎士比亞、歌德諸人,也沒有一個不是修養出來的。莎士比亞是一般人公評為天才多於學問的,但是誰能測量他的學問的深淺?醫生說,只有醫生才能寫出他的某一幕;律師說,只有學過法律的人才能了解他的某一劇的術語。你說他沒有下功夫研究過醫學、法學等等?我們都驚訝他的成熟作品的偉大,卻忘記他的大半生精力都費在改編前人的劇本,在其中討訣竅。這只是隨便舉幾個例。完全是“天生”的而不經“造作”的詩人,在歷史上卻無先例。
孔子有一段論學問的話最為人所稱道:“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這話確有至理,但亦看“知”的對象為何。如果所知的是文學,我相信“生而知之”者沒有,“困而知之”者也沒有,大部分文學家是有“生知”的資稟,再加上“困學”的功夫,“生知”的資稟多一點,“困學”的功夫也許可以少一點。牛頓說:“天才是長久的耐苦。”這話也須用邏輯眼光去看,長久的耐苦不一定造成天才,天才卻有賴於長久的耐苦。一切的成就都如此,文學只是一例。
天生的是資稟,造作的是修養;資稟是潛能,是種子;修養使潛能實現,使種子發芽成樹,開花結實。資稟不是我們自己力量所能控制的,修養卻全靠自家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