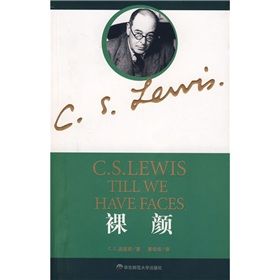編輯推薦
一部好的文學作品,蘊含了人類共通的經驗或情感,以一種被精心設計過的形式呈現出來。當讀者在品讀時,就好比進入另一個世界,隨著作者安排過的字句,隨著對文字的體認與想像,逐漸引發出認同的情感,而產生共鳴。C.S.Lewis的《裸顏》,可說是一部小說中的經典之作。·《人生不設限》超級暢銷勵志書>>·《史上最好玩教養法》獨家50折熱賣>>
內容簡介
北歐、肥腴月灣、愛琴海沿岸、尼羅河畔……凡是神話發達的地方都流傳著一則類似的神話故事,雖然情節各依地理風貌和民族想像變化多致——有一位神,死了,卻又復活;他的死給大地帶來新的生機。在牛津大學教授古典文學的大學者C.S.路易斯,將這些神話玩味再三,仿佛傾聽到上帝要傳遞給人類“道成肉身”的信息,亘古以來,沿著人類意識的幽峽不斷迴蕩,至今不絕……
目錄
譯者序:託夢——夢覺邊緣的啟示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童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童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童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精彩書摘
第一章我老了,無牽無掛,再也不怕神發怒了。丈夫、孩子,我沒有;也幾乎沒有叫人牽腸掛肚的朋友,好讓諸神藉著他們折磨我。至於我的身軀,這具枯瘦卻仍需天天盥洗、餵養、妝扮的肉體,只要他們願意,盡可趁早毀滅。王位的繼承已有了著落。我的冠冕將傳給侄兒。
既然毫無牽掛,在本書中我將直言不諱,寫下幸福在握的人沒膽子寫的事。我將揭發神的暴行,尤其是陰山上的那位。換句話說,我要從頭訴說他如何播弄我,就像申訴給法官聽,請他評評理。可惜的是,神和人之間並沒有仲裁人,陰山的神也不會做出答辯。天災和瘟疫不算答辯吧!我決定採用師父傳授的希臘文寫,因為若有機緣,說不定哪天有個人從希臘來,住進這宮裡翻讀這本書,他會把這本書的內容傳講給希臘人聽。那裡的人享有言論自由,可以放膽談論有關神的事,他們當中的智者或許能辨明我的控訴是否正確,也能判斷陰山神是否無辜,萬一他做出答辯的話。
我名叫奧璐兒,是葛羅國國王特婁的大女兒。從東南方來的旅人會發現葛羅城位在舍尼特河的左岸,由南方邊陲重鎮寧寇北行至此,約需一天光景。城建在岸邊不遠、婦女步行約莫走二十分鐘的地方,這是因為舍尼特河每年春天會固定泛濫。也因這樣,到了夏天,河的兩岸布滿乾泥,蘆葦叢生,水鳥成群棲集。河對岸,安姬神宮與葛羅城遙遙相對,由安姬神宮一逕往東北行,不久便抵達陰山山麓。那恨我入骨的陰山神正是安姬的兒子。他並不住在神宮中,安姬獨自坐鎮那裡。她坐鎮的內宮黝黑得讓人認不清她的樣子。不過,每到夏天,陽光從宮頂的通風孔瀉進來,人們可以依稀看見她的相貌。這位威風凜凜的女神原是一塊沒頭沒臉又沒手臂的黑色大石。我的師父,大家稱他“狐”,說,安姬相當於希臘人的阿芙洛狄特;但本書的人名地名,我一律採用葛羅語的稱法。
我將從母后去世——也就是我斷髮——那天說起。根據習俗,服喪的女兒必須把頭髮剃光。後來狐告訴我,這習俗乃仿自希臘。葩妲,我們的奶媽,把我和蕾迪芙帶到宮外,在沿著陡峭的山坡修築的御花園坡底斷髮。蕾迪芙是我的妹妹,比我小三歲;那時,父王只有我們兩個孩子。當葩妲把著剃刀一綹綹剃掉我們的頭髮時,站在一旁的女僕們每隔一會兒便捶胸痛哭,哀悼母后的崩亡;但是,哭歇的片刻,她們卻一面剝果仁吃,一面嬉笑。蕾迪芙美麗的捲髮隨著剃刀咧咧落地時,女僕們無不同聲驚呼道:“多可惜啊!所有的金髮都不見了!”葩妲剪我的頭髮時,她們並未這么嘆息。不過,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個夏日的午後,當我和蕾迪芙一起捏泥巴築土屋玩時,只覺頭頂清涼,脖子後面卻被太陽曬得火辣辣的。
葩妲奶媽是個骨架大、腕力重,有著一頭金髮的女人。她是父親從行商那裡買來的,他們把她從遙遠的北地帶到這兒。每當我們挑三揀四為難她時,她總會說:“等著瞧吧!哪天王上娶了個新後作你們的後娘,那時,可有好日子過了。休想吃蜂蜜蛋糕,有硬乳酪啃就不錯了。也甭想喝紅酒,有稀奶啊,就謝天謝地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有後娘之前,我們先有了另一樣東西。那天下了一陣嚴霜,蕾迪芙和我特別穿上靴子(平常我們打赤腳或穿拖鞋),打算到圍著木柵的舊宮後院去溜冰,的確,從牛欄到垃圾場,遍地鋪著一層薄冰,連水窪、撒在地上的牛奶和家畜的尿都結凍了,只是地面不平,溜起來不很順暢。這時葩妲從宮中跑出來,鼻子凍得發紅,大聲叫嚷著:“快!快!哇,多髒啊!趕快洗乾淨了去見父王。猜猜誰正等著你們,好傢夥,這下可有好日子過了。”
“是後娘嗎?”蕾迪芙問。
“比這還糟糕,等會就知道了。”葩妲說著,一面用她的圍裙擦蕾迪芙的臉,“你們兩人啊!就等著天天挨板子、扭耳朵,做一大堆功課。”
我們被帶進用彩色磚砌成的新建宮室中,那裡,到處站著全副武裝的衛兵,牆上掛有獸皮、獸頭。父王站在棟樑室的壁爐旁,正對著他的三個人風塵僕僕,是我們認識的每年必來葛羅三次的行商。他們正把秤具放回行囊,必定方才成交了什麼,其中有個人收拾著腳鐐,可見賣的是奴隸。站在他們前面那個短小精幹的漢子顯然便是被賣的人,因為他的腳踝上還有鐵鐐留下的腫痕。不過,這個人倒不像我們見過的其他奴隸。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發須灰中帶紅。
“希臘仔,”父王對這人說,“我有把握不久會生出個王子來,這孩子,我打算讓他接受希臘學識的薰陶,現在,你先用這兩個小妮子練練功夫(父親指向我們),一旦能把女孩子教會,任憑誰都教得通了!”把我們遣走之前,父親加了一句:“尤其是大的,試試能不能把她調教得聰明些,這是她唯一可能做到的事。”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但知道自記事以來,人們談到我時,總是這么說。
“狐”,父親這樣稱呼他。在所認識的人當中,我最喜歡他。你也許以為,一個希臘的自由人淪為戰俘後,被賣到這遙遠的蠻邦當奴隸,必定十分沮喪。狐偶而會這樣,或許比童稚如我所能想像的更常這樣吧!但是,我從未聽他抱怨過,也未聽他像其他外地的奴隸那樣誇稱自己在本國是何等有頭有臉的人。狐有許多自娛的妙論:“若能認清整個世界原是一座城,哪來流落他鄉的感覺?”又:“處境是好是壞,全看自己怎么想。”不過,依我看,使他快樂的真正原因是求知的熱忱。我沒見過像他那么愛問問題的人。他渴望知道一切有關葛羅的事,包括我們的語言啦、祖先啦、神啦,甚至一花一草。
這便是為什麼我會告訴他安姬的事。我說有許多女孩住在神宮中專門供奉她;每個新娘子都必須送她禮物;凶年時,我們甚至割破某個人的喉嚨,用血澆奠在她上面。狐聽得直打哆嗦,口中喃喃。一會兒之後說:“沒錯,她便是阿芙洛狄特,雖然像巴比倫的阿芙洛狄特多過於像希臘的。讓我講一個有關阿芙洛狄特的故事給你聽。”
他於是清清喉嚨,以輕快的聲調吟唱出阿芙洛狄特愛上安喀塞斯王子的故事。安喀塞斯在伊達山腰替他父親牧羊,阿芙洛狄特迷上了他。當她朝著安喀塞斯的茅舍走下綠草如茵的山坡時,成群的獅子、山貓、熊和各類的野獸一路隨著她,像狗一樣搖頭擺尾。過了一會兒,它們成雙結對地離開,各自去享受歡狎的樂趣。阿芙洛狄特收斂起耀眼的神采,使自己看來像個凡問女子。她前去勾引王子,兩人終於上了床。我想狐本想就此打住,但是歌吟至此,正人高潮,欲罷不能,只好再繼續講唱後來發生的事。安喀塞斯醒來看見阿芙洛狄特站在茅舍門口,光芒四射,不像凡間女子。他發現跟自己睡覺的人原是女神,霎時驚惶失措,遮著眼睛尖叫道:“殺了我吧!”
“這種事未曾真正發生過,”狐趕忙說明,“純粹是詩人的杜撰。孩子啊,這根本不合乎自然。”無論如何,狐所說的足以讓我認識到:希臘的女神雖比葛羅的女神漂亮,卻是同樣 狐就是這樣子,他總是羞於承認自己喜歡詩(孩子啊!那全是痴人說夢)。為了從他身上擠出一首詩來,我總得寫很多作業,讀一大堆書,包括他所謂的哲學。但是,這么點點滴滴的,他還是教了我許多詩。他說自己最欣賞的是“美德必須辛苦追求”這首。這可騙不了我。其實,每當我們吟著“帶我到 結滿蘋果的園子裡”或——
月西沉了,我卻
獨自一人躺臥
他的聲調馬上轉為輕柔,眼睛發亮。他總是無限溫柔地吟誦這首詩,仿佛對我有說不出的憐愛似的。他喜歡我勝過蕾迪芙,蕾迪芙不愛念書,常常嘲笑他、折磨他、指使別的奴隸捉弄他。
夏天,我們在成排梨樹後的草坪上念書。那天,父王便是在這兒找到我們的。見到他,我們全都一骨碌站起來,兩個孩子加上一個奴隸,眼睛盯著地面,雙手交叉在胸前。父王熱絡地拍著狐的背說:“加油吧!快有個王子讓你調教了,若是神容許的話。你真應該感謝神哩,因為替我岳父那樣威振四方的王管教孫子,是希臘人少有的榮幸。你該不會像只笨驢似的不領情吧?從前在希臘,你們不都是販夫走卒嗎?”
“所有人身上不都流著同樣的血液嗎?”
“同樣的血液?”父王瞪大眼睛,拉開嗓門像牛哞般地笑著,“很遺憾!我可不這么認為。”
結果,第一個告訴我們後娘已有著落的,是父王,不是葩妲。父王攀上了一門好親事,他將娶凱發德國的三公主為繼室。凱發德王是我們這邊世界最顯赫的國君。(現在,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凱發德捨得把女兒嫁給像我們這樣貧窮的國家了,當初父王為什麼察覺不出他的岳父其實已日漸式微,而婚盟的本身恰是證明。)
婚禮應該是幾個星期後的事,但記憶中,籌備工作似乎延續了一整年。宮門附近所有的磚造物全都髹成大紅色。棟樑室加掛了許多壁氈,父王並且發狠買了一張皇室專用的床。這床是用一種東方特產的木材搭成的,據說這種木材很靈,在上面生的孩子,五個中有四個是男的。(“真是愚蠢啊!孩子,”狐說,“生男生女是自然發生的,哪由得人左右。”)當喜李愈來愈近時,成天只見家畜被趕進來宰殺,緊接著是烘焙、釀酒,整座院子散發著獸皮的腥臊。我們這些小孩從一個房間鑽到另一個房間看熱鬧。不過,好景不長。父王突然靈機一動,決定叫蕾迪芙、我和其他十二位女孩——全是王公貴族的女兒——合唱新婚頌,並且特別指定要希臘的頌歌,因為這才能叫鄰國的國君羨慕、欽佩,這是他們辦不到的。“可是,王上……”狐說,眼中漾著淚水。“教他們呀!狐,教他們。”父王嚷道,“如果你不能為我在新婚之夜呈獻一首希臘歌,長久以來,我不是讓你白吃白喝了嗎?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沒有人要你教懂她們希臘文。她們根本不必懂得歌詞,只要能發音就夠了。照著去辦,否則,小心你的背會比鬍子紅。”
這計畫真會把人逼瘋。後來狐說,教我們這些番女唱希臘歌,使他僅存的一些紅髮全愁白了,“從前,我是狐,現在可是獾了。”
當我們學得稍微像樣時,父親帶安姬宮的大祭司來聽我們唱歌。對這大祭司,我一向十分懼怕,那種懼怕與對父親的懼怕不同。年少的我以為使我害怕的是環繞在他四周與神有關的氣味——那與寺廟分不開的血腥味(大部分是鴿血,有時用人血)、燔炙的脂肪、燒焦的毛髮、奠酒和濃得變臭的薰杳——這就是安姬的氣味。也許,他的穿著也令我害怕:瞧那一身獸皮、那用曬乾的動物膀胱作成的水囊和那掛在胸前形狀像鳥的面具,仿佛一隻鳥從他身上長出來! 他不僅歌詞聽不懂,連曲調也不懂,只會問:“這些小妮子帶不帶面紗呢?”
“還用問嗎?”父王哈哈大笑,翹著姆指朝我指來,“你以為我敢讓這張面孔把皇后嚇昏嗎?當然要帶面紗!並且需是厚厚的一層。”有個女孩吃吃竊笑著。這是我第一次徹底察覺自己長得很醜,我想。
這使我更怕後娘了,以為單單因我長得醜,她會對我比對蕾迪芙凶。其實,使我想到就怕的,不只因為葩妲平日的恐嚇,更因我在故事書中讀到的後母很少是不惡毒的。這天,夜幕低垂時,我們全都聚集到柱廊,眼睛被火炬熏得昏花,拚命想照著狐的指導把歌唱好。狐一會兒皺眉,一會兒又微笑點頭,有回甚至驚慌得雙手停煞在半空。整個過程中,跳動在我眼前的,儘是故事裡一幕幕後母虐待小女孩的情景。後來,外面突然人聲歡騰,有更多的火炬燃起,須臾,他們已將新娘抬出轎子。她帶的面紗同我們的一樣厚。只見她非常瘦小,好像他們抬著的是個孩子。這並沒有減輕我的恐懼,“矮仔毒”,俗語這樣說。我們一邊唱著,一邊把她抬進洞房,掀開了她的面紗。
回想起來,我的確見到了一張漂亮的臉,但當時,我可沒想到這些。只見她比我還害怕,應該說是驚恐。我透過她的眼看清了父王的相貌,因為前一分鐘她才見了他第一面,那時父王正站在柱廊內迎接她。他的眉目、嘴巴、腰乾、身材或聲音都不是讓小女孩安心的那型。
標緻的妝扮被我們一層又一層地卸下之後,她顯得更加嬌小。我們把她那發抖的、晰白的身軀和那雙嚇得發直的眼睛留在父親床上,然後成群離去。老實說,我們唱得難聽極了。
第二章
關於父親的第二位太太,我沒什麼可寫的,因為她來葛羅不到一年就死了。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她很快便懷孕了,父王非常高興,每當狐出現在眼前,總會向他提起這位將出生的王子。此後每個月,他都大祭安姬一次。至於他和皇后間相處的情形,我並不清楚。除了有一回,凱發德派了個使節來,我聽見父王對她說:“小妮子,看來我是上當了,把羊群趕到生意清冷的市場還不自知。原來你父親早就失掉了兩座城,不!還是三座哩!雖然他裝出一付蠻不在乎的樣子。拖我下水之前,若先告訴我他的船正往下沉,我會感激他的。”(那時,我方浴罷,靠在窗台上唏發,他們在花園裡散步。)不管如何,她的確非常想家,而且生長在南方的她,對我們這裡夏天的氣候非常不適應,不久,就變得又瘦又白了,於是我發現她實在沒什麼好怕的。起初,倒是她怕我,後來,怯怯地疼我,與其說是後娘,不如說是姊姊。
當然了,臨盆的那天晚上,宮裡的人沒有一個敢睡覺,因為,他們說只要有人睡覺,胎兒便會拒絕睜眼進入這世界。我們全都坐在棟樑室和寢宮間的大廳里,四周點著火紅的迎生燭。燭焰乍生乍滅,搖晃得非常厲害,因為所有的門都洞開著,若有一道門關了,便會使母親的生門閉合起來。廳的正中央火燃得很旺,安姬宮的大祭司每個小時繞行火盆九次,依照風俗丟進一些合宜的東西。父王坐在他的位子上,整個晚上連頭都不動一下。我坐在狐的旁邊。
“公公,我好害怕!”我低聲對他說。
“孩子,”他也低聲回答,“對於自然帶來的東西,我們要學會坦然面對。”
這之後,我大概睡著了,因為接下來我所聽到的是婦女們哀嚎和捶胸的聲音,像母親去世那天一樣。在我睡覺的當兒,一切都變了樣。我冷得直發抖,廳中的火要熄不熄的,父王的位子空著,寢宮的門緊閉,先前從裡面傳出的那駭人的號啕已經止息了。剛才一定有過一場獻祭,因為聞得到殺牲的氣味,地上有血泊,而且大祭司也正擦拭著他那把聖刀。剛醒過來的我,頭昏昏的,竟然突發奇想,要去探看皇后。還沒走到寢宮的門,狐就一把抓住我,“孩子啊!等會兒。你瘋了嗎?王上他——”
這時,門突然打開,父王走了出來。他臉上的表情把我嚇醒了,因為他氣得臉色發白。我知道他氣紅臉時,雖會大發雷霆,可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當他氣白臉的時候真會出人命的。“酒!”他的聲音並不大,這反而是惡兆。奴隸們即刻推出一個父王平日喜愛的男孩來,這是他們害怕時的慣常反應。這個男孩臉色和父王一樣慘白,穿著一身標緻的衣裳(父王喜歡童奴穿得漂漂亮亮的),他急忙將酒瓶和父王專用的酒杯拿來,踩到血泊時滑了一下,身子一晃,把酒瓶和酒杯摔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