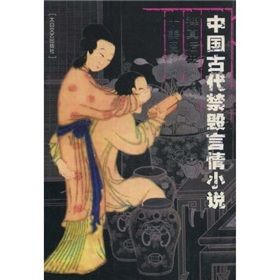內容簡介
唐貞末年,上帝為掃除人間暴亂,殄滅妖氛,令已成仙的薛舉下凡,降生為人,名瞿琰。瞿琰經仙僧指點,通五經,精武藝。年長後誅異僧、服生番、剿邪魔、敗權奸、滅毒疫、賑饑荒、除孽鱷,利物濟世,屢立奇勳,歷任司理、侍中、大理寺少卿、兵部左侍郎。後隨仙僧林澹然修煉,駕雲升天。《禪真後史》與《禪真逸史》二書在敘事時間上有聯繫,部分人物先後承接。但其主要的聯繫還是在於思想內容方面。目錄
第一回 耿寡婦為子延師 瞿先生守身矢節第二回 醉後兔兒追舊債 夜深碩士受飛菑
第三回 二真仙奇遇傳方 裘五福巧言構釁
第四回 聽讒言潑皮興大訟 遇知己老穆訴衷情
第五回 裘教唆硬證報仇 陸夫人酬恩反目
第六回 商天理肆惡辱明醫 秋傑士奮威誅劇賊
第七回 窺珠玉諸凶謀害 觀梅雪二友和詩
第八回 舞大刀秋僑演武 拜花燭耿憲成親
第九回 戀美色書生錯配 貪厚贈老嫗求婚
第十回 慶生辰妯娌分顏 慪閒氣大家得病
第十一回 全孝義郁氏善言 看風水葛鷦詭計
第十二回 寫議單敗子賣填山 假借宿禿囚探訊息
第十三回 華如剛藏機破法 龔敬南看鷂消閒
第十四回 凌老道華禿死奸 葬師母耿郎送地
第十五回 躍金鯉孝子葬親 築高壇真人發檄
第十六回 葉鍊師回神復旨 張氏女妒孕生情
第十七回 問肚仙半夜有餘 薦醫士一字不識
第十八回 全伯通巧處生情 郁院君夢中顯聖
第十九回 五彩落水全生定 媚姐思兒得受病
第二十回 瞿廷柏母子重逢 劉廉訪弟兄蒞任
第二十一回 好施小惠恆招禍 急為偷生反喪軀
第二十二回 叛獄賊市口遭刑 燒香客廟前斗寶
第二十三回 惡公子見財起意 老闍直口訴冤冤
第二十四回 存公道猴蟹歸原 正法度主僕受責
第二十五回 木馬驛劍俠談心 蒙山洞苗酋作亂
第二十六回 眾百姓鼓勇逐蛇 三洞主改邪歸正
第二十七回 劉仁軌激蠻攻蠻 骨查臘用計中計
第二十八回 墨頂朱衝波救主 哈一喃出獵興兵
第二十九回 崆峒嶺二賢敘舊 龍門府四將攻城
第三十回愛良馬番將獻謀 掛數珠猢猻念佛
第三十一回 黃鼠數枚神馬伏 奇童三矢異僧亡
第三十二回 劉經略執旗督陣 瞿司理上表辭官
第三十三回 瞿二郎吞符卻病 黨氏女刺繡見妖
第三十四回 藍面鬼撲捉黨翼兒 大將軍錘擊滑道士
第三十五回 瞿氏子放雷逐怪 車雲甫挺斧劈邪
第三十六回 攝魂和尚訴真情 覓利黃冠謀放債
第三十七回 厚贈侍兒為妾媵 訴芟權惡謁相知
第三十八回 印常侍利口飾非 許侍郎庇奸獲罪
第三十九回 眾冤魂夜舞顯靈 三異物宵征降禍
第四十回散符療疫陰功大 掘鼠開疑識見多
第四十一回 白馬寺懷義嫉賢 大峽山羊雷仗義
第四十二回 卞心泉賂貴救親 羊大郎肆凶拒捕
第四十三回 三戒銘心權避跡 一餐大嚼定交情
第四十四回 嘍羅贈寶救冤民 孔目收金寬獄犯
第四十五回 二寨主停杯審事 四冤犯遇赦遠奔
第四十六回 俠士戮奸伸大義 簿司移釁詐平民
第四十七回 談積弊防禦明心 試神臂二雄納款
第四十八回 告病還鄉期避世 割襟為聘結良緣
第四十九回 收番禮金吾護法 慕瘏黎王氏偷情
第五十回 為渡銀河妝蹶躓 因方花貌受熬煎
第五十一回 勞夫人夢裡簪花 來毓秀灶前說苦
第五十二回 小蘭獻主解重圍 我惜貪歡嬰內疾
第五十三回 田寶珠挨身入戶 沈三昧借港行舟
第五十四回 嵇西化縱慾傷人 瞿道者登橋援難
第五十五回 戮奸僧立時正法 救蠱婦子夜擒魔
第五十六回顧大郎為弟求醫 顏氏女訴冤索命
第五十七回 程員外聆音擇婿 張別駕設計傾賢
第五十八回 南明山玩景遇饑民 西屏嶺焚祠驅孽鱷
第五十九回 赴井泉棄名避世 隱岩壑斂跡修真
第六十回 棲霞洞四道敵魔 毗離村七仙人聖
精彩書摘
第一回 耿寡婦為子延師 瞿先生守身矢節詩曰:
清商蕭颯漢江秋,紅紫枝頭色正柔。
墜葉逐流隨月渡,殘芳帶雨倩風揉。
鶯簧漫擬鳥鵬調,蝶拍空傳鸞鳳儔。
不是鬚眉異巾幗,倫常墮地仗誰收?
話說隋末時,盧溪州辰谿縣毗離村裡有一秀士,姓瞿名天民,字子良,生得長須秀目,白臉豐頤,舉止從容,天然風度。
幼喪父,家業甚窘,娶妻郁氏,苦守清貧,朝耕暮讀,以養其母元氏,年過三十,未有子嗣,忽一日,進城訪友,談及艱難一事。這友人姓劉名浣,與瞿天民幼同筆硯,最相契愛。當下留住吃了午飯,二人籌畫資身之策,商議了半響,無計可施。
瞿天民正欲作別起身,忽聽門外有人聲喚,劉浣道:“仁兄且慢坐,待弟看是甚人,然後送兄。”瞿天民依允,坐於軒內,在窗眼裡張時,只見劉浣揭起竹簾,迎進一個人入來。那人頭戴尺余高一頂尖角扁巾,身穿一領淡青粗布道袍,足穿高跟深面蒲履,與劉浣禮罷,移過杌子並坐了,附耳低言。說了一會,袖中取出一個柬帖,遞與劉浣。劉浣含笑接了,看罷,起身進軒內來秤銀子。瞿天民問是何故,劉浣搖手道:“少刻便知。”
一徑出客座里,將銀子送與那人。那人接了,千恩萬謝,臨出門時回頭叮囑道:“老哥千萬話勿得個,千萬話勿得個!”劉浣點頭應允,那人歡喜作別而去。劉浣拍手笑將入來,瞿天民迎道:“那人卻是兀誰,賢弟這等好笑?”劉浣道:“仁兄不知,這人姓邊名薦,插號叫做籩箕。原籍海州人氏,腹內頗通文墨,在外設帳十餘年了,只為著一樁毛病,往往館事不終。
今日此兄卻又做出這睧兒來了。”瞿天民問:“那人有甚么毛病?”劉浣道:“這籩箕倒是個有趣的朋友,酒量好,棋畫也好,說科打諢更好,錢財也不甚計較。奈何酷好的是這一著,每每為此事打脫了主顧。目今在敝鄰耿寡婦家處館。這耿氏家道富足,且是賢德,丈夫耿鼎早亡,止生一子,將及十歲,館穀有二十餘金,款待甚是殷勤,朝暮酒肴茶飯的齊整,自不必說。這小邊看上了他家一個小廝,叫名錦簇,在館中做伴讀的。
兩個正在花園裡行事,被他父親撞見了,當面搶白了一頓,不容進館。他如今在這裡安身不穩,就欲起程回去,因無盤纏,將這張關約押弟五錢銀子,豈不是一場好笑?”瞿天民道:“那廝既是無恥,賢弟不該將銀子借他。況這紙關券,乃無用之物,要他何乾?”劉浣道:“這銀子專為仁兄而發。不然,怎生輕自與他,這柬帖兒更是有用處。”瞿天民不解其意,細問其故,劉浣道:“仁兄訴說寥落無措,小弟躊躇難決。適間小邊失館,其中似有一個好機會,故此不惜小費,收了關約,為兄一圖,不識可乎?”瞿天民道:“深感賢弟盛雅,此館得成,老母甘旨有望,煞強似耕種的清苦。只是一件,彼已長往,留此廢約為質,惟恐無成,徒為畫餅。”劉浣道:“邊兄一時露醜,惶愧無地,故著忙要去。若遲延數日,則愧心漸解,必夤緣求懇,捱身入戶矣。故小弟收約賚銀,使彼死心塌地而去,為兄圖館,一也;耿寡婦之父濮員外與弟有一脈之親,今日弟即親去力薦,或者有幾分成就之意,明日便見訊息了。”瞿天民歡喜作謝,辭別而回。
當下劉浣逕往濮家來,恰值員外在側廳內與一少年圍棋。
兩下相見,禮畢,員外道:“久不相會,今日何事下顧?”
劉浣道:“有一言求教,特此奉謁。”員外笑道:“足下請坐,待老朽完此殘局請教何如?”劉浣道:“絕妙,晚輩正欲一觀。”
那少年道:“老伯已拜下風,不必終局。”員外道:“局上未分勝負,小子何得狂言!”兩下互相笑謔。劉浣候二人棋畢,即將薦館與瞿天民之意細細說知。員外道:“舍甥小館已有一位姓邊的朋友在彼,難以斡鏇。”劉浣又將小邊逐出情由說了,員外笑道:“斯文中做此道兒的極多,何足為異。邊先生既已辭館,老朽就與小女說,擇日奉請令友便是。但不知瞿君舉止抱負何如,不要蹈老邊的舊轍才好。”劉浣道:“敝友才識不凡,立身誠實,斷不似舊師的景態。”那少年道:“凡人家請師長,必須有才、有法、有守的方好。”濮員外道:“請問兄長,何為才、法、守也?”少年道:“凡為師長的,飽學不腐謂之真才,善教不套謂之得法,誠實不偽謂之有守。師長具此三德,子弟們方有教益。”劉浣道:“敝友瞿君,三德未必俱備,然真誠質樸,教法亦精,斷不誤卻令甥功課。”濮員外道:“尊駕之友,決非妄誕者,老朽力言,管取館事立就。”劉浣歡喜自回。次日,濮員外親到耿家,見了女兒,備言劉浣薦館之事,又說瞿先生恬靜飽學,教法最精,兼且近便,不可挫過。濮氏從了父親之言,即寫下關約,著蒼頭送到劉家。劉浣自令人通知瞿天民,不必細說。此時正值四月初旬,這耿寡婦是個節儉的女人,預先送了兩個請帖,趁著立夏節日,順便排下筵席,邀瞿先生進館,濮員外、劉浣賓主三人,盤桓了一日。次日,依然令小廝錦簇伏侍小主耿憲讀書。
光陰荏苒,不覺又早月余。濮氏見兒子功課不缺,舉止端詳,與前大不相同,心下十分喜悅。家下人又言瞿先生溫柔雅量,待人以禮,更兼善教不倦,甚堪敬重,故此濮氏管待倍加豐厚。忽一日晚上,濮氏吃罷晚膳,正欲脫衣尋睡,猛聽得床頭戛戛之聲,急執燈看時,卻是一對蠶蛾,兩尾相接,在那裡交媾,四翅扇撲,故此聲響。濮氏疑道:“此物從何而來?”
掀起枕席瞧看,見一個破損空紙包兒。問兒子時,答道:“早上在花園內撲得的,故包了放於枕下作耍。”濮氏哏了一聲,將蠶蛾擲於床下,息燈睡了。閉眼一會,轉輾思量,睡不安枕,翻來覆去,心緒如麻,長吁數聲,披衣而起。此時天色曛熱,紗窗半啟,只見一輪月色,透入羅幃。濮氏輕身下床,移步窗前,憑檻玩月,不覺慾火如焚,按捺不下,倚著圍屏,立了一回,奈何情興勃然,勢不可遏。一霎時面赤舌乾,腰酸足軟,反覺立腳不住,急縱身環柱而走,如磨盤一般。團團鏇繞有百十個轉身,愈加遍身焦熱,心癢難禁,口咬衫襟,凝眸佇想,恨不得天上墜下一個男子來耍樂一番。又想著家下有幾個小廝,年俱長成,已知人事,尋覓一個消遣也好,只是壞了主僕之體,倘若事露,醜臉何以見人?呆思一會,猛然想起瞿師長青年美貌,篤實溫雅,若諧片刻之歡,不枉人生一世,縱然做出事來,死而無怨。正是色膽如天大,只因睹物生情,拴不住心猿意馬。
當下側耳聽時,譙樓已打二鼓,回頭看憲兒和侍女們皆已熟睡,忙移蓮步,悄悄地開了房門,輕身下樓,踅出銀房,黑暗裡被胡床絆了一跌,急躍起轉過軒子,趁著月光,一步步捱出茶廳,早見是書房了。濮氏四顧寂然,伸出纖纖玉手,向前敲門。卻說瞿天民正在睡夢中,被剝啄之聲驚醒,心下疑道:“更闌人靜,何人至此?”急抬頭問道:“是誰?”門外應道:“是我。”
卻是一個婦人聲音。再問時,依舊應聲:“是我。”瞿天民驚詫道:“這聲音分明是耿徒之母,夤夜至此,必有緣故。”原來濮氏與瞿生雖未覿面相見,然常出入中堂,呼奴喚婢,這聲音卻是廝熟的。當下瞿天民口中不說,心下思量:夜深時分,嫠婦獨自叩門,必有私意存焉。不開門,慮生嗔怪,坐館不穩;若啟門,倘以淫污之事相加,如何擺脫?正暗想間,敲門之聲愈急,外廂輕輕道:“瞿相公作速開門,奴有一至緊事相懇,伏乞見納。”瞿天民聽了濮氏嬌嬌滴滴的聲音,不覺心動,暗算計道:“這是他來就我,非是我去求他,無傷天理,何害之有?不惟他妙年麗色,抑且財谷豐饒,私情一遂,餘事可圖。”
即起身離床,正待啟門,忽抬頭見天光明亮,又猛省道:“阿呀,頭頂是甚么東西!咦,只因一念之差,險些兒墮了火坑矣!
堂堂六尺之軀,頂天立地一個漢子,行此苟合之事,豈不自恥?
此身一玷,百行俱虧,快不宜如此!”一霎時,念頭端正,邪欲盡消,側身而睡。又聽得門外唧唧噥噥,推敲不已。瞿天民心生一計,哼哼地假作鼾聲,睡著不理。濮氏低聲叫喚,無人偢倸,又延捱了一會,不見動靜,跌腳懊恨而回,徑進房內,恰好憲兒醒來聲喚,濮氏撫息他依然睡了。此時更覺欲動難禁,頻咽津唾,兩頰赤熱,小腹內那一股邪火直衝出泥丸宮來,足有千餘丈高,怎么遏得他下?自古道:婦人慾動而難靜。耿寡婦被這魔頭磨弄了半夜,無門發泄,恨的他咬定牙根,雙手摟抱一條黑漆廳柱,兩足交叉,直至小腹中卷了一回,豁刺地一聲響,一塊物件從牝門裡脫將下來,就覺四肢風癱,一身無主,忽然暈倒床邊,半晌方蘇。又不敢驚動侍兒,只得勉強撐起,把一床單布被將那脫下的物件取起包裹了,藏於僻處,又取草紙試抹了樓板,撇在淨桶里,才摸到床上,和衣眠倒,不覺沉沉睡去。直到次日辰牌時分方才醒來,覺得身子睏倦,不能起床,一連將息了數日,漸得平復。心下感激瞿先生好處,不然已為失節之人了;還喜得隔門廝喚,未審何人,事在狐疑,幸不露醜,暗中自恨自悔。忽一日早上,見房內無人,將門閉上,取出那脫下的物件來看,原來是一團血塊。濮氏看了又看,心下暗忖道:“這一團血肉是婦人家色慾之根,若不天幸墜將下來,這禍孽何時斷絕?”嗟嘆了一會,將此物依舊包藏過了。
自此以後,濮氏竟絕了經水,毫無情慾之念。後人看此,有偈為證:空彼欲想,斬去騷根。
阿彌陀佛,救苦天尊。
再說瞿天民自那夜閉戶不納,坐到天曉,自想道:“慚愧呀,也做了一個魯男子。但是婦人家水性,見我拒而不理,必生嗔怒,不知這館事如何?大抵事有定數,只索由他!”當下自猜自疑,又早過了數日,依然僕役們伏侍殷勤,茶飯上更加醲釅,心下放寬了。不覺又是季夏,因見天氣炎熱,暫且歇館回家,並不將這事對母親、妻子說知。在家過了月余,天色漸涼,仍然赴館,一來師徒相得,二來情義優渥。在耿家處館三年,這耿憲經史漸通,十分文雅,當年初冬,與一宦家結成親事。不期岳翁寫一帖子,差家僮接女婿明春到衙里讀書。濮氏難於推辭,暫且應允。至散館前一日,接父親濮員外商議道:“如今新親家請你外孫明年往他家下攻書,這事萬分難卻。但這瞿師長教憲兒何等用功!況且為人謙厚,在此三年,並無一言半語,怎好辭卻?事在兩難,如何區處?”這員外手拄拐杖,側著頭,不知答應甚話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醉後兔兒追舊債 夜深碩士受飛菑
詩曰:
保全節操賴書生,願托千金報爾恩。
蠢隸漫辭招劇盜,俯思得失總無憑。
話說濮員外因女兒商議外孫讀書一事,當下復道:“新親翁見招,理應遷就。瞿先生在此數年,爾家禮數卻也不缺,便辭他諒亦無礙。”濮氏道:“爹爹講的是。兒還有一件事體與爹爹酌議。當初你女婿在河南做客時,被一盧店戶拖欠下絨緞銀一千餘兩,將及十年光景,並無下落,止留下一張空券。數日前,有一船戶來通訊息,說這店家近來發跡,每思往彼取討,奈無可托之人。今欲煩瞿師長帶一蒼頭同到河南,清楚帳目,倘得銀時,就將百十兩謝他也不為過,不知爹爹尊意若何?”
員外點頭道:“好,好!這人可托,諒不誤事。我也有些帳尾在彼,一發勞他順便取之,一舉兩得也。”濮氏甚喜。當晚整下散館酒席,濮員外、憲兒相陪。數杯之後,濮員外道:“舍孫賴老師培植,大有進益,理應久侍絳幃。奈何敝親翁韋君賜翰相招,不得不往,明歲有違大教,心實歉然。”瞿天民道:“小生樗櫟庸材,荷蒙不棄,在茲三載,叨擾多矣!令孫少年英偉,飛黃可待,既是令親翁相迎,理應趨命。但小生無寸功而屢蒙厚貺,含愧不勝!”耿憲道:“先生待我如子,受教實多。母親另欲從師,不知是何主意?岳丈處明歲是斷然不去的。
先生呵,你也怎忍棄我而去?”說罷,不覺淚垂雙頰。瞿天民也撲簌簌流下淚來,勸慰道:“不是我無情相撇,奈是令岳接爾赴館,萬萬不可卻者,豈可因我負了你岳丈美意?幸我家下不遠,時常來望你便了。”濮員外又將河南取帳情由,對瞿天民細說一番。瞿天民道:“感承老丈與令愛盛情,這是有益於小生,怎么不去?但未稟知老母,不敢輕諾。”濮員外道:“老夫人薪水之費,早晚自著人饋送,不必在心。小女說千金之託,因不得其人,故遲延十載。若得老師慨允一行,不惟亡婿感恩於九泉,而老夫亦沾余惠矣!”瞿天民再三遜謝。夜深撤席,濮員外也在書房內歇宿。次早,酒飯罷,送出修儀盒禮,著蒼頭挑了先行。瞿天民面謝了濮氏出門,濮員外領了外孫遠送一程。濮員外道:“日昨所懇之言,萬乞留神,燈夜後相約動身,切莫推故。”瞿天民應允,兩下作別而去。
不說濮員外二人回家,且說瞿天民趕著蒼頭,同出城外,到家中見了母親、妻子,忙備酒飯款待蒼頭,寫下謝帖,打發去了。晚間,瞿天民將耿憲定親、明春到岳丈家讀書並濮員外所說要他往河南取帳原由,一一對母親說了。元氏道:“汝在他家三載,看待十分盡禮。耿郎既已另從師傅,明春汝又失館,既有這條門路,甚是好事。取得帳目歸來,諒他決不薄你,再來講時,切莫推卻。”瞿天民見母親允了,心下暗喜。
話不絮煩,轉眼之間,又早冬去春來。上元佳節,瞿天民進城看燈,就便探望劉浣。劉浣整酒敘情,瞿天民又將前事說了,劉浣攛掇該行。酒罷,二人攜手出街閒玩,正遇著耿憲行過,定要留二人到家下吃茶。瞿天民道:“天色將暮,不必茶了。去歲令外祖所談河南一事,老母已允,尊堂處乞為轉達。”
耿憲別了自回,徑對濮氏說知。濮氏即接父親商議定了,一面整頓行囊,令人相邀瞿天民,預約定了起程吉日。至期,瞿天民別了妻母,逕到耿家相會。濮員外交割了文券,撥一個家僮,名喚兔兒,向來原隨亡主出外,一應帳目皆經他手,故此著他挑行李,陪伴同往。吃罷酒飯,濮員外等送出門外相別。
此時正是二月初旬,天氣晴和,百花開放。二人行至傍晚,投店安宿,次日五更動身,一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不一日已到河南蔡州府地界。二人進城,逕到盧家來。盧店主問了來意,倒也歡喜,迎入客座酒飯,隨即打掃一間淨室,與二人安頓,早晚殷勤相待。忽一日,整備酒筵,遜瞿天民坐了客位,接親友們數人相陪,酒至半酣,盧店主取一拜匣放於席上,對瞿天民道:“昔日令親耿君賒緞匹一千餘兩與小店貨賣,不期令親棄世,小弟連年眐訟,店本消乏,以致拖遲日久,未得奉還。近賴四方客長扶持,漸復舊業。今蒙大駕光顧,該當本利一併奉上,奈春初眾客未齊,生計蕭索。”指著匣子道:“止措辦得本銀六百兩,外有些粗緞布匹雜貨等項,總計一百餘兩,作為利息,伏乞笑納。余欠本銀四百兩,另立券約,冬底奉償,令親處煩乞鼎言,感戴不荊”說罷,取過天平拜匣,將銀兩對眾兌明,一封封疊起,又喚伴當捧過布緞雜貨,稱估停當,一併當面交割。瞿天民叫過兔兒,令其檢點收貯。兔兒踉踉蹌蹌,走向前來,瞅著眼道:“相公且慢著。當初敝主在日,和盧長者交契甚厚,往來最久,故將這若干緞匹托在寶店貨賣。
敝主亡後,已及十年,論來一本一利也該還我二千餘兩。今日止還這些,本不足,利又薄,教小人怎么回復主母?”盧店家笑道:“管家講得有理,奈本店生意淡薄,一時抽拔不出,以致如此。所欠之銀,只在歲底奉還,決不爽約,令主母處乞為方便。若說利息,不過表情而已,莫論厚薄方妙。”瞿天民道:“盧老丈是一純厚長者,既已分付年畢見賜,今且遵命,待冬間再來趨領。”兔兒道:“我的爺老子,你講的是太平話兒,官路做人情,誰不省的?我小人吃他家的飯,穿他家的衣,領了他家的嚴命,銀子不足斷不回鄉!不然,早晚的熬煎怎了?
這二千兩銀子,一文也少不下的!”瞿天民道:“你家主母最是賢德,我回家面言,管教你不受氣便了。”兔兒道:“瞿先生,你回家見我主母,一言兩語便自去了,終不然在我家過了生世?”瞿天民怒道:“這廝不痴不醉,為何這等胡談,甚為可惱!”盧店官並眾客一齊勸道:“耿管家面色似有幾分酒意,一時唐突,不必介懷。”兔兒睜眼道:“吃你家的酒不成?不是誇嘴說,我小兔在家朝朝七夕,夜夜元宵,誰似在你尊府,不偢倸,撇人在冷房裡坐。若不是小兔身旁有幾文錢時,眼灼灼看你們呷酒。”盧店主笑道:“適才已備些薄酒在彼,少刻老夫親自陪你吃三杯,不必著惱。”兔兒道:“咦,驚死人,希罕你家酒吃!不敢欺,小兔是酒里養命的,那一日不醉飽,老盧你不要忒煞欺人,鰟皮魚兒也有三寸肚腸。瞿先生是落得做好人的,凡事還有小兔做一分主,老人家不要差了念頭!”
這話分明是要店家暗中買他的意思。此時合座親客皆怒,一齊道:“不還銀兩,你待怎的?這蠢狗不過是富家一個奴才,卻也恁地無狀!”兔兒道:“是、是、是,我是奴才。但不曾賣與你家盧老官,你接這夥人來罵我,敢是設計賴我的銀子?我小兔是不懼的。二千兩白銀,若少了一文也休想我出你家門去!”
盧店主笑道:“要還也不難,明早講話。”瞿天民氣滿胸膛,奈在客中不好發話,只得耐住了性子。眾客焦躁,酒不盡歡,各各辭去。瞿天民謝了盧店主,回客房尋睡去了。
當晚無話。次日早上,盧店主到親戚處措置了四百兩銀子,下午依舊接了親友,又邀下幾家鄰舍,坐下茶罷,對眾將昔日欠耿家銀兩情由逐一告訴,又道:“昨日老朽備下小酌,先奉還耿宅本銀六百兩,余欠四百兩,意欲歲畢找足。感此位瞿相公慨允不辭,不期耿管家發言發語,要本要利。眾位高鄰在此,我與耿家生意往來,又非私債,怎么算得利息?”說罷,取出銀兩與眾人看了,道:“這是白銀一千兩,求老管家收去,即刻賜還文券,外要甚么利錢,一毫休想。不然,任你告理,寧可當官結斷!”眾鄰舍一齊道:“我們做店戶的拖欠客銀,此是常例。要象這盧老丈肯還冷帳的,千中選一。老哥呀,你收了去的便宜。若到官時,連本也送了,休怪!”兔兒道:“凡事有瞿相公作主,我小人怎敢多言。”瞿天民冷笑道:“我是外人,怎敢做主?我瞿相公是落得做好人的,收與不收,請君裁處!”兔兒道:“咦,相公好點掇,小人醉中言語,你大家認起真來。”眾人一齊大笑。盧店主道:“恁地講時,我也不教你空過。”喚伴當取出昨日檢過的粗緞布匹雜貨來,又稱出散碎銀三十兩,送為路費,兩下歡喜,一邊收下銀兩物件,一邊接了文券。一面搬出肴饌,眾人坐下飲酒,側廳里另設一席,款待兔兒,大家盡歡而散。瞿天民為代濮員外取討帳目,耽擱了十餘日,方得起身。盧店主又贈禮物下程,親送至郭外分別。
二人行了兩日路程,乃是永陵鎮上。看看天色傍晚,尋一熱鬧客館,兔兒歇下行李,伏侍瞿天民淨了手腳,同在房中吃飯。
兔兒道:“兩日擔子甚重,險些兒壓死了人,明早雇一腳夫挑去方好。”瞿天民道:“正是,我也量這擔子不輕,明日僱人送到白露河口,下船回去,豈不輕便?”兔兒歡喜道:“甚好,甚好。”說罷,熄燈安宿不題。
且說盧店主有一鄰人,姓秋名僑,排行第八,原是響馬出身,最有義氣。射得一手好箭,況兼武藝精通,智勇出眾。少年時習成一行藝業,做了數千金家業。娶個渾家,極是賢惠,苦苦勸諫丈夫改惡從善。這秋僑一時回心,在城內租了房屋,開一生藥鋪。初時生意頗興,只因他眼界寬大,看銀子不在心上,終日裡好酒好肉受用,更兼酷愛的是賭博,數年之間,囊橐消乏。正在愁煩之際,恰值盧店主邀他做眼,兌銀子與耿家。
他見了一千兩雪白大錠銀子,不覺昔日念頭又起。當下一面吃酒,一面心下籌畫這事,瞞著渾家,預先暗中約下舊時夥伴,只待瞿天民出門,便行動手。當夜瞿天民正在濃睡中,忽聽得喊聲大起,開眼看時,滿室通紅,數個大漢搶入房裡來。
瞿天民在黑暗中止提得一件下衣閃入床下,這也是數不該絕,恰好床下半堵泥壁原是破的,瞿天民即從破壁鑽入去,乃是一間內室,即蹲在室內不動。這店主人是個聾子,不聽得喊聲,只瞧見門外一派亮光,疑是失火,忙奔出來看時,早被一棍打倒。這兔兒夢中驚醒,見火光爍亮,眾大漢奔將入來,已知是盜,欲躲時,無處可避,也被一斧砍倒房中,銀兩貨物等項盡被搶劫一空。此時各房客商,合家老小,各各驚惶躲閃,直待賊人去了許久,一個個聚集商議。瞿天民從內室大寬轉捱出來,只見中門口店主人頭顱中棍身死,客房內兔兒面中一斧,在那裡掙命。瞿天民跌足嗟恨,眾人皆驚駭嘆息,店家老幼一齊嚎篊大哭,引動地方鄰里都來看視,喧鬨直到天明,這兔兒也氣絕死了。齊往縣中呈與,縣官審了口詞,隨即僉牌,差人往店家檢驗屍傷,著落屍親辦棺收貯。一面呼喚一班緝捕公人,責了限狀,差委分投四下緝訪正盜。此事遍處傳揚。這訊息傳入盧店主耳中,驚得這老兒目瞪口呆,急忙裡騎馬星夜奔到永陵鎮來,見了瞿天民,悽慘不已。瞿天民道:“耿家兔兒已死,又拖累店老官身喪,行囊財物盡劫無存,我孤身狼狽,難以還鄉,又負卻舍親之重託,怎么是好?”盧店主道:“風波賊盜,前生冤孽,命中注定,萬不可逃。尊駕且請到寒舍權居,候本縣老爺緝獲這伙強徒,追贓正法。倘一時擒究不著時,老夫亦贈盤費,喚人送公回府,不必愁煩,以傷貴體。”瞿天民感謝不荊盧店主又雇下一匹驢子,與瞿天民騎了,同取路復往蔡州城來。到了家下,日逐價殷勤相待,委曲寬慰。瞿天民在縣前打探,催併縣官責限緝捕人等。守候月余,並無蹤跡,因與盧店主商議這事如何了落,盧店主道:“足下離家日久,不如暫且回鄉。這裡事務老夫一力承當,天幸倘獲得賊時,所追贓物一一收留在此,以候尊駕來齲”瞿天民拜謝,打點起身。
盧店主又贈盤纏衣被,欲著家僮相送,瞿天民辭道:“行囊不多,小生單身盡可去得,不必勞動尊使,即此告辭。”盧店主置酒餞行,兩下分別。有詩為證:萍水相逢岐路人,幾番贈別意何勤。
阱中下石輕浮子,鑒此寧無反愧心?
話說瞿天民別了盧店主出門,背馱包裹,手提雨傘,淒淒涼涼,獨自一人趲路。行了數日,不覺已到鼎州地界,穿城而過,只聽得一派鑼鼓之聲,喧闐振耳。近前看時,乃是城河內划龍舟作耍,心內忖道:“愁緒如麻,已忘時序。明午正值端陽佳節母親壽日了,怎么是好?”帶著煩惱行路,漸覺身疲力倦,舉步難行,勉強捱出城外。又行了一里余路,忽見樹林中有一古廟,即移步走入廟裡,放下包裹、雨傘,在側首石條上坐了半晌,靜悄悄並無人跡往來。忽聽得一派笛音從廟後而出,清亮愛人。但不知這吹笛者卻是甚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二真仙奇遇傳方 裘五福巧言構釁
詩曰:
袖手亡羊泣路岐,空林邂逅授仙機。
宿愆未盡遭萋斐,頃刻風雷駕禍梯。
話說瞿天民隨著笛音,循步踅出廟後,只見後殿牆外是一片荒草地,內中有幾株大槐樹,槐樹之下有二乞丐席地而坐,品笛飲酒。左邊的鬚髮皓然,身上穿著一領厚重衲衣;右邊的骨瘦如柴,渾身精赤,止將一片荷葉遮於腹下。地上橫放著兩條短竹杖。二人對飲,談笑自若。瞿天民將傘柄拄地,佇目旁觀,那赤身的猛抬頭見了,舉手招瞿天民道:“來來來,卮酒解熱,莫嫌腥穢。”瞿天民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二人同聲道:“妙人妙人!”瞿天民也塌地坐了,那須白者斟過酒來,一連吃了數杯,配酒的是一味苦菜,兩色果品:一樣是鮮荔枝,一樣是新柑子。瞿天民心下驚疑,動問道:“這荔枝出自廣閩,離此較遠,二丈如何得來?況柑子此時方得開花,焉能有果?事屬奇異,敢請玄教!”那瘦子道:“君雖敏悟,豈解我方外之玄。看君氣色晦滯,有一大難,不可不慎。”瞿天民道:“小生值一幾死之難,僥倖獲生。”即將客店被盜之事說了一遍,瘦者笑道:“此是他人之難,與爾何預,即日還有縲紲之憂,猶慮死生難定。”瞿天民驚愕,已知此二丐決非凡人,忙長跪懇求避難之術。發白者扶起坐定,又熟視一會,笑道:“不妨。看君部位,似有喪亡之厄,幸印堂里隱隱黃光相映,陰德紋已露,雖見災危,尚有一線百生之機。平日君有甚濟人守己的好處,明與吾言,吾即示爾生路。”瞿天民道:“小生貧寒之士,自給不暇,焉能濟人,但守己一節,似或有之,不過是安貧守分而已,余無德業可稱。”瘦者道:“陰德者,在於冥冥之中行的好事,不喪自己的心術,不玷他人的節義,光明正大,人所不知,方謂之陰德。君若隱而不言,是欺我也!”瞿天民想起昔日夜間耿寡婦叩門,拒而不納,莫非是這一樁陰德?正欲開言,心裡又想道:“若與他二人說知,豈不玷辱了濮氏名節?”隨復閉口不言。瘦者道:“君欲言又忍,是何緣故?”瞿天民道:“某深思半生履歷,兢兢自守而已,非是隱忍不言,實無一長可齲”二人一齊稱羨道:“誠篤君子也,誠篤君子也!有實行而不矜,更能隱人之惡,當今之世,如君者能有幾人?”瞿天民躬身遜謝,白髮者道:“汝今到家之後,即有禍事臨身。但當逆來順受,不必憂煎。”指著地下柑子、荔枝之核:“這二物是救汝之靈藥也。”瞿天民懇問道:“此二物何以救得小生之命?”白髮者道:“看君氣色,直交上元節候,方得脫災。其中遇一貴人內室有難,汝當救之,不惟離卻囹圄,而且獲其重報,自此後君家永無災眚,壽高祿厚,兼有子嗣。”又撿起柑瓤三片、荔核五枚,交與瞿天民,細細開傳秘法。瞿天民拜受,請問二仙長姓名,瘦者道:“予二人乃方外逃名之士,不必相問,君宜速往,少刻雷雨至矣!”瞿天民狐疑不信,還欲盤桓,霎時間陰雲四合,漸聞隱隱雷聲,瞿天民道:“雨已之頭,不如權在廟中躲避,候天霽再行。”瘦者笑道:“汝在廟中避雨,眼見得命在須臾。這殿角頭有一孽畜作怪,應在令日申時起蜃,故吾二人在此鎮伏。不然,這滿村百姓盡為魚鱉矣!”瞿天民大驚失色,那瘦者將那一片遮身荷葉覆在瞿天民頭上,分付道:“君只在此向北而立,不可移動,直待雨止天清,速速離此前去。”說話未畢,忽然狂風驟起,雷聲震擊,電光閃爍,大雨如注。少頃,一股惡氣如煙如霧,從殿角上直衝起來,腥氣觸人。只見那白髮老者袖內取出一把長柄摺疊扇子來,對那惡氣扇將去,漸漸煙消霧滅。猛聽豁刺地一聲響亮,恰如山崩地塌之勢,有一赤龍從殿角上飛將上來,煙霧奔騰,霹靂大震,火光繚繞,冰雹拋擲。那龍初飛出殿角時,不過長得丈余,乘著風雲之勢,半空中盤鏇奮躍,頃刻間長有數十餘丈,昂頭向天,將尾反搠入殿下亂攪,只見一股黑水骨都都倒滾上來,倏忽之間,平地水高數丈。瞿天民幸與二仙長同站在園內,冰雹不能著身,黑水滾至足邊即退。
此時水勢洶湧,風雷愈猛。白髮者手提竹杖,大喝一聲,騰雲而起,迎著龍劈頭打去,那龍奮勇來斗;這瘦者也提了竹杖,飛身直上,向前助戰。瞿天民仰面看時,那兩條竹杖變成二口寶劍,去砍孽龍。那龍公然不俱,揚鱗舞爪,抵死相敵。兩下鏖斗良久,被瘦者一劍砍中龍尾,那龍負疼向北逃遁,這二仙隨後趕去。一霎時,雲清風息,雨住天晴,黑水盡退。瞿天民驚得面如土色,半晌不能舉足。奈何日色兩沉,取下荷葉,摺疊藏於袖內,提了雨傘包裹,乘濕而走離古廟。又趲過三里多路,到一村坊,尋覓客店投宿。吃罷晚飯,對店內眾人細說二仙趕龍之事,眾人各各驚異。店家道:“我適才見狂風驟雨,雷電交作,諒來是有龍起蜃,後來見天地昏黑,似有喊殺之聲,合家慌張起來,不期幸有二仙追殺孽龍遠去,是我敝地百姓之大幸也。”三三兩兩,四處傳揚,地方保正人等科斂富戶銀兩,在古廟之中造一伏龍祠,即依瞿天民所說二仙形象裝塑金身,牌位上鐫著十三個金字“通靈顯聖除孽濟民惠德二真君”。這是後話不題。
卻說瞿天民次日算還店錢,趁早行程。一路無話,不覺已到故鄉。當下一面行路,心下算計道:“離家數月,理應先見母親。但耿家知道,未免生疑。今且先公後私,如此如此方妙。”
取路進城,逕到濮員外家下來。員外接見,迎入中堂,禮畢茶罷,濮員外問道:“耿家兔兒為何未到?所煩些須帳目,不知能明白否?一路風霜勞頓,何以為報!”瞿天民道:“一言難荊小生有負重託,甚覺赧顏。今得與老丈一面,亦出萬幸。”
濮員外驚駭,細問來歷。瞿天民將盧店主還銀、兔兒酒後爭論並收得員外零碎帳目、路中被盜、兔兒與店家殺死情由,細細告訴一番。濮員外跌腳叫苦,嘆息道:“老夫些須之物,不足掛齒,但耿家人財兩失,何以解分?”又問:“尊駕曾回府么?”
瞿天民指著雨傘包裹道:“小生若回寒舍時,怎么又帶這物件來?”濮員外點頭道:“正是,正是。”瞿天民低頭長嘆。濮員外寬慰道:“這事分明是老夫與小女命薄,反累足下受驚,事皆前定,不必愁煩。”留住瞿天民酒飯畢,二人同往耿寡婦家裡來。濮員外請瞿天民客廳坐地,自先入內室來與女兒相見,備將前項事說了,濮氏驚惶無措。旁邊惹動一人,捶胸頓足,號哭起來,口裡埋怨道:“一家男女十餘個,都吃大娘子的飯,偏獨我的丈夫是該死的,差他遠出,教他死在他鄉外土,屍首不得還家。我的天呀,好苦!”這哭的女人正是兔兒的渾家皮氏。濮員外道:“不要啼哭,從容數日,我出盤纏,著一人取你丈夫棺木回來便了。”皮氏不理,且哭道:“我少年夫婦,半路分離,不知那個不愜氣,故意定要他遠出,教他死得好苦。
這瞿先生好沒分曉,兩人同去,止你一個回鄉,單是他不會躲避,死於強盜手裡,偏你生三頭六臂、七眼八腳的好漢,能會走脫?這人死得不明,莫不是謀財害命,將我的老公斷送了也不見的!”濮氏跌足道:“這歪婦又來胡講,瞿相公在外聽得了成甚體面?”皮氏嚷道:“怕甚么,瞿相公跛相公,要他還我一個活老公來只索罷了,不然正要和他費嘴哩,有甚體面?”
濮氏道:“這潑貨恁的可惡!兔兒在家時,鎮日裡和他廝鬧,咒生罵死,絮聒個不了,以致兔兒忿氣出去避你。臨出門時,還對我說:‘大娘,我這一去不回來也罷,討得個耳根清靜。’可憐他死於非命,都是你這淫潑婦咒詛死的,反出言吐語傷觸他人!瞿相公是一讀書君子,終不成他見財起意,謀死你家老公?況劫搶殺人,事非小可,已驚動地方官府,難道是遮掩得過的?還不閉了鳥嘴!”皮氏道:“大娘,你不要一面情詞,聽人邪說,閻王殿前沒個咒殺鬼。我那不識好歹的兔兒自取其死,與我何乾?你說瞿先生是個讀書君子,大娘,你還不曾著道兒哩。世上不公不法的事,俱是讀書人會做。自古道:財動人心。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看了那千餘兩大錠銀子,又有許多貨物,怎不動火?暗中安排死了,假理會作強盜掩飾,我與你婦人家坐在家裡,那曉外邊事務。據他說驚動官府地方,我們曾親見么?自的家奴死了,並不悲苦,反護他人!”說罷,敲桌打凳,放聲大哭。濮氏大怒道:“我聽了這個訊息,心內好不耐煩,正沒做理會處,反淘你這潑狗婦的氣!”奪過濮員外手中竹杖,劈頭劈腦打去,打得皮氏滿地打滾。濮員外拖住女兒,著力解勸,方才住手。這皮氏一面啼哭,披著發大踏步奔出廳外來。恰值瞿天民獨坐在廳門首,被皮氏兜胸脯一頭撞將來,險些兒撞了一跌。瞿天民驚道:“這、這是何故?”皮氏道:“何故?你娘的鳥故!你為何謀財害命,殺我親夫?”
瞿天民平素是極孝的,聽皮氏罵了一句“你娘的鳥故”,不覺怒從心起,口裡恨的一聲道:“潑淫狗,怎么傷我母親?”只一腳尖,踢中小腹,皮氏大叫一聲,望後便倒。裡面跑出數個婦女來攙扶,只見皮氏唇青面紫,暈倒地上。濮員外見勢頭不好,慌忙將瞿天民扯出門外去,丟個眼色,瞿天民一道煙溜了。
少頃,皮氏漸漸甦醒,眾婦人扶進臥房睡了,只見地上一帶淋漓鮮血。原來這婦人有四個月身孕,被瞿天民踢傷了胞胎,捱至更深,小產血暈而死。當夜,耿寡婦慌做一團,密請親戚來商議了兩個更次,只得令人到皮氏親兄家通知。其兄叫做皮廿九,原是個破落戶,聞此凶報,乘夜而來,逕入妹子房裡,一面啼哭,一面詢問妹子病死根由。眾丫鬟男婦人等,都是主母叮囑過的,只推說瞿相公從河南回來,訴說被盜、兔兒身死情節,嫂子聽了,一時顛狂大哭,以致小產血崩身死。皮廿九也沒話說,鬧哄哄直到天曉。濮氏秤些銀兩,就教他去買辦棺木衣衾,打點晚上入殮。皮廿九吃了些酒飯,自去備辦去了。
不期耿家間壁有一光棍,姓裘名為五福,年有二旬之外,生得白淨溫雅。這皮氏平日間常去撩撥他,兩下眉來眼去,彼此有心偷會,只困濮氏拘束嚴謹,無隙可乘,兩下未曾到手。
當下裘五福已備知皮氏與主母相爭、瞿天民踢死之事,向來與皮廿九識熟,諒定決來尋釁,熬著瞌睡,在那裡探聲候氣。自夜至曉,不見動靜,心下氣忿,要替這皮氏報冤,侵早即站在門首窺伺,只見皮廿九急忙忙從耿家奔出來,往對巷徑走,裘五福從後尾將去,穿過了三五條巷,行至一僻靜去處,裘五福叫道:“皮大哥,那裡去?”皮廿九立住腳,回頭看時,認得是小裘,答應道:“小五哥,一向少面來。”五福進前一步,廝趕著走路,將手搭著皮廿九肩膊,笑道:“阿哥,好利市得彩,也攜帶弟兄們吃一杯酒!”皮廿九笑道:“小不死,又來扯淡,有何利市彩色?”裘五福指著皮廿九的衣袖道:“這裡邊落落動的,豈不是個彩色?”皮廿九道:“好苦呀,這等的彩色讓與你罷!你曉得我向來空缺處,仗有耿家妹子掏摸些幫助,如今不幸他夫妻兩個雙雙死了,教我向後望著誰哩?這袖中是耿大娘子與我的銀兩,替亡妹買辦棺木衣衾,乃是皮門不幸。賢弟不去沽一壺請我解悶,反講恁地得彩,豈不是落寞我也?”裘五福笑道:“活賊,恁他話瞞的誰過?令妹升天,是老哥一碗濫飯,大錠囫圇的東西請自受享,把那鏨下的零星散碎請我小兄弟,也彀幾十場醉飽。”皮廿九道:“這話從何處來的,教人摸不著頭腦!”裘五福冷笑了一聲,掇轉身自念誦道:“寧可私鹽重犯,莫惹人命乾連,管他做甚?”拱著手道:“老哥請了!”低頭徑走。皮廿九猜疑道:“這廝言語蹺蹊,莫非我妹子死得不明?且去兜他轉來,問個明白。”當下急急趕上,將裘五福衣襟扯住道:“好兄弟,和你吃三杯了去。”
裘五福道:“小弟有事,不得領情。”拽脫衣襟就走。皮廿九又一把拖住,扯到一家冷酒店裡,揀付座頭坐下,喚酒生搬過幾樣菜蔬,燙熱了兩壺酒,打發去了。
二人對面吃了一回,皮廿九再四詢問妹子死的根由,裘五福方才說出前因後跡皮氏致死的緣故。皮廿九聽了,袖中取出一塊銀子,約莫錢數多重,丟與裘五福道:“煩兄弟算帳,我不得奉陪,先行一步。”說罷就走,裘五福一手拖定不放。不知二人說出甚地話來,再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