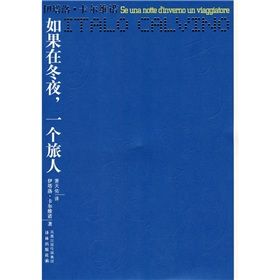編輯推薦
框架故事和嵌入小說兩部分組成。框架故事以男性讀者“你”作主角,“你”是整本書的“隱設讀者”,也是實際在進行閱讀的讀者。話說,你興致勃勃地買來卡爾維諾的新小說《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正看到入迷之處,沒想卻因書頁裝訂錯誤而被迫中斷閱讀。你迫不及待地去尋找下文,不料拿回來卻是另一部小說,讀到高潮迭起之際,書又戛然而止……如此這般的陰錯陽差一再發生,你鍥而不捨地追索其下文,一部接一部地找來讀,前後總共閱讀了十部互異其趣的小說之開頭,這些“嵌入的小說”的標題正好串成一個句子:(1)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2)在馬爾泊克鎮外,(3)從陡坡斜倚下來,(4)不怕風吹或暈眩,(5)在逐漸累聚的陰影中往下望,(6)在一片纏繞交錯的線路網中,(7)在一片穿織交錯的線路內容簡介
《如果在冬夜,一個旅入》的第一版是由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發表的。在書出版之時,卡爾維諾在報紙和雜誌上的許多採訪中談到它。但是對這本書的結構和意義進行思考和辯論的最好機會是由批評家安傑羅·古列爾米的一篇評論提供的:卡爾維諾用如下的這篇評論回答了他,這篇標題為《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的評論發表在《字母表》月刊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號上。伊塔羅·卡爾維諾的名作《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它不僅僅是一部小說,更嚴格的說而是一部關於小說的小說,一篇關於說故事的故事,一本關於閱讀和寫作的書,一份關於文本的文本,一部明顯具有後現代特徵的後設作品。
這部作品由框架故事和嵌入小說兩部分組成。框架故事以男性讀者「你」作主角,「你」是整本書的「隱設讀者」,也是實際在進行閱讀的讀者。話說,你興致勃勃地買來卡爾維諾的新小說《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正看到入迷之處,沒想卻因書頁裝釘錯誤而被迫中斷閱讀。你迫不及待地去尋找下文,不料拿回來卻是另一部小說,讀到高潮迭起之際,書又戛然而止……如此這般的陰錯陽差一再發生,你鍥而不捨地追索其下文,一部接一部地找來讀,前後總共閱讀了十部互異其趣的小說之開頭,這些「嵌入的小說」的標題正好串成一個句子:(1)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2)在馬爾泊克鎮外,(3)從陡坡斜倚下來,(4)不怕風吹或暈眩,(5)在逐漸累聚的陰影中往下望,(6)在一片纏繞交錯的線路網中,(7)在一片穿織交錯的線路網中,(8)月光映照的銀杏葉地毯,(9)環繞一空墓,(10)什麼故事在那頭等待結束?
這本書有時隱約,有時直接地把閱讀(及寫作)和性愛等同齊觀,混為一談。不少章節的前文和各篇嵌入小說皆涉及情慾挑逗,描寫露骨,香艷刺激,不亞於坊間所見的煽色腥小說;同時又隱含深刻寓意,可從心理分析的角度加以詮釋。光從這一點,就可以約略看出,這是一本後現代作品:兼容並蓄嚴肅和通俗文學的特色於一爐,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正好人人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光看熱鬧的話,我們會發現本書中十篇嵌入小說全是緊張刺激的驚慄故事,諸如偵探、間諜、科幻、成長故事、日記體小說、新恐怖小說、感覺派小說、西部故事等;敘述模式則包含現代主義、意識流、魔幻寫實、政治小說、心理分析等,變化多端;描寫細膩,構想奇妙;在在發人省思,頗堪玩味。
從嚴肅的文學角度來說,這是一本後現代主義的活教材,書中處處可見結構主義後起的批評理念。讓我們從它的「後設」或「自行反射」成分談起:本書與傳統的寫實主義小說迥異其趣,非但不刻意經營令人信以為真的幻覺,反而經常提醒讀者,你正在閱讀的是虛構的小說;除了訴諸諧擬,顛覆既定的小說習套和觀念之外,並常自行暴現創作之設計伎倆。
此刻我最想讀的小說,應是那種以敘述的欲望為驅動力,堆砌一篇又一篇故事,而不企圖把人生哲理強塞給你,只讓你觀察小說本身的成長,像一棵樹那樣,枝葉交織糾纏。
前面說過,這是一本關於小說的小說,其主旨之一在探討小說的閱讀及寫作。除了嵌入小說部分的自行反思之外;框架故事直接探討有關小說的各種問題,並涉及(原)作者、譯者/偽造者、讀者、文本之間的互動,(想像)虛構與事實(真相)的關係等等,可說是鉅細靡遺。讀者「你」在追求閱讀的過程中,除了女性讀者魯德米拉之外,還遇見了包羅甚廣的不同類型的各種讀者和作者,諸如拒絕看書的非讀者;仰賴電子儀器,割裂文本,斷章取義,以支持己見的女性主義讀者;披閱並口譯已失傳之死文字的教授;從事職業性閱讀的出版社老編;翻譯家/偽書製造者;名滿天下的暢銷作家;負責審核禁書的官員等等。他們各自不同的閱讀旨趣和見解有助於揭發小說閱讀和寫作的現象和本質,同時也呼應了後結構批評流行的按語:一切閱讀都是誤讀。
這本書中最主要的誤讀/詮釋者自然還是主角「你」本人。事實上,卡爾維諾的這本書可說是獻給讀者的,它一開始便直接對「你」說話:
你就要開始讀伊塔羅.卡爾維諾的新小說《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放鬆心情。集中精神。什麼都不要想,讓周圍的世界漸漸消失掉……
強調讀者(基於作者)在詮釋上的地位,乃是晚近各派批評理論的共同趨向。本書中的讀者不僅只是隱設讀者和實際讀者——閱讀的主體,也是小說的虛構框架中的主角——吾人閱讀的對象,他同時又扮演作品意義的生產(作)者和批評者,因為他在追求閱讀的過程中,一再陷入晦澀文本所布下的迷宮,必須自行尋覓出路,不斷地被迫修定自己對小說的觀念和期待。
本書的「讀者」同時具備個別性和一般性,甚至連姓名、身體特徵、職業、年齡都付之闕如,為的是讓實際讀者(我們)容易產生認同,一起參與「他」的追求,在第二章接近結尾處,他自問道:
讀者,你究竟是誰?你的年齡、地位、職業、收入……這樣問或嫌輕率。那是件的私事,你就是你。重要的是你目前的精神狀態……自從昨天以來,事情起了變化,你的閱讀不再孤單:你想到彼讀者,她也在同一時刻打開書;待閱讀的小說與待展開生活的可能的小說重疊在一起,那是你和他的故事之延續,情況更好的話,一個可能之故事的開始。這就是你昨天以來的轉變,你原來堅稱自己喜歡書籍,那是紮實的東西,擺在你眼前,容易界說,享受,無風險,勝過實際生活經驗——總是捉摸不定、不連續、爭論不休。難道這意味著這本書已經變成一種工具,一種溝通的管道,一種約會?但這並不是說,閱讀這本書對你已經比較沒吸引力了:相反的,它的力量增加了。
讀者對於中斷的小說和對彼讀者魯德米拉的期待和欲望一再被挑起,一再延宕——一切欲望原本源生自欠缺。隨著框架故事的發展,兩種欲求愈來愈難區分。在第六章,「讀者」自己發現:「追蹤那本中斷的書,給你注入一股特殊的亢奮,因為你和彼讀者一起在進行那件事;但到頭來卻變成和追求她是同一件事,她以繁衍變化的神秘、詭計、偽裝逃避你……」
到了第七章,閱讀和戀愛兩件事終於合而為一,男女讀者兩人在床上相互閱讀對方的身體,以閱讀來詮釋做愛,其中有一節強調:「閱讀與做愛兩者最相似的地方在於:在這兩件事之中,時間與空間皆開放,與可以丈量的時間和空間不同。」
本書處處暗示閱讀即是欲望的運作。敘述的聲音時而扮演提示者的角色,敦促讀者採取行動。例如第九章如此描述一位女性寬衣解帶,對讀者你投懷送抱:
讀者啊,你在做什麼?你不抗拒嗎?你要逃避嗎?啊,你在參與……啊,你也投身進去書唯一的主角,嗯;但你就因此認為你有權和所有的女性角色發生肉體關係嗎?
第八章的前半部,那位暢銷作者日日以望遠鏡偷窺另一個山坡上的女性讀者(即彼讀者)在閱讀,進一步探討了寫作與情慾的關係。此書也訴諸讀者的窺淫慾望,來誘引並滿足讀者,第八章之後的(月光映照的銀杏葉地毯》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此書中的兩種追求,閱讀方面備受干擾,有無止盡;但愛情的追求卻有所「斬獲」。在第十一章,讀者在跑遍山涯海角,尋書未果之後,歸返故里,前往圖書館,並聆聽七位讀者發表迥異其趣的閱讀策略,第七位讀者質問道:
你認為每篇故事都非要有個開端和結局不可嗎?古代的時候,故事只有兩種結局:男女主角在歷經一切考驗之後,結成眷屬;要不然,就是死掉。一切故事所指涉的終極意義有兩個層面:生命的延續以及死亡的不可避免。
聽到這裡,我們的讀者「你」突然若有所悟,當下決定要和魯德米拉結婚。
在最後一章,我們看到男女讀者已結成夫妻,並臥床上,進行同步閱讀,準備熄燈就寢。男性讀者即將讀完的卡爾維諾的小說,是否會有最終的結局,或者從前的閱讀經驗會重演,我們不得而知。這個以喜劇收場的通俗結局,倒可看成原型批評家傅萊所稱的春天模式的文學:熄燈之後,可望埋下子孫繁衍的種子,不虞將來缺乏小讀者,這的確是讀者(消費者)誕生的時代。
前言
《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的第一版是由埃伊納烏迪出版社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發表的。在書出版之時,卡爾維諾在報紙和雜誌上的許多採訪中談到它。但是對這本書的結構和意義進行思考和辯論的最好機會是由批評家安傑羅·古列爾米的一篇評論提供的:卡爾維諾用如下的這篇評論回答了他,這篇標題為《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的評論發表在《字母表》月刊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號上。親愛的安傑羅·古列爾米,“在這一點上我要向卡爾維諾提兩個問題”,你寫道,但事實上,在你發表在《字母表》第六期上的正是以“給伊塔洛·卡爾維諾的問題”為題的文章中,關於我的“旅人”,你提出了好幾個或明確或不明確的問題。我將盡我的能力回答你。
我將從你的文章中不提問題的部分,也就是你的言語和我的言語相一致的部分開始,然後去發現我們的道路互相分開並開始互相遠離的那些點。你非常忠實地描述了我的書,特別是精確地定義了被陸續呈現給讀者的十個小說類型:“……在一本小說中,真實性就像霧一樣是不可獲得的;在另一本小說中對象被表現得帶有甚至是過於稠密和情慾的性格;在第三本小說中獲勝的是內省的探求方式;在另一本小說中起作用的是一種被拋向歷史、政治和行動的強烈的生存緊張;在另一本小說中還爆發了最為殘忍的暴力;然後在另一本小說中增長著一種無法承受的不適和焦慮的感覺。然後有色情墮落小說,大地原始小說,最後是啟示錄式小說。”(五年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義大利文化學院舉行的一次講座中,卡爾維諾在他對於這本書的定義和描述中大概是想起了這些話:“試圖寫‘偽’小說,也就是我想像出的由一個不是我並且不存在的作者所寫的小說,我把這種活動一直推行到了我的書《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的最深處。這是一本有關閱讀小說的樂趣的小說;主人公是男的讀者,他十次開始讀一本書,而這書由於一些與他的意願不相關的周折而未能結束。因此我必須寫十個由想像出來的作者寫的小說的開頭部分,他們全都以某種方式不同於我並且互不相同:一篇小說全都是懷疑和混亂的感覺;一篇全都是肉體的和血腥的感覺;一篇是內省和象徵性的;一篇存在主義革命的;一篇無恥殘忍的;一篇帶著固執的瘋狂;一篇是邏輯和幾何學的;一篇是色情墮落的;一篇是大地原始的;一篇是啟示錄式寓意的。我試圖不僅將自己同化於十部小說的每一個作者,還同化於讀者:再現一種特定的閱讀的樂趣,而不僅僅是真實的和特有的文本。但在某個時刻我感到自己仿佛被這十個不存在的作者的創造能量所貫穿。但我特別努力要揭示這個事實,即每一本書都是當著其他的書的面產生的,產生於和其他的書的關係和對話中。”)正當大多數的批評者為了定義這十個“開頭詞”而尋找它們可能的模式或來源(並且常常從這些作者名單中跳出一些我從來就沒有想過的名字,這件事喚起了對一些一直到現在尚未被很好開發的領域的注意:心理聯合在一些不同的文本間如何運行,我們頭腦中的一個文本通過哪些途徑與另一個文本相一致或相近)時,你追尋著我的方式,也就是時常向我自己提出一種文體的和與世界的關係的確立(然後,圍繞這個確立,我讓對已讀的那么多書的回憶的回聲自然地聚集)的方式,你在全部十個事例中完善地定義了這一確立。
在全部十個事例中?如果仔細地看,我發現你所給出的例子只有九個。有一處脫漏,以句號和“於是後來……”標示出來,這個“於是後來……”對應著那個鏡子的故事(《線上條交叉的網中》),也就是說對應著一個傾向於像一個理性活動或一個幾何形狀或一局棋那樣構成的講述的例子。如果我們還想要考察專有名詞的近似,我們可以在愛倫·坡身上找出這種敘述模式的最傑出的父親,而在博爾赫斯身上找到其在目前最完善的到達點。在這兩個儘管相距遙遠的名字之間,我們可以放置所有那些傾向於將最離奇的激情在一個具有稀薄化了的抽象活動、常常被裝備了某種學識淵博的矯揉造作文體的心理氣候中加以過濾的作者。
《線上條交叉的網中》曾被另一些批評家非常強調(也許是過分了?),但卻是你遺忘的唯一的小說。為什麼?我說,因為,如果你考慮到它,你就肯定會意識到在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的那些文學形式當中,有“被關閉的”和“被計算好的”作品,在這種作品中,封閉和計算是荒謬的打賭,這種打賭所做的只是指出與形式本身似乎意味著的那種(具有齊全性和密封性的)令人安心的真理相對的真理,也就是說傳遞一個不平穩的、處在破碎狀態中的不確定世界的意義。
但是,如果你接受這一點,你就必須承認“旅人”這一整本書在某種程度上符合這個模式(在一開始,是對一個普遍密謀這個古老的傳奇topos的利用——這個體裁的特徵,這個密謀是由一些不可控制的勢力,以至少是從切斯特頓開始的寓言喜劇的調式進行的,並由一個變化無常的deux-ex-machina操縱的;大騙子這個人物,你會指責我,認為是個太簡單的發現,在這種情況下,就是一個我幾乎要說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這種模式中,首要的遊戲規則就是“使賬對得上”(或者不如說:使得看上去賬對得上,而我們知道其實對不上)。“使賬對得上”對於你只是一個妥協,而它完全能夠被視為一種用來挑戰—和指出—下面的空虛的雜技動作。
總之,如果你沒有從表格上跳過(或者刪除?)“幾何小說”,你的一部分問題和反對意見就將最終失敗,就將從有關“不可作出結論性”這個問題開始。(你憤怒,因為我作出結論,於是你自問:“作者的一種漠不關心是什麼?”不,正相反,我非常關心,同時計算一切,以使最為傳統的“輕鬆結局”——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最終封住擁抱著總體混亂的畫框。)至於有關“沒有結束”的爭論—你就這個主題說了些在一個普遍的文學意義上是非常正確的話—我想首先要把可能的誤會都從場地上清除掉。
特別有兩點我希望是更加清楚的:一,處在我書中心的閱讀對象並不是“文學的”,而是“傳奇的”,也就是說是一個確定的文學程式—它本身是民間敘事文學的和消費的程式,但是以各種形式被文人的文學所採用——它首先是以將注意力強制在對正在發生的事的持續等待過程中的一個情節上的能力為基礎的。在“傳奇”小說中,中斷是一個外傷,但是它也能被制度化(連載小說的篇章在高潮時刻的中斷;章節的切分;“我們回過來再說”)。把情節的中斷轉變成為我的書的一個結構動機,這一事實有這種確切的和限定的意義,不涉及藝術和文學中的“沒有結束”的問題,那是另外一回事。不如說,這裡的問題不是“沒有結束”而是“中斷的結束”,是“結局隱蔽或難以被讀出的結束”,不論在文字的意義上還是在隱喻的意義上都是如此。(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生活在一個由開始但沒有結束的故事構成的世界裡。”)二,也許確實我的篇章被中斷了?某個批評者(請看盧切·代拉莫,“宣言”,九月十六日)和某位有鑑賞力的讀者堅持說不:他們認為這是些已經完成的小說,它們講了它們應該講的所有東西,沒有任何東西要添加給它們了。在這一點上我不發表意見。我只能說在一開始我想要寫一些中斷了的小說,或者不如說:再現對被中斷了的長篇小說的閱讀;後來我得到了大量的文字,我甚至能夠將這些文字作為短篇小說獨立地發表。(這是相當自然的事,因為我一直主要是一個短篇小說作者而不是傳奇小說家。)這本“傳奇”小說的自然的收件人和享受者是“一般讀者”,由於這個原因我希望他也是“旅人”的主人公。這是雙重的主人公,因為他分裂成了一個男讀者和一個女讀者。對於男讀者我沒有給出一個性格特徵,也沒有給出準確的愛好:他可以是一個偶然的和折中的讀者。女讀者是一個志願讀者,她善於解釋自己的等待和拒絕(這些等待和拒絕都是以儘可能最不理智主義的詞語表述出來,儘管—甚至正是因為—理智的語言一直不可避免地在日常所說的語言之上退色),這是一個由於無私的激情而對自己作為女讀者的社會角色感到非常驕傲的“一般女讀者”的升華。這是我相信的一個社會角色,這是我的勞動的前提,而不僅僅是我的書的前提。
正是關於這種面對“一般讀者”,你磨尖了你的最明確的“深入”,你問:“只是和柳德米拉在一起,卡爾維諾,也許是無意識地吧,將一本誘惑的(奉承的)作品引向後來是他的書的真正讀者(和買者)的一般讀者,同時向他提供不可超越的柳德米拉的一些特殊的品質?”這段話中令我不能接受的東西是“也許是無意識地吧”。怎么:無意識地?如果我將男讀者和女讀者放在書的中心,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一分鐘也沒有忘記(因為我享有作者的權利)讀者是買書者,書是一個在市場上被賣的物品。認為可以不考慮生存的經濟性及經濟性所包含的所有東西的人,永遠也得不到我的尊重。
總之,如果你說我是引誘者,饒了你;說我是阿諛奉承者,饒了你;說我是集市上的商人,也饒了你;但如果你說我是無意識的,那么我就憤怒了!如果在“旅人”中我想要再現(並用諷喻方式敘述)讀者(普通的讀者)在一本他從來也沒有預料到的書中的糾纏,我只不過是使我先前所有的書中那種有意識的和持久的意圖明確化了。如果是這樣,在這裡將展開一場閱讀社會學(甚至是閱讀政治學)的談話,它將使我們遠離關於所涉及的書的本質的爭論。
最好還是回到兩個主要問題上來,你的爭論就是圍繞這兩個問題而形成的:一,為了自我的超越,可以指望自我的增多嗎?二,所有可能的作者能被減少到十個嗎?(我僅僅是出於代記憶而這樣綜合的,但在回答你時,我努力考慮到你的文章的所有論據。)對於第一點,我只能說,通過一個有著各種語言學可能性的目錄來追尋複雜性,這是這個世紀文學的整整一個部分的一種特徵性方式,它開始於那部在十八章中講述一個都柏林人的隨便一天、並且每一章有著各不相同的文體構建的長篇小說。這些著名的先行者並不排除我總是喜愛要達到你所說的那種“可支配性的狀態”,“靠著這種狀態,與世界的關係就能不僅是以認識的術語展開,而且是以探求的形式展開”;但是,至少在這本書的持續時間裡,“探求的形式”對於我來說仍然是與背景的主題統一性相匯合(或從這個主題統一性散發出來)的一個多樣性的——以某種規範方式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沒有特別新的東西:在一九四七年,雷蒙·蓋諾就發表了《風格練習》,在這本書中,一件只有幾行的逸事被用在九十九個不同的版本中。
作為典型的傳奇小說的情形,我選擇了一個草案,我能這樣來確切地說明這個草案:一個以第一人稱講述的男性人物發現自己要充當一個不是他的角色的角色,他處在這樣一個形勢中,由一個女性人物實施的吸引和一個敵人集體的暗中威脅的逼迫,在他身上毫無退路地糾纏在一起。這個基本的敘述核心,事實上我在我的書中以《一千零一夜》的偽故事的形式表明了出來,但是我覺得沒有一位批評者(儘管許多人都強調了書的主題統一性)將這種形式指明出來。如果我們願意,同樣的情形可以在這本書的框架中被辨認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說主人公身分的危機來自沒有身分這個事實,他是一個“你”,而任何人都能在這個“你”中認出他自己的“我”)。
這個情形只不過是我強迫自己玩的遊戲的限制或規則之一。你已經看到在“框架”的每一章里,將要緊跟的小說的類型總是通過女讀者的口指明出來。此外,每一本“小說”都有一個標題,這個標題也回答著一種必要性,因為接下來被讀到的所有標題也將構成一個“開頭”。由於這個標題從文字上看一直是從屬於講述的主題,每本“小說”都將從標題與女讀者的期待的巧合中產生,這個期待在前面的那一章中已經被她表述出來了。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告訴你,如果你好好地看,你找到的不是“在其他的自我中的認同”,而是一些必經之路的格柵,它是這本書的真正的生育機器,就像雷蒙·盧塞爾作為他的傳奇小說活動的出發點和終點向自己提出的那些頭韻法。
這樣我們來到了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正好是十個小說?回答是明顯的,並且你自己在更前面的某一段給出了這個答案:“必須確定一個適當的界限”;我當時也可以選擇寫十二個,或七個,或七十七個;寫為了傳達出多樣性的意義所必需的那樣多。但是你立即拋出這個回答:“卡爾維諾過於明智地確定了十個可能性,為的是不暴露出他進行綜合的意圖和他本質上對於一場更加不確定的比賽的不可支配性。”我在這一點上向我自己提出質問的同時,我幾乎要考慮:“我陷入了怎樣糟糕的境地?”事實上,關於全體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一種反感;我不承認自己有“綜合的意圖”;但是,還是寫出來更令人放心:在這裡我說的—或者我的人物西拉·弗蘭奈里說的—正是“全體”,是“所有可能的書”。問題涉及的不僅僅是“所有的”書,更是“可能的”書;你的反對意見針對的就是這裡,因為第二個問題立刻就被你這樣重新表述出來:“難道卡爾維諾相信……可能的事物與存在的事物是一致的?”並且你非常暗示性地威脅我“可能事物不能被列數,它從來也不是一個加法的結果,並且它主要的特徵是一種消逝的線,在這條線上每一個點都分享著整體的無限特徵”。
為了試圖擺脫這種糟糕的境地,也許我應該向自己提的問題是:為什麼是這十個小說而不是別的十個?清楚的是,如果我選擇了這十個小說類型,這是因為我認為它們對於我更有意義,因為它們最適合我,因為它們最使我樂於寫它們。有另一些小說類型不斷地出現在我面前,我本來能夠將這些類型添加在列表中,但是,或者是我不肯定自己能成功,或者是它們沒有呈現出一個我認為是相當強的明確吸引力,或者乾脆就是這本書的草案已經足夠充實了,我不想擴充它了。(例如,有許多次我想:為什麼敘述者我必須是一個男人?而寫出的文字是“女性的”?但是存在一種“女性的”文字嗎?或者能不能為每一個“男性的”小說的例子想像出“女性的”對等者?)於是我們說在我的書中,可能的事物不是絕對地可能的事物,而是我認為可能的事物。但也不是所有的我認為可能的事物;例如,我沒有興趣重新經歷我的文學自傳,重做我已經做過了的敘述類型;它們應該是一些處在我所是並所做的可能事物之外的可能事物,能夠被由我向外的一個跳躍就達到,而我則停留在一個可能的跳躍的界限之內。
我的書的這種限制性的定義(我把它提出來,以否認你強加給我的那些“綜合的意圖”)有可能最終將給予這本書一個貧窮化了的形象,如果它沒有考慮到一個始終與這本書相伴隨的相反方向的動力:這就是我當時一直在自問我正在做的工作會不會有一個不僅僅對於我而且對於其他一些人的意義。特別是在最後的階段,當時這本書實際上已經完成,它的許多連線處不許可有進一步的調整,我焦急地想要確認自己能不能在概念上為它的情節、它的過程、它的次序作出解釋。我為了我的專用的個人的解釋,嘗試了各種不同的梗概和草案,但我從來沒有成功地使它百分之百地達到精確。
在這個時刻我請我的一位最明智的朋友讀我的稿件,想看看他能不能給我解釋這件事。他對我說,他覺得這本書在連續的刪除中進行著,一直到刪除“啟示錄小說”中的世界。這個意見和我在同時對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接近阿爾莫塔辛》的再閱讀促使我重讀我的(這時已經完成的)書,把它當做對“真正的小說”和對於世界的正確姿態的探求所能夠是的樣子來讀,在這種探求中,每一個開始並中斷的“小說”都對應著一條偏向的途徑。在這個觀點看來,這本書(在我看來)於是就再現了一個消極的自傳:我以後將會寫的和我已經偏離的小說,還有(對於我和對於別的人來說)一份各種生存態度的指示性目錄,這些生存態度通向同樣多的被禁止通行的途徑。
這位明智的朋友提及柏拉圖在《智者篇》中為了給釣魚者下定義而使用的雙重選擇:每當一個選擇項被排除時,另一個選擇項就分岔為兩個選擇項。這個提醒足夠讓我致力於根據這種方法畫出一些草圖,以說明書中的這種明確路線。我告訴你其中一幅草圖,在這幅草圖中,你將發現,在我對十個小說的定義中,幾乎總是你使用過的那些語言。
在最後一個環節能夠與第一個環節連線在一起這個意義上,這個草圖可能有一種循環性。那么,是不是綜合性的?在這個意義上,確實,我很高興它能這樣。在被這樣畫出的落空的邊界之內我圈出一個白色範圍,在這裡放置對於你所提倡的唯一的不具有欺騙性的世界的“否認”態度,因為你宣稱“世界不能被見證(或宣揚),而只能被否認,被用每一種個人的或集體的保護所資助,被復原到它的不可還原性”。
(陸元昶譯)
精彩書摘
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故事發生在某火車站上。一輛火車頭嗚嗚地鳴叫著,活塞冒出的蒸汽瀰漫在本章的開頭,一團煙霧遮蓋了第一段的一部分。火車站的氣味中夾雜著一股小餐館的氣味。有人透過霧氣蒙蒙的玻璃向外觀看,他打開玻璃門,酒吧裡面也霧氣騰騰的,就像近視眼或被煤灰刺痛眼睛時所看到的景象。這本小說的文字模糊,就像舊時火車上的玻璃窗戶結滿了水汽一樣,霧氣罩住了書頁。這是個冬雨淅瀝的夜晚,主人公走進酒吧,脫下潮濕的外衣,一股水汽頃刻裹住他的身軀。火車的長鳴在雨水中閃爍著寒光的鐵軌盡頭漸漸消逝。
年邁的小酒吧店員正用蒸汽咖啡機煮咖啡。咖啡機發出嘯叫,噴出水汽,仿佛店員在發出信號,起碼小說第二段的一連串句子給人這么一種印象。聽到這個信號,坐在桌邊玩撲克的人立即把排成扇形的牌往胸口上一貼,分別轉過脖子、肩膀和椅子望著這位新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