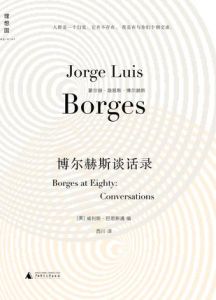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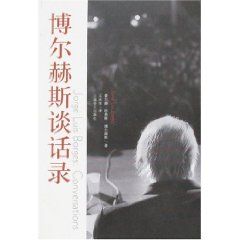 0
0平裝:330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32
ISBN:7532744159,9787532744152
條形碼:9787532744152
商品尺寸:20.8x14.4x2cm
商品重量:340g
品牌:上海世紀
ASIN:B00168V78E
內容簡介
《博爾赫斯談話錄》是博爾赫斯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談話集,開啟博爾赫斯哲思迷宮之門的秘訣。從某種意義上說,虛構小說和源於環境的小說同樣真實,也許更真實。因為說到頭,環境瞬息改變,而象徵始終存在。假如我寫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街角,那個街角說不定會消失。但是,假如我寫迷宮,或者鏡子,或者邪惡和恐懼,那些東西是持久的——我是指它們永遠和我們在一起。許多人把我看成思想家、哲學家,甚至是神秘主義者——當然,我只能感謝他們。事實上,儘管我認為現實令人困惑——而且程度越來越嚴重——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思想家。人們以為我專心致志於唯心主義。唯我主義或猶太教神秘哲學,因為我在小說中引用了它們。其實,我只想看看它們能派什麼用處。有人認為,如果我派了它們用處,那是因為我受它們的吸引。當然,這沒有錯。但我只是個文人,我利用那些題材儘可能寫點東西而已。
編輯推薦
《博爾赫斯談話錄》從某種意義上說,虛構小說和源於環境的小說同樣真實,也許更真實。因為說到頭,環境瞬息改變,而象徵始終存在。假如我寫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街角,那個街角說不定會消失。但是,假如我寫迷宮,或者鏡子,或者邪惡和恐懼,那些東西是持久的……我是指它們永遠和我們在一起。許多人把我看成思想家、哲學家,甚至是神秘主義者…當然,我只能感謝他們。作者簡介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阿根廷詩人,小說家、翻譯家。一九二三年出版第一部詩集,一九三五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奠定在阿根廷文壇的地位。曾任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館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哲學文學系教授。重要作品有詩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激情》、《老虎的金黃》,短篇小說集《小徑分岔的花園》、《阿萊夫》等。
目錄
引言博爾赫斯論博爾赫斯
文學的活迷宮;主要作品;納粹分子;偵探小說;倫理學、暴力和時間問題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訪談錄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博爾赫斯在紐約大學
和博爾斯一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同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的談話
如今我多少成了我自己
十三個提問:與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對話
博爾赫斯:哲學家?詩人?革命者?
訪問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訪問記
博爾赫斯論生死
年表
文摘
博爾赫斯論博爾赫斯理察·斯特恩/一九六六一九六六年採訪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的這篇談話錄成了一九七九年三月我訪問南美的名片。(我的贊助人事先分發了談話錄。)在南美廣袤的土地上,博爾赫斯幾乎成了英雄入物,即使沒有看過他作品的人,或者厭惡他的政治觀點的人對他也十分尊敬,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他給民主作的定義是四乾萬個傻瓜選了一個把他們剝奪得一無所有的傻瓜。作出這個有影響的定義的入在胡安·庇隆上台後的第二天辭去了自己的職務。)一九七九年三月,他年已八十,看上去身體不錯但自我感覺很差。(“我支持不了很久,”他對蒙得維的亞的一家報紙說。)但是我們不停歇地談了兩個小時,內容涉及文學、歷史、政治,還說了一些笑話。兩星期後,他從羅薩里奧和科爾多瓦講學歸來,我又去他在馬伊普街的小公寓,朗誦白朗寧和羅塞蒂的詩給他聽。他指點我的朋友阿蘭·羅林斯和我到他視力所及的書架那邊去。(我提到嬌生的一首詩時,他說:“我有那首詩,但是不知道擱在什麼地方了。”)我們十分興奮。他大聲念出詩行,說道:“瞧,瞧,那簡直絕了,"或者抓住我的胳膊大聲說:“多美,多美啊。”感動我們的那首詩是《蔡爾德·羅蘭來到陰暗的塔樓》。“儘管我從來沒有明白它的意思。”
正如一個瀕臨死亡的病人
仿佛已經死去,淚水已經乾涸,
同每一個朋友都告了別……
在空蕩蕩的起居室里,坐在失明的老人身邊,羅蘭的尋找看上去並不怎么神秘,只是令人興奮得無法形容而已。
一位老夫人走進房間,我沒有,也不願意停下來。我們都沉浸在那首詩里,無法破壁而出。博爾赫斯和我一起吟詠最後那行詩:“蔡爾德·羅蘭來到陰暗的塔樓。”
接著是沉寂,回到了小房間,黃色的沙發,白色的書架。“這裡有人,”我說。白髮的老夫人走到站起來的博爾赫斯身前。“喬治,”她說。“是我,埃斯特。”“我的表妹,”博爾赫斯向我們介紹。“剛從歐洲回來。”該是我們告辭的時候了,“你給了我一個十分愉快的上午。”
一年後,他仍舊那樣優雅和結實,又來美國講課,或者不如說來參加那些沒完沒了的問答會。他露出大門牙,視而不見地朝那些最熟悉的提問人微笑,有問必答,仿佛覺得反正沒有什麼秘密。他在一次聚會上背誦日耳曼和盎格魯一撒克遜的詩句,問人們讀了什麼書,有什麼想法。芝加哥負責接待的雷內·達科斯塔扶他去盥洗室,雷內後來說博爾赫斯帶著同樣的學者式的興趣背誦了他記憶中在巴黎、羅馬和布宜諾斯艾利斯舊時的廁所牆上的塗鴉。
芝加哥遊藝場裡那座傻裡傻氣的混凝土展館是成人繼續教育中心。(進行繼續教育最多的地方是工業聯合會。)底層低矮的、潛艇般幽暗的過道外面是芝加哥大學廣播電視部。博爾赫斯來到這裡,他身軀瘦長,虛弱,步履有些歪斜,有人攙扶著。他臉龐也瘦長,臉頰上垂直的紋路更加重了長臉的感覺。從體格上說,他不是壯實的人,但是在儀態和姿勢方面卻與眾不同。他握手時湊得很近,一雙鼓突的、模糊的、藍灰色的眼睛離與之握手的人只有幾英寸遠。“我能辨出明暗。”一個很快就能打動人心的和善的人。
正如普魯斯特稱國王們總是頭腦簡單得令人驚異那樣,長期受到讚揚的優秀作家們總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年輕的同行。他們如果身體比較瘦弱,往往會養成一種卓別林式的、緩解一切知名人物都會遇到的敵意的刺痛。(瘦小的薩特匆匆忙忙地跑來跑去,給人敬煙點菸,請人喝酒,周圍大量的蠢話和詈罵幾乎把他淹沒,他卻面帶微笑坐著傾聽,就是一個絕妙的例證。)
前一天晚上,博爾赫斯對一批高興的聽眾談論惠特曼。一篇親切的講話,顯然是憑藉記憶,而不是照本宣科或者即興發揮,稍稍有點鬆散和冗長,但閃爍著西班牙語的魅力。講話最精彩的部分是回憶他在日內瓦求學時期閱讀惠特曼的情景,“讀惠特曼的詩就像是喝一帖藥。”記憶中的惠特曼,《草葉集》的作者,“超凡入聖”,像吉訶德和哈姆雷特那樣終古常新,完全不同於那些奔走於布魯克林和曼哈頓渡輪碼頭之間的沒精打采的新聞記者。
博爾赫斯和我面對面隔著桌子坐在一個小錄音房裡,麥克風懸掛在我們鼻子上方。我為我對西班牙語、南美洲、西班牙語文化里的文學和風俗的無知表示歉意。他回答說,他在這方面的無知可能比我更嚴重。調度發出信號,下面就是錄下來的大部分談話。
斯特恩昨晚你談起惠特曼的多樣性。讀你寫的詩和短篇小說時,人們看到的博爾赫斯至少也有好幾個。有時候,比如說,在那篇可愛的《博爾赫斯和我》裡面,你也提到了這一點。
博爾赫斯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吉基爾博士和海德先生,無數的吉基爾博士和無數的海德先生,其中還有許多別的人。
斯特恩這些年來,你成了經常接受採訪的人物,你經常評論博爾赫斯其人或者他的作為。你有沒有發現一個新的博爾赫斯,一個在公眾關注下應運而生的博爾赫斯?
博爾赫斯但願發現了。我年輕的時候,不指望有誰會看我寫的東西,因此我愛寫得怎么巴羅克就寫得怎么巴羅克。我的寫作風格十分牽強做作。可是現在我得為讀者考慮,那當然有助於形成優良的文學風範。不同的作家作風各各不同。有的試圖寫得晦澀,一般說來都做到了。可是我力求做到清晰易懂,我認為——人們也這么說——我做到了。現在我打算在回到家鄉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後,就開始寫一個同吉卜林的《山中的平凡故事》風格相仿的,簡單明了的短篇小說集。不是他後期寫的那種非常複雜、非常難懂,並且非常傷感的東西。我想用直截了當的方式寫簡單明了的小說。我還想避開迷宮、鏡子、匕首、老虎這一類的主題,因為我開始有點厭倦那些東西了。我想嘗試寫一本非常好的書,誰都猜不到會是我寫的。那就是我的目標。
斯特恩這些故事會像吉卜林所寫的山林那樣嗎?回憶往事,回憶那些人?
博爾赫斯是的,會是那樣的。我打算回憶我兒時的情形,因為我認為作家應該避免現時的題材。假如我試圖描寫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特定地區的一家特定的咖啡館,人們會發現我犯的各種各樣的錯誤,當我寫六十來年前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部或者北部貧民區的事情時,誰都不會注意,也記不清。那一來,我就有一點文學創作自由發揮的空間。我可以海闊天空地幻想,我可以隨心所欲地想像。我不必描寫細節。我沒有必要做歷史學家或者新聞記者。我只要想像就行了。假如事實基本正確,我不必擔心情況是否屬實。我打算出版一本包括十個或者十五個短篇小說的書——比如說,每篇小說有七八頁。每篇都相當清晰。我已經寫好了一篇。
斯特恩雖說你不指望有誰會讀你寫的東西,你生活中某些時候是不是出現過這種情況:即你寫的故事、短篇小說和詩歌不僅是經過修飾的幻想,而且是行動的記錄?
博爾赫斯兩種情況都有。當然,重要的是區別它們究竟是回憶呢,還是幻想。當然,把它們寫在紙上是相當麻煩的事,但也給了我很
多樂趣。我記得當我在寫一篇相當可怕的小說時……我覺得很高興,因為作家寫作時應該覺得高興。
斯特恩當作家寫得精彩,或者自以為寫得精彩的時候。
博爾赫斯我不知道能不能說寫得精彩。但是到了我這個年齡,我知道自己的發展前途。我知道我不會寫出比我現有的作品好得多或者差得多的東西。因此我聽其自然。我是說,到了我現在的年齡——我已經六十八了——我認為已經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和位置。
斯特恩可是你說要換一種寫作方式。
博爾赫斯是的。我的意思是說我要寫簡單明了的東西,但是,當然啦,我是作家。我不能脫離我自己;我希望能那樣。當然,我也受到過去的限制。
斯特恩你不喜歡藝術是個性表現這一觀點。
博爾赫斯我寫過一篇寓言似的東西,講一個人繪製一幅巨大的畫面,仿佛是地圖,上面有山巒、馬匹、溪流、游魚、樹林、塔樓、人物和形形式式的東西。到了最後,當死亡的日子來臨時,他發現畫的是他自己。大多數作家的情況都是這樣。人們認為我們應該寫各種各樣的事物。事實上最後剩下的只是我們的記憶。我是說讀者最後發現的是我們的面龐,我們的相貌,雖然我們對此早有思想準備。這就是說我們無法擺脫我們自己。但我們也沒有必要這么做一我們內心裡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探索。
斯特恩你大概記得詹姆斯小說中地毯圖案的故事。你在什麼地方寫過相似的情節。我想大概是在一個註解里。你提到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把人們一生所有的姿態都累積起來,輕而易舉就能辨出形狀,正如三角形的三條邊那樣。你六十八歲的時候,已經寫了五十年小說和詩歌,你認為作家看到的地毯上的圖案和生活里的圖案有什麼聯繫?
博爾赫斯那種事情很難說明白。我寫作時總是試圖忘掉自己,把思想集中在要寫的題材上。我也想到讀者。儘量讓讀者看得懂。我發現事實上我翻來覆去寫的是同樣的題材。比如說,我寫了一首獻給撒克遜詩人的詩。當時我心裡想的是《漫遊者》的作者。一年後,我寫了一首同樣題材的十四行詩,自己卻渾然不知。至於我寫的短篇小說,我認為有兩篇完全不同。可是後來一位評論家發現雖然背景不同,故事發生在不同的國家,情節基本上是一樣的。
斯特恩是不是可以說評論家的關注創造了一個博爾赫斯呢?
博爾赫斯我認為以我的情況而言,我真正了解的是自己的局限陛。我指的是某些事情是我不敢企求的。比如說,我認為自己策劃了一個新的情節。我講給一個朋友聽,他說:“那固然很好,可是你已經用過了。”他隨即說出了我寫的幾篇小說的篇名。
斯特恩你是不是認為想說“這無非是老調重彈”或者“我必須嘗試一些新的東西”的衝動是生活在文藝復興時代之前的作家才會考慮的事情?
博爾赫斯不,我認為他們考慮不到,因為那時候他們的題材十分有限。我認為人們不指望作家會知道。那也許是件好事,因為你寫一個讀者已經知道情節的故事時,你可以省去許多麻煩,因為既然讀者知道了情節,你就可以集中力量寫細節。以白朗寧為例,他在第一卷中交代了情節,就可以按圖索驥,發展全部相互關係。再舉例說,許多畫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的畫家做的是同樣的事情。
斯特恩朗吉努斯說多數“現代”文學作品(公元一世紀的文學作品)是追求新奇的畸形產物。
博爾赫斯你有什麼看法?我指的是朗吉努斯。當然,荷馬是作家中間的元老。但是,舉例說,我知道有些人了解我國的北美印第安人,他們毫無歷史意識。我記得我們的一位將軍同一位印第安酋長談話,將軍對酋長說:“你們曾是大草原的主人,後來自人來了,現在你們被趕了出去,對你們說來,這事太難堪了,想起來就傷心。”印第安酋長詫異地瞅著他說:“不。我小時候就見過白人。我想起祖母對我說過他們家有過奴隸,奴隸當然住在主人家裡。我問祖母奴隸有沒有覺悟,是不是知道他們的祖先是從非洲來的,他們是在市場上被拍賣的。祖母說他們一無所知。他們對歷史的記憶只能追溯到兒童時代,他們對祖先等等沒有概念,因此從來不知道他們來自非洲。”
斯特恩你提到你的局限性。依你看是什麼呢?
博爾赫斯舉例說,我永遠不會嘗試寫長篇小說,因為我知道在我寫完第一章之前我就會感到厭煩。我還知道,我不能嘗試描寫,我認為心理分析是我應該避免的領域,因為我幹不了。但是如果我能想像一個人的情況,我會試圖通過他的行為顯示他的心理活動。斯堪的納維亞的薩迦傳奇就是這種情形。薩迦從采不說人物在想什麼,但是你從人物說的話,或者更好的是從人物做的事裡有所了解。
斯特恩你沒有感到繼續和人物相處,通過他們和其他人物之間的關係來顯示他們的衝動?
博爾赫斯我對於那一類小說不是特別感興趣。我的朋友說我身上有些十分孩子氣的東西,因為我特別熱衷於情節,而一般認為聰明人不需要利用情節。當然,你一旦真正欣賞一部沒有什麼情節的小說,而其中的人物整天被當作偶像來崇拜,那種小說我是不會看的。
斯特恩去年(一九六七年)有人問斯特拉文斯基今年文學界有什麼新事。他說他從來沒有想到人們居然能根據這么少的材料寫出這么多的東西。他是讚揚貝克特——
博爾赫斯這是真正的讚揚嗎?
斯特恩我的口氣聽來像是反話,他卻沒有嘲諷的意思。
博爾赫斯我的感受不是那樣,不過還是非常可愛的。我不妨講給你聽聽。我記得我看過里卡多·羅哈斯編的《阿根廷文學史》。那部書有八卷之多,我看完全書後發現裡面空空如也,一無所有,我覺得這個人太聰明了,居然能寫出這部書。他寫了書,儘管言之無物,他出了名,受到尊敬。
斯特恩大象不能讓螞蟻替他寫墓志銘。我們要不要談談決定其他藝術因素的簡潔問題?我們很少談到簡潔之類因素的後果。你寫的故事和詩歌,據我所知,都很簡潔。
博爾赫斯當然,這是由於偷懶的緣故。
斯特恩偷懶可能是根源,不過我仍有懷疑,因為四五十本作品的成績至少是某種力量的證明。
博爾赫斯我說偷懶,是指懶於拿起筆來書寫。當然,我不認為我懶于思考和幻想。書寫是思考和幻想之間的活動。開頭你有個幻想,接著,你得設法把它固定下來。
斯特恩與簡潔同來的或許有一種對稱或者絕對性?看你的作品時,我注意到了這種東西。你說:“人人都作出某種選擇,”或者“無人反對”。
博爾赫斯唔,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你是不是想說簡潔有利於公平?
斯特恩不,我不是那個意思。簡潔有利於某種——
博爾赫斯總括性的說法。
斯特恩不錯。
博爾赫斯是啊,如果你用簡潔的方式寫作,卻混雜著“我認為”,或者“也許吧”,或者“可能”,或者“不是不可能的”,就沖淡削弱了你說的話。因此,那一類事情統統留給讀者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