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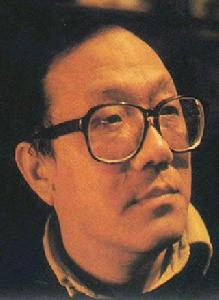 史鐵生
史鐵生 史鐵生
史鐵生最後到了現在,這個男人只記得那個女人對他說過一回,“我就住在太平橋。”
他慢慢地把這句話又默念了一遍。這時候空中有了光亮,仿佛天在升上去,地在沉下去,四周的一切看得清楚了。不過當初忘了問她太平橋在哪兒。想到這兒他爬起來披上衣服,東翻西找從床底下神出一本地圖,彈去上面的塵土。橫的豎的斜的弧形的街道密密麻麻,象對著太陽看一片葉子時看到的那些精緻的網脈,不同型號的鉛字疏密無序又象天上諸多的星座。找不到太平橋。
夜裡做了好多夢。夜夜如此。一個夢醒了又是一個夢,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沒完沒了。都是很精彩很有意思的夢,可是記不住。自己做的自己又記不住,天一亮就全忘了,光記得都很有意思,都很精彩。
有兩個孩子在窗根下說話,一個總是說:“喲——,真叫多喲!”
另一個老說真長:“哎呀,真——長。”這聲音隨著安靜的濕漉漉的黎明一同流進屋裡,又乾淨又響亮,攪起回聲流得到處都是。
他又拿起地圖小心翼翼翻了一遍。還是沒有太平橋這么個地方。有那么半支煙的工夫,這個男人認真地懷疑那個女人是否也是一個夢。為了這個愚蠢的懷疑,他叼著另外半支煙開始穿衣服,順便在身上掐了一把,被掐的地方確實很疼。
這個男人第一次見到那個女人是在很久以前了,在一個朋友家。這朋友叫天奇。天奇的妻子叫曉堃,曉堃剛好是那個女人的朋友。只一間小屋,似乎是說只有這一個世界,夫妻倆各占一角和自己的朋友傾心交談——一邊是“阿波羅登月以及到底有沒有飛碟”,一邊是“要孩子還是不要孩子”。嘰哩咕嚕嗡嗡嚶嚶,中間隔了三米飄忽不定的浩翰宇宙,談話聲在那兒交織起來使空氣和煙霧輕輕震動,使人形失去立體感。在兩邊的話題碰巧都暫停的時候,發現這屋裡還有一座落地式自鳴鐘,坦蕩而鎮靜地記錄著一段過程。這時男人和女人互相看一眼,既熟悉又陌生。嘰哩咕嚕嗡嗡嚶嚶空氣和煙霧又動盪起來,淹沒了鐘聲。“既然我們可以到月亮上去,更高級的智慧型為什麼不會到我們這兒來?”“這已經不是問題了,問題是他們來幹嗎。”女人們還是說孩子:“要是讓一個生命來了,你就得對這生命負責。”
“你也是一個生命,你也來了,誰對你負責?”……那是在他們的朋友剛剛結婚不久的時候。
第二次見面竟是在差不多十四年以後,在法院的大門口;他的朋友和她的朋友在大門裡的某個地方辦理離婚手續。太陽又升起來,照著門旁的衛兵和灰色高牆上的爬山虎。爬山虎的葉子正在變紅,不久以後將變成黑褐色然後在這一年裡消失。他比她來得晚。
“是您?您還記得我嗎?”男人問。
女人把他看了好一會:“喔喲,有十好幾年了吧?”笑一笑伸出手來。
“可不是嗎,十四年了。”男人說,“他們在裡頭吧?”
“進去好一陣子了。”
“情緒怎么樣,他們倆?”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看不出來。”
“到底怎么回事?”
“您指什麼?”“他們倆,怎么會鬧到這一步?”
“怎么您不知道?您是他們家的常客呀!”女人說。
“我這幾年去得少了。總有事,也說不清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最近又寫什麼呢?我看過您的小說。”
“是嗎?”男人笑笑,退步到牆邊的陰影里,太陽一直晃得他睜不開眼睛。“我也正在想我寫的都是什麼。”
女人也走到陰影里,兩個人在法院對面的大牆下並排站著。爬山虎在風中輕輕抖動,整座牆都在動。每年的這個季節都有挺長一段好天氣,鳥兒飛得又高又舒緩,老人和孩子的說話聲又輕又真切。
“前些年他們倒總是吵,”男人說,“吵起來凶得一個要把一個吃了,恨不能吞了。”
“是嗎?可真想像不出來。”
“我也不說誰更凶,半斤對八兩。”
“嗯,我想是。我想準是旗鼓相當。”
“這幾年好像不了,安?好像不怎么吵了,是不是?”
“這兩年他們可簡直是相敬如賓。”
“是嗎?這么嚴重?”男人說,“這我還不知道。”
女人很快地仰起頭看了男人一眼,頭一回看得這么認真,這么不平靜。
“要是這樣就沒什麼可奇怪了。這就快完了。”
“已經完了,”女人說,“沒辦法了。”
大門裡,也許是在白色的走廊上,也許是在別的什麼地方,有一隻鍾,不動聲色地走個不停。大牆下的陰影漸漸窄了。
“您得等他們出來嗎?”男人問。
“得等。曉堃得有人陪她一段時候。您不嗎?”
“不。我只是來看看,沒什麼事也沒什麼辦法就行了。天奇最不願意在他倒霉的時候有人特意來陪他。”
“男子漢,是嗎?”女人說,語氣不大客氣。
他驚訝地扭轉臉看她:“不,我沒這么說。”目光磕磕絆絆地下移,停在她胸前的扣子上。“不過是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可能有的人更習慣一個人聽聽音樂,喝喝酒。”
“真多,喲——,真多喲!”
“真長,是吧?真——長。”
原來是一對雙胞胎的兄妹倆蹲在窗根下數螞蟻。兩個孩子和一幕蟻群遷徒的壯觀場面:千萬隻螞蟻一隻挨一隻橫著鋪開縱著排開,一支浩蕩的隊伍彎彎曲曲綿綿延延不見頭,每隻都抱了一份口糧或一隻白色的蟻卵,匆忙趕路。
孩子問一個過路人:“它們在幹嗎呀?”
“大概是搬家。”
“幹嗎搬家呀?”
“也許是去旅遊。”
“上哪兒去呢?”
“無所謂。說不定就是出去逛逛。”
“逛逛呀?”
兩個孩子正正經經地想了一會,想螞蟻出去逛逛的事,也想起自己出去逛過的事。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幾乎是同時來到這世上,之後在某一個早晨,父母打發他們到院子裡去玩,在那個令人驚訝的窗根下,世界變得更真實更具體了,更美妙也更神秘。
讀後感
 1991年8月,史鐵生在北京家中。(資料圖)
1991年8月,史鐵生在北京家中。(資料圖)史鐵生一直是中國當代文壇中一個極為獨特的存在。這不僅體現在他那特殊的人生經歷上,還表現在他對生命困境的執著探索與超越中。深入史鐵生的創作,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他總是在回望苦難歷程和力圖超越命運困境的矛盾中艱難地行走。一方面,史鐵生從殘疾出發,不斷地尋找命運的真相,體悟生命的本真狀態,並在勘破人生之謎中彰顯了獨特的人生智慧;另一方面,在面對生命本相時,他又感到內心蘊藏著巨大的悲苦與虛無,這直接引發了他的“宿命”感。但史鐵生並不願意在宿命中沉淪,而是以頑強的毅力和深邃的思考,不斷向命運發問,孤獨地行走在人類的精神荒原上。也正因如此,史鐵生才一步步走出殘疾人的世界,發現整個人類的殘缺,並對“人的殘疾”進行了終極性的追問與思考。
縱觀史鐵生的人生,有兩次經歷對他的影響尤為重要:其一是1969年的插隊生涯,這一生活閱歷成了他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資源。在插隊的生涯中,史鐵生獲得了與同時代知青共同的生命體驗和心理結構。當知青們心中的英雄主義理想氣質被殘酷的現實無情澆滅之後,史鐵生很自然地站在這一群體的位置上,開始反思這段歷史對人性的摧殘和扼殺。其二是1971年的雙腿癱瘓,這徹底改變了史鐵生的人生體驗。史鐵生從此告別了健康的世界,不得不以輪椅代步,隻身走進陌生而絕望的殘疾世界。殘疾的身體,飄忽的命運,迷惘的前途……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殘酷人生,史鐵生開始在寫作中尋找慰藉。也正因如此,史鐵生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殘疾人獨特的生命體驗。這種生命體驗,主要表現為殘疾人在面對正常世界時所產生的自尊、自卑甚至是自暴自棄的心路歷程,以及為了得到世人的承認所表現出的歇斯底里般的追求等。
在他的小說中,史鐵生把敘事的視角放在了自己獨特的經驗範圍之內,他總是義無反顧地把小說中的人物粗暴地推向殘疾的深淵,從而深味殘疾生命與生存衝突之下的心靈之痛,以他那哀婉、惆悵的筆調,為殘疾人唱了一曲曲如泣如訴的命運之歌。史鐵生清醒地意識到,殘疾人的困境,除了肉體的殘疾之外,還在於價值感的失落,甚至可以說,價值感的失落才是殘疾人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因為如果一個生命失去了價值感,也就喪失了人之為人最起碼的尊嚴。因此,只有重新找到殘疾人存在的價值感,才能獲得生存的家園。為了找到殘疾人存在的意義,為了重新建構起殘疾人存在的價值感,史鐵生開始了漫長的尋找和籲求。
如果史鐵生只是選擇在殘疾人的世界裡重新建構人生價值,可以想見,他必定會在已經成型的小說模式下,執著地訴說殘疾人不幸的遭遇,詛咒命運的不公。所幸的是,史鐵生在叩問命運這一“斯芬克斯之謎”的過程中,逐漸領悟到了苦難之於人生的意義,從而走出了殘疾人的悲苦世界,進而發現了“人的殘疾”。
從“殘疾的人”到“人的殘疾”的轉變,並不僅僅意味著史鐵生走出了殘疾人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這一發現改變了他的世界觀,也使他的創作擁有了更廣闊的世界。
史鐵生生平
史鐵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原籍河北省涿縣,1951年出生於北京,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9年去延安清平灣插隊。因雙腿癱瘓於1972年回到北京。後來又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維持生命。2010年12月31日凌晨3點46分,史鐵生突發腦溢血逝世。史鐵生自稱“職業是生病,業餘在寫作”。而他創作的散文《我與地壇》鼓勵了無數的人。2002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作家協會副主席。
史鐵生作品集
| 史鐵生,中國電影編劇,著名小說家,文學家,因突發腦淤血去世。本任務羅列了史鐵生先生的作品以紀念他在文學上的巨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