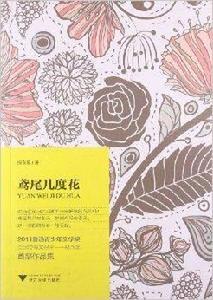內容簡介
《鳶尾幾度花》編輯推薦:鳶尾花,藍紫色,形似翩翩起舞的蝴蝶。它象徵著“光明”和“自由”,代表了“力量”與“雄辯”,是文學所追求的境界;鳶尾,也可解讀為“想念你”,也代表著文學之悲憫情懷。五月,鳶尾花開之時,一隻只藍色蝴蝶飛舞於綠葉之間,仿佛要將春的訊息傳到遠方去。《鳶尾幾度花》記錄了其中學時期的隨感與隨思,詩、散文、小說、戲劇各種文學體式均有呈現,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那種可貴的構想能力與創新精神。
時光會在記憶回溯中開出鮮艷的花朵嗎?鳶尾花開在春天,夢想啟程在春天,這一切都同青春一般美好。2011魯迅青少年文學獎,全國特等獎得主——祝含瑤首部作品集!浙江大學中文系原寫作教研室主任、浙江文學院特約評論員、文學博士陳建新為《鳶尾幾度花》寫序,他在序中不吝讚譽之詞:“含瑤在這部文稿中,顯示出了豐富的想像力,而想像力是作家的基本素質之一”;“含瑤駕馭文字的能力超過同齡人許多”!
該書是作者的作文集,書中內容從作者的高中黃金時代開始,一年一年追溯下去,到輕狂時代,到竹馬時代。有柔情有硬氣,有憐憫有叛逆,有含蓄有鋒利。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過程,看文字由青澀稚嫩的學生腔蛻變成成熟歷練,又看著複雜糾纏的文字回歸到最初的天真與純粹。在這裡,瘋狂與無邪並存。厚厚一疊,沒有形式只有真實。在這裡,有無數等待證實的夢想。厚厚一疊,沒有形式,只有真實。在這裡,可以聽到筆鋒劃破紙張的聲音,是情感的顛簸。厚厚一疊,沒有形式只有真實。
作者簡介
祝含瑤,1994年6月生,現於紹興縣魯迅中學高二在讀,從小便有讀書寫作的習慣,文章多於《新民晚報》《紹興晚報》等報刊雜誌上發表,曾獲第三屆魯迅青少年文學獎全國唯一特等獎殊榮。該書文章題材涉及詩歌、散文、小說等,共收錄了作者從國小時期至高中所寫的80餘篇文章。
圖書目錄
推薦序一 陳建新
推薦序二 蔣國洪
推薦序三 許吉安
黃金時代
循環虛像 003
在與非在 009
桂花 019
人間 032
伽藍 046
對窗 054
最後一場劫殺 062
我,巴士,河流,時間 068
有味 070
像象那樣思考 072
底層 074
被上帝寵壞的孩子 077
長亭送別 079
凡三境 081
莊子意象·魚·相忘 087
我將 090
啊呀,我是瘋子 098
我看阿Q 104
金灰相間的麥浪 108
被物慾囚禁的人性 112
巴士,站點,風景 116
去屋頂上讀書 120
鞋裡的石子 123
春曙 126
黍離賦 128
清狂時代
煙火臆想 133
陽光,在籬笆外奔跑 137
前方 141
那些年飄著的 143
他們 147
少不識愁 150
無題 152
秋水霓裳 154
品夜·囚夜 156
端午懷想 158
暖日 160
小城逢春 162
你的淚水我記得 165
拾荒者的春天 168
人在初三 171
這不是風景 173
一個平常的星期 176
生活在風雨之中 179
尋找站點 181
重溫 183
游“園”驚夢 186
邊緣 189
秋夜·漫步·起舞 191
念 193
被歲月珍藏的童年 195
生命熱血流淌不息 197
筆下的友情紙上的藝術 200
有時,我也想長不大 203
老爺子的吝嗇 205
帶月荷鋤歸 207
我可以選擇記憶嗎? 209
我眼中的陶淵明 211
朋友 213
幼時那些事兒 216
幸福的顏色 218
在學海中游泳 220
我想要的眼睛 222
游三清山 224
知足就是幸福 227
最後 229
沙漠·城市·仙人掌 23l
蝸牛的抉擇 233
偶然的發現 235
校服的“誘惑” 238
櫻桃樹 240
我的一天代工 242
暑假日記:你好,夏天 244
田埂上的記憶 249
三次電話鈴 25l
幸福的付出 253
竹馬時代
陽光的味道 257
絕招 258
飛天夢 261
《貓和老鼠》番外 263
四雙鞋 265
八月中秋 267
三顆小豌豆 269
蟲子們的禮物 271
後記:只記花開 273
文摘
循環虛像
杲杲日光,灼灼年華。
早起時發現自己瞎了。
用媽媽的話說,近視便等同於殘疾,睫狀肌可憐巴巴地拉扯著晶體,即使是雷射手術也無法改變視覺的病變。
我向著眼前模糊的黑窗走去,房裡的一切擺設再熟稔不過,卻仍舊是被絆了一跤,冬日裡留下的老傷永遠都好不了,硌在陰冷的地板上隱隱生疼。每年如此,膝蓋上的凍瘡還沒來得及癒合便一次又一次復發。
“嘶——”地拉開窗簾,聲音有幾分悽厲,給黑暗劃上一道致命的傷口,強烈而鋒利的光芒刮過視網膜,殷紅一片,繼而轉為溫和,是暖心的橘紅。緩緩睜開眼,看起來是還沒瞎透,至少我可以憑著曖昧不清的光線,勉強看清高樓狹縫上一小片天。我猜得到天很晴,晴得連一朵雲都沒有,興許會有一架潔白的紙飛機在湛藍的天幕下滑翔而過。
耳邊的鳥叫啁啾幾下就立即消逝去,我知道耳疾又犯了,這些年向來如此,時好時壞,無法預料。
這天,我沒同往日一樣從抽屜里摸索出那副厚如啤酒瓶底的眼鏡,只是倏地不願重複前幾日單調乏味的生活,於是從這個被我看得已面目全非的房間走了出去,踱步到另一個模糊的浴室。
憑著養好的慣性,利索地拿起右邊第二隻杯子,擠出剛好一小格牙膏,用熟悉的力道刷牙,聽著水龍頭裡流出一成不變的節奏,循環往復,不緩不急。我明白,這一切即使我閉著眼也可以做得一樣流暢。浴室里的霧氣開始氤氳,洗完後鏡子上蒙了一層薄而脆弱的水霧,我輕輕撥開它,試圖從裡面窺見自己的臉,但擦了一遍又一遍,是永遠撥不開的一層,望見的永遠是模糊的重影。眼前像是隔著一塊淋不濕的毛玻璃,抑或一場終年不化的大霧。
洗漱完以後人精神了許多,踱步回到房裡,取出厚重同酒瓶底的眼鏡,這時耳邊的啁啾又開始了,耳目清明,空氣被陽光洗乾淨了許多,一種極不真實的感覺。
趴到陽台邊緣,我窺到一盆泥土,霜裡帶著綠意。三月果然是最殘忍的,它殺害了冬,荒蕪的原野開始長紫丁香,給萬物以生機,卻偏偏要攏上一層刺骨的霜凍,壓抑根的欲望。
也許四季皆如此。
抬頭望天,它並無我之前想像中那么澄澈,總有那么幾條灰色帶過。嘩啦啦,一群麻雀忽地撲拉著翅膀黑壓壓從頭頂蓋過,樓下馬路上也晃過一大片深灰的影子。我往裡退了退身子,習慣性挪開椅子坐了下去,扭轉檯燈,攤開荒廢了一個假期的函式題,拋物線在腦海里盤旋、變形,開始了它的一生。這是一個開口向下的,與x軸有兩個交點,有極大值、無極小值的完美圖線,形成一個極致的半循環,激烈地揚起繼而猛地跌宕至下。這個拋物線想了一生,來了又回去,卻沒有結合點,只能無限延長,各自擴散開去。
如人生。
如人生。最為悲哀,明明從同一個起點出發,彼此卻越走越遠,緩慢而折磨的相離過程。如人生。前半生不斷積累,留後半生來不斷失去。何不多留一點時間給失去,這才是拋物線的美學,瓜熟蒂落,得以完整。人正是因為執著於得到,不斷爭取,才顯得面目可憎。多留一點時間給失去吧!
心有不甘。函式題的答案已經在腦海幽幽顯見,卻缺少了將它提筆蓋論的勇氣。
煩躁地摘下眼鏡。於是,模糊的燈光,模糊的筆桿,模糊的拋物線。試想著,就這樣朦朧一天也罷,體驗這久違的踏實感。
打開廣播,“茲茲”的聲波是不插電的記憶,讓人想到老家那台隔幾分鐘就會出現滿屏雪花的電視機。打開電視仿佛是為了看雪花,倒計時,三,二,一,瞬間螢屏又亂了,黑的白的,明昧不清,無數光點沸騰著。 心也跟著亂了。
這種預知循環的感覺會讓人上癮。如阿司匹林掩蓋下的痛苦,被藥物麻醉的痛覺忽然失去慣性,在半夜復甦。倒不如每一刻都等待著它來侵蝕,至少踏實,至少知道它的頻率,它的輕重緩急。
聽覺又回來了一半。廣播裡男人的嗓音充滿磁性,夾雜著尼古丁的味道,用一種鬼魅的色彩蠱惑著人心。人活到一定年齡的時候會發現,認識的人中,死去的比活著的更多,等你離開,又會有一個人發現他生命中消失的人過半了……
魯迅的敘說抵達現實如此迅猛,就像子彈從現實的軀殼中穿脫而出,這般犀利,而不會留在他的體內。
阿Q則是一個被打得千瘡百孔的人物。從國小、國中,乃至高中,每每出現在課本中,便眾說紛紜。有人說自嘲精神,有人說樂觀精神,也有人說精神勝利法。眾人似乎很能接受這個悲傷之中充滿喜感的人物。
也許我至今無法真正理解魯迅寫阿Q的真正用意,就像《了了》一樣,用幽默凜冽的筆調去刻畫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也許是最好的方式,患得患失,患喜患憂,無謂其它,從阿Q身上,我只看到一絲戾氣,一絲憤慨,只看到千百年來,國人身上的一種奴性。
何謂奴性?即滿清遺毒,國父之痛,孫中山怎么也想不到,現今的國人,身上仍殘留著這種卑賤的氣息。的確,千年的君主專制,唐風宋雨,李杜詩篇,皆化為一抔黃土,期間的剝削,壓迫,霸凌,乃至日軍暴行,奴化教育,把國人訓得同傀儡一般。歷史的流水浸過,留下血跡斑斑,“諂媚”地譏笑,看著我們這群多么懂得“明哲保身”,懂得奉行“忍”之道,懂得暴君暴官的聰明的奴隸。
國父驅除韃虜,驅何?還終究是改不了這劣根性,國人一身奴顏媚骨。唯剩魯迅,毛澤東曾嘆,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難能可貴的性格。正是在這個人筆下出現這么一位人物——阿Q。魯迅並沒有像對待孔乙己那樣對待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文帶過,虐著阿Q的肉體,尊嚴,靈魂。
試看阿Q的外貌,癩掉的頭皮,窮得只剩一條褲衩,滑頭滑腦,舉止屈躬卑膝,人前人後判若兩人。待看魯迅,那版畫上最為深刻的便是兩道凜冽的橫眉冷對,刀削般鋒利的面龐,嚴謹的氣質。
魯迅曾戲言,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譬如說這屋子太暗,須開一扇窗,大家一定不允許。但如果你主張掀掉屋頂他們就來調和說開窗罷。看來人們都願意奉行“中庸之道”啊!沒有人擁有像晏子說的那樣“順於己者好之,逆於己者惡之。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的確,做人便是要有分明的是非,熱烈的好惡。
現今下級與上級之間,後輩與先輩之間,亦少不了阿諛奉承。如明知城市市政規劃設計有缺陷,領導已拍板,下級便不敢有異議;民工進城,揮汗灑淚,到頭來,得不到報酬竟畏畏縮縮不敢抗訴。國人的腰板何時能挺起。誠其意,慎獨之,人前人後當如一人。即使是面對現實生活的殘酷,《傷逝》中那一對看起來勇氣可嘉,卻在現實生活中敗下陣來的所謂“新青年”就是很好的例子。
抗壓能力弱的人們也許可以找藉口,常言昔日寒山問拾得,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待幾年?這豈不可笑,又為何不奮起反抗,用骨子裡血一般辛辣的熱情。難道國人甘願被謗、被欺、被辱、被笑、被輕、被賤、被惡、被騙?再問現今學者,筆者,有幾人敢言,直言? 有如魯迅兩把鍘刀一般乾脆利落的情緒,而不是阿Q的討好讚美。
後記
人是愛回憶的動物。
我們不知道命運如何安排相逢,相逢後又會發生怎樣的故事,那些逝去的舊時光是否真能在回憶里不朽而開出花朵來?鳶尾花開在五月天,深陷於回憶的一切事物都已美艷到不可方物。
沒由地覺得,最美好而深刻的不是現在成熟的文字,而是國小里那稚嫩的筆劃。也許是很多第一次都留給了童年,那種感受最為真切,等長大後再次嘗試,卻找不回當時的快樂。國小的內容沒有在本書中完整呈現,即——竹馬時代,它來自一本未遺失的日記本。最悠然的時光,最踏實的步履,最令人回望的年華,沒有華麗的詞藻,卻甚一切而美。像是《陽光的味道》的豐盈,《四雙鞋》的溫情,《三顆小豌豆》的童趣……這一切都要感謝國小語文老師對我的文學啟蒙。
看著文字從幼稚到成熟,又借時光回溯,看著它由繁複晦澀回歸到天真樸實,發現我們的形容詞越來越多,可是動詞卻越來越少。殊不知,動詞是構成文字的骨架,長篇空話越來越多,簡單感動的敘述卻越來越少。
截至交稿前一天晚上,我仍在修改著這篇後記。
競開始擔心是否顯得做作,以至於有一種想把大段大段文字刪掉的衝動,人總是會因為接觸太多的過往而變得敏感,抑或是脆弱。當有人說中學生寫文章大多是無病呻吟、隨意批判、泛泛而談時,我曾固執地認為把憂傷留在紙上,把快樂留給生活是正確的,卻不知童年的我字裡行間都是天真感動。捫心自問,我們到底失去了多少東西?
無憂年華不再,如今的瘋狂年代最合適構築夢境,我的青春沒有白衣飄飄眉清目秀的少年,也沒有穿棉布長裙扎麻花辮的小清新,慶幸有你們,因而一樣真實無邪。也曾想過我的未來,無盡的路,滾動的石子,沒有指示牌,然而我期待有你們的存在。是不是,只要我們選擇的路,就算跪著也要走完。
將竹馬丟在長乾里,起風了,回首青梅染黃。在緊密縫合的歲月罅隙中,偶爾撥開一點微光,看看雲,聽聽雨,然後再次遇見你們。
出書緣於2011年第三屆青少年文學獎獲獎之後,磨合了近一年的時間才有這決定。但我更願意將它歸於幾年來冥冥之中堅持著的某種信念。
這期間,要感謝國小、國中和高中語文老師的欣賞栽培,以及交流寫作時難得的默契。要感謝一些教授的寬容接納和耐心指點,要感謝學校提供的平台與支持。
總之,感謝命運的一切安排。
似乎一切到這個點上都該結束了,過去的好壞輕重已經放在這兒任人評說,我能做的只是筆耕不輟。
鋒利的筆尖一次次將紙戳破,不知是路途的顛簸,還是情感的顛簸。
耽於回憶總是過分蒼老的心態,而回憶是為了使當下更有意義,因為不管怎么說,這一切都是今生今世的證據。
然而,以後只記花開。
序言
序二:在途中
稽山巍巍·鑒水清清。歷史文化名城紹興.人文薈萃,文化底蘊深厚。鍾靈毓秀,哲學家王陽明,文學家徐渭,詩人陸游,皆出於此。近現代更不用說,有教育家蔡元培,“民族脊樑、中國新文學奠基人”魯迅·主張以“人的文學”作為新文學基本主題的周作人,開創女性文學新階段的“鑑湖女俠”秋瑾,還有朱自清、許欽文、劉大白、魏金枝、夏丐尊、柯靈……紹興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所有這些均構成越文化的精神線索,形成其文化血脈。而另一方面.紹興人居粉牆黛瓦,至黑至白,給人“是非涇渭,愛憎分明”的感覺。紹興山岩壁立千仞,千峰竟秀,湖水悠悠,碧波漾漾,山至剛,水至柔。紹興戲劇中的紹劇與越劇,紹劇高亢激越,充滿著陽剛之氣,越劇委婉柔和,盈溢著陰柔之美,可謂剛柔兼修。山水環境濡染著紹興人的性格脾氣、情感價值,一定程度上來說,環境、氣候等自然條件與“風俗人文、精神氣候”等社會條件影響著文學藝術的走向發展。
而今天隨著新課程改革的深入,學校教學相對寬容,使學生能個性化地生動自由地發展,讓學生有尊嚴地學,“以生為本”已成為一種理念。校園文學教學的相對活躍.無疑為學生寫作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校園文學寫手也便應運而生。
我縣學子祝含瑤同學在文學這塊園地上脫穎而出,也與“江南名校”紹興魯迅中學的特色辦學分不開。魯中一貫踐行“抱誠守真”的校訓,堅持“尊重個性,張揚精神。整體最佳化,重點培養”的“立人”理念,傳承魯迅精神,構建精神家園,努力為國家培養多元人才。
本書的出版自有其意義在,它見證著新課改的成果,作為學生個人出版的純文學專著,為紹興縣學生多樣化發展開了一個好頭!
本書以“從當下開始”為起點,光影逆轉,時間回溯,呈現出作者的真情實感,這樣的閱讀往往會給你一種體悟與啟迪,是一種對話的愉悅。你將目擊到那些優美動人的文字,那些可愛的小精靈在你的眼前舞動,如“將酸酸楚楚的怨消弭於喃喃梵唱中,將重重思念鎮壓於油光的藏經箱中,將心底對兒女最殷切的祝福鋪散於迷離的檀香霧問”(《伽藍》),“人有六根‘眼耳口鼻舌身意’,相對應為‘色聲香味觸法’,我們可以抵擋得了金錢權利的誘惑,唯獨美食讓人慾罷不能,難逃一劫”(《有味》),“一杯濁酒,相離醉了誰?一眼回眸,塵緣痴了誰?一句珍重,天涯送了誰?一痕秋水,回首少了誰?”(《長亭送別》)……或樸素或典雅,或靈動或沉穩,那簡直是一種美的享受,字裡行間更是自然有一股浩然之氣在!
本書是作者階段性的總結與反思,承載著對文學的追求.是作者生命成長的一個新的台階!它是雨後的春筍,它是破土的幼芽,它是初融的冬雪,它是山間的小溪!
當然作為學生著書,其中也一定存在有待商榷之處,懇望得到方家之教。
夜沉靜下去了,我的心也沉靜下去了,不禁想道:以後的路正長著呢,而此刻,正在途中……鳶尾幾度花?我們期待著數度花!
是為序!
蔣國洪
2012.3.28
於古城紹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