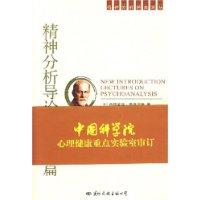內容簡介
精神分析學說是奧地利精神病醫生、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在20世紀初創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為神經病學家和精神科醫生來從事研究的。其研究對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發現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於生理的原因,而是在於深刻內在的心理因素。他將這種存在的心理因素歸結為兒童期被壓抑的性意識,並由此創立了“無意識性本能學說”,認為神經症的發作就是性意識的長期壓抑最後總爆發的結果。弗洛伊德將他的發現加以總結,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最富創見的心理學說,並將這一學說全面推廣到哲學、社會、宗教、文化領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
本系列叢書共18種,精心選取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阿德勒、榮格、荷妮和弗羅姆的經典之作,分別從性慾、社會、生活環境、文化傳統等方面對人的狀態心理——大至精神病串,小至日常筆誤、舌誤等過失進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讀書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確的分析態度去研討這些著作,汲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為我所有。
作者簡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ud,Sigmund1856-1939)猶太籍精神病醫生,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生於現屬捷克的摩拉維亞的弗賴堡,1873年入維也納大學學醫,1881年獲醫學博士學位。1882年與精神病學家J.布洛伊爾合作,用催眠術醫治並研究癔病。1885年和1886年間,先去巴黎就學於J.M.沙可,後赴南錫參觀催眠療法。回維也納後認識到催眠療法的局限性,1895年後改用自己獨創的精神分析或自由聯想法,以挖掘患者遺忘了的特別是童年的觀念和欲望。在治療過程中,他發現患者常有抗拒現象,認識到這正是欲望被壓抑的證據,因而創立了他的以潛意識為基本內容的精神分析理論。初期概念有防禦、抗拒、壓抑、發泄等。在臨床治療時患者還出現了對醫生的“移情”現象,從而認為人的神經活動大都以性慾為基礎,被壓抑的欲望絕大部分是屬於性的,性錯亂是產生神經症的根本原因。1909年應美國克拉克大學校長、著名心理學家S.霍爾邀請,與榮格等赴美國參加該校20周年校慶紀念,並與美國著名心理學家W.詹姆斯、E.B.鐵欽納、J.Mck.卡特爾等晤面。發表了以精神分析為主題的演講,聲名遠揚。回國後,他的一些弟子A.阿德勒、C.G.榮格和O.蘭克反對他的泛性論,先後背離他而自立門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他不斷修訂和發展自己的理論,提出了自戀、生和死的本能及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三分結構論等重要理論,使精神分析成為了解全人類動機和人格的方法。30年代他的理論登峰造極。1930年被授予歌德獎金。1936年壽辰時,榮任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他在最後16年曾與口腔癌作鬥爭,堅持工作。在納粹分子的脅迫下,1938年被迫離開維也納去倫敦。1939年9月23日在倫敦死於癌症。主要著作有:《夢的解析》、《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引論新編》、《弗洛伊德自傳》。
目錄
總目錄
精神分析論講演講稿
精神分析綱要
序言
第二十九講 關於夢的理論的修正
第三十講 夢與神秘論
第三十一講 關於心理人格的剖析
第三十二講 焦慮與本能生活
第三十三講 女性心理
第三十四講 闡釋、套用與展望
第三十五講 關於世界觀問題
……
序言
《精神分析導論講演新篇》序言
我的演講《精神分析導論講演》是於1915-1916年和1916-1917年兩個冬季學期分別做出的,演講是在維也納精神病醫療院的一個講堂里為大學裡各院系的教職員及學生所作的。演講的前半部分是臨時湊成的,事後我立即將它寫了出來;後半部分的講稿是在薩爾茨堡(Salzburg)度暑假時寫成的,當年冬天才逐字逐句地講述。在那時我還有著留聲機一般的良好記憶力。
這些新的演講稿和以前的那些演講不同,我以前從未講過。我的年齡已為我免除了通過演講為我的大學同事作解釋之苦(在任何情況下它都只是一種表面的義務);同時,一次外科手術使我暫時不能對公眾演講。因此,如果可能,我將在想像中置身於講堂之內,以完成此稿之寫作;這種想像也許會幫助我在深入闡發主題時不會在內心忘記對於讀者的責任。
這些新的演講稿絕對不是要取代以前的演講。在任何意義上它們都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統一體,也不可能指望有一批自己獨有的讀者;它們只是以前演講的續編和補充材料,按照它們與前期演講的關係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15年前曾經討論過的問題,由於知識的加深,觀點的修改,於是不得不重新加以論述,這就要求我們今天做出不同的說明——也就是說,這一類是批判性的修正。其餘兩類包括了新增加的內容,它們所討論的問題在以前的演講時還不曾存在於精神分析領域中,或者那時還不明顯具有另列專章的必要性。如果新的演講中某一些部分融合了這幾類的特點,那也是無法避免的,大可不必為此而遺憾。
我根據以前的演講而核定這些新演講稿編排的先後,以此表明新的演講對《精神分析導論講演》的依從性。故而我把本書第一章定名為第二十九講。像以前的演講一樣,這次演講沒有給職業分析家提供多少新東西;它主要是獻給一大批受過教育的人,這些人我們也許可以認為對這門新興學科的特點和發現具有雖謹慎卻不失善良的興致。這次我還是按我以前遵循的宗旨,不為追求簡練、完滿的外表而作任何刪削;既不隱藏任何問題,也不否認缺點和可疑之處。或許在其他的科學研究領域不必誇飾如此謙遜的意圖,它們往往是不證自明的,公眾所希望的也不過如此。例如,閱讀天文學著作的讀者肯定不會因為作者聲明在某些新領域中我們關於宇宙的知識還不夠明白而對它產生失望和蔑視。但是在心理學上卻並非如此,人類缺乏科學研究素質的弱點在這裡充分顯現出來了。人們從心理學中希望得到的似乎並非知識的進步,而好像是另外其他想法的滿足;每個未解決的問題、每個被承認的可疑之處都被轉化為對於心理學的一種責難。
任何關心精神生活科學的人都必須與這門學科一起承擔那些不公正的對待。
弗洛伊德
1932年夏於維也納
文摘
只是因為自卑情結變得相當普遍,我才敢大膽在這裡給你們講一點題外話。我們這個時代有一個著名的歷史人物目前仍然活著,雖然此刻已隱退到幕後。他的某個肢體因出生時損傷而殘廢了。一個很出名的當代作家特別喜歡編輯名人傳記,他描述了我正在談的那個人的生活。現在寫傳記要想限制剖析人物心理深度的要求是很困難的。由於這個原因我們的作者做了一次冒險,他試圖把主人公性格的全部發展過程都建立在他認為是由生理缺陷所導致的自卑感的基礎上。這樣做時,他卻忽略了一個雖然微小但卻意義重要的事實。一般來說,對於不幸而生下了一個有病的或在其他方面有缺陷的孩子的母親,她們都是以過分的愛去補償孩子所遭受的不公平的缺陷。但在我們所舉的這個例子中,傲慢的母親卻採取了另一種作法;她因為孩子有病而收回了她的愛。當孩子長大成一個具有極大權力的成人時,他用行動明確地表明他從未忘記他的母親。當你認為母親的愛對於幼兒精神生活很重要的話,你無疑會在自己思想中對那名傳記作者的自卑理論進行修正了。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談超我。我們已經設定超我具有自我監視、良心以及(維持)自我理想的功能。根據我們關於超我起源的說明,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生物學事實和一個重大的心理學事實構成的前提:即,人類幼兒時對父母親的長期依賴和俄狄浦斯情結,這兩個事實又緊密地相互聯結。超我是每一個道德限制的代表,它是追求完美的倡導者——簡單地說,超我就是我們從心理學方面所能夠把握的、被描述為人類生活的較高層次的那種東西。由於它本身起源於父母、教育者等人的影響,所以如果我們探究這些起源,就會更好地理解它的重要性。一般來說,父母以及類似於父母的有權威的影響者,是根據他們自己的超我的教誨來教育兒童的。不論他們的自我與超我達成了何種諒解,他們在教育兒童時都是嚴厲和苛刻的。他們已經忘記了自己兒童時期的困難,他們很高興現在能完全仿同他們自己的父母,他們的父母過去也是以同樣嚴厲的限制來管束他們的。故此,兒童的超我的形成所依據的模式實際上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父母的超我;兩種超我的內容是相同的,它成為傳統和所有抵抗世俗風氣的價值判斷的承載物,這些價值判斷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傳。諸位可以很容易地猜測到,在我們理解人類的社會行為——例如,過失問題——時,考慮到超我將會給予我們非常重要的幫助,這種考慮甚至可能給予我們有關教育問題的富於實際價值的提示。唯物史觀的失誤看來很可能就是低估了這個因素。他們提出人們的“意識形態”只是同時代的經濟條件的產物和上層建築的主張,而漠視超我。這種觀點是真實的,但很可能並非全部真理。人類從未完全生活在現實中。過去的種族和民族的傳統以超我的意識形態保存下來,它只是緩慢地向現實的影響和新的變化讓步;由於它是通過超我施加影響,所以它在人類生活中可以獨立於經濟條件而發揮強有力的作用。
1921年,我試圖利用超我和自我的不同來研究群體心理學。我歸納出了這樣一個公式:心理群體是這樣一些個體的集合,他們把同一個人引入他們的超我,並根據這個共同的成分在他們的自我中相互仿同。當然這僅適用於有領袖的群體。如果我們擁有更多的這類套用,我們就可以完全理解超我的假說,並且,一旦我們熟悉了潛意識心理領域之後,在進入更為表面的、更高層次的心理結構時,至今仍然困惑我們的難題就可以消失了。當然,我並未認為分離出超我就是解決了自我心理學的根本問題。相反這只是第一步;但在這種情形下還不僅僅是第一步艱難。
然而,現在另一個問題在等待我們去解決——在自我相反的一端,正如我們即將提出的。實際上,在以前的分析工作中,觀察就已經向我們顯示這個老問題了。由於這個問題常常發生,所以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了揭示它的重要性的關鍵所在。正如諸位所知,全部精神分析的理論事實上是建立在對抵抗的理解基礎上的。當我們力圖使病人的無意識變為意識時,病人就會表現出抵制的行為,這種抵制的客觀標誌是病人的聯想失敗或遠離所涉及的主題。他也可能在主觀上意識到抵制的存在,這通過當他接近論題時便產生種種痛苦的感情這一事實表現出來。但這最後一種標誌也可能缺席。當病人處於抵制狀態時,我們對病人說,從你的行為推斷,你現在正處於抵制狀態;病人回答說他對此毫無所知,只意識到他的聯想變得更困難了。結果證明我們是對的;但在那種情形下,病人的抵制也是無意識的,正如我們在研究如何加以提升的被壓抑物是無意識的一樣。我們很久以前就已經提出過這個問題:這種無意識的抵制產生於心靈的哪一部分?精神分析的入門者將準備立刻回答:它當然是無意識的東西產生的抵制。這是一個模稜兩可而毫無用處的回答!如果它意味著抵制從被壓抑物中產生,我們必須回答說:肯定不是!我們應該認為被壓抑物具有一種向上的強大的內驅力,具有一種努力進入意識狀態的衝動。抵制只能是自我的一種表現,它最初強力實行壓抑,現在又希望保持壓抑。而且,這就是我們一直採取的觀點。由於我們已經假定在自我中有一種特殊的機構,即超我,它代表了各種具有限制和否定特徵的要求,我們也許可以說壓抑是這個超我的工作,超我或者親自實施壓抑,或者由自我按它的指令實行壓抑。如果我們在分析時遭遇的抵制未被病人所意識到,那么就意味著在某些相當重要的情況下,超我和自我都能夠無意識運作,或者——這也許更重要——自我和超我的某些部分都是無意識的。在此兩種情形下,我們都被迫考慮這樣一種令人不快的發現:一方面超我、自我與意識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被壓抑物與無意識也不完全一致。(P6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