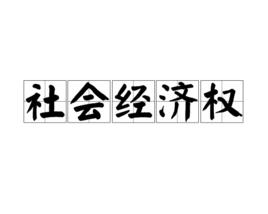相關資料
新中國憲法規定公民社會經濟權利始自於五四憲法。其中除財產權經由2004年憲法修正案發生規定上的根本變化外,這種變化包括了立憲思想、權利內容、保護方法等多個層面,其他社會經濟權利雖經憲法的四次全面修改,卻大抵只有規範表現形式的不同。在中國法制發展最低潮時期出現的七五憲法,對許多重要制度、公民基本權利採取了忽略、否定的態度,但它也在27條第2款明確規定了:“公民有勞動的權利,有受教育的權利。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物質幫助的權利”。箇中原因,頗值得進一步釐清。
一切權利制度的安排都與關於權利的價值理念密切相關。從比較法制的視野而言,西方國家社會權的入憲,與社會國理念的出現有因果的關聯。“社會國理念的發想本是指向於對工業化與資本主義所帶來之負面後果的修正,其立意乃是在於對社會現實中的弱勢群體提供平衡性措施,彌補其不利的立足點,以增進其充分發揮自我的機會。”它由“早期的防治貧民暴動、維持社會治安,經由工業化、社會解構之後以避免社會問題為目標而由國家承接社會照顧的責任,演變到以法定強制保險來保護國民免於一般性的生活風險(生老病死)……”[2]在中國,社會權規定在憲法中被認為是國家政權的性質和社會主義制度所決定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應該優越於資本主義制度的體現。[3]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新中國的制憲者主張公民基本權利應具有現實性,“現在能實行的我們就寫,不能實行的就不寫。比如公民權利的物質保證,將來生產發展了,比現在一定擴大,但我們現在寫的還是逐步擴大……”。[4]在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中國整體的國力並不強大,經濟文化發展的整體水平也較低,那時的公民社會經濟權利是依靠系統性的制度來予以保障的。比如:以公有制為核心的所有制制度、以計畫經濟為主要形式的生產交易制度、覆蓋全國的公費醫療體系、在農村普遍實行的“五保”制度[5]等等,這樣一種保障重在強調公平,並以滿足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為主。1993年憲法修正案對憲法第15條作了重大修改。原來的規定是:“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畫經濟。國家通過經濟計畫的綜合平衡和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保證國民經濟有計畫按比例地協調發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任何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破壞國家經濟計畫”。修改後的內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巨觀調控。”“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憲法的修改不僅意味著我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化,也意味著過去的一套公民社會經濟權利的保障制度,不再適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其表現在:城鄉保障水平極不平衡,保障標準的高低、保障設施的分布和保障投入的多少明顯不合理;社會保障的規範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不高;政府在整個保障工作中的主體作用不明顯等……。2004年憲法修正案在現行憲法第14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四款,即“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市場經濟以自由競爭為原則,強調對個人利益個人權利的最大尊重。憲法的上述修改所導致的中國公民社會經濟權利的內容及保障制度等方面的變化,頗需深入地研討。
性質
國內學者都藉由比較法的研究成果,運用西方憲法學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提出自己的見解。國外學者早期主張社會經濟權利屬於一種“綱領性規定”。如日本學者伊騰正己就認為此類權利並非一般私法上所言的具體性權利,而只是宣示了國家在法律上的政治性與道德性的義務,即只向國家課賦了命其今後應當通過立法和行政活動,為國民能夠維持健康且有文化水準的最低限度生活而採取適當措施的義務;基於如此之綱領性規定,國家採取何種保障“最低限度生活”的社會保障立法,或者如何在行政上將其予以具體化,均應委任於立法裁量或者行政上的自由裁量,而且在這樣的裁量範圍之內,個別具體國民不能主張自己的生存權利。繼“綱領性規定”的理論主張之後,後期的學者又分別提出了“抽象性權利”和“具體性權利”兩種不同的主張。“抽象性權利”學說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日本的松本公亘先生,此學說主要的觀點是:在關於生存權等權利的憲法規定之中,確實賦予了國民要求國家在立法行政上採取必要措施以維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權利,國民可以以此為法的依據,請求立法實施保障生存權的相關立法,或者請求政府採取保障生存權的相應措施;國家同時被課賦了為保障國民的“最低限度生活”而進行立法和採取行政措施的法的義務;規定生存權的憲法條款,並不直接對應國民保障其具體的生存保障請求權;包含於生存權中的國民的權利和國家的義務,均為抽象性的,不具有強制性質,也沒有審判規範性,因而在該權利遭到侵害之時,或者在國家不履行義務之時,國民個人並不能以規定生存權的憲法規定為法的依據,直接追究國家不作為的違憲性責任。“具體性權利”學說的代表人物首推大須賀明。該學說認為:生存權是一種法的具體性權利,而並非需要藉助另外具體立法才能具體化的的抽象性權利,更並非僅僅規定國家立法指針的、作為綱領性規定的單純的政治性權利。生存權的權利主體,是經濟生活處於“最低限度生活”基準之下的國民;生存權的權利內容,是要求國民保障所有國民能過確保人的應有尊嚴的“像人那樣的生活”;生存權實際的承擔對象,是三權分立體制之下的立法部門和法務部門。由“具體性權利論”出發,可以引申出以下結論:國民對於國家享有具體請求權,即可以請求國家在立法與其他國家行為上採取必要的相應的措施,以能充分維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是為國家的一種憲法義務;司法權對於憲法生存權負有實施性司法保障的法義務,憲法的生存權條款本身,具有明確的審判規範性效果。[6]國外的這些權利性質分析範式對於建構中國公民的基本權利體系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並不能完全嵌入中國公民基本權利制度之中。其理由在於:第一,權利性質的理論所依據的制度事實是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法治國、福利國的國家理念,這樣一套整體的憲政設計基礎要么中國不予採行,要么基於某些條件的制約而暫時並不具備。現行中國憲法是以1954年憲法為藍本修改而成,其制憲理念和制憲基礎與西方國家憲法大有區別。現行憲法1993年才規定中國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1999年才規定國家舉措的制度性宣示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此之前關於國家性質功能的認知、關於國家與人民關係的憲法理解與西方國家憲法大有區別。第二,現行憲法並沒有明確規定公民的生存權,關於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規定藉由2004年憲法修正案安排在總綱第14條,總綱條款在中國憲法理論中通常視為國家政策性條款,其他具體社會經濟權利規定在公民基本權利條款中。而西方憲法卻明確生存權、最低生活水準權、其他社會經濟權利,在立憲體例上這些規定都安排在人權或公民基本權利條款中。按照憲法文本釋義的一般原則,可以認為這兩種憲法制度下的權利性質並不相同。第三,中國的憲制安排不承認法院有憲法解釋、適用憲法的權利,所謂“憲法司法化”一直流於理論學者的主張,而沒有轉為正式的制度安排。權利性質理論中所討論的具體請求權其實關涉司法訴訟請求權。這樣的討論至少目前在中國缺乏制度基礎。第四,權利性質的學說討論隱含的邏輯前提是各種國家權力之間有明確界限,每種國家權力的權力範圍是清晰的。但這與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制度邏輯並不融洽,中國憲法第62條第15款就規定全國人大可以行使“應當有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其他職權。”由於解釋憲法的機關是作為全國人大常設機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因此早期中國憲法學者甚至主張全國人大具有全權性機關的性質。1999年憲法修正案規定“中國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按照系統解釋和目的解釋的憲法解釋原理,儘管可以合邏輯地解釋為中國接受了有限國家和有限政府的理念,但這樣一種解釋如何與憲法第62條兼容,仍是亟需探討的憲法問題。第五,在現實的憲政運作中,對公民社會經濟權利的保障一直採取了將憲法條款立法具體化的途徑。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將民生立法作為立法工作重點,制定了許多包含公民社會經濟權利保障的法律,主要包括《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婦女權益保障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等。某種制度運行一旦變成一種慣行,對法治整體運行的安定性、可預期性便形成一種支撐,形成契合一種一國歷史與現實的制度空間。人大的上述立法作為,是基於她自身作為人民利益的代表機關角色意識使然,並非基於某種權利性質理論的指引。